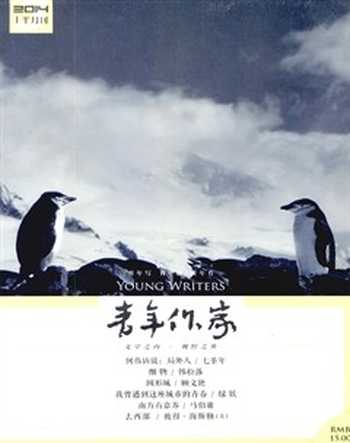何伟访谈:局外人
七堇年 刘思扬
他是全球著名的旅行观察者,也是获得许多文学殊荣的自由撰稿人。他对中国社会剖面的观察和描述,以一种未受干扰的寂静,清晰地呈现在他的文字中,被誉为“当今美国采访写作中国第一人”,他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他有一个在中国很常见的名字——何伟。
何伟最新的短篇杂文合集《奇石》,是他过去十年内在中国和美国所写的散文或特稿(报道)的集萃。《奇石》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描写中国,正如他在其他访谈中解释其书名一样:“中国就像是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如此形容何伟的作品:“何伟的作品平静而充满自信,以绝妙的语调和姿态赋予他所描绘的时刻生命。他知道何时应该参与行动,何时应该等待事情发生。”
2010年,何伟来到埃及,居住在开罗,学习阿拉伯语,参与当地的生活。他预告在2015年会再度回到中国,继续书写新的中国传奇。
问:你的新书《奇石》(Strange Stones)中的前言部分介绍,这本书是你最优秀作品的合集。你能谈谈这本书的主题吗?因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很快就要发行了,能与我们说说你之所以选择将这些作品收入本书,都受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答:我决定出版这本书有两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我曾创作过一些自认为比较优秀的作品,那些故事的描写题材也都是我非常关心的,但它们都仅仅发表于杂志上,从来没有以书的形式呈现。当为杂志写作时,你是无法完全控制编辑以及修改过程的。你可能会受到字数的限制——这很常见——或者杂志风格要求你做出一些并不愿做的改动。但是如果你写一本书,你就能对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完全的掌控。所以,我希望挑选出我喜欢、曾经发表过的作品,把它们整合成一个我喜欢的形式进行出版。
另一个原因是我希望我书中出现的故事不仅仅跟中国有关。这本书中有些我非常喜欢的故事是写于我离开中国之后,比如《去西部》(Go West)这篇是写于我搬回美国之后,《唐医生》(Dr.Don),写的则是一个生活在科罗拉多州乡村的药剂师的故事。我希望大家对我的印象并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只写中国故事的作家。这也算是为我搬迁到埃及所做的准备。
问:1996年你是因为受“和平部队”的任务调遣,还是自愿向组织请求而来中国的呢?
答:是我向组织请求调遣来中国的,本来我并不应该向“和平部队”主动提出调遣要求的,但我还是这么做了。他们本想把我调去蒙古或是俄罗斯,我告诉他们我并不想去那些地方,我有来中国的充分理由。我都在那些国家旅行过,所以做这个决定是有理有据的。
来到中国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文化观念上,更是心智上的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我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感觉到了的。加入“和平部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一种对生理的挑战,比如你被派到一个非洲遥远的村落,你需要面对糟糕的食物和艰辛的生活条件。当你克服了这些艰难之后,它可能会成为生命宝贵的一课,但它并不是我所想要的。这些也许是跟我在念本科和研究生时的经历有关系,那时我是一名长跑运动员,常常需要承受多方面的生理考验。但对于加入“和平部队”,我希望被派遣去的国家有一种复杂精妙的语言、一段令人深思的文化历史的。我知道我永远可以在中国学习到新鲜有趣的事物。
问:最初,你是否有长期待在中国的准备呢?是什么促使你留在中国,并开始写关于中国的系列书的呢?
答:加入“和平部队”的时候,我预感到我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会在两年以上。因为我一旦决定做某件事情,会一直把它坚持到底,这也算是我性格的一面吧。并且,我一直也希望以一种相对有条不紊的节奏入驻、熟悉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到,两年对于我来说太快了,并不能完全了解中国。当然,我那时也并不知道我将要干什么,包括对于《消失的江城》的写作计划。我大体上的规划是,学习中文,之后希望能在“和平部队”谋到一份记者的差事。但事情的变化太快了,在加入“和平部队”的六个月后,我的前任导师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鼓励我写一本书讲述我在涪陵的日子。突然之间,关于《消失的江城》的写作计划便有了头绪。
我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是1999年初,在完成《消失的江城》的初稿之后返回北京所做的。原本我以为会在美国待上一段时间,但我那时非常想念中国,我觉得我不应该停止对汉语以及其他事物的学习,所以我决定回到中国。到那时,我才认识到这着实是一个长期的决定,我当时希望至少在中国待上五年,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将永远地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一直有预感,和我走进婚姻殿堂的人将是一个会说中文并且能在中国一起生活的人。甚至在我遇到我现在的妻子张彤禾(Leslie)之前,我就有这种强烈的预感,我是不会和一个与中国缺乏强烈纽带的人结婚的。
问:你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中,曾亲眼目睹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下中国更是日新月异,你认为其中最为显著及意义深远的变化是什么呢?
答:毫无疑问是城镇化进程。一切都变了,他们与家庭、邻居、伴侣、孩子以及环境景观的关系都变了,他们的经济状况更是如此。当然,在西方社会也有过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历史,但从来没有这般迅速。
问:你的非虚构写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小说写作呢?你有打算在将来尝试小说或是短篇作品的写作吗?
答:我对写小说并不感兴趣,大学时我念过虚构文学,并计划过写小说或短篇,但最终我走上了另一条路,并从没想过要回头。我从来没有任何想要继续像在大学时候写小说的念头。我认为,非虚构写作才是我应该做的。我喜欢写作,但我也喜欢学习新知,我喜欢与人交谈,观察他们,采访他们,尝试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以及想法。如果我开始了小说写作,就可能会失去实地调查的机会了。非虚构写作,它正是我要走的路。
问:你是否写了很多关于西方社会或是关于你自己国家的作品呢?比如以欧洲或是密苏里州为背景的故事?
答:当我在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会写。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有一些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是在我和妻子住在科罗拉多州那段时间里写的。将来,我也会写更多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但我和我的妻子张彤禾(Leslie)决定当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还年轻的时候,我们会一直住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意义对于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来说,比对于美国重大得多。我希望见证这段历程,并且记录下它。今后当我老了的时候,可能我才会写些美国故事吧。
问:可能有人会说,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与本国人相比,局外人的身份能够使你以一种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你同意这种观点吗?如果真有不同的角度,你觉得它们是怎样的呢?
答:就现在来说,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局外人,因为我很少和与自己相像的人群相处。举个例子,我成长于一个密苏里州虔诚的天主教家庭,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这两所高校均是培养精英的学府。之后,我加入了“和平部队”,在中国内陆一个狭小而贫穷的城镇做志愿者。之后我花了八年的时间生活在北京,那之后我又花了四年时间生活在一个仅有七百人的科罗拉多小镇。如今,我生活在社会革命阶段的埃及。我所有生活过的地方、亲身体验过的经历,都将赋予我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即使我回到美国,我也将以“半个外国人”的眼光看待我的国家。
问:你的妻子张彤禾(Leslie T.Chang)的作品《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与你的写作风格非常相似,也是纪实文学。你们是否与对方交流分享观点和灵感呢?在写作方面,你们常常给予对方启发吗?
答:我遇见张彤禾(Leslie)的时候是1999年,当时我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约会的。可以说,在那之后我们对彼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能够理解彼此的作品。在两个人都年轻、都希望开始建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发展感情是非常困难的,它缺乏保障且包含未知。与张彤禾(Leslie)在一起的时候,她能够理解要做一个事情需要花费和投入的是什么。如果我因为需要展开一个实地调查不能够陪伴在她身边,而且这项调查我可能需要再待上两天,她会理解我。对于她,我也同样地理解和支持。
我们一直都在谈论我们所做的项目,有什么想法都一起分享。但你知道,其中很多只是我们在维系关系,互娱互乐的。婚姻常常是无聊的,我认为。但如果两人的兴趣、情智水平相当,那将给生活增添极大的丰富性。
问:我们得知你曾计划与你的妻子在中东生活大概五年,能说说为什么选择中东吗?你有关于中东的非虚构写作计划吗?
答:我和我的妻子选择埃及是有原因的,埃及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写关于那座城市的书和故事,并且有杂志和出版商愿意让我们发表。埃及的语言不仅精妙,学习起来更是一种享受。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如今正经历着社会的巨变,是过去与当下的结合体,而这也是当代中国让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过去两年我为许多杂志撰写了关于埃及的特稿,而且我想可能很快我将结集出书。我现在刚好身处于讲阿拉伯语的环境中,如此一来我也正在努力地学习更多东西。这是非常好的经历。我和张彤禾(Leslie)都非常高兴我们做出了来这里的决定。
问:在你的写作里,你似乎更喜欢描述一个事实而不是对事实去做判断。虽然每个读者都带着自己特有的角度和经历去解读一部作品,但你的写作方式不免让你的作品看起来更加中立一些。那么从主观的角度来说,你希望读者从你的作品里得到什么呢?
答:我希望我的读者通过阅读我的作品,能够对我笔下的人物和地方有更多的了解。我希望得到一种共鸣,我不希望我的作品看起来那么的异类、可怕或是可悲。我不希望人们读我的书后想,“中国人真奇怪”,或者“埃及人真可怜”。对于我来说,那样的读后感是一种失败。我相信人性深处总有许多地方是能够产生共鸣的,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很多时候让人们感受不到那种共鸣。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我的职责就是通过写作帮助人们跨越那些隔阂。
毕竟,判断是非不是最重要的。我并没有尝试地去给出一个答案或提供一个解决方法。我的写作更加注重描述性,而不是指示性。我从来不希望告诉中国人或是埃及人他们应该如何去做,他们自己会知道。我的工作仅仅是描述我所看到的。
问:在经过这么多年对中国的写作之后,你是否认为你的作品逐渐肩负一种让西方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责任呢?
答:许多作家都在尝试做这件事情,而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是西方讲述中国的作品比以前要好很多(在我看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文,并且他们受过一定的写作训练,自然而然作品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我非常自豪我是这群作家和记者中的一员。
问:你是从世界知名学府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的,与此同时,你也旅行过不少地方。你是如何看待你的教育背景和旅行经历的呢?
答:对于能拥有这样的教育背景,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时代,我遇到了非常优秀的写作教授,他们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普林斯顿和牛津都是精英学府,但如果你希望写的内容是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你就应该离开那些像常春藤名校之类的这种地方。我在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意识到这点,在这样的地方呆六年足够了,接下来是时候把书本与现实相结合了。接下来,我应该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真实世界的体验结合起来。于是,我加入了“和平部队”。我无法解释对于我来说当时做那个决定有多么的困难,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自己,我知道我的选择让我逐渐远离了一个本可以很顺利的职业道路。但我知道,我的选择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一个更好的人。到最后,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是最为重要的。当我把我的学术背景和我在涪陵的深刻经历结合起来的时候,我的第一本书就此诞生了。
问: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经历了许多困难的时刻,比如你也曾不断地被《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时代杂志》等这样资深的报纸杂志拒绝过。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他们请求你写稿件。你从那时的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悟呢?对于也许当下正在经历你曾经所经历过的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来说,你有什么想要与他们分享呢?
答:我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前生活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上,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对我的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有一定的优势。但我当时并不富有,在普林斯顿上学的时候,我甚至深感自己的贫穷。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人会感到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给你举个例子吧,在美国的大学里,如果一个学生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他或者她应该努力在东海岸的知名报纸或杂志社拿到一份暑期实习。这份实习通常薪水微薄,而在像纽约和华盛顿那样的大城市,房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的经济状况使我无法在那样的城市实习。大学期间的每个暑假,我都会回到密苏里州,与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并在本地找暑期工。对于我来说,那样的条件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优势。也许就是因为我并没有一份华丽的简历,我在离开“和平部队”之后根本找不到一份工作。
一次,我在《滚石杂志》上读到了鲍勃·迪伦的一篇访谈,他讲到了他在明尼苏达州的成长经历。他说,“当你来自那种地方,一切都在与你较劲。”美国人对于种族话题和性别话题非常敏感,但对地域差异却不那么敏感。所谓地域差异,指的是生长美国内陆地区的人遇到了在西海岸或东海岸的精英人群后所产生的心理隔阂。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和来自中国内地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我能明白那种感觉,当人们觉得你比他们更加“没文化”而实际上你只是对他们所处的世界并不熟悉的时候,那种陌生感使你感到尴尬和不堪。直至我大学毕业的许多年之后,我都是那么觉得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另一个世界而来的优势逐渐显现,我甚至都能从我的暑期工里体会到。暑期我回到密苏里州后,在当地的医院找到了工作,内容是为医院的研究项目采访病人。这样的宝贵经历教会了我如何与人沟通交谈。在大三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在密苏里州南部,密西西比河域附近的一个叫赛克斯顿(sikeston)的小镇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采访人们并写一个关于该城的报告,这是为了完成一个组织的长期调查。这个工作是写《消失的江城》之前的一次完美试水,虽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小镇和长江边上的一个古城的故事,并没有那么的不同。
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时,我感到愚昧和无知,因为当时我并不是任何精英团体的成员,也不知道在那样的人群中何去何从,但我知道的是如何跟普通美国人进行对话。我的高中是一个由各个肤色组成的公立高中,我认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同学,我也知道如何与他们进行沟通。那样的经历帮助了我,使我能够在中国与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交流。事实上,这种本领是大部分“普林斯顿”精英们没有的。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这个道理。这是我想告诉来自中国内地的人们,你永远有这样一种不知名的优势,它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更容易适应环境,也更加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