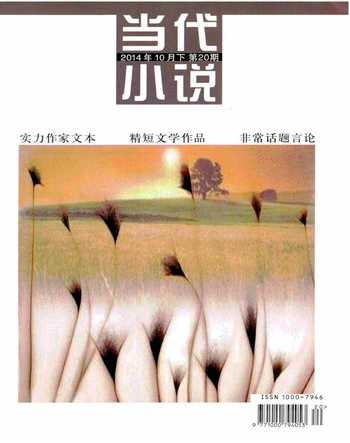故乡
孙平
泉水由石洞里清灵蹿出,蛇妖般闪着银亮的光。月亮躲到云中的一刻,在水波的响动、秋虫的叫声、偶尔生发的女人叫声中,七八只美人鱼或蹲或坐,在这个张着大口的黑夜,各自展露出曼妙的身姿,看上去是在这湾清凉凉的泉水旁嬉戏,其实是在和这水波比身段比灵秀比光亮,羞怯却肆意地诱惑着这个无辜的世界,让世间的一切都在这儿瞬间窒息。
那时候,混在这群美人鱼中玩耍的兰兰还只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兰兰从沟里走出,沿着一条弯路走去,走回到家中,躺倒在已经睡着的大姑身旁。
“哈哟,你的身子好凉!”大姑叫道。
大姑很快又睡过去,过了一会儿,兰兰也睡着,睡得很沉。第二天,等她使劲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当她看到大姑盖的被单正整齐地码在那里,抬头再看挂钟,不偏不倚,挂钟正指在七点三十的位置。院子里有人在说话,不时有吵闹的声音传进耳朵。从窗户眼里,她看到大姑跳起来要打二姑,伸出手,二姑抓住了大姑那只伸出的胳膊。奶奶拄着根棍子,从屋里走出。到这时,小姑才夺路而逃。
“哼,不得好死的穷东西。”朝着街门口的方向,她的奶奶破口大骂。
这天的早晨,因为奶奶没有吃饭,她也就没有吃饭,就这么空着肚子去了学校。每每早上空着肚子上学,她最害怕上的就是体育课。这天上午,第三节正好就是体育课。兰兰还是不敢相信,这天给她上体育课的不是姓李的那個严厉的老师了。太阳底下,老校长正眯缝着眼睛站在那讲话。
校长是一个肥胖的老头,教他们班里的地理课。半大节课下来,老校长早已大汗淋漓,不断地抬手臂擦汗。
“小白脸怎么没有来呢?”她踮起脚尖,朝校门口的方向看。也终于地弄清楚,小白脸正请假在家,忙活盖房子的事。利用入厕的机会,兰兰拐过弯朝南走出百十米,远远看见河沟东岸正闹出很大的动静。
小白脸家的房子就在河沟的东岸,此时,他家的脚手架已经搭起,脚手架旁堆了很高的一堆土,小白脸就站在那堆土的旁边,他的从城里娶来的老婆不断地进去出来的忙活。
到了学校放秋假的时节,嚯,兰兰还就真的看到河沟东岸冒出的大房子!那房子可真高,不但比屋后头的草房高出半截,房子的身下还挖空;里面像一个场院一样宽敞,出进口处有一道铁门布在那,是一上一下两层的房子呢!但是直到假期过完,明明这家人都搬进了新盖的房屋,就是在学校看不到他的影子。这天放学回家,兰兰在小姑刚刚坐过的凳子上捡到一张照片,照片虽然只有手掌那么大,却能看得出,是一个和小白脸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嚯,好爽噢!”她十分欢喜,将照片上上下下打量一番。
“把照片给我!”一只手伸过来,伸到她的跟前,是小姑。看她那眼神,像是谁偷了她家的东西。
兰兰赶紧把照片还给小姑,小姑从小就谁都不怕,可凶呢!接过照片,小姑眼睛里闪烁着,两行热泪慢慢从鼻子两侧淌下。小姑明天就要进城打工了,是舍不得家吧?望着小姑脸腮上流淌下的热泪,兰兰多少有点责怪奶奶,自小姑下了决心进城,奶奶的脸色没有一天好过。有一次,奶奶和小姑吵起来,骂小姑道:我看你是天生长了一副贱材骨头。小姑当时正在梳头,扔了梳子,弯腰从缸盖上抓起根绳子就朝外跑。小姑往外跑,奶奶便扯着嗓门喊人,胡同里立刻便招来了更多的人,年轻的和小孩子都跟着跑,剩下的跑不动的便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议论。后来小姑总算被撵回来了,人是撵回来了,但心仍然不在家里。
小姑到底是走了。自小姑离开,家里的大人每天都哭丧着个脸,好像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不好的事,都是因小姑而起。在这期间,学校里的体育老师换了一个更年轻的人,这个年轻的老师什么都不懂,连口号都经常喊错。兰兰非常思念小姑,想着小姑被奶奶宠着的那段日子。那时,即使家里经常被小姑闹得鸡犬不宁,奶奶也还会哼起歌干活,爷爷的脸上也常常挂着笑容。小姑去了城里,家里的笑好像就都被藏了起来。兰兰想不明白,不清楚小姑为什么会去城里,城里有王家沟好吗?清泉水仍然从石洞子里流出,小鱼小虾儿在清凉凉的水中游啊游,不出一点动静。往日的那份热闹哪儿去了?河沟四壁的树叶一点点泛黄,有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常常地,兰兰会不自觉地走到小白脸家的大门前,走上台阶,摸一把那把锁住两扇大门的大铜锁。
老校长依然在教地理,他的地理课迷倒了兰兰,每每提出的问题得到解答,兰兰对这个老校长会佩服到极点,感觉这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
“老师,我们这些小孩子将来长大了,是不是都要进城呢?”那节地理课上完,她问这位像爷爷一样慈祥的校长。校长扫视了一眼正等在那等他回答的全班级的学生,“同学们,这个问题是不是理当由你们自己做出回答呢?”以缓慢的口气展开提问。
“是!”
“不是!”
“是!”……
教室里立刻像炸了锅一样的热闹起来。
校长的脸红了一阵又白了一阵,依然笑着,点名班长,要他带兰兰到他的办公室去趟。教室里便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搞不清楚哪出了差错,便各自无趣地走开。有几个调皮一点的,便尾随兰兰,一起来到校长办公室的门口。
“上课的时候,为什么要胡思乱想?”
“村里有好多的人都进了城,还有小姑……”
开始,窗户外的几个人还都为兰兰捏着一把汗。“噢,原来如此啊!”校长突然如同一个孩子一样的哈哈大笑。窗外的几个人吓了一跳,有一个还吓尿了裤子。校长不知道有人在偷听他的说话,他告诉说,像姑姑进城,是去城里干活,像从前的体育教师李向阳进城,是去城里做生意……校长向兰兰讲了很多村里人人在外打工的事,整个班空,兰兰的时间都耽误到了这。
岁月悠悠。随着岁月的流逝,长大成人的兰兰,成为了一名记者。兰兰一踏进故乡的土地,当她走过从前读书的地方,望着干枯的河流,仍然能够回忆起在小溪流洗澡、没有月亮的那个属于女儿的世界的夜晚。也正是在那个夜晚,小姑让她自个儿走回家去,小姑去哪了,她回答不了奶奶。在兰兰躺倒睡下后,小姑也还没有回家呢!在那时,对于这个家,小姑做的这些个不好的事,还仅仅只是个开始。后来,当小姑被人从城里抬回来,已经是一个死人。又过了几年,小白脸也从城里窜回来,住进了早些年盖着的那座大房子。
小白脸自个儿住在镶嵌着窗玻璃的大房子里,他的老了的父母住在镶嵌着小窗户的老房子里,老得再也做不动饭。某一天,兰兰不小心走进这座老房子。小白脸的母亲好似已经很老,脸上的皮肉好像熟透的春蚕一样透着光亮。看见来了生人,很久没有看到外边世界的两个老人格外欢喜,高兴得合不拢嘴。这母亲的话多起来,唧唧呱呱的告诉,似乎在努力讲明白一个故事:不知怎么,有一天,那狐狸精跑到了村东的河沟,在月亮藏进云彩那会儿,混进正洗着澡的大闺女中间,眼睛专管朝四周看。这下可好,月亮刚好出来,我儿自学校走出,那女妖精不早不晚,恰在这时尖叫一声,故意弄出动静,一来二去,把我儿的魂给钩了去。为躲避这个冤家,我儿才进的城。谁知道呢,这边前脚刚走,她就跟去了。我的老天爷呀,这个冤家一进城,可就苦了我的贤惠的儿媳妇了,我到现在都说,人家媳妇说什么就是不跟咱了,能赖人家吗?是咱的孩子把人家的心伤透了!我儿媳妇苦啊,在那会儿那叫过得啥日子?——手里一个钱没有,见天推着个车子去工地卖饭,这我都知道。要说媳妇,可真是不孬,给咱家拉扯着两个孩子,该吃的苦、不该吃的苦,硬是一个人扛,硬是咬着牙挺过来。话又说回来,老天爷不会让一个人永远有咽不完的苦水对不对?没过几年,那狐狸精竟然中煤气死了!这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吃不了得兜着走?……这母亲说到难过处,先是在笑,后来就抬起袖子擦起眼泪。这当口,老头坐那一声不吭,只不断地卷烟卷,每卷好一支,用舌头舔了,把细的那头伸進嘴里,“咔”的一声打着火机,火机上跳动的火苗舔舐着烟卷,烟雾在烟卷的上方形成一个螺旋状,既而扩散开来,闷得人透不过气。擦罢眼泪,这母亲继续讲下去,讲小儿子是如何的孝顺,如何在每天的早晨过来探望。“你怎不说大儿子向阳每天过来做饭的事呢?”老头闷声闷气地说道。老婆便不再吭声。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么的不可预料和千奇百怪。有一天,当兰兰按计划做完一个采访稿,从建筑工地出来,看到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妇人推着个卖饭的车子走来。那妇人推着的车子上罩了个玻璃罩,玻璃罩下的饭菜花样繁多,很快吸引了兰兰的眼球。
“喂,大婶!”看见饭菜,兰兰的肚子不听使唤地叫起来,这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吃早饭。
那妇人停下车子,脸上堆成菊花的形状。这个四十出头、五十不到的女人是谁?是她吗?兰兰记起小白脸女人的模样。不是她才怪!她记起小时候奶奶带她到小白脸家串门,看见他的媳妇脸色不是怎么样的好,大概是病了,连笑都是那么的费劲,只见无数条的沟沟挤在一起,使两腮形成菊花的形状。
“我见过你!”说过这句话,兰兰便愣在了那儿。
“你是李家沟的?”那妇人抬起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身子轻微地晃动。
“婶,没事吧?”出于本能,兰兰走过去,扶住就要倒下去的这个女人。
“喂,来碗米饭加土豆丝!”一个带橘黄色安全帽的民工打饭来了。
“来!”兰兰喊了他一声。
“来呀!”单靠兰兰一个人,实在是扶不动一个就要倒下去的人。在她也要跟着倒下去的一刻,感觉扶着人的一边轻起来,身子又很好地站在了那儿。只见小伙子拉了一把的当口,卖饭的女人已经缓过气,她一只手放在胸口间,慢慢挪动脚步,在一处花坛旁边的石块上坐下。又过了一会儿,一个骑红木兰的瘦高个女孩赶过来,一直等在那买饭的五六个民工才得到照应,各自买好饭菜离开。
“您也来份?”女孩朝站在一边的兰兰招呼。
“她是你的妈妈呀?”兰兰欢喜地叫道。
“是谁又招惹她了呢?”女孩点点头,朝女人坐着的地处努努嘴巴。
“像,像,真的很像!”兰兰欢喜地端详着女孩。
“你神经病吧你?”女孩大概知道接下来兰兰要说的话。
“你就那么恨你的父亲?”兰兰帮她将母亲送回到家,两个人一同在城市的街道上踱步。
“笑话,一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人还能称得上父亲?”女孩儿直视着前方。正是上班的高峰期。这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段。人群中三两个抬起手臂,似乎是有意和小白脸的女儿打招呼的人。女孩儿只管走自己的路,根本就不理会。在这条街道上走路,她是一个局外人。
是她的父亲将她变得这么难过的吗?小姑死了,不会再回答这些问题,小白脸也死了,也不会再回答这些问题。兰兰的记忆里,自小白脸的母亲死后,小白脸仍然在给父亲做饭。小白脸和城里的媳妇已经离婚多年,种地的本事很差,又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挣两个钱,他常常地在春天去山上,满山遍野地寻找苦菜。挖回苦菜,简单地吃过饭,他会将带根的苦菜捆成把,第二天带到城里去卖。到了秋天,山上的桃林里也仍然少不了他的背影。他弯腰曲背,在枝条泛滥的桃树下钻来钻去。这些拾来的尚好的“煤球”会保证他一个冬天不会挨冻。冬季河里结了冰块的时节,在他家的炉膛里,这些个小不点在炉膛中燃烧,送给他些微的暖和,保证了他住着的这所空旷的大房子不会结冰。“你在城里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他的一个本家实在看不下去,想着实地说他两句。“要不是我父亲这个老东西没死,我早就到城里去混了!”他微微含笑地回答,看上去,人很老实。等他的父亲死了,他的日子也更不好过,衣食无着,人很快便潦倒,得脑血栓住进城里的医院。医院是住了进去,但病看了一半,姐姐弟弟给他凑的钱便都花完了,医院便再住不下去。即使再也拿不出钱,拿不出给这个倒了霉的弟弟看病的钱,他的姐姐仍然不甘心,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他的前妻。结果去那后,这位姐姐回来时就拿回了六百块钱。
“她说什——什么了吗?”
他将钱推开,如同看到死亡一样的惊惧。
“说了。她要我告诉:就这六百了,要你回去养着!”
弟弟将他推开的钱塞回去,看着他装进口袋,跑出去办了出院手续。过了不长日子,再也做不了饭的小白脸,就这么地死在了那所大房子里。死后,送葬的人只有他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叔叔、姑姑。
村里人说,他干皮包公司,找着相好的那阵,为讨相好的喜欢,他在从前的家一分钟都不想多待。在他拿着离婚证和随身的衣服离开那天,为让父亲多留一会儿,刚上初中的女儿跑上去抱住他的腿,却被他蹬开了。正是他的这一脚,将女儿的心蹬到了千里之外,事后,不管他怎样的巴结,女儿再没有理过他,也再没有喊他一声爸爸!
起雾了,雾霾之下,城市里亮起了灯光:路灯的灯光,车流的灯光,到处是闪烁的灯光。处在灯光包围中的兰兰,眺望着百十里地外老家的方向,想像着老家的模样。故土离她是这么的远,又是这么的近,好像只有咫尺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