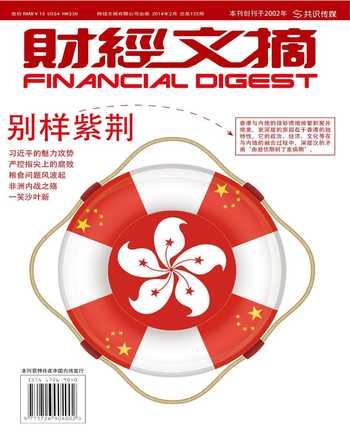一笑沙叶新
谢子菲



尽管也有“幽默”“喜剧”这些字眼出现,可“站”在资料里的沙叶新看起来仍是一副略皱着眉头、心怀担忧的模样,即便笑,似乎也多是无奈、嘲讽的冷笑。他针砭时弊的笔触,不少剧作在大陆被禁演的现实,让这模样显得理所当然。
故事常在“但是”后写出另一面,一次简短的面见访问就成了对沙叶新印象变化的“但是”:言语间,平和、有趣、心怀希望才是他给人最深的感受——正如那句他年轻时抄录在日记扉页上的话:“我是一个快乐的大牛虻!”
沙叶新又是极愿意将这种快乐传递的,剧作是他的方式之一。去年十月在香港公演的最新话剧作品《邓丽君》中,就满载他对邓丽君的感动。而观众看得酣畅甚至落泪,沙叶新便“惊呆”“喜傻”不再“不安”了。
何日君再来?今日君已来
“我张开一双翅膀/背驮着一个希望/飞过那陌生的城池/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在台湾金门劳军的邓丽君,正动情地唱起一曲《原乡人》。
这并非纪录片片段,而是共识传媒主办的“今日君已来——《邓丽君》剧本朗读表演同趣会”中的一幕。2013年12月21日,未能在大陆获准公演的话剧《邓丽君》,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北京共识堂,吸引了百余人。沙叶新亦受邀参加。
称为同趣会,不仅因为有《邓丽君》,更趣在演职人员:《投资时报》总编何力、独立学者柳红……如此一场由非专业演员带来的演出,沙叶新并不觉有什么不妥:“他们都很认真,感觉更好的是他们很快乐。”
如果说感觉到演员的快乐是一种情绪感应,那么,写作《邓丽君》可以当成是沙叶新与邓丽君之间的“心灵相通”。用沙叶新自己的话来说,“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温柔、典雅几乎是所有人对邓丽君的印象。在完成剧作的7年中,沙叶新辗转日本、法国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寻访,从未遇到有一个人说邓丽君不好,或有所顾虑欲言又止。因而在下笔时,要不要将邓丽君更私密的形象写出来,沙叶新不是没有过纠结,也曾担心观众、歌迷是否能够接受。最终,“我想通了。她敢于裸泳,敢于找个比自己小十四岁的外国人同居、不结婚,这是人性的飞跃,是一种自由的解放。而我们至今还受到很多很多压抑不敢自由。”
剧团的人很是兴奋,对沙叶新说“我们有演出裸体衣”!自然也有很多人劝阻,沙叶新却反问回去:“你们爱邓丽君吗?她这样做幸福吗?爱她就应该爱她所爱,应该以她的快乐为快乐,这才是真正的爱。”
当年,沙叶新在邓丽君墓前鞠躬,说:“邓小姐,请放心,我会呕心沥血,一往情深,一定不让你失望。”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一切都因为自己被邓丽君的精神深深感动。“为了如生命一般的歌唱事业,她牺牲了很多,童年、教育甚至婚姻、爱情,但为了正义她可以牺牲歌唱,真的很了不起。” 1984年,尽管大陆有关方面一直在联系,邓丽君仍坚持“没有道歉便不去演出”的原则,“她的所作所为不是出于党派意识、政治情结,只是人性。她以她的方式在抗议,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作为一个男人在她面前我都觉得很矮小。”
除却感动,沙叶新于邓丽君,大约也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他亦是位始终坚持自己原则、敢于追求自由的人。
那时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带着“为什么经历过‘四人帮迫害的干部们,在重新开始工作后,自己又被腐败特权打垮了呢?”的尖锐出世,在1980年初引发一场座谈会。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以一句“这个时期,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作品,归根到底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肯定了它。然而在阿克苏知青“逃亡”事件后,态度转变的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大会上表示:“至于剧本怎么办?我觉得好办。讨论后,如果作者自己觉得不成功,需要认真修改,那就自告奋勇:‘改不好我赞成不演。暂时停演。”寓意明显。在修改上演与不改禁演的选项间,沙叶新选择了后者。
至今,《假如我是真的》仍未解禁。至今,沙叶新仍有许多作品在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命运,但他却从未停笔,也不恼怒,还抱着非常感谢的态度:“禁止的苹果是甜的。这里被禁止了,别人有逆反心理啊,觉得可能是好的,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国际的舞台,用禁止的方法宣传了我。”
將“您是与邓丽君特质相像的人”的想法说给他听时,沙叶新笑笑:“是保持真纯的人。”金钱、地位、掌声、鲜花、女色……这个世界的迷惑太多,在他看来,人一定要有这种警醒:“人是会变的。所以每到一处有掌声啊鲜花啊,我真的很紧张,习惯了就糟糕了。别人抬举你是一回事,他可能很真诚,认为是应该的,但自己千万不能这样想。我就是平常人,不过是比别人努力用功、比别人掌握更多的资源,或者有些聪明才智,仅此而已喽。”
从这点来说,保持“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警醒,不盼“何日再来”,只知“今日已来”的主题倒十分贴切了。
“但我信,终有日”
2014新年伊始,沙叶新发了一条微博,对他的孩子们道新年好:“小时我要求你们‘自立、诚实、有爱心,今以新年贺词共勉之,望笑纳,我爱你们。——老爸。”自立、诚实、有爱心。简单七个字,是沙叶新从父母那里所得,又送给下一代。他说自己与孩子们都没做到满意的程度,但“还是在努力做,绝对不做和这些相反的事”。
对比老先生的努力,如今有些年轻人倒是抱着物质、金钱为上的价值观,做到这七个字反而很难。沙叶新却觉得这并不是大问题,时下存在于青年身上的不成熟、不理智,他认为是还没过“第二断奶期”:“千千万万不要对他们失望,当他们结婚、走向工作,成家立业也有孩子了,就会有责任感,这时对社会的不满或一些正常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思考‘为什么,而不是忙乱着闹啊打啊。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当然要靠中年的努力、老年的经验,但也要靠青年的破局,缺一不可,要互相理解、包容。有时候反而是中老年人的抱怨太多了。”
说到这儿,沙叶新一笑,举了个自己“对青年人有执见”的例子:某天在健步走的他看到社区河边坐着一对青年情侣,女孩儿旁边放着刚喝完的饮料盒。认定女孩儿离开时肯定不会把空盒扔进垃圾桶,沙叶新决定帮她“扫尾”,为此更改了健步走的路线,在离情侣不远的地方来回转。不曾想临走时女孩儿把空盒拿起来扔进了垃圾桶。“她捡起来的不是一个废物,捡起来的是我对青年人的信心。这其实就是一种中老年的成见。青年人非常怕委屈,他们有很多积极的要求,你只需要给他一点鼓励,帮助他融入大人的世界、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这时的沙叶新,确是那个不说暗话的人了。作品被禁,多也是因为这样,从《假如我是真的》,到《腐败文化》系列长文,他只会更加直白犀利。明禁、暗示下,沙叶新却又乐了:“我很高兴啊,说明戳到地方了。就像医生给病人检查,找到病症了。但病人要不要治那是另一回事。”
相较之下,以共识的态度相对才是沙叶新更喜欢的。“首先要了解对方真实的想法。然后要谅解,虽然我们的意见不一样,但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能先认为‘你就是坏心眼。再进一步是理解,之后才能找到共识,也就是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共同的部分。懂得双赢,才能和谐。”
但他并不执着于要立竿见影。在他看来,“不能只想着去改变别人。但你可以影响,让他自己改变”。
说话间,看着身边的老伴儿嘉华,沙叶新说:“夫妻间也是这样啊,”又哈哈一笑,“就是她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说了也很难改,现在我对她就是笑,绝对不指责。”接着乐呵呵说起昨晚老伴儿帮他放洗澡水的故事:“放了一缸最烫的水,因为她没事先调水的习惯。哎呦,那是烫鸡啊,我哇一声跳起来了。还好没有那个,不然就是浴室谋杀案啊!哈哈!”他说,如果不能改变就发怒,实在是太伤感情了,因此即便禁戏,“我也笑笑,挺好。”
不着急,笑呵呵地面对,相信未来总会好。一个个细节,堆出沙叶新的模样。可又无需赘言,只在一句回答里就尽显了——“我不知,但我信,终有日。”《邓丽君》香港公演后,许多观众问沙叶新此剧何时登台大陆,他这样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