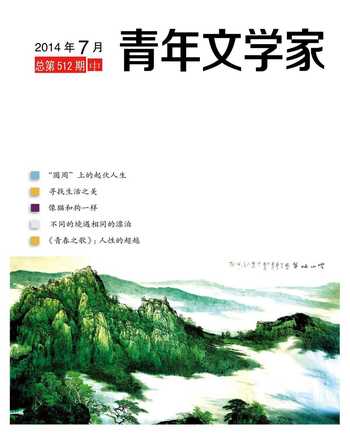西方文学中的原罪与救赎
摘 要:本文试图从对西方文学的梳理中,形成对“原罪”与“救赎”的深入思考,指出对于宗教的原罪心理形态,不仅影响过去的文学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同样因为也对日后的文学发展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原罪;救赎;思考
作者简介:徐一丹,女,山东莱州人,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0-0-02
“原罪”一词来源于基督教的传说,它指人生而俱来的、无法洗脱掉的“罪行”,是人思想与行为上犯罪的根源,是各种罪恶滋生的根,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我们大多知晓“原罪”是由于在《圣经》中有这样一则原罪故事:亚当和夏娃原本生活在伊甸园中,因受了蛇的诱惑,违背上帝命令,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并使其罪过传至后代。自此便有了“人生而有罪”的原罪说法。但是《圣经》中并没有“原罪”明确的定义,据称它是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神学家图尔德良最先提出,并被圣奥古斯丁加以发挥和充实。
既然“人生而有罪”,那么人活一世便要“赎罪”。人间由于罪而充满罪恶,神派耶稣降世,拯救人间。耶稣为赎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人们为了赎罪便信奉耶稣。关于“赎罪”,赎罪教义有四种说法,即赎金说、胜魔说、满足说和道德感化说。在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原罪”和“救赎”经历了一个理性与感性不断反复交替的发展过程,到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学,感性的原罪观和救赎观高于理性,占据重要思想地位。
在古希伯来时期,摩西先知为达到复国目的而宣扬信奉耶和华复兴的说教,在巴比伦形成了神权统治。更为了宣传耶和华,通过整理希伯来民族文化编纂了犹太教的经典——《旧约》,也就此形成了圣经文学。圣经文学中的“原罪”与“救赎”被后世文学作品拿来模仿、借用和改编,逐渐形成了原罪原型与救赎原型(或者是寻找救赎原型)。但与此同时,在《雅歌》中对男女恋情的描写大胆直率,是處在“伊甸园”中的,带有反对宗教禁欲的感性色彩,第一次对传统的原罪做出来颠覆性的描写。不过相对于该时期的其他文学作品,这种力量则显得力不从心,不足与整个时期的圣经文学的原罪救赎观相抗衡。
在中世纪文学的前期,作为其文学类型之一的教会文学在此时期的文学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基督教教义的核心观念是原罪观和救赎观,因此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利用教会文学中的“原罪”与“救赎”宣扬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达到一种教化百姓、巩固统治的作用。此时期的大多作品出自僧侣之手,其创作主要是对之前的如《圣经》、《创世纪》等一些文学作品在文学形式上进行创新改写,其主题思想依旧照搬基督教教义。如英国的《凯特蒙特组诗》其中的几篇和法国的《亚当的滔天罪行》,强调后世对“原罪”的“救赎”。在这一时期,原罪观和救赎观中理性高于感性的状态约长达5个世纪。
从教会文学之后,西方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并且迅速发展,骑士文学、城市文学应运而生。在这些文学形式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家对于资本积累的原罪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但是并没有新的造诣。文学家站在一种高于时代的立场上,只是对一种社会新现象进行描写,主要为了反映贵族、市民的精神世界,用于阅读消遣,没有着重于原罪观的探讨。但也不乏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原罪观开拓展的研究道路。如《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红与黑》中的于连等人物都是在资本社会迷失自我的人物,从迷失中探讨原罪与救赎是这一时期原罪的时代特征。
在中世纪文学的后期,诗人但丁在《神曲》中对于保罗和弗洛切斯卡的在当时看来是“不伦的恋情”描写开始带有人物主义色彩,重新对禁欲主义持批评态度。弗洛切斯卡是拉温纳领主奎多达坡伦塔的女儿,由于政治原因嫁给詹卓托玛拉特斯塔。其后与詹卓托之弟保罗通奸。约1285年,詹卓托识破奸情,把两人杀死,入地狱。据薄伽丘的说法,詹卓托貌寝而瘸,其弟保罗则美貌非凡。弗洛切斯卡嫁给詹卓托是受到欺骗。
但丁目睹了他们在地狱受到的赎罪惩罚:“地狱的飓风,一直在吹刮不已”,惨叫、哀嚎、痛哭、怨声不断。在目睹了惩罚和听罢他们的诉说后,对两人的恋情是持有同情态度的,因此在描写他们时笔调温柔;并且在描写弗洛切斯卡的同时也描写了保罗听到她诉说时的表现:
“当这个幽灵叙述当时的情景,另一个就哭泣。”①
弗洛切斯卡和保罗都已对自己犯下的罪进行救赎,有善良悔过的心。但丁肯定弗洛切斯卡和保罗的原罪,但又同时对此产生同情。因此把二人安排在地狱而非炼狱进行赎罪。但丁作为中世纪时期向文艺复兴时期过渡的一位重要诗人,虽有人文主义的色彩,开始了人们对于原罪观和赎罪观的重新思考,期望弗洛切斯卡和保罗无罪,但还是被中世纪文学的传统思想所缚。
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开始对过去固有的“原罪”和“救赎”思想产生了犹豫和怀疑。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一句“To be or not to be”表面是写哈姆雷特找不到复仇方法的矛盾心理,实质是对关于人类生命本体的“罪”的探讨。按照过去的原罪救赎观点,克劳狄斯弑兄篡位,是罪恶的表现。哈姆雷特为父报仇杀死克劳狄斯是正义之举。但是在哈姆雷特准备复仇的时候,他看到的不仅是他人心灵的丑恶,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心灵的软弱和丑恶。哈姆雷特在犹豫:为父报仇而杀死自己的叔叔是不是一种“罪”?把叔叔杀死了是否真正得到救赎?
直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时期,原罪与救赎完成了从理性到感性的观念转变。在但丁的《神曲》中,虽对于保罗和弗洛切斯卡的爱情持有同情态度,当仍把他们放在地狱赎罪。但是后来在霍桑的《红字》中,我们就看到了人们对于“原罪”新的定义。
《红字》以移殖民时期的严酷教权统治为背景,描写了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霍桑同情海丝特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爱情,虽然这种爱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人们所不齿,为教义戒律所谴责。霍桑对善与恶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美丽、健康是天性上的善,神圣是道德上的善;丑陋、死亡是天性的恶,罪恶是道德上的恶。海丝特白兰遭受了妇女所能遭受到最恶劣的刑罚。她从戴上红字的那一刻便开始了自己的“救赎”:在邢台上受罚,在海边小屋“赎罪”的凄苦生活,红字给予她沉着的烙印,珠儿给她的道德上的折磨。她的赎罪最后也得到镇上人们的认可和接受,灵魂的救赎才是通向光明彼岸的正途。丁梅斯代尔一直在善与恶直接徘徊摇摆,一生不得安宁,终于在承认的那一刻耗尽了生命,在他临死前也说出“我们已经用这一切的悲苦彼此赎了罪”。齐灵沃斯为了复仇想尽一切办法。“像一个矿工在寻找金子,像一个掘墓工在挖掘坟墓,像一个贼在进行偷窃。”②作者最后也表明,齐灵沃斯才是真正的罪人。这也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原罪”定义。而珠儿,与其把她看做是白兰和丁梅斯代尔原罪的恶果,不如把她当做是他们的原罪与救赎的结晶。
在宗教精神中,“人生的偶然,变迁和灾难是尘世生活转瞬即逝及不随人意的本质之明证,他们教导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告诉我们人的痛苦,错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迷恋来自他们对肉体及其情欲,情感和需要的屈服,因而救赎就是让人通过修行超脱和祈祷逐渐地从时间之轮和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尽管仍然活在这躯体里,但他却越来越多的生活精神中”。③霍桑以上帝的名义来解脱主人公所忍受的折磨与痛苦,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周期的开始。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要从“原罪”中寻找根源,人类本身的内在世界得到净化,外部世界的罪恶便会消失不见。霍桑在《红字》中肯定了某些清教信条,但更多的抨击了清教的残酷的条例和律令。他认为上帝是博爱的,人人都有被救赎的可能,但更多的宣扬的是人性的张扬,赞美对幸福应有的强烈的追求。这也把原罪与救赎的传统教义变得更通人性,更感性。
在“原罪”和“救赎”的发展过程中,是理性与感性的不断完善交替的过程,原罪与救赎永远都会带有理性和感性交织的色彩,纯理性或纯感性的原罪观是不成立的。从理性到感性的发展历程,同样也是人们逐渐“认识自己”的一种渐进历程。对于宗教的原罪心理形态,不仅影响过去的文学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同样因为也对日后的文学发展有深刻影响。
注释
①摘录自但丁《神曲》(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年9月第1版)
②摘录自霍桑《红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10月第1版)
③(英)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沈弘,江先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