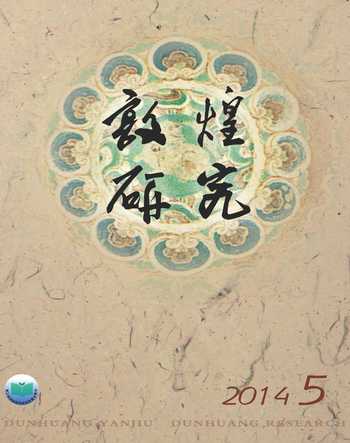“观子户”还是“馆子户”
内容摘要:学界对于敦煌所出《索铁子牒》的释读上有一些分歧,对于其中的“观子户”一词更是众说纷纭。本文整理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部分内容的释读提出了新的看法,并推定补充了原文书部分残缺的内容;至于“观子户”一词,本文以为是“馆子户”之音讹,并结合唐宋时期的重处色役问题,进行论述。
关键词:归义军;《索铁子牒》;观子户;馆子户;重处色役
中图分类号:G25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5-0095-07
“Guɑnzihu(观子户)” or “Guɑnzihu(馆子户)”
—Restudyi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Suo Tiezi Die
ZHAO Daw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Abstrac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uoTiezi Die(an official document of SuoTiezi, a manuscript among Dunhuang documents)have led to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words“guanzihu(观子户).”This paper sorts out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poses new opinion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of the contents, and supplements the missing parts of the manuscript. As for the word“guanzihu(观子户),” this paper regards it as a corrupted version of“guanzihu(馆子户),” and discusses this problem by associating it with the heavy taxe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words: Return-to-Allegiance Army; SuoTiezi Die; guanzihu(观子户); guanzihu(馆子户); heavy taxes
收稿日期:2013-07-11
作者简介:赵大旺(1989— ),男,江苏省泗阳县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方向硕士研究生。
上海博物馆藏,编号为上博8958(2)号文书,是一篇被学界称为《索铁子牒》的牒状。沙知、姜伯勤、唐耕耦、朱雷几位前辈都曾对该文书做过研究,但是因为对文书的不同理解,对文书的录文也有一些不同,尤其对于牒文中出现的“观子户”一词,几位学者莫衷一是。因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文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供批评之需。
一 文书录文及相关研究
唐耕耦、陆宏基先生对此文书的研究,体现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收录的录文中,并将其定名为《年代不明平康乡百姓索铁子牒及判》[1]。朱雷先生在《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一文也予以介绍[2],沙知先生的《跋上博藏敦煌平康乡百姓索铁子牒》也有文书的录文[3]。笔者对照图版,并参考几位先生的录文,重新释录,并略作说明:
(一)录文释校:
(2)此处唐耕耦先生将句子断在“三”处,我赞成这样断句。前已推测索定子户应继承的份额由其子索富昌继承,而索定子没有份额,所以,笔者也斗胆将此句补为:“索定子下更无二三,把分数如行。”
(3)朱雷先生将此处断为“富昌意安宅,官劫得”,沙知先生和唐耕耦先生在此处均未予断开。笔者以为在向官府呈上的牒文中,用“劫”字来表述官府行为似为不妥,故将“安宅官”①断在一处,宅官是归义军内宅司的官员,对此学界已有论述,不予赘论。
朱雷先生在前揭《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中考定该文书写成年代在曹元忠统治时期,沙知先生在《跋上博藏敦煌平康乡百姓索铁子牒》进一步将其定年在975—980年。此外,牒文中出现的索铁子与索富昌还出现于其他大致写于这一时期的文书(表1)。
(二)表1相关文书释校:
(1)据丘古耶夫斯基先生研究,《欠柴人名目》中18人见于P.3379显德五年(958)之三人团保文书,故将此文书定于958年前后[4]。另外,笔者曾以P.3231《平康乡官斋籍》为研究对象,将其中参加官斋劳动的人员在其他文书中出现的情况,以及与其同时出现者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发现《欠柴人名目》中有11人见于其中,可以明确年代的6人均在967—984年之间;1人(安丑胡)经前人研究定在10世纪后半叶;3人所在文书虽有前人研究定在9世纪后期到10世纪前期,但笔者以为应在10世纪后半叶;1人(张善子)所在文书,难以断年(见文末附表1),故而笔者以为《欠柴人名目》写成年代应当是在958年之后,距972年不远。
(2)此文书定年依据见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5]。
(3)见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第二章第二节[6]。刘著将P.3236《壬申年官布籍》中“壬申年”定为972年,并指出P.4525(8)《官布籍》与其年代相近。
(4)此文书定年参看荣新江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7]。
据上表,在索富昌合家被收为“观子户”之前,在文书中出现过两次,他参加《官斋籍》中的“官斋”劳役的次数可说明一些情况。雷绍锋指出,官斋劳动属于官府征发的力役,征发的原则是按百姓占有耕地面积来征调劳动力,富者多劳,贫者少劳,因此可以从百姓参加劳动的次数来考察其经济状况[8]。这或许可以用来考虑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索铁子、索富昌的家庭情况,在七次官斋中,二人均只参与一次,由此推测两人的家境大致相同。而索富昌在Дх 2149《欠柴人名目》中免柴原因不详,笔者推测,可能是由于承担某些色役,而享受到免柴待遇,也可能是因为贫困,经过申请,得到了暂缓纳柴的凭证,亦即“有凭”。
二 也说所谓“观子户”
牒文中出现的“观子户”,沙知先生在《跋上博藏敦煌平康乡百姓索铁子牒》中从一般字面意义推测其为供道观驱使的人户[3]238。姜伯勤先生也认为这里的“观”指道教宫观,并引此文书证明此时归义军政权继续将一些罪人配充为寺观的依附人口[9]。朱雷先生在《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中,指出“观子户”相对于历史上的“僧只户”,是封建制下的农奴,但对于“观”字,朱先生不同意释为“道观”,而是将其解释为“台榭”,而“观子户”就是执行洒扫台榭之类的杂役[2]72-79。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正如朱先生所言,归义军统治时期并未见到道教活动,道教宫观、经典亦不再出现,所以,将“观子户”理解为供道观驱使的人户似为不妥。而朱先生引以证明“观”为“台榭”之意的文献,均属汉以前的用例,唐人用例鲜见,因此笔者认为仍有剩义可探。此外,传世文献或出土文书中,“观子户”一词,笔者仅此一见,未有其他用例作为佐证,也是以上解释面临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考虑“观子户”为“馆子户”之谐音的可能性,正如沙知先生在前揭文章已经指出,此件牒文谐音别字屡见,所以,不应排除“观”也属谐音别字的可能性。
笔者之所以将“观”改为“馆”,首先是因为在其他文书中出现过“馆子”这样的称谓。吐鲁番阿斯塔纳第36号墓出土的编号为64TAM36:7(6)的《唐残钱帐》记载:
2. 廿九贯三百六十文钱。
3. 一十贯三百六十文应在。
4. 四千文帖张思林宅。
5. 一千一百一十四文,神龙元年馆子张怀藏等欠课。
6. 五千二百卌六文,典张相去欠。[10]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也介绍了一份关于“馆子”的文书,即《唐郭奉琳牒》:
(前 缺)
再则,传世史籍中虽然未见到“馆子”一词,但《隋书》卷25《刑法志》记载北齐制度曰:“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14],而据《通典》卷33《职官十五》“乡官”条,在“三十里置一驿”下,杜佑注曰:“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15]可见馆、驿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那么索定子盗马逃亡导致合家被官府充为“馆子户”,这应当与北齐刑法中规定将犯罪逃亡的人“甄其一房配驿户”是相同的处罚措施。另外,此制度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制度有很多继承性,吐蕃统治时期也能看到将人户配充驿户的情况。如S.1438《吐蕃沙州某都督状稿》记载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氾国忠等“去年兴心,拟逃瀚海,远申相府,罚配酒泉”,而其后又在状文中述及氾国忠等起义时,称其身份为“玉关驿户”[16],所以,氾国忠是因逃跑未遂,吐蕃统治者将其配充驿户作为惩罚①。可见,这种配充馆驿劳役人户的惩罚手段在敦煌地区应该是一直存在的。总之,以上材料表明,将“观子户”改为“馆子户”更有文献以及制度渊源上的说服力。
三 馆子户与重处色役
上文指出“观子户”实为“馆子户”之讹。那么,为了考察合家充为馆子户这一惩罚措施的性质及特点,需要将其与唐宋时期相似的惩罚措施进行比较。《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中“其应徒则皆配居作”,其下注云:“在京送将作监,妇人送少府监缝作;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及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犯流应住居作者亦准此,妇人亦留当州缝作及配舂。”[17]唐初的这条法律文献在归义军时期能否适用尚难确定,兹列举晚唐五代时期关于配役的资料,以便说明。据P.4040《后唐清太(泰)三年(936)洪润乡百姓辛章午牒》记载:
1. 洪润乡百姓辛章午 状
2.右章午只缘自不谨慎,冒犯
3.官□□条□格(?)偷牛,罪合万死。
4.伏蒙
6.一人收将北宅驱使。伏奉处分
7.遣章午与氾万通家造作,三五年
8.间,便乃任意宽闲。章午陪牛之
9.时,只是取他官布一匹,白羊一口,余外更不
10. 见针草。章午女子亦早宅内驱将,
11. 总合平折以了。如此公子百姓,被
12. 他押良为贱,理当怨屈。伏望……[1]294
辛章午偷牛,得到的惩罚是女儿被配充归义军北宅执役,而其本人被配在氾万通家造作,应当是为了赔偿偷牛的价值。以上事件与索铁子事件都发生在归义军时期,可见在归义军时期将罪犯合家配役并非仅见。此外还有一些只针对犯罪者本人的配役,不殃及家口。如P.3257号文书《后晋开运二年(945)十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押衙王文通牒及有关文书》(三)记载寡妇阿龙的遭遇:
14. 问得陈状,阿龙称有男□□□(索义成)犯公条,遣着瓜
15. 州,只残阿龙有口分地三十二亩……[1]297
索义成被配役到瓜州,而其母阿龙仍留在家中守着口分田地,可见并未受到牵连。
关于这一时段的传世史籍中,以配役为处罚措施的资料也很多。后晋天福八年(943)三月十八日敕文:
如乡村妄创户,及坐家破逃亡者,许人纠告,勘责不虚,其本府与乡村所由,各决脊杖八十,刺面配本处牢城执役。[18]
《五代会要》卷27记载显德二年(955)改正盐法条款,对犯盐人的处罚:
诸色犯盐人,今下三司依下项条流科断:……十斤以上,不计多少,徒二年,配发运务役一年,捉事、告事人赏钱十千。[18]430
又,《旧五代史》卷46《末帝纪上》后唐末帝时有:
丙午,以前兴州刺史冯晖配同州衙前安置。晖为兴州刺史,屯乾渠,蜀人来侵,晖自屯所奔归凤翔,故有是责。[19]
综合以上史籍和敦煌资料的情况,作为处罚措施的配役均属于较重的劳役,而将“观子户”解释为执洒扫之役者,恐怕很难算是重役。且除了辛章午的案例外,其他人均发配为官府执役。事实上,历经唐宋五代,配充官府执役这一规定是一脉相承的,《天圣令》卷27《狱官令》记载宋代的配役规定是:
在京分送东西八作司,在外州者,供当处官役。当处无官作者,留当州修理城隍、仓库及公廨杂使。[20]
这与《唐六典》的规定是一致的,即均为配充官府执役。那么,将“观子户”解释为寺院劳动人户似与以上情况不符。另外,不论是法律规定,还是现实操作,配役均有年限。辛章午是“三五年间,便乃任意宽闲”,而索义成虽未明言配役年限,但根据该文书的(二)第2行中,索怀义陈辞,“比至义成到沙州得来日”[1]296,可见索义成差往瓜州是有年限的,只不过是因为身死瓜州,无法回来。那么这些繁重的劳役处罚,应当就是唐宋时期史籍中常常出现的“重处色役”①。
这些色役名目,在一般百姓都是轮番执役,索富昌被配充“馆子户”,与普通百姓不同之处在哪呢?唐代史籍中未见“驿户”或“馆子户”,但参考唐令中关于厩牧的规定似可类推。据《天圣令》卷24《厩牧令》复原的 “唐8”在“其赏物,二分入长,一分入牧子”下注曰:“牧子,谓长上专当者。”[20]400以此推测,“馆子户”应当也是长上专门承担馆驿劳动的。鲁才全先生将一般百姓所充当的驿丁与白直进行比照,认为驿丁是番役,每年三番上下,也可能与白直一样,“周岁而代”[21]。笔者以为鲁先生的推测是正确的。据《天圣令》卷24《厩牧令》复原的“唐34”规定:
诸驿马三匹、驴五头,各给丁一人。……其丁,仰管驿州每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豫勘来年须丁数,申驾部勘同,关度支,量远近支配。[20]403
这条律文清楚地说明驿丁是每年勘配一次,也即周岁而代。同卷同条载驿丁是“仍分为四番上下”②,那么充当“馆子户”是否分番,是否“周岁而代”呢?据《唐六典》卷6“都官郎中员外郎”条载“凡配官曹,长输其作;番户、杂户,则分为番”,其下注曰:“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当番请纳资者,亦听之。其官奴婢长役无番也。”[17]193笔者以为,五代时期可能与唐前期的法律有所区别,参照《唐六典》对于“官奴婢”的规定和辛章午的案例,索富昌户被充为“馆子户”应当是有一定配役期限,在此期限内是“长役无番”的。
以上是笔者对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以及牒文中出现的“观子户”的思考。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仍然远未结束,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以期更深入地认识唐宋时期赋役制度以及刑罚制度。
参考文献:
[1]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二[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319.
[2]朱雷.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6):72-79.
[3]沙知,跋上博藏敦煌平康乡百姓索铁子牒[G]//敦煌研究院.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234.
[4]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M].王克孝,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8-109.
[5]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379.
[6]刘进宝.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8.
[7]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56.
[8]雷绍锋.《癸酉年至丙子年敦煌县平康乡官斋籍》之研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2):17.
[9]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8.
[10]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33.
[11]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341.
[12]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507.
[13]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总第11辑):256.
[14]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706.
[15]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924.
[16]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318-320.
[17]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190.
[18]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20.
[19]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640.
[20]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416.
[21]鲁才全.唐代前期西州宁戎驿及其有关问题:吐鲁番所出馆驿文书研究之一[G]//唐长孺.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364-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