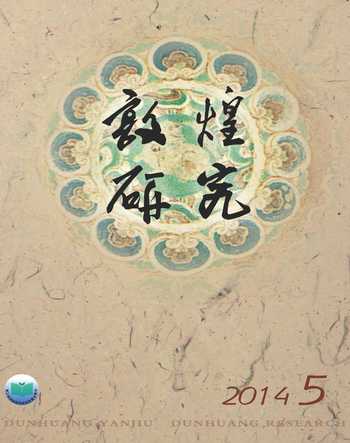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普查与分类研究
王晶波 邹旭 张鹏
内容摘要:本文在全面普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的书写符号按照性质、作用分为标示性符号、应用性符号、校改性符号和表意性符号四个大类,概括总结了各类符号的源流特点和使用情况,并探讨了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在符号发展历史中的作用、意义。
关键词: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写本;分类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5-0071-10
A General Survey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Written Symbols in Dunhuang Documents
WANG Jingbo ZOU Xu ZHANG Pe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Dunhuang Document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written symbols into four categories in terms of their nature and function: identifiers, applied symbols, collative symbols, and ideographic symbols. The study then summarizes 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s, and usage of these categories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each within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symbols.
Key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written symbols; manuscript; classific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收稿日期:2013-02-20
作者简介:王晶波(1964- ),女,吉林省洮南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献及敦煌学研究。
邹旭(1986- ),女,辽宁省本溪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张鹏(1986- ),男,安徽省蚌埠市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
一 序 说
写本时代书写符号的使用情况,是文献学、书籍史等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文献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曾荣汾[1]、李正宇[2-3]、林聪明[4]、邓文宽[5]、黄征[6]、方广锠[7]、张涌泉[8-10]等学者都曾撰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专门讨论,其他研究者有关标点符号的论著中也有所涉及[11-15],但因敦煌文献卷帙浩繁、陆续公布,尚有一些符号未进入前人研究视野;且已有研究成果或是针对某种符号的专门探讨,或是单纯罗列各种符号及用例,未经系统地归纳总结,尤其是未能对数万件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故所论仍有未足者。笔者在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历史文献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讲授《敦煌文献学概论》课程时,与听课学生一同普查了英、法、俄、日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国内各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图版照片,将全部所见符号按照性质、作用分类列出,概括总结了这些书写符号的特征和源流,并结合整个符号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试图更为清晰地揭示写本时代,特别是唐到宋初刻本出现之前的书写符号的使用情况及其特点,为全面认识中国符号的发展演变,尤其是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在符号发展历史中的作用、意义,以及更准确地释读敦煌文献,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二 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普查分类
首先要说明的是,因为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现代意义上标明句读和语气的标点符号,敦煌文献也有别于后世单向用于阅读的定型不变的文献,所以本文使用“书写符号”而非“标点符号”一词,来总称敦煌文献在书写、修改、阅读使用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符号{1}。
根据我们的普查,敦煌文献很大一部分写本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抄写过程中随同底本文字一次性抄写标注上的,但更多的符号是在校勘、修订、改动、阅读、使用、勘验等过程中标注加入的;既有原件抄写(书写)者所写,亦有阅读、使用、校勘者所注;有用墨笔书写的,亦有朱笔添注的,形式多样,用途广泛。
根据在文献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本文将书写符号分为四大类:
1. 标示性符号,起到断章析句、区分层次、提示强调等辅助阅读的作用,对文书内容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影响。
2. 校改性符号,包括插入、删除、改字、倒乙、移位等符号,对文书内容起到修正作用。
3. 应用性符号,如常见的勘验勾销、签押等,它们是文书在实际使用中留下的印记,虽非对文书内容的标示或修正,但其存在对文书的性质及其意义有重要影响。
4. 表意性符号,如重文、省代,它们代表文字,或者起到与文字同等重要的表意作用。
以下便按此分类,以表格形式总结普查所见符号。部分分类及定名与前人有异,将在备注中加以说明。另外此表格重点在于呈现符号的性质及在文献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于某些书写随意性很强的符号,如签押等,仅举若干常见形态而并不罗列其全部书写形状。
(一)标示性符号
这一类符号的起源很早,在甲骨、金文文献中就有出现。它们主要是用横线、竖线或是留空的方式来区分内容层次。由于书写工具与材料的局限,这一时期存留的符号很少,但是早期的标示性符号已经出现。到了毛笔开始使用的春秋时期,句读性质的点号出现。如《侯马盟书》中就出现了标示断句的不规则点号{2}。随后在秦代的竹简上,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就开始流行用于分章、分节、断句的点号、勾识号等{3}。
到了两汉,标示性符号开始大量出现,特别是“句读”一词开始出现。而且由于经学的发展,分章析句在汉人的经注中常有体现,如通过句后作注或章后作注的方式来分章析句。汉代还出现了专门论述符号的理论,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某些符号已有专门解释,如“■”部:“■ ,有所绝止,
■ 而识之也”[16]。可看作是对符号运用的一种理论总结与归纳。
从魏晋一直到隋唐五代,被认为是标点符号的保守期,这时大体上延续了两汉以来的符号种类,但是用法却比之前要大幅增加。袁晖等人通过敦煌文献概括了这一时期写本符号的状况[13]88-89,但因作者未做全面普查,得出的敦煌文献仅使用18种符号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通过我们的普查发现,隋唐五代时期虽然沿用了两汉以来的许多符号,但是也有很多创新。特别是由于此时期佛教的发展,大量佛教文献中使用的层次符号、图解符号、提示符号等,不论是形状还是用法上都较上一阶段要丰富与复杂很多。归纳如下表(表1):
(二)校改性符号
敦煌保留的大量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写本中,既有正规的经抄、官府文书,也有卜书、医书、学郎习字、契据杂写等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文稿、记录等,反映了这一时期写本的原始生态。这一特点是其他文献所无法比拟的,如简帛文书,虽然也有大量出土,但是因为书写材料与文化普及程度的限制,可承载的书写内容少,参与书写的人也少。而敦煌文献多为纸质,书写方便,承载内容多,并且由于文化普及程度的提高,参与书写、记载的人数众多,因此所反映的书写时的状况与符号使用情况就更加实际而客观,包括大量“二次加工”{1}的痕迹。也正因为敦煌文献的原生态及实用性的特点,保留下来大量的校改性符号。这些符号大多都被后世所沿用,影响到刻本甚至现代校对符号的发展。这些符号对正确理解敦煌文献有着重要意义。归纳如下表(表2):
此外,在敦煌文献中还多次见到校勘意见,虽非符号,但也属于文献二次加工过程的一部分,故在此略作说明。如最常见的“兑”字,或写作“兊”“■”,有时写于文书天头,有时写于文字上。Дx00795、甘博06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九十九》、浙敦089《光赞经》等写卷均有出现。关于其义,一说为“脱”字之省,一说为兑换之意[6]25-26。经考察,写有“兑”字的文书,其错误或为脱文、或为衍文、或为文字差错较多,似宜理解为兑换之意,即抄写不合要求,拆下换纸重写。有时“兑”字旁标有人名,疑为校勘人员。其中津艺172号文书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该文书正面由五代多种写卷不规则粘接而成,包括《梵网经序》《大宝积经》等佛教文献,均为兑废稿,除若干“兑”字外,还写有“董亥融”“阎海珍”等人名,背面定名为“兑纸别记”,上写“董押牙兑清张”“阎珍兑”等字样,应该就是正面出现的“董亥融”“阎海珍”。背面文书至今未见相关研究。我们怀疑与官府抄写文书出现错误兑废后向上级请给新纸的制度相关,若如此,则“兑”不只简单地表示兑换,同时也是请纸制度中的一种固定用语。
除“兑”字外,所见校对意见尚有“错”“请坼(拆)下”“却浣(换)纸”等字样,同样表示该文书需废弃换纸书写。又有注明不同版本异文的文字,如上图154《大乘无量寿经》第23行“尔时复有一百四姟佛”,天头写“番经作八十四”,应是记录书写或校勘者所见异文。
(三)应用性符号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很多实用性的文书,如入破历、勘经文书、社司转帖、契约文书、官府文书等。这些实用性的文书在汉简中也有出现,但是如此大规模地出现,敦煌文献是第一次。这些应用性文书中大量出现的一些应用性符号,可帮助我们大致勾勒出中古时期应用性文范的面貌,了解文书的使用方式。归纳如下表(表3):
(四)表意性符号
表意性符号,虽然是符号,但是具有代表文字的作用,主要有重文(或合文)与省代两种,这类符号出现也很早,在甲骨、金文中就有发现。可能由于当时铸刻麻烦,书写人尽量用很少的笔画来表达意思,像用简单的笔画来代替重复出现的文字,于是就出现了表意性的重文与省代符号。后世为了书写方便,沿用了这些符号,在敦煌文献中,这种表意性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多,而且用法丰富,特别是重文,有一字重、两字重、多字重等等。归纳如下表(表4):
三 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特点及其成因
(一)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特点
敦煌文献体现了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写本中书写符号的使用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将这一时期描述为旧式标点符号的保守期,认为这一时期介于汉宋之间,所使用的书写符号大部分在前代已出现,理论上也没有太多创新[13]88-89。但也因此,在符号发展史中,这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就敦煌文献来看,体现出如下特点:
(1)符号的使用渐趋普遍,分布于各种性质和内容的文献中。
(2)出现了一些书写形式更为繁复的新符号,集中体现在层次、标题符号中。
(3)一符多用、一号多符的现象广泛存在,符号使用上随意性与规范性并存。
(4)某些常用符号的形状和用法趋于稳定,从而为接下来刻本时代书写符号的成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在普查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敦煌文献中符号的使用是否规范,与文献内容关系不大,而与符号类型以及文献的正式程度相关。一般来说,“·”“、”与“。”形的句读符号,横折形的分隔符号、绝止符号、敬空符号、勘验勾销符号,燕形的经名号,“=”形的重文符号、省代符号,涂抹、圈除、点、卜字等删除符号,“√”形的倒乙符号等,在各种文献中通用性很强,使用广泛,符号形状也较固定,其中一些在之后的刻本时代继续沿用;其他一些符号的使用则随意性较强,尤其是层次、标题、签押符号,难以一一罗列其形状。此外,文书的正式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经反复校勘、缮写整齐的定本,其符号类型较少,往往局限于句读、重文,形状也比较固定;而草稿、学童抄本等文书中符号则往往是随手添加,较为随意杂乱。
(二)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成因
至于为何在这一时期,敦煌写本中的符号会呈现出如上特点,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 书写材质与工具的改变
随着书写材料由简帛变为纸张,书写工具也由鹿毛笔逐渐演变为更适合在柔软材料上书写的兔毛笔[21],同时以竹、木等材料削磨制成的硬笔也在敦煌地区广泛使用[22]。由此带来的不仅是书体上由隶书到楷书的转变,对符号的书写形态也有着一定影响。与简帛相比,在纸张上书写运笔可以更自由灵活,从而出现了形似火焰、莲花、螺旋、花蕾等书写形式较为繁复的新符号。而简帛文书中常见的表示断读或层次的黑方号,在敦煌文献中却销声匿迹,应该也是由于这一符号更适宜在简帛上顺着木纹或布纹描画,而在纸张上则不如圈句、三角等符号便于书写。此外,毛笔与硬笔的同时使用,“一个是面性笔画,一个是线性笔画”[22]18,也使同一种符号呈现出不同的书写形态。
2. 文书性质及内容的影响
敦煌文献中,很多并非完善规范的书籍写本,而是废弃草稿、学郎写卷、实用文书等,这些文书或抄写粗率,或反复改动,留有大量“二次加工”的痕迹,且所用符号往往依书写或阅读者的习惯率意为之。
此外,文书内容对书写符号的使用亦有影响。如经部文献写本中,出于阅读需要,书手或阅读者往往会在文书上进行断句,并且为区别正文和注疏使用分隔符号,为使双行小字注文左右长度一致而使用占位符号等,由于很多写卷是学郎所用,这一现象尤为明显。而佛经注疏的层次关系比传统典籍更为复杂,相应的其中层次符号也更为丰富,并且为了能更加直观明了地说明其层次关系,图解符号应运而生。而莲花形、火焰形符号大量见于佛教类文书,也是因为这些图形所起到的宗教象征作用。
3. 文书抄写的职业化规范化
敦煌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职业书手或官府文吏抄写的。这些文书往往经过反复校对,书写工整,符号种类不多且形态较固定,而在校对过程中所产生的兑废稿里又可见大量的校改符号。在多人反复校改同一文书的情况下,必然要求各书写者和校对者在书写格式、符号使用上都遵守共同的规范,这种职业化、规范化的文书抄写,也成为后代校改符号规范化的先声。南宋绍兴六年(1136)制定的馆阁《校雠式》称:
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23]
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规定,如删除时的涂抹、圈除,插入时的字侧添入、上下空纸标写,倒乙时的乙字,以及行侧、行中点断等,在敦煌文献中均已普遍使用。
四 余 论
纵观整个书写符号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符号处于贯穿始终的核心地位,如上文提到的断读、删除、倒乙、重文符号等,上可追溯至甲骨文、金文时期,下则一直沿用到现代,并且历代多有相关理论及使用规范,如断读符号“■”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提到。而另一些则在流变中逐渐被淘汰,如部分层次、标题符号。
另外,一符多用,一号多符的现象大量存在,说明至少在敦煌文献的时代,人们观念中对一些书写符号的区分并非十分严格,很多时候是随手书写,有助于理清文意、标示重点即可。因此,当我们以现代观念试图细致分类时往往陷入困境,如断句、分隔、层次符号在某些情况下难以严格区分。
随着出土文献的日益增多,在以后的研究中,若能还原古人关于书写符号的观念,了解在特定时期人们对符号使用达成怎样的共识,在整个符号体系中哪些处于中心,哪些处于边缘,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书写符号的使用情况定将大有助益。我们期待着。
附记:感谢所有参与敦煌文献书写符号普查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10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谢谢你们的辛勤工作。
参考文献:
[1]曾荣汾.敦煌写卷书写符号用例试析[J].木铎,1979(8):349-372.
[2]李正宇.敦煌遗书中的标点符号[J].文史知识,1988(8):98-101.
[3]李正宇.敦煌古代的标点符号[J].寻根,2010(3):82-94.
[4]林聪明.敦煌文书学:敦煌文书的符号[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245-270.
[5]邓文宽.敦煌吐鲁番文献重文符号释读举隅[J].文献,1994(1):160-173.
[6]黄征.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12-26.
[7]方广锠.略谈敦煌遗书的二次加工及句读[G]//方广锠.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19-233.
[8]张涌泉.敦煌写本重文号研究[J].文史,2010(1):107-127.
[9]张涌泉.敦煌写本省代号研究[J].敦煌研究,2011(1):88-93.
[10]张涌泉.敦煌文献习见词句省书例释[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1):65-71.
[11]萧世民.校对符号源流考略[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27(2).
[12]袁晖.标点符号辞典[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0.
[13]袁晖,管锡华,岳方遂.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14]萧世民.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标点符号考释[J].宜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26(5).
[15]萧世民.中国历史上的标点符号规范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7(6).
[16]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14.
[17]于淑健.唐写本《抄十七地要》考释[J].敦煌研究,2001(3):124-125.
[18]艾丽白.敦煌汉文写本中的鸟形押[G]//耿昇,译.敦煌译丛:第1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189-217.
[19]赵贞.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8(2):10-28.
[20]张锡厚.全敦煌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6677.
[21]藤枝晃.汉字的文化史[M].翟德芳,孙晓林,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79.
[22]李正宇.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兼论中国书法新史观[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23]陈骙.南宋馆阁录:卷3:储藏[M].北京:中华书局,19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