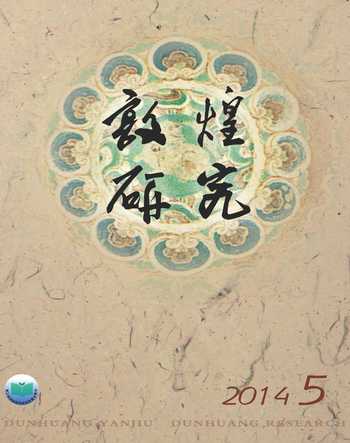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经典的种类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唐敦煌汉文文献中的“佛教经录”与敦煌汉藏对译文献P.2046“佛学字书”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这些文献中记录的佛经名称,并且对其中的密教经典进行了重点分析,总结出蕃占时期密教经典在敦煌收藏与流行的基本情况。
关键词:敦煌文献;佛经目录;佛学字书;密教经典
中图分类号:G256.1;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5-0059-05
Categories of Dunhuangs Esoteric Buddhist
Scriptures during the Tibetan Occupation
—Researches on Middle Tang
Esoteric Buddhist Texts (III)
ZHAO Xiaoxing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Centering on the Middle Tang catalogue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recorded in Chinese) and the Buddhist wordbooks recorded in P.2046 (in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itles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discusses the esoteric manuscripts among them and the popularity of such scriptures in Dunhuang during the Tibetan Occupation, ending with a summary of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collection.
Key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catalogue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Buddhist wordbooks; esoteric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收稿日期:2013-06-21
基金项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中唐敦煌密教文献研究”(20110113)
作者简介:赵晓星(1980- ),女,吉林省梅河口市人,历史学博士,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敦煌地区寺院收藏的密教经典有哪些,其中比较常用与流行的是哪些?本文试就上述问题及蕃占敦煌对密教经典的影响,梳理分析如下。
一 敦煌“佛教经录”中的密教经典
关于敦煌文献中的“佛教经录”,方广锠先生的《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一书是至今在这一方面研究最为全面的专著[1],其中那些确定为中唐时期的“经录”直接反映出蕃占时期敦煌密教经典的收藏与流通情况。方广锠先生《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中《〈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龙兴寺藏经目录〉研究》也成为敦煌保存密教典籍情况最清楚的资料[2]。马德先生《敦煌文书〈诸寺付经历〉》刍议》一文,对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敦煌文书WB32(3)1《诸寺付经历》(原系滨田德海旧藏115V)做了专门探讨,并在文后附录《吐蕃时期敦煌诸寺付经历类文书举要》中,对数件付经历进行了整理与录文[3]。除了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这件《诸寺付经历》外,敦煌文献S.3071V、P.3205V也是方先生书中没有收录的,应属其所列之“转经录”类。
综合以上两位先生的研究,敦煌文献中时代大致为中唐时期的“佛教经录”约45件,可分为以下7类:
1. 全国性经录:(1)《大唐内典录》,P.4673;(2)《大唐内典录抄》,P.3877V+S.10604V+S.6298V
+P.3898。
2. 品次录:(1)《大般若经会、卷、品对照录》,P.2361V;(2)《进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表(附总目)》,P.2314;(3)《大般涅槃经帙、卷、品及首尾经文录》,P.3150+P.3150V;(4)《维摩诘经品名录》,P.2222FV。
3. 藏经录:(1)《龙兴寺藏经目录》,P.3807、S.2079;(2)《龙兴寺供养佛经目录》,P.3432;(3)《寺名不清藏经录》,P.4664+P.4741+P.4664V、P.3060b+P.3060Va、Φ179。
4.点勘录:(1)《亥年四月二十九日勘南寺经录》,BD11493(北临1622);(2)《酉年三月十三日于普光寺点官〈大般若经〉录》,P.2727;(3)《戌年十月十六日谈■律师出〈般若经〉录》,P.2727V;(4)《寺名不清〈大般若经〉点勘录》,S.6314+
S.6314V、BD9322(北周043);(5)《点勘杂录》,S.5676。
5. 流通录:(1)《诸僧欠经历》,S.1364;(2)《壬寅年灵图寺索法律欠经历》,P.4754V;(3)《诸寺转经欠经历》,P.3654+P.3654V;(4)《归真借经函》,P.4707;(5)《光■催经状》,S.3983;(6)《交剖藏经手帖》,S.2447;(7)《归真致师兄书》,S.8566。
6. 转经录:(1)《诸寺付经历》,滨田德海旧藏115V;(2)《诸寺转<大般若经>录》,P.3336+
P.3336V;(3)《某年后六月三十日赞普新加水则道场转经等录》,BD15473+BD15473V(北简68104+北简68104V);(4)《卯年九月七日当寺转经付经历》,S.4914;(5)《灵树寺众僧为本州节儿作福田转经历》,BD06359V-3(北咸059);(6)《转经杂录》等,P.3060a、P.3060Vb。
7.配补录:(1)《龙兴寺历年分配补藏经录》,P.3010、P.3010V。
实际上,敦煌文献中吐蕃时期的“佛教经录”远不止上述的这45件,但为了谨慎起见,仅以这些有明确纪年或吐蕃特征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其中前两类,全国性经录不能体现敦煌本地在蕃占时期的藏经情况,品次录中没有密教典籍,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其他涉及密教经典的文献共有8种。
1. 敦煌文献P.3807+S.2079《龙兴寺藏经目录》,时代为吐蕃后期,其中记录佛教经典696部(包括名称重复者,以下统计同),包括密教经典43部{1}。
2.敦煌文献P.3010、P.3010V《龙兴寺历年分配补藏经录》,时代为吐蕃时期(808—823),其中记录佛教经典391部,包括密教经典49部{1}。
3. 敦煌文献P.3060Va《寺名不清藏经录》,时代约为9世纪上半叶,记录佛教经典45部,其中密教经典2部,即《大灌顶经》和《如来方便经》。
4. 敦煌文献P.4664+P.4741《寺名不清藏经录》,时代为吐蕃后期,约9世纪上半叶,记录佛教经典58部,其中密教经典1部,即《陀罗尼杂集》。
5. 敦煌文献P.3432《龙兴寺供养佛经目录》,时代为吐蕃时期,约8世纪末或9世纪初,记录佛教经典116部,其中密教经典6部{2}。
6.敦煌文献S.5676《巳年七月十四日点付历》,时代为吐蕃时期,记录佛教经典50部,其中密教经典3部,即《大法炬》《大灌顶经》《药师如来经》。
7. 敦煌文献S.3983《某年十二月五日光催经状》,时代为吐蕃时期,约9世纪上半叶,记录佛教经典18部,其中密教经典1部,即《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
8. 敦煌文献BD06359V-3《灵树寺众僧为本州节儿作福田转经历》,时代为吐蕃时期,记录佛教经典12部,其中密教经典《无量寿咒》2部。
以上8种文献反映出蕃占时期敦煌密教经典的三种情况,即收藏、供养和使用。敦煌文献P.3807+
S.2079《龙兴寺藏经目录》和P.3010、P.3010V《龙兴寺历年分配补藏经录》说明吐蕃时期敦煌的官方寺院龙兴寺收藏的密教经典有60余种(同经异名者除外),P.3432《龙兴寺供养佛经目录》说明有6部密教经典曾作为供养经使用;S.5676《巳年七月十四日点付历》和S.3983《某年十二月五日光催经状》说明《大法炬》《大灌顶经》《药师如来经》和《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等4部经典在实际流通使用;BD06359V-3《灵树寺众僧为本州节儿作福田转经历》说明《无量寿咒》在转经时曾使用。其中,能够体现密教经典流行的应是后3件文献中提到的5种密典,因为这些经典是实际使用过的。此外,汉藏对译经名文献中记录的密典也应是应用较为广泛并被汉人和吐蕃人共同尊奉的。
二 敦煌文献P.2046汉藏对译经名
敦煌文献P.2046(P.T.1257)是一件汉藏对译的重要资料,其中包括两个重要的部分,即“汉藏经名对照”与“佛教词汇对照”。《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记录此文献:“由10叶组成的一本书卷(29.5×39),无页码……其中3叶为用藏文和汉文写作并校对过的一些佛教著作的标题。7叶为藏-汉词汇。用汉文写有Mahāmeghavihāra(Ta Yun SSeu)的名字。此卷即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特藏目录第2046号。”[4]《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中提到的“Mahāmeghavihāra”指文献中部汉文杂写的“大云寺”,这段杂写位于“汉藏经名对照”与“佛教词汇对照”两部分的中间,主要写了“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的几句话,句首则书“大云寺张阇利上”。此件文献在古藏文与汉文佛教用语对译方面极为重要,因此多位学者对其进行过专门研究。其中所涉及的经名,既然需要汉藏对照书写,可见这些经名在当时应为时人所知,属于在此时流通的经典,此号文献前半部所记密教经名共11个(表1)。
敦煌文献P.2046所载经名共85个,其中密教类经典共8部{3},即占全部经名的十分之一弱,如果算上带有密教性质的大乘经典《八吉祥神咒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和《密严经》的话,密教经典的数量则超过十分之一。除《六门陀罗尼经》外,其他10部经典在蕃占时期龙兴寺的藏经目录中均有出现,说明这10部经典是敦煌当时比较流行的密教典籍。其中的《大灌顶经》和《药师经》,在上文的汉文文献中也频繁出现,可见这两种经典在蕃占时期的密教经典中最为流行。从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记载来看,这些经典的藏译本多为吐蕃译师耶喜德和伯哲所译,从侧面可以说明这些经典均存在汉藏两种译本,并在中唐时期同时流行于吐蕃和敦煌。
三 吐蕃占领敦煌对密教典籍的影响
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还有一些密教经典也非常流行,并在敦煌文献中大量保存,如《金有陀罗尼经》《大乘无量寿经》和《诸星母陀罗尼经》,为什么这些经典在以上的汉藏文献中都没有提及?这里,我们不得不考虑敦煌藏经目录与实际流通经典间存在的出入。P.2046中提到的11种经典在敦煌文献中均有收藏,其具体情况详见笔者《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陀罗尼密典》[5]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持明密典》[6]两文。P.3807+S.2079《龙兴寺藏经目录》、P.3432《龙兴寺供养佛经目录》和S.5676《巳年七月十四日点付历》等文献,似乎都与《大唐内典录》关系密切。有关敦煌龙兴寺藏经录与《大唐内典录》之间的关系,方广锠先生在《佛教大藏经史》中已有详细论述[7],并指出吐蕃时期敦煌龙兴寺的藏经目录是以《大唐内典录·入藏录》的分类形式为蓝本的。《大唐内典录》由唐道宣于麟德元年(664)编成,将所有佛经分成“大乘经一译”“大乘经重翻”“小乘经一译”“小乘经重翻”“小乘律”“大乘论”“小乘论”和“贤圣集传”等。除了敦煌龙兴寺的藏经目录采用了同样的分类方法外,S.5676《巳年七月十四日点付历》中经名的缩写与顺序也与《大唐内典录》一致,说明这些目录都是依照《大唐内典录》的。那么,由于《大唐内典录》编撰的时间早于敦煌陷蕃近百年,以此为范本的敦煌藏经目录中没有及时补入《金有陀罗尼经》《诸星母陀罗尼经》《大乘无量寿经》(法成译本)等吐蕃时期才翻译的经典就很正常。特别是根据当时佛经的分类,并没有单独分出密教类,敦煌蕃占期的密教经典都是归入相应的大小乘经典类别的,这些经典所属的类别直到元代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中仍是如此。在布顿大师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中这些陀罗尼密典主要被归入了“大乘诸经类”,而不是密教类,因此书依据了吐蕃早期的译经目录,说明在吐蕃早期这些密教经典仍是作为大乘经典一部分的,这与汉藏大藏经是一致的。
敦煌蕃占期的这些密教经典主要属陀罗尼和持明密教类,可见这两种密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密教类型。与保存至今的敦煌汉藏文献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其中没有纯密经典与晚期藏传密教的经典,说明后两种密教形式在这时并不十分流行,因此在藏经目录与汉藏对译的经名中没有体现。这点也能说明蕃占期对敦煌密教典籍的影响,因为在开元三大士入华之后,中原的密教进入了密宗时期,密宗经典在中原开始流行。而敦煌由于吐蕃的占领,中断了原来密教发展的进程,没有像中原那样进入汉传密教的密宗时期,而是更多地保留了陀罗尼密教与持明密教的特色。在经典方面,密宗经典不占主流,但敦煌名僧如法成在这一时期翻译的密教经典《金有陀罗尼经》《诸星母陀罗尼经》却非常流行,并成为敦煌密教信仰的主要经典,这是同时代中原所没有的。此外,根据吐蕃时期编撰完成的《旁塘目录》和《钦浦目录》,在吐蕃王朝翻译的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四部密典中[8],有数种在敦煌的古藏文写本中均有收存,如事续部的《顶髻尊胜陀罗尼》和观音类经续、无上瑜伽续部的《呬噜迦续》和《金刚橛续》。事续部的《顶髻尊胜陀罗尼》和观音类经续存在汉藏两种写本,在敦煌曾经比较流行,这些佛顶与观音类的密法存在汉藏的相互影响。无上瑜伽续部的《呬噜迦续》和《金刚橛续》的出现说明吐蕃翻译的密典传到了敦煌,其所包摄的密法可能也一度在敦煌传持。也就是说吐蕃密教对敦煌产生过一定影响,只是影响面要小于上述汉藏共有的经典与密法。
从以上汉藏文献中密教经典所占的比例来看,对于文献中的全部佛经来说,密教经典的比例不大,几乎不到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特别是在敦煌吐蕃时期盛行的转经活动中,现存仅见到了《无量寿咒》,其他均为《大般若经》等大乘经典。但是,时代不明的P.3854《转经录》值得注意,这件文献与其他转经录不同,在涉及的53部佛经中,包含了30部密教经典{1}或陀罗尼,占了转经的大部分。这件文献中还特别指出其中一部分是在道场中转经念诵的,这说明这些密典或咒语是应用于实际佛事当中的。这种大量应用密典的情况可能是为了特殊的法事活动,有待于进一步考证。而这种大量诵读陀罗尼与咒语的情况,让我们联想到吐蕃时期开始以汉文和古藏文大量汇抄密教咒语,即可能与这种法事活动有关。这件文献至少可以说明,密教文献在转经活动中有大量的应用,但可能只是针对特定的法事。而且,在这件文献中某些陀罗尼如《金刚罕强陀罗尼》是在传世的汉文经典中完全没有记录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自蕃占后在密教典籍方面与中原的差别。
通过以上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理清中唐敦煌密教典籍的情况,此时敦煌收藏的密教典籍约有60余种,比较常用的有10余种,最为流行的可能是《大灌顶经》和《药师经》。吐蕃的占领对敦煌密教典籍的收藏与流通有重大的影响,此时的敦煌密教典籍仍以陀罗尼和持明密典为主,并加入了这一时期在敦煌及周边地区新译的密教经典。
参考文献:
[1]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5-193.
[3]马德.敦煌文书《诸寺付经历》刍议[J].敦煌学辑刊,1999(1):36-48.
[4]王尧.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68.
[5]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陀罗尼密典:中唐敦煌密教文献研究之一[J].敦煌研究,2012(6):65-72.
[6]赵晓星.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持明密典:中唐敦煌密教文献研究之二[J].敦煌研究,2014(2):60-67.
[7]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07-115.
[8]索南才让.西藏密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81-183.
{1} 《药师经》《六门陀罗尼》《尊胜咒》《如意轮》《无垢净光》《药师咒》《大佛顶》《密严》《般若无尽藏咒》《尊胜》《五髻文殊陀罗尼》《金刚罕强陀罗尼》《香王菩萨陀罗尼》《大轮金刚》《灭恶趣》《药师》《七俱胝咒》《密严经》《大佛顶陀罗尼》《尊胜陀罗尼》《如意轮陀罗尼》《阿弥陀陀罗尼》《药师陀罗尼》《阿閦佛陀罗尼》《五髻文殊陀罗尼》《香王陀罗尼》《七俱胝佛母陀罗尼》《大轮金刚陀罗尼》《大威德陀罗尼》和《金胜陀罗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