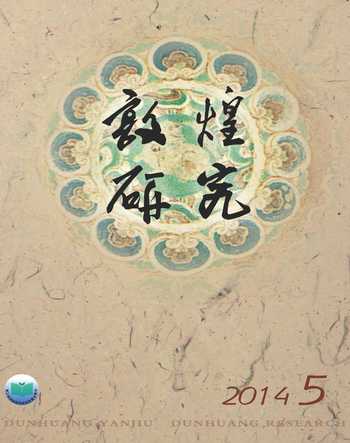从乃甲切木石窟看庆喜藏系金刚界坛城在后藏的传播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藏日喀则地区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金刚界坛城窟中的石胎泥塑造像、定结县琼孜乡恰姆石窟中残留的金刚界诸神背龛入手,结合现有文献对位于康马县萨玛达乡江浦寺主殿二层金刚界大日如来殿中塑像所据文本的初步判定,以探讨庆喜藏系金刚界坛城在后藏的传播。
关键词:乃甲切木石窟;恰姆石窟;江浦寺;金刚界坛城;庆喜藏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5-0010-10
收稿日期:2013-12-02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至13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14ZDA11)
作者简介:王瑞雷(1983- ),男,甘肃省庄浪县人,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藏佛教美术史研究。
开凿于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中期的乃甲切木石窟,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岗巴县昌龙乡的纳加村[1],该地处于以楚坦尼玛拉雪山为轴心的朝圣古道上{1},东接亚东商道,西临上部阿里。自8世纪中期,印度高僧莲花生(Padmasambhava)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之邀到西藏传播密教,返回印度时曾途经楚坦尼玛拉雪山,并在此地修行弘法[2]。石窟坐落在苦曲藏布河北岸一座砾岩小山的断壁上(图1),现存5座洞窟,洞口皆朝南,距地面高约10余米,按从西到东的顺序排列,5座洞窟分别编号为K1—K5。其中K1、K2、K5窟均不完整,且窟内无雕像壁画。K3窟残存有壁画痕迹,但因烟熏无法辨识,K4窟(以下称为金刚界坛城窟)存石胎泥塑的早期造像。
一 乃甲切木金刚界坛城窟图像分析
金刚界坛城窟是乃甲切木石窟群中保存相对完好的一个洞窟。窟内呈圆角方形,纵深3.2米,宽3.7米,高3.2米。窟顶平整,绘有壁画,因日久烟熏已模糊。窟门高2.2米,宽1米[1]180。窟内四壁在1.5米以上部分均为石胎泥塑造像,造像细长弯曲的眼睑、方圆前突的额头、细小而棱角分明的鼻子、抿起弯曲的嘴唇以及扁平的头颅和其上高耸厚重的顶髻等,无不传递着印度波罗艺术风格的特征,而宽阔的双肩与收紧的腹部所呈现出倒立梯形的体形似乎也延续着早期上部阿里的造像特征。
石窟北壁(正壁)中央为大日如来(图2),狮子座,左手臂虽然残缺,但从遗留的痕迹看应结智拳印。身后有椭圆形的头光和后人加绘的背光。主尊右侧上方为羯磨,下方为莲花;左侧上方为金刚,下方为宝。
东壁分两区,东壁北侧的主尊为东方阿閦佛(图3),象座,右手触地印,左手禅定印。主尊右侧上方为金刚王,右手置于胸前,左手位于腰间残;下侧为金刚萨埵,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金刚铃。主尊左侧上方为金刚爱,右手于胸前持物残,左手于胸前持弓;下侧为金刚喜,两手于胸前作金刚拳善哉姿势。
东壁南侧的主尊为南方宝生佛(图4),马座,右手与愿印,左手禅定印。主尊右侧上方为金刚光,右手于胸前持物残,左手扶左胯;下侧为金刚宝,右手上举于额部,持物残缺,左手扶左胯,持物破损。主尊左侧上方为金刚幢,右手于胸前朝下半握拳,左手举至左肩并持幢;下侧为金刚笑,左右两手置于胸前,持物残。
西壁亦分两区,西壁北侧为北方不空成就佛(图5),迦陵频伽座,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禅定印。主尊右侧上方为金刚护,两手举至两肩侧作持铠甲状;下侧为金刚业,双手上举于头部,头部及双手持物残缺。主尊左侧上方为金刚牙,两手于两肩前朝内持金刚牙;下侧为金刚拳,双手于胸前,右手朝上,左手朝下,两手疑似相握五股杵。
西壁南侧主尊为西方阿弥陀佛(图6),坐具残缺,应为孔雀座,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主尊右上侧为金刚利,右手于胸前持剑,剑的上段残缺,左手于胸前疑似持梵夹;下侧为金刚法,右手于胸前作揭莲花状,左手持莲。主尊左上侧为金刚因,右手疑似于胸前持金刚杵,左手扶腿;下侧为金刚语,两手于胸前持金刚舌。
南壁窟门上方分为两排,上排为站立的内外八供养菩萨(图7),头戴三叶宝冠,上身裸露,下着长裙,腰肢纤细,臀部较宽。下排为四摄菩萨,天窗左侧为金刚铃和金刚锁,右侧为金刚钩和金刚索。
从眷属的配置及坐具来看,该窟供奉的是金刚界诸神(图8)。本因造像破损严重,尤其是主尊及眷属的手部持物大多已残缺不全成为断定该窟图像所据文本的一大难题,但庆幸的是围绕该窟金刚界坛城主尊大日如来四方的四波罗蜜菩萨是用四部中的三昧耶(图9;是指在金刚界坛城中,围绕在主尊大日如来四方的金刚波罗蜜、宝波罗蜜、法波罗蜜和羯磨波罗蜜菩萨不是以具体尊格——女尊菩萨形的形式出现,而是用金刚、宝、莲花、羯磨——物形代替)而非具体菩萨装的尊格形表现。因此,这一特征成为研究该窟金刚界坛城图像流派的突破口。
关于金刚界坛城,觉囊达热那他在《后藏志》中曾详述了其文本依据和著译源流,他指出:
一般而言,金刚界坛城的主尊是大日如来,另有三十七尊神佛,此系《摄真实性根本续》(De nyidduspairtsargyud)四品中第一品规定。注释这一本续的曾有三人:善巧词、义者之阿阇黎庆喜藏(sLobdpon kun dgasnyingpo)的注释本分上下两卷,上卷在仁钦桑波时译出,下卷在尼泊尔大悲(Balpo thugs rjechenpo)和尚噶(Zangsdkar lo tsāba)时译出;善巧内容的佛密(Sangsrgyasgsangbo)和善巧辞令的释迦友(Shākyabshegsgnyen)的注释为《阿瓦热达》(Aba ta ra)和《乔萨罗庄严论》(Kosalairgyan)。以上注释谓金刚界坛城的主尊大日如来。[3]{1}
8世纪的佛密、庆喜藏及释迦友被称为《真实摄经》{2}的三大注疏家。西藏的金刚界坛城图像除依据佛密的《怛特罗义入》{3}、释迦友的《俱差罗庄严真实摄疏》{4}、庆喜藏的《真性光作》{5}这三大注疏之外,另有庆喜藏的金刚界曼荼罗仪轨书《一切金刚出现》{6}、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初印度密教成就者无畏作护的诸尊观想法《究竟瑜伽鬘》{7}及与此构成姊妹篇的曼荼罗仪轨书《金刚鬘》{8}。其中,在《怛特罗义入》中并没有对坛城中的具体尊格予以描述;《俱差罗庄严真实摄疏》除五佛之外对其他尊格的尊像也未详述;庆喜藏的《真性光作》和《一切金刚出现》给出了具体的尊容,并将围绕大日如来的四波罗蜜菩萨用四部中的三昧耶形式表示{9};而在《究竟瑜伽鬘》中则给出了四波罗蜜菩萨的具体尊形{10}。
从中可以发现,乃甲切木金刚界坛城窟中的造像更接近于庆喜藏的《真性光作》或《一切金刚出现》[4-5]{11}。但由于该窟造像破损严重,对于采用二者中的具体哪一文本却难以推定,可以肯定的是该窟应沿用了庆喜藏注疏的粉本{1}。
与乃甲切木石窟相邻的位于定结县琼孜乡恰姆村以南3公里处的恰姆石窟I区1号窟(IK1)[6]也是一座反映金刚界诸神的坛城窟{2},石窟营建于11世纪前后{3}[7],位于中尼边界的果美山南北走向的给曲河西岸,整体面东。峭壁上布满了密密匝匝的蜂窝式洞穴,多数为早期人类的穴居窟和禅修窟,初步调查I区残留塑像和壁画的洞窟有3个,均破损十分严重。
恰姆石窟IK1窟是一座以悬塑形式表现金刚界诸神的造像窟,单室,坐西朝东,窟内壁面弧状,平面呈马蹄形(图10)。泥塑和壁画主要分布在西、北、南三面墙壁,现仅存若干头光、背光以及五组五方佛高浮雕基座(图11)。泥塑造像已毁坏,仅东南方靠门处存一菩萨的下肢部分及坐具。南壁和北壁的头、背光之间有彩绘的上师像和供养人画像(图12—13)。由于后人在上部贴有擦擦,早期的壁画破坏严重。窟顶呈半穹窿形,密布着四方连续形的填花图案。在四朵团花相连构成的八角形图案中央绘有一只小舞狮(图14)。
IK1窟现存完整的泥塑背光32个,分别分布在南、西、北三壁。另外,在东北壁上方有残损的背光痕迹(图15)。倘在没有塑像仅存背龛的情况下很难判定该窟金刚界坛城是依据哪一派系塑造的,但从现存完整的32个背光加上残损的1个总共33个理解的话,该窟很可能亦受庆喜藏派系的影响。因为在庆喜藏所传金刚界坛城这一派系中,四波罗蜜菩萨是用四部中的三昧耶形式代替,且往往在塑像中有被省略的现象{1}[5]117[8]。因东壁窟门上方坍塌严重,不知之前是否有塑像,但从石窟整体布局分析,在窟门上方仅有的空间之内再塑四尊尊格凑够金刚界37尊是很有难度的。由于不是完整的造像窟,所以也不能排除该窟受其他派系的影响。
不管怎样,该石窟采用的悬塑造像样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西部阿里11至12世纪的造像传统。这一传统经定结沿线的恰姆石窟和乃甲切木石窟,朝东一直延伸到萨玛达地区11至12世纪的佛教寺院造像,甚至在15世纪初叶江孜白居寺大殿西配殿的金刚界坛城中还留有其余晖。恰姆石窟窟顶的团花纹样与印度西北部的塔波、青藏高原西部边缘的阿奇佛殿及东嘎石窟藻井装饰纹样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椭圆形的背龛承接着雅鲁藏布江流域山南扎囊县11世纪末扎塘寺泥塑头光的传统,尤其是该窟供养人的造型、衣着穿戴与萨玛达地区11世纪早期艾旺寺供养人像(图16—17)有着惊人的相似。石窟虽然残损不全,但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上承西部阿里,下接亚东至江孜商道萨玛达地区的早期寺院造像,是西部阿里造像样式和佛教绘画题材通往后藏东部的必经之路。
二 萨玛达至江孜商道沿线的
金刚界坛城遗存
经朗达玛灭法,10世纪末赴安多跟随喇钦贡巴绕赛(892—975)及其弟子求法的洛顿多杰旺秋和仓尊喜饶僧格学成返抵后藏,分别以年楚河流域的白朗、江孜、康马为基地进行弘法,延续法脉。洛顿主要活动在年楚河下游地区,仓尊主要在上游地区[9]。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建立了寺院[9]38{1},广弘佛法。随着寺院的建成,僧人四处求法成为当时的热潮。年楚河上游的江浦·白玛、江浦·却(曲)伦(洛)和年堆·介夏等人是前往上部阿里地区求法的首批人物,他们拜师于当时阿里三围享有名气的大译师仁钦桑布和小译师玛雷必喜饶学习上部佛法[3]35-36{2}。江浦·却伦学成返回年楚河上游修建了江浦寺{3}[10-11]。他为了弘传自己在阿里三围所学之法,还专门在江浦寺传授瑜伽续和《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的教义[9]50-51。
江浦寺原址位于日喀则康马县萨玛达乡西1.5公里、江孜南约68公里处,恰好处于通往锡金的交通要道上。寺院现已不存,只能借助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于1932年至1941年间的考察记录及相关藏文史料予以研究。
金刚界大日如来殿位于主殿二楼北侧,内主供金刚界诸佛(图18—19),塑像现已毁坏。据图齐考察图像资料看[12],五方佛及眷属头戴五佛冠,脸方圆,双眉狭长弯曲,鼻梁直而鼻翼小巧,双耳垂珰、胸饰璎珞,两臂戴臂钏和手镯,深受印度波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最引人瞩目的是五方佛(除西方阿弥陀)的过肩饰带及菩萨裙裤上所饰团花和连珠纹纹样亦受西域于阗造像纹饰的影响。关于金刚界坛城殿的悬塑造像,图齐并没有详细地描述,只是谈及该殿坛城再现了《真性集》相关曼荼罗或金刚界曼荼罗[11]84。
据《后藏志》记载,11世纪尼泊尔大悲译师和尙噶译师曾在年堆江若的叶塘寺受寺主觉塞京巴尔的资助将仁钦桑布有生之年未翻译完的庆喜藏对《真实摄经》的注疏之下品《真性光作》翻译成藏文[3]36{1}。叶塘寺与江浦寺同处年堆江若,两寺相距很近,大悲译师和印度班底达旬努邦常驻锡在江浦寺,尙噶译师甚至圆寂后将自己的心脏供养在江浦寺内用白旃檀制成的宝盒中[3]36{2}。江浦寺金刚界坛城殿的塑像或许与11世纪初大悲译师与尙噶译师在叶塘寺对庆喜藏的注疏《真性光作》的翻译有某种关联。
大译师仁钦桑布曾三次赴迦湿弥罗求学,不仅在那里依止了许多上师,而且还将众多班智达迎请入藏,在阿里地区建立了瑜伽部怛特罗之传轨。这些怛特罗传轨中主要以庆喜藏的著述为主[13]。仁钦桑布在瑜伽理论学派中研习《真实摄经》甚优,他不仅仅翻译了该部经典,还翻译了其重要的注疏之一,即庆喜藏《真性光作》的前半部分,以及该传轨的众多仪轨书[7]26{3}。仁钦桑布第一次从克什米尔返回阿里后,江浦·却洛前往谒见并师从他学习由信作铠所传的金刚生起灌顶和《俱差罗庄严》;仁钦桑布第二次游学克什米尔回国后,他又从大师那里听受了《最上本初怛特罗》注释的未尽部分和之前遗留部分[13]218。江浦·却洛作为大译师仁钦桑布的弟子之一曾两度深受其教诲,大译师的瑜伽理论学派势必会对他给予影响,虽然他从大师那里受过释迦友对《真实摄经》的注疏《俱差罗庄严》,但不能排除他对大师最为擅长、研究颇深的庆喜藏对《真实摄经》的注疏《真性光作》的了解,且在注疏《俱差罗庄严》中除五佛之外没有对金刚界坛城其他尊格做详细描述。
从以上两点来分析,江浦寺金刚界坛城殿中诸尊造像与庆喜藏的注疏《真性光作》有很大的关联,其殿内的造像很可能就是依据该注疏完成的。
萨玛达乡朝北约68公里处,建于1422年间的江孜白居寺大殿一层西配殿的金刚界坛城彩塑造像(图20)[14],再现了藏传佛教泥塑造像最后一抹晚霞的光辉,它将西藏悬塑造像之美推到了至高点,自此之后在西藏本土再难以找到如此精美的塑像了。该殿堂内安置了33尊金刚界诸神,据日本学者田中公明的研究,该殿内的造像仍延续了早期庆喜藏系金刚界坛城造像的题材[5]104-125。
三 余 论
乃甲切木石窟处于西藏西部阿里与卫藏腹地的相接地带,为古代交通要冲。从乃甲切木石窟出发,东经岗巴县,转东南至嘎拉措,再朝北便是亚东古道通往江孜年楚河流域的萨玛达乡;西接西部阿里,紧临定结县东南部的恰姆石窟(图21);朝南沿叶如藏布江至今天的岗巴县昌龙乡,经曲登尼玛寺和楚坦尼玛拉山口,即可进入锡金;从西南方翻过尼拉山口后,有数条通道连接尼泊尔。沿高山草场与河流两岸形成的通道使东西南北相连,为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亦是西部阿里上路秘法东传的必经之地。
以楚坦尼玛拉为轴心的定结沿线的乃甲切木石窟、恰姆石窟及东部年楚河流域亚东通往江孜商道上的江浦、白居等寺中的金刚界坛城造像是延续着西藏西部早期悬塑造像的传统手法。《真实摄经》作为大译师仁钦桑布瑜伽理论学派之一,自11世纪初已被他和克什米尔译师信作铠翻译成藏文。尤其是大译师虽未译完但一生研习尤甚的庆喜藏对《真实摄经》的注疏之下品《真性光作》,是由尼泊尔的大悲译师和尙噶译师在年堆江若的叶塘寺翻译完成的,叶塘与江浦两寺相距不远,两寺僧人日常往来密切。11世纪前后至12世纪开凿的恰姆石窟、乃甲切木石窟及萨玛达地区江浦寺所盛行的金刚界坛城造像,很可能与大悲、尙噶译师对《真性光作》的翻译有关,或与当时赴西部阿里求法的僧人深受后弘期初新密教的开创者仁钦桑布瑜伽部怛特罗阐释之传轨特别是庆喜藏的注疏及金刚界坛城著书有关。
乃甲切木石窟石胎泥塑的造像样式,尤其宽肩收腹突出三块腹肌的造像手法和恰姆石窟窟顶团花绕舞狮纹样及供养人形象,以及江浦寺金刚界坛城殿中的西域于阗绘画纹饰的采纳,无不渗透着不同地域文化中艺术交流的因子。该时期后藏石窟寺院处于形成与发展阶段,高度融合了各种艺术风格和各种教义。从艺术风格角度来看,它把波罗艺术风格、西藏西部及西域艺术因素变体糅合到了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藏族艺术表现模式;从宗教角度来看,它是藏传佛教后弘期阿里三围和后藏地区佛教流派的交汇点。
附记:本文乃甲切木石窟中所采用的图片由西藏青年报特邀摄影师、西藏文化爱好者范久辉老师提供,恰姆石窟及白居寺金刚界坛城殿中的图片由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的谢继胜教授提供,在此致以谢忱。
参考文献:
[1]何强.西藏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J].南方民族考古, 1991(总第4辑):183.
[2]霍巍.关于卫藏地区几处佛教石窟遗址的调查与研究[J].西藏研究,2002(3):53.
[3]觉囊达热那他.后藏志[M].佘万治,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54.
[4]松長惠史.インドネシアの密教[M].京都:法蔵館,1999:222-223.
[5]田中公明.インド·チベットの曼荼羅の研究[M].京都:法蔵館,2010:117.
[6]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西藏定结县恰姆石窟[J].考古,2012(7):68-82.
[7]谢继胜.羌姆石窟揭示西藏腹地佛像样式来源的秘密[J].中国国家地理,2012(8):52.
[8]图齐.梵天佛地:第3卷: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象征: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6-17.
[9]Roberto Vitali. 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M].London:SerindiaPbulications,1990:38.
[10]Ulrich von Schroeder.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M].Hong Kong: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s Ltd,2001:844.
[11]图齐.梵天佛地:第4卷:江孜及其寺院: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3.
[12]图齐.梵天佛地:第4卷:江孜及其寺院: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5-30.
[13]郭诺·迅鲁伯.青史[M].郭和卿,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217.
[14]熊文彬.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