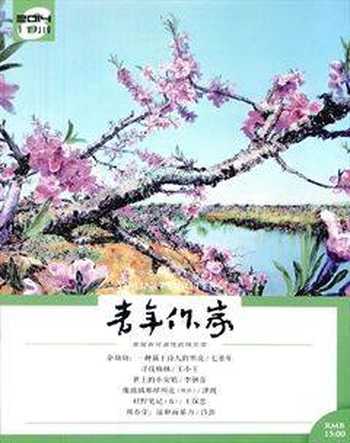老张
老张是单位的清洁工和杂役,当我们还在老院子办公、住宿的时候,他和老婆住在单位的公厕楼上,负责打扫全院(包括各个角角落落)。每当要开会时,我们会去叫他:老张,10点以前把会议室打扫出来,烧上开水,把杯子摆一下。然后,开会的时候,一切都整整齐齐了。排练场需要几张桌子,我们会去叫:老张,把仓库的那几张桌子搬到小剧场。不一会儿,桌子就搬来了。办公室还没配上饮水机的时候,老张还负责在一楼楼梯间烧水,储水器里没水了,大家会叫:老张,没水了,把水加满。有时到中午了,老张和老婆在后院食堂旁的狭窄通道上煮饭,我们也会去叫:老张,去把运来的复印纸搬到楼上办公室去。我们都会叫:老张、老张……我们叫的时候,都很理直气壮,没人觉得不应该。
而老张呢,永远是一种表情,就是木讷得没有表情,但绝不是拒绝,他身形瘦小,鼻头永远是红的,眼睛善良而无辜,他好像看着你,又好像不敢看,半垂着头,喉咙里诺诺着,表示他听见了。不一会儿,交待他的事就做好了。但我从没听见过他说话,也没看见过他笑,有时问他什么,他也说不出,只含糊地答几声,听不清,我们也就算了。
后来,单位因拆迁搬了新址,老院子即将拆了,但因里面家属众多,老张留在了那边,继续负责打扫清洁等杂事。
我们在新的办公楼里,又增添了几名保安、做清洁的聘用人员,杂事又有人做了。没人想起老张,他本来就是单位的一个隐形人啊,迎面碰见了没人招呼他,没人对他点头微笑,也没人跟他客套,像没看见一样,我也一样,最多把头低下来,免得那么趾高气扬,大家只是在有事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会不假思索地喊:老张、老张……
2012年,我们在新办公楼安顿下来,开始热火朝天地工作起来,老张早就不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直到有一天,突然从老院子那边传来消息:老張喝农药自杀,正在医院抢救。原因是有个人的自行车丢了,怪罪到老张头上。
老张原来这么不堪一击,我想一定是多年的无形压力堆积起来,丢车事件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个人,除了自己的老婆,没人爱、没人疼、没人尊重、活得还不如一只宠物,人人都可以使唤他而人人都只当他是一个可用的物件,没有谁把他作为和自己同等的人,那他该怎么办呢?我想,除了把自己的尊严扔掉,做好一个奴隶、做好一只泥鳅,别让别人觉得硌涩,甚至让高高在上的人们体会到使唤人的快乐,那他就成了。
但老张不是这样的人,他心很重,不随便,有话又说不出来,闷在心里,闷出了病,自行车丢了,他觉得是天大的事,委屈,又觉得这个责任自己无力承担,还有压在心底的自尊,他找不到出口,唯有以死明志。
人心还是善的,接着,单位掀起了给老张捐款救治的热潮,捐款进行了两轮,因为是个穷单位,第二轮的时候,有人又觉得不适了,我也有些嘀咕:不是捐过了吗?
我们对老张没有感情,单位里人与人之间不是靠感情维系,人的地位微妙而敏感,做弱者是难受的。
但捐款还是顺利地完成了,数目不大,但对于老张来说足够了,因为当他专门到新办公楼来时,我看见他在微笑,并且完整地说了两句话,他被农药烧过的嗓子不仅没有沙哑,而且比他以前的嗓子还要清亮。他活过来了,而且获得了新生!
老院子那边贴出了老张家属们写的大红感谢信,老张真的很感激,人们没有忘记他,人们帮助他渡过了难关,人们对他是有善意的,原来,这个单位不是那么冷漠和残酷的。老张终于笑了,这可能是他几十年里第一次笑。
虽然人们依然是带着潜在的优越感在伸出援手。
我很惭愧,我犯过嘀咕,我的心有些冷。
[作者简介]周南村,女,四川成都人,出版个人诗集《花雕》;供职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