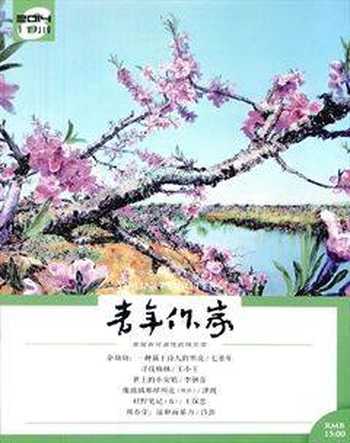村野笔记(选)
[风掀起了村庄的白发]
进村的路肯定不只这一条,可它就在公路北侧,因而,虽已驶过了路口,我还是把车掉了个头,然后顺着仅可通过一辆车的坡路,猛地扎了下去——路,夹在两道土崖间,与路基构成一个45度角——到了坡底,视野就开阔起来,绿的树和褐色的窑院尽收眼底。窑院都是浮石垒就的,依着坡势,层叠而上,一排比一排高,是典型的山村布局。
村庄背靠的那座山,叫黑山。
大半个县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座山,山顶上的烽火台像个小老头,一年年站在那里,离着老远就瞭得到。好多次,我在火山间的阡陌游荡时,总会看到这个日渐衰老的村庄,尤其是一场大雪过后,那斑斑驳驳的老窑洞更是让人牵挂。这也是我此次进村的目的——近距离地拍摄一下这些窑洞。
我把车丢在路边,和朋友一起进到村中转。
天上有云,也有风。风赶着云在村庄的上空游走。
这是村东头,一抬眼就能看到北边那条大壕堑,它与远处的黑山沟通起来,将东边的几处窑院与整个村庄隔开。一处院子的西墙根下,停着辆卸了轮胎的三轮车,不远处的干草堆前,有几头毛驴在吃草,还有几头毛驴不吃草,脸拉得长长的在沉思,也像陷入了无限的忧伤中。见我在看它们,就也抬起长脸看我,看了一会儿又低下头吃草。靠近南边公路的土崖下,有十来孔土窑,都装着门,有铁皮的,也有木制的,锁得紧巴巴的。门框两边裱了砖,看得出花费了不少心思。我猜想,这些窑洞可能是存放山药的。
村中只有东西一条街,路是水泥面的,也只能供一辆车通过。路南有几排窑洞,更多的窑洞都在路北。窑洞都很老很老了,老得长出了白发,风一刮,白发就贴住了头皮,风过后,又站了起来。其实窑顶上长的不是白发,是一种叫白草的草,毛绒绒的,让阳光一照,很耀眼。路南的巷子口,坐着个老妇人,风也掀起了她的白发,就跟窑顶上的白草似的。
那些窑顶都长着白草呢。朋友忽然说。
怎么整个村庄都长出了白发呢,真是老了,老了。朋友又说。
说话时,我看到风正掀起了窑洞前老妇人的白发。风让这个村庄更老了。
我们沿着这条街继续走。我发现路北的好几条巷子都封了,巷口用浮石拦了墙,墙上堆着些干杏枝。不用说,有好多窑院已没人住了,院墙里杏树的枝枝杈杈却探出了墙头,眼下,叶片已展开,将墙头也染绿了。我给这些墙头都立下了存照。
我拍照时,有位老者一直坐在附近的一个门楼下望着我。那应该是他自家的院子——门洞敞开着,浮石垒就的窑洞和院子里吃草的驴都暴露了出来。我走过去时,他还坐在那块石头上,连抬抬屁股的意思都没有。一边还有块大小一般的黑石头,全都是我们这个地方常见的火山岩。我去过的一些类似的农村,几乎所有的门楼前,都有两块这样的石头,相当于安放了两只把门的石狮子。通常,这样的石头上总会有老者坐在上面。有时候,他们会在这里坐上一整天,你不知他们都在想些什么。
我向他打问起了村中的一个人——十几前的老冯村长,他半天也没听清我说的啥意思,只是嗯嗯啊啊地应承着。我只得从他面前走过,走了一段路再回过头时,他还在看着我,我冲他点点头,笑笑,他马上就把头扭到一边去了。又走了一段,我又回过头,发现他还是那样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大概在想,这个拿相机的人到底想干啥?这些破窑洞真就有那么好拍的?朋友笑道,这老头不会把我们当贼了吧?我说,有可能吧,他以为我们是进村摸底的,白天察看好了,夜里就会摸进来,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你看你看,那老头儿还在盯着我们看呢。走出老远,朋友又说。
这有啥稀奇的,来的人少嘛。我说。
对了,听你刚才那么和他说话,你好像来过这个村?朋友想起了什么。
那当然,我还在这个村当过工作队长。我说。
吹牛吧,咋从没听你说起?朋友又笑。
我没去争辩,但十几年前,我确实在这个村当了三个月的工作队长,是抽调下去搞宣讲的,至于宣讲了些啥,最后又搞出了个啥名堂,现在一点都记不起了。這个村叫东阁老山村。虽是建在了黑山坡脚下,可能是因为离着公路南的阁老山更近吧,就得了这个名字。与黑山一样,阁老山也是这个老火山家族的一员,且很有些名气。这山,清代以前叫栲栳(kǎo lǎo)山。栲栳,乡间称作“栳栳”,也叫“笆斗”,用竹蔑或柳条编制而成,上下粗细一致,形状像斗,是专门用来打水或装东西的一种用具。我又看了看公路南的山,但从这个角度看不出它像个栲栳,只觉得它像堵厚实高大的墙。
阁老山的西边也有个村子,也叫东阁老山村,准确地说,那是新村,我当时就住在那里。现在我驻足的是旧村。说来好笑,当时听村干部说旧村没几户人家,竟然就没过来走一走。那时候还是个生瓜蛋,对身边这些老火山几乎没一丁点兴趣。快离开时,住在旧村的村长请我去他家吃饭,那天好像下着雪,我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路上,从新村到旧村,走在浮石墙垒砌的巷子里,耳边只有咯吱咯吱的踩雪声。大地是白的,窑顶也是白的,走在雪里的鸡呀狗呀也是白的,而头顶上方是白茫茫的火山。
真像是做了个梦,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感叹起来。
看来,你还真在这村住过。朋友好像相信了。
是,又不是。我说。
你说得越来越玄乎了。朋友说。
我没去理会,带着他往一条巷子里走。脚下的路是一面坡,朝着北面的黑山渐渐升高。这其实是条街,过去村子很红火时的街吧。老远就能看到那个粮囤似的水塔,水塔是潮湿的,可能还在用,边上是一根电线杆,我照水塔时电线杆总是想挤进取景框里,让你无法回避。
还有几只鸡也进入了我的镜头,鸡们可能是村庄里最低调的活物了。早起打过鸣之后,接下来的一整天,它们好像就再不去发言或讲话,就那么默默地刨食了。要不是突然闯进了镜头,肯定也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狗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村子的狗,根本就耐不住寂寞。我才照了几下,一条大黑狗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冲着我咬。汪,汪汪,汪汪汪,唬,汪、汪、汪,汪汪汪。巷子空空荡荡的,这条狗发出的声音就分外的响,亮,亮得像它身上黑色的皮毛。我见到的狗,一般是,你不去理睬它,它汪汪几声也就走开了。这条狗不是,这条狗好像是狗类的一个异数,顽固得很呢,越咬越凶,看那意思,不把我们撕成两半它就不打算离开。我想我不能胆怯,我要是稍微露出一点害怕,它可能真就扑上来了。可是朋友却有些害怕了,直我往身后躲。
别真让它咬上一口。朋友说。
你越怕,它越会咬你。我笑了笑。
我就是不怕,它也可能咬我。朋友腿哆嗦起来了。
我一弯腰,捡起了块石头。狗怕弯腰,这是我小时候就接受过的教育。果然,这条狗一夹尾巴,开始后退了,退了一段,它又停了下来,抬嘴冲着我汪汪汪地咬。这厮太不友好了,我骂了一句,手中的石头即刻飞了出去。其实我也就是想吓它一吓,并没有要击中它的意思,所以石头就长了眼睛,绕着它射出去了。但这条狗还是给吓坏了,尾巴一夹,箭也似地射得不知踪影了。
我还是想错了,当我们顺着巷子继续北上时,先前给吓跑了的那条大黑狗又复辟回来了,身后跟着五六个同样颜色的帮凶,形成了一个气势汹汹的黑色方阵。我知道遇上麻烦事了,提醒朋友沉住气,不能让这些家伙看出我们的害怕。我们定定地立在那里,面对着它们的万丈狂吠。还是那条大黑狗打头,其余几条,都团结在它的周围,这样对峙了几分钟,这群狗明显有些怯阵了。我觉得该出击了,一弯腰又捡起块石头,这是真正的浮石,掂在手里轻飘飘的,可我知道,这也足够了,果然,石头飞出去时,它们抢在前边跑了。跑了一段,又停下来,冲着我们狂吠。我觉得这回它们是真正的怯阵了,尽管还在狂吠,也是极度害怕中的狂吠——面对两个蓦然闯入的陌生人。
我拉着朋友,接着往村庄的高处走。
在高处的一排房院前,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妇人,她腰背弯得像张老弓,身子松垮得像要散架似的。她从她的窑院那边走过来,可能是要到这边的巷子口站一站,但是我等了好久,也没见她过来,她走得实在是太慢太慢了。我与她之间隔着一堆庞大的农家肥。这时候太阳已经西斜,可能是受不了光的刺激吧,她一边走,一边腾出一只手在眼前搭了个凉篷。她走得可真慢啊,我本来想问她句什么,可她就是走不过来。我只得朝巷子深处走去,后来的情况是,等我再回过头时,这个老妇人竟然不见了。我不知她往哪里去了,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还是她本来就不存在?只是我的个幻觉?
我并没有走到巷子尽头,巷子口给一处快要废弃的窑院堵上了。这一排院子前,有一片空阔的场地,我拍了门户前堆放的葵花秆垛,秆子让雨水侵蚀得已经生了锈。不知为什么,每次见到这样的垛子,我都会生出一些感慨,好像这是垛在一起的旧时光,老年代,或许它们真是时光的标志或化石?后来,又走过了一条狗,不是我见过的那一群的一员。这条狗不咬也不叫,只是默默地盯着我,一点都没有离开的意思。沉默的狗比狂吠的狗更让人害怕。老话早就说了,咬人的狗不叫。我和朋友相互对视了一下,匆匆地沿着原路返回,走到那座水塔下时,那几条狗还在,一看到我们,立刻又吠叫起来。
本来,我是要把这个村子走遍的,可这些狗这么热情地一叫,就再没了心情。
我们决定打道回府。
到村东头取了车,顺着那条东西向的水泥路,一直开向村中心。路过一个巷口时,先前那几条狗又追了过来,我没搭理它们,它们追了一段路,不再继续追了。但那吠叫声却追了我们很远,总觉得有几个狗影在后视镜里晃。风还在刮,我看到它掀起了老窑顶上的白发,掀起了村庄的白发。
出了村,就放松下来了。
这条路与我进村时看到的截然不同。
路边是一条浮石沟,沟里滚的尽是褐色的浮石,沟坡上站着一些杏树,有十几棵,也许二十几棵。坡上沟下也生着那种白草,风一吹,草就伏到了地上,风过去了,草又站了起来。春日里,我曾经以这些杏树作前景,照过那些绵延的火山。那时,杏花开得正旺,也就过了一个月吧,枝头就结满了拇指肚大的杏儿了。那时,还看不到这种白草,或者它们才刚刚钻出地面,还没有形成声势呢。
我们不由得下了车,站在树下,看着那些绿杏拥挤在枝头。这些杏树长得很安稳,好像从来没有人来过这条沟,也从没有人发现过这条沟。再过一段时间,杏儿成熟时,会不会有人来采摘?我摘了一颗,吃进嘴里觉得又酸又涩。突然,我听得沟底有人在日骂牲畜,一看,是一群羊和一个挥鞭的汉子。汉子正赶着羊往北边的沟崖上爬,我接一个电话的功夫,他已把羊赶到坡上去了。可能是发现有人过来了,他不再骂羊了。我和他隔着沟说开了话。
老人家,放羊呢?
嗯。
给谁放呢?
给我自家放啊。
您放了这么多啊。
這还多?我还觉得不多呢。
多少是个多?
至少百十来只,能给孩娃们换个媳妇吧。
哦,老人家,几个孩娃?还有没成家的?
三个,老大老二都成过了,老三没成过,还在外边做工呢。
哦,沟里的杏树谁的?
谁的都不是,野杏树啊。
好像没人来摘杏啊。
人都没了,村子都空了,谁还来猴害啊。
我忽然不知说什么了,看着他赶着羊走远,消失在了山那头。风又刮过来了,掀起了浮石沟的白发。风把这浮石沟也刮老了。
[作者简介]王保忠(1966— ) 男,山西省大同县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家》执行主编。在《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山花》等刊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诗歌300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新华文摘》转载,部分小说被译介到国外;曾获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全国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奖、剑南文艺奖。
——《青瓷》作者的人生哲学
—— 《青瓷》作者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