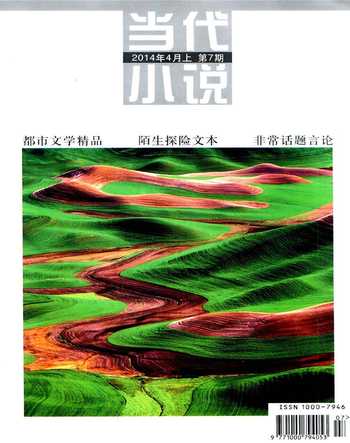暮春时节
汪泳
暮春时节,一个细雨微濛的早上,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标准的普通话让我感觉是在深夜里听调频立体声电台女主持人的节目,遥远而亲切。
她叫珂珂,上初中时是我的同班同学。她在我们班里是最标致的女生。那时,我不敢主动接触她,只感到她的冷艳有种逼人的气势,只把她当作女神在心中暗暗供奉着。
初中毕业后,因为爸爸调动工作,我们全家迁到北京,我从此再没有见过她。但她的名字我仍然记忆深刻。
当我接到她的电话,她报出名字时,我不由得怦然心动。她说:“我是珂珂,有印象吗?”
我定了定神说:“珂珂,你一直镌刻在我心中。”
她笑起来:“谢谢你还记住我。我这次进京主要是为了见你。”
我说:“你还能想到我,我好感动!分别十几年了,这会儿要见我?”
她有些伤感地说:“顺便找你谈点业务。老同学了。再不见面,一晃都老了。可以请你共进晚餐吗?”
我说:“珂珂,你设的不是鸿门宴吧?”
珂珂笑吟吟地说:“那么我可以摔杯为号喽。”
我说:“好吧。我情愿单刀赴会。”
我精心挑选了一款意大利产的进口羊绒衫夹克穿在身上,看了一下表,然后带着一副忐忑的心情走出家门。虽说已到暮春,斜风细雨依然将空气割刮得极其清凛,丝丝凉意不停地在刚刚泛绿的枝头抽动着。我把头深藏在立起的夹克领子里,用鼻梁托住一副宽边水晶眼镜,样子跟某些枪战片里的猛男颇为相似,但我隐藏在墨镜片后面的眼睛里,却分明透出几分掩饰不住的倦态。这个季节里我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想珂珂与我分别十几年了,这会儿突然要见我,我的脑海里油然生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
路上太堵,我没有开车,而是搭了辆出租。坐在车里回味刚才电话里珂珂的声音。她的声音很清脆,也很柔媚,是媚而不是嗲。我在心里玩味着。嗲多半是出于一种职业需要,或是为一种功利目的而故意做出来的,比方说餐厅酒吧的销酒小姐,再比方说那些纷纷遵命前来谈生意的凌厉的公关小姐,往往是用撒娇做嗲先攻下你的裤腰,然后再攻下你的钱包。那一套老鼠逗猫,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已经玩腻了。
而柔媚却大不一样。媚多半是由于女性的天性使然,给人以悦耳而不失风范。在这个无聊的阴晦的雨天里,电话里珂珂清脆且柔媚的声音激起了我些许兴致。具有这种纯美音色的女人大概也应该是柔情似水、风情万种吧?我想起了过去的珂珂,几许不安分的想法慢慢地漂浮了上来,却很快又隐没了下去。
我在一家颇具规模的音像制作公司做发行工作,几年来接触到的女孩子很多。我始终不敢肯定,那些争相以身相许,或者稍微给一点暗示就能牵引着上床,并且趁我耳聋眼瞎就要进入快感极致状态却趁火打劫谈生意条件的女人还算不算女人,同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这般视上床如入厕的人心中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爱情萌生。金钱早已坏掉了我对女人的兴趣,连同对美的鉴赏也一道给毁掉了。没有谁能够拯救得了我,也没有一颗心灵能够向我逼近,我常常为自己的心灵得不到满足而感到悲哀,而这悲哀,很快又被新一轮的肉体快感冲淡了。
我不知道这次来京洽谈业务的珂珂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女人。有一点让我感到有趣的是,珂珂将我和她会面的地点设计得别出心裁,会面的地点不是在宾馆大堂或饭店里,而是在英皇咖吧一间叫作“维也纳”的雅间。在雅间里我能和她做些什么?我暗暗地笑了,有意不再往深处去想,以便让这个女人的小聪明小算计有点得逞的机会。
我当然也猜想不到珂珂在放下电话,准备迎接我到来之前,先将干湿粉饼和双色唇膏等器物小心翼翼地放进蛇皮手袋里,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开始勾勒整个事件发展的每一处细节,作为男主角的我便被放置在故事高潮中最起伏跌宕的位置上。而我此时正在来的路上百无聊赖地发着冥想。
离约定的时间还早,我在“英皇”零点大厅里等待珂珂。我喜欢“英皇”咖吧。临窗的咖啡座,通透的落地玻璃使你仿佛漂浮在空中,使你生出转瞬即逝的那么一种虚假的优雅感。你似乎视野开阔,可以扬起下巴看远处夕阳照耀下的玻璃幕墙和花岗岩组合超现实主义般的建筑,也可以压着眼皮看窗外那些穿行的人流在脚下静静地流淌。我的同学珂珂也会出现在这样的人流里。
珂珂进来了,面带微笑径直朝我走来。她依然漂亮得令人炫目,和少女时期相比,她也有些变化,变得有一种成熟女人让人百看不厌的美丽,既没有鹤立鸡群的冷艳,也没有让人费力伤神的娇纵,她只是怡然、婉约、韵味无穷。她身穿一件印满鹅黄色碎花的薄呢裙招招摇摇摆动着的时候,我的眼里就印满了一朵朵鹅黄色的诱惑,就有水一样很细泽的东西充溢在眼底深处,想要去罩住那些个摇摆的花朵。我百无聊赖慵倦的心绪便化解了许多麻木的末梢神经,也仿佛有了酥痒痒的蚁走感觉。
珂珂见到我,似乎微微愣怔了一下,她大概也没有想到,在我所在的那个号称“京城痞腕”集团公司中,除了那些直勾勾盯着女人使些坏心思的胡同串子外,我还会保持着英俊儒雅的方正造型。刹那间的感觉失准后,珂珂旋即便调整好策略,吟吟笑着,矜持而又优雅地定格以待。
我说:“珂珂,你没变,但更具杀伤力了。”
她莞尔一笑说:“老同学,你也没变啊,还有一股书卷气。”她伸出手来礼节性地和我钩了钩,便做了个请的手势,我们一起朝“维也纳”雅间走去。
品着咖啡,珂珂几句不多的话语,便把我这几年的生活搞清楚了。我虽然嘴上说自己的经历不值一提,但在得知珂珂是大学毕业后才辞职下海的,便十分乐意把自己也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还有读研经历和盘托出。通常我从不在人前炫耀自己的文化水平,怕跟圈里的哥儿们爷儿们造成隔阂,被人骂成是显摆,也怕公关小姐们抓住我的文人弱点轻易将我攻破。但是对于珂珂我却乐意告知,一则是见到珂珂便回忆起了往事,感慨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珂珂让我想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真我和全部;二则是我确实欣赏这位昔日的“女神”,包括她的气质、笑容、谈吐、举止,以及她的一切。我想,过去我把她当成天上的星,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她就在我面前,我甚至想像出我进入她的世界之后的琴瑟和谐。
珂珂很快把谈话转入正题。她由衷地说:“老板派我来时我不太愿意接这活儿,对北京的侃爷们心怀惧意。能见到你是我的福分。”
我说:“你是我的老同学,我会全力帮助你的。”说这话时,心里捉摸,我无法判明分别多年的珂珂是个有多大底蕴的女人,但我知道她跟别的前来洽谈生意的女人的目的是一致的,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我又很希望她跟其他女人能够有所区别。
珂珂甜甜地说:“老同学,你能帮我,谢谢你。”她让服务员撤去咖啡,上了一瓶法国产“蓝菲”红酒。然后问我:“想吃点什么菜?”我说:“随便点,吃什么我都顺口。”
她笑了一下,开始看菜谱。在一片犹豫不定的心情里,我仔细打量着这位昔日的女同学,看她熟练地点着菜,又看她为我要上一盒“大中华”,从烟盒底部撕开,熟练地弹出一棵,嗅了嗅烟丝,检查着标牌的真伪,完全一副老到的男子气派。
这种男子似的潇洒与她那娇艳的女性身份产生了巨大反差。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很默契地充当着观众,觉得她的一举一动很有情趣,不时递予激赏的眼神,鼓励她把演出一直进行下去。
珂珂的手指优雅地托着酒杯,目光盈盈地盯着我问:“老同学,你还满意吗?”
我坏笑着说:“你指什么?是这桌酒菜,还是指人?”
珂珂定定地注视着我,眼睛晶莹闪烁,幽幽地说:“两者都有。”
我说:“如果指菜,你没必要这么花费,光这瓶‘蓝菲就值上千元。我们之间随便吃点就行,又不是外人。如果指人,我怕是摔杯为号,你要在生意上直奔主题了?”
珂珂脸色陡然一沉,轻声说:“老同学,没想到你原来也是这样煞风景。我还以为我们之间有更多的话题可谈呢。”
我的兴趣被调动起来了,紧盯着她问:“哦,这么说我让你失望了?”
她叹了口气说:“不,只是有点儿伤感。我一直希望有那么一个时刻,能忘掉生意,忘掉工作,一心一意沉浸在某种氛围里。难道你不希望如此吗?”
我说:“珂珂,对不起,是我把这种氛围破坏了。”
珂珂摇了摇头说:“没什么。毕竟我们在商海里呆得太久了,总脱不掉职业习气。”
我心里疑惑起来,珂珂找我不就是谈生意吗?难道还有其他目的?
珂珂的目光又定定地射了过来,我有些心慌,不敢去接她的眼神。窗外正闲散地飘着似有似无的小雨,浇得人心情也是飘飘忽忽的,有些不着边际。我极力将一颗戒心定紧。珂珂的这种谈话方式我还是头一次领受,应答起来显得有些吃力。这本来是我过去娴熟使用的一套话语,是我在客厅书斋朋友聚会场合耳熟能详的,如今已经变得相当陌生。珂珂的话将我的记忆唤起了,竟让我有了恍然如梦之感。
珂珂说:“老同学,我们活着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我瞅着她不语。此时,她妩媚的双颊变得飘忽迷离了,喃喃地说:“人活着似乎总要为点什么,从云云纲常到庸常的鸡零狗碎。”我笑着说:“看你说话的语气,好像苦大仇深似的,谈谈自己好吗?”她抿嘴一笑说:“喜欢听我说吗?”我说:“当然喜欢。我和你交谈就是接受再教育嘛。”她轻声一笑说:“那我讲给你听,我的经历足可以写部长篇小说。你可是要付听课费呀。”她沉思了一会儿,开始叙说起自己的故事。她辞职。她下海。她不得已离婚。她一次次碰壁。她偶尔得胜的战绩。她屡次三番的跳槽。故事陈旧得跟任何一个潇洒走南方的女子经历毫无二致。但当这些话面对从一个沾着酒精的红唇中轻轻吐出来,并且又是那么真诚、坦率、毫无保留,我的思路还是不自觉地被牵引过去,艰辛和感慨无形中成了我们共同的际遇,我的胸膛也在激烈地起伏着,我们之间谈话的气氛一时变得既浓且纯,两颗心也似乎在淡黄色液体的浇灌中迸溅起一朵朵火花。珂珂的脸蛋正在泛起好看的嫣红,她的两眼也闪烁着让人心醉的光彩。
我试探着说:“我想问你个问题,可以吗?”
她说:“问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为什么离婚哪?”
在出现短暂的沉默之后,她叹了口气,说:“我的前夫是一个医生,人很斯文。我们有了个女儿,活泼可爱,长得伶俐,该上小学二年级了。本来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他背叛了我。”
我说:“夫妻之间能走到一起很不容易。你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吗?”
她看了我一眼,哑声说:“他不太有记性,我对他失去了信任。”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感到她的话像戳到了我的软肋,有些伤感。她感慨地说:“老同学,看你活得多滋润,不费劲考上了重点大学,读了研究生,工作几年就当上了部门经理,在商海里还挣到了钱,有一个幸福的家……”我赶紧打断了她的话,低沉地说:“我也离婚了,现在仍然独身。”
她笑眯眯地意味深长地问:“想必老同学也是咸猪手伸到篱笆外了吧?”
我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很复杂,说不清楚。”
听了这话,珂珂默声不语,一手支腮,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过了片刻,她才沉沉地说:“好了,都过去了,不谈这些了吧。”
在“维也纳”雅间,不知不觉三四个钟头已经过去,但我对时间的流逝毫无所感。到目前为止,珂珂对生意的事闭口不谈,仿佛忘掉了此行的目的。她那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沉醉状态,将我深深导引进一种知音难觅的欣喜里。我内心深处那层冷漠的东西正一点一点摧散开来,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这样毫无功利的清谈了,尤其是跟一个我早已向往的漂亮女人做这样你来我往的清谈。温情正在我的血管里慢慢散开。
珂珂说:“我现在所在的这家音像公司是我跳得第五个单位。老板这次派我进京跟你谈这笔影带生意是对我的一次试用,还不知能不能保住这个饭碗。”说这话时,她两眼盯住手中的杯子,一副茫然无助的神态,一反刚才的干练潇洒。
生意场上的戒心,我差不多解除光了,换上了对这个昔日的女同学曾经饱经坎坷柔弱无助的恻隐。
喝了蓝菲,头有些晕,当然我没醉,我是顺水顺风进入了珂珂安排的角色。珂珂喝得玉脸绯红,与她碰杯时从她眼睛里我读到了从别的女人眼里见过无数次的爱情诗行。
珂珂说:“老同学,你在这个行当里干的年岁多了,经验也相当丰富,请你一定多多关照我,帮我过了这一关。”
我点了点头,说:“我会尽力的。”
珂珂买完单,起身时仿佛不胜酒力似的摇晃了一下身体,我赶忙上去扶她,她便趁势靠在我身上,像一只柔顺驯服的小猫。我轻轻拥抱了下她,觉得心里有股温热慢慢通过我的神经末梢向全身扩散。
当我和珂珂从咖吧出来时,天已经暗了。门前广场湿润的水泥地面折射着桔红色的灯光。我和珂珂像初恋情人一般在深夜的广场小路上散步,她纤细的右臂挽住我,我也顺势拦住她的细腰,慢慢向她的住所方向走去。我最喜欢在小雨中散步了。珂珂伸出—只手去当空触摸若无若有的雨水。我举着伞,她偎依着我。这种情景能让我想起一切美好的日子。
是的,一切都很美好。我感受到紧靠在我身旁这个炫目女人的体温,嗅着她瀑布般长发间散发的淡淡的清香,揽她的一只手在夜色中感触到她腰间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肌肤,使我有些心猿意马。中学时代一幕幕蒙太奇般的往事,接到她的那个电话,与这个迷人的女人久别重逢,酒杯中那透明绵软的液体,还有那些如泣如诉的话题……一切尘间烦恼都逃出了现实,一切都美好得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的思维正屡屡顺着珂珂的牵引不断延伸下去,随着她的忧伤而忧伤,随着她的欢喜而欢喜。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打动了我的心,让我和她之间如此默契呢?我的心深深沉入一种诗意的幻觉里。
这是对她由往时的暗恋升华为爱情吗?我已经把这种久违的情绪假定为爱情了。爱情的来临,有时竟像猫一样悄无声息。爱情就像今夜的广场,广场上的纪念碑,纪念碑上的浮雕一样濡湿而美妙。珂珂的发丝偶尔会随风轻拂过我的脸庞,我忍不住侧过脸将她细细打量着,不由得心旌摇荡:是谁把这个漂亮女人给我送来的呢?是缘分吗?
广场一角正插放着不知是谁的歌,男歌手唱得很投入,我很快沉浸在伴着萨克斯音色中的歌词里去了。
全是你的影子,留恋在风中
不能褪去,诉说你衷情
诉说往事的回忆
在这漫长岁月里
心中拥有了你……
我想音乐有时候真是个好东西,身处其中让你体会到生活中美妙的一面,让你疲惫的心灵得到真实的感动。
怀着对某种激情的神往,我们穿过广场中林间小道,又绕过一簇簇开着花的灌木丛,一直走进珂珂下榻的贵宾楼里。进得门去,珂珂刚一把壁灯扭亮,我便不相信珂珂有经济能力住这么阔绰的房间。珂珂像是看出我的疑惑,轻笑着说这是一个朋友替她租的,朋友曾欠过她一份人情。珂珂打开冰箱,取出一罐台湾产椰子汁递到我手里,道了声“抱歉”,转身进了洗手间。我仍旧不能够释然,搞不清珂珂究竟有多大的神通和能量,会有人为她租下如此高档的睡房。刚刚窥得一点真面目的女人转眼间又变得神秘了。
在沙发上坐定以后,我的心绪慢慢缓解了,开始细细品味房间里的舒适和温暖。温柔敦厚的窗帘把一切可视物都拦在了窗外,剩下的,满眼就是那张横陈的床,以及暧昧不明的浅红色灯光。那张宽大的席梦思是那样肆无忌惮地裸着,轻软地释放着无限的魔力,我遐想这应该是等同于珂珂约我来房间与她做更深层次接触的无形含义吧?我的肉体一时间产生了几丝迷乱,一些联想的肢体动作开始在我脑海里舞动,在这种深入的迷乱之下我有了卑鄙的反应。
“是要茶还是要咖啡?”
珂珂笑吟吟地站在我面前,我一惊,忙从沙发上提了提身子,正襟危坐呆好,床和灯也迅即和幻觉分离,各自归位恢复成普通家具的模样。珂珂像变魔术一样,换了一袭无袖的刺绣玉兰花旗袍出来,瀑布似的长发已挽成一个髻,旗袍的袖口和开叉处将她光洁的手臂和秀美的双腿生动完美地显示着。我看呆了,情不自禁以激赏的目光定定瞧着,以为这爱情差不多已是袒露无疑了。
我喃喃地说:“珂珂,你可是真美。”
“谢谢。”珂珂轻轻地应着,款款地走过来,在我身边,隔着茶几坐下,坐在我伸手可触而又遥不可及的地方。
我的心头有一股巨大的热望被强烈激发起来,很想急迫地采取行动,尽快逼近珂珂的身体。但我还是努力将自己遏制住,不使自己的行为显得粗鄙。以往对待其他女人的种种滥情游戏技巧和手段,对于眼前这个让我心仪的女人全不适用,我想用爱情来给我和珂珂这种关系定义,用爱情的名义赢得我新的婚姻。我只是等待,等待着一种高尚的类似水到渠成的冲击。
“老同学……”珂珂侧过脸来,羞于开口似的嗫嚅着。我的心此时怦怦跳动着,以为时候到了,便将鼓励的眼神传递过去,分明是有些急切地渴望下文。
她吞吞吐吐地说:“老同学,你愿不愿意……”
“什么?说吧,我听着哪。”
“你愿不愿意帮我……”
“哦?”
“你愿不愿意帮我做成这笔影带生意,把带子的价格再压低些?”
我一时无语,我还没有从刚才的思绪中转过神来,只是听凭她一个人继续说下去。
“我们这个公司组建时间不长,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全靠你这些带子打开销路,你订单上的价码太高了,至少得给我压低500万,我们才能买得起。”
我一愣,一丝警觉袭上心头身躯也随即有些僵硬。我本能地用职业口气说:“珂珂,你这是从七位数上和我杀价,你不如说让我把带子拱手相让得了,我们全体员工两年多的辛苦也就此泡汤了。”
“500万不行,那么老同学,你觉得我值多少?”珂珂的眉梢轻轻一挑,似挑逗,又似挑战。
我的心里怦怦紧跳几下,循声问道:“假如我压低价位把带子卖给你,我能得到什么?”
珂珂不急不愠,吟吟笑着,流光溢彩的眼睛紧逼着我问:“老同学,你想得到什么?”
我瞅着她的目光紧紧盯了一会儿,我和她都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她那丰美的胸脯在旗袍下笑得微微轻颤,落在我眼里,这轻颤已经变成了挑战的鼓点,全没有挑逗的蜜意了。
电话铃响起来,珂珂起身去接。我便对这个咫尺天涯的洁白色侧影,发着紧张的思索。电话里好像是有什么人请她去吃夜宵,她在婉言谢绝:“我现在正陪着一个朋友,脱不开身,就不去了。”她回身刚刚坐下,又一个电话进来了,有人约她去KTV,她又一次谢绝了:“我今晚陪一个重要的朋友,脱不开身,不能去了。”珂珂特别在“重要的”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重新坐定以后,珂珂用期盼的眼神问我:“老同学,你能给我一个结果吗?”
我意味深长地说:“我也希望有个结果。何况你为我辞了这么多约会,把我当成重要朋友看,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也不能白担了朋友的名分,就帮你这回忙。这样吧,我给你压价250万,这是最后的价码,不能再低了。”
珂珂毫不迟疑地接口说:“哟,看你这小气样。300万,就这个数成交。”
我定定地瞅着珂珂,她脸上的线条瞬间已变得坚定和刚毅,并没有柔媚出我预期的欣喜和感激。我有些失望,脑子里呈现出一片空白。稍顷,才回过神来,挥了一下手说:“好吧,就300万。明天上午你去我那儿,我签份正式合同给你。好了,告辞了。谢谢你的宴请。”说完,我站起身,看也不看珂珂此时的反应,走出门去。我也搞不清自己的动作和言语是怎样变成如此衔接的,只是觉得此时的我必须这样做,非这样做不可,因为我已经不能够做别的了。
这一夜我彻底失眠了,带着失意和惆怅辗转反侧,对自己和这个世界都变得没有把握了,仿佛又陷入孤独和冷漠里兀自漂浮着。说实在的,珂珂是我离婚后遇到的最可心的女人,美丽,知性,干练,让人着迷,如果和她在一起,我的生活肯定是另一副样子。这真是一首诗意盎然的美妙情歌啊,可我是那么难以洞察她的内心,难道只是自己低智商时的自作多情吗?难道她也不过是一个善变的美女蛇用姿色将我利用和戏耍?她真是魔鬼与天使啊,两者之间有时连一张纸都不隔。我不敢再想下去了,我多么希望和珂珂的交往不是这些,我渴望和她有一种深长隽水的承诺。
等到珂珂如约来我家取合同的时候,我已经在客厅和卧室里把一切氛围营造好了。珂珂依旧神采奕奕,温婉可人。看得出这笔交易的成功让她昨晚有了一个甜甜的睡眠,我的心不禁有些微微发痛。
进门以后,珂珂便四下环顾着,对居室富丽堂皇的装饰表示赞赏,又把脚步移向靠墙的一大排书柜前细细浏览着,那些脆硬的书页上曾经倾注过我过去年代里骚动的理想,如今都阒静无声的尘封了。
珂珂拿起桌上一帧三口人的全家福对我说:“这是你妻子吗?她可真漂亮。”
我淡淡地说:“从前是,现在她是别人的妻子。”
“哦,对不起。”珂珂“哦”了一声,复杂的表情转瞬又变得晴朗,“你儿子长得真可爱,十分像你。”
“是吗?他跟着他妈妈走了。”
我平静地说,转而把话题调转过来,“这是合同文本,你先看一下吧。”
珂珂接过合同书,坐在沙发上翻看着。我紧挨着她坐下,也坐进了长沙发里。没有了茶几之类讨厌的障碍物作阻隔,珂珂变得十分真切了,就在我身边存在着。我的鼻息正拂在她的头发上,发丝便微微波动起伏着。我能感到珂珂在我焦灼的目光压迫下,似乎有了几分窘迫,目光散乱地开始在纸上游移,手中的纸也仿佛有千钧重量似的托抓不稳,扑簌簌的竟有几分倾斜。我的肢体不由得火热起来,心也开始怦怦狂跳,这是许久不曾有过的动情的狂跳,因为我太想确认我和珂珂之间关系的实质了。
“珂珂,”我低唤着,“你让我动心。从中学时代你就让我动心,只是那时我对你是种胆怯的暗恋。”
珂珂头也不抬,两眼仍盯着手中的合同书,轻声说:“是吗?”
“是的,你会让任何一个男人动心。谁也抗拒不了你的魅力。”
她抬起头,优雅地坐着,大人看小孩似的露出开心的笑容,轻声说:“你是我接触过的最有个性的男人,你身上具备了许多貌似矛盾的特点,比如说你有时候冷僻成熟,有时却像小孩般可爱……使你有这样的魅力……”
“噢,你这样认为我?”我已经把这当成某种允诺的信号,脸颊通红地燃烧着,缓缓地接近珂珂那温热的双唇,不再在意她那种欲擒故纵成竹在胸的表情……
写字台上的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了。我的情绪被迫中断,无奈地走过去,接起手机。是公司里的恼人事,我简单地敷衍几句,马上把手机挂断,同时用身体挡住珂珂的视线,顺手关闭了手机。
回转身来,见珂珂已端坐在沙发里,身体显露出拒人千里的僵硬姿势,脸上毫无表情。我笑了笑,顺手旋开了发烧组合音响,舒缓的音乐顿时像光一样洒满全屋,落在我们的脸上、身上,也笼住了屋子的四壁和墙角。洒在珂珂头发上的光是那样柔曼,仿佛要把她的每根发丝都揉起来,揉成暖暖的一团。珂珂的肢体在音乐的感染中舒缓了,棱角不再那么明显。
我靠近珂珂,梦呓般地问:“珂珂,还满意吗?”
她缓缓地侧过脸来,脸上露出迷茫的神色,不解地问:“什么?”
“一切。”
她恳切地说:“是的,对一切都相当满意。这都亏了你,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盯住珂珂姣好的面容,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不,你知道。”
珂珂的脸上掠过一丝迷乱,随即镇定下来,像想起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哦,对了。”她旋即打开身边的手提袋,从里面抽出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是张信用卡,她递到我面前说:“这是15万元钱,作为对你的一点酬谢,请收下吧,你千万别嫌弃。”
我的面部肌肉登时发僵,进而急遽扭曲着,像是有些不懂似的诘问:“你真的认为我要的就是这个吗?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珂珂被我的表情震慑住了,睁大眼睛疑惑地问:“这有什么不对吗?那么你还想要什么呢?”
我忽然觉得有些无措,有些语噎,有些空落。发烧组合音响一长串音符轻捷地在我的大脑皮层里划着,苍白地滑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全是空白,空白得是那样滞胀,阻塞,让我的心已经难以承受了。我有些伤感地说:“钱就是情,情就是钱。这世界很现实……”
她茫然地问:“你说什么?我不懂。”
我不语。
“老同学,”沉默了一会儿,珂珂轻唤着我,将我从怔忡之中拖回到现实中来,“如果你没有什么异议的话,请你在合同上签字吧。”
“哦,好吧。”我木木地应着,手里举着笔,却半天都落不下去。一切为什么竟是这样残酷,这样倏忽即逝?等我的笔一落,我和珂珂的联系就算彻底完结了。其实从头到尾,维系我和这个女人的,也不过就是这一张纸。婚姻、爱情、生命,为什么轻薄如纸?
珂珂轻声问:“老同学,你还犹豫什么呢?”
“你不再仔细读读了?”
她嫣然一笑,透出无比的魅力:“老同学,难道我还不相信你吗?”我心里一阵揪紧,定定地瞅了珂珂几眼,才在合同上签了名。
我强打精神问:“什么时候走?我为你饯行,走时我开车送你到机场。”
她甜甜地说:“我下午回。中午有个应酬。有朋友送机。不麻烦你了,谢谢!”
“好了,你可以回去交差了。”我疲惫地一扬手,“请吧。”
我盯着她离去时浑圆饱满的臀部,心里一丝酸楚涌上心头……
我浑然不动地坐在沙发里,让暮色一点一点把我吞噬进去,空寂的屋子被黑暗笼罩着,感到一种孤寂与怅然。手机一关掉我就可以暂时与这个世界隔绝,我心里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愿意去想,就这样静静地坐着。虽然没有报时钟响,但我仍可以感受到珂珂乘坐的那趟班机已经驶过了我的头顶,把这个美丽的女人送到南国一个新兴城市去。时光一刻一刻过去,凭时辰,我估计珂珂已经下了飞机,正兴冲冲地奔向她的老板处报捷。我在黑暗中睁开眼来,重新打开手机,然后拨往了珂珂所在的地方。
“珂珂,你好!”
“老同学,请问还有什么事?”话语里她的声音依旧很清脆,只是再也听不出柔媚了,语调有点疲倦。我此时亦是心止如水。
我平静地说:“珂珂,祝贺你生意取得成功。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复制合同文本时,我忘了把‘发行权字样打上了。就是说,你购买的只是影带的复制权,却没有发行权。你有权拷贝出一卷卷的胶片或磁带,却不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发行。我重新准备了一份比较完备的合同,不知你是否愿意一切从头再来?”
听筒里一时寂静无声。我似乎看到珂珂那欲哭无泪的眼神。我暗暗笑了,然而笑得很苦。
游戏过后,还会有什么能在我们心头永驻?
我听到听筒那边一片忙音,我知道珂珂把电话挂断了。我怔了一会儿神,筋疲力尽地又坐回到沙发里,随着暗暗降临的夜色一道,又坠入到无边的空虚里去了。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