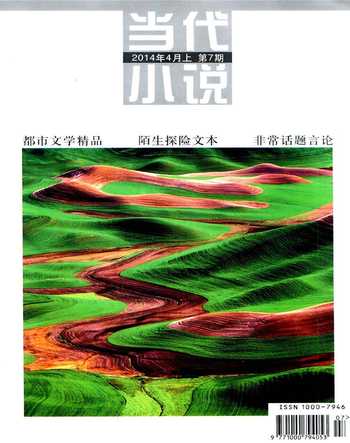老余
郝炜
此地人对外地人的称谓很有意思。比如把山西人称作“老西子”,说“某老西子”;管山东人叫“山东子”,说“某山东子”。这里面没啥褒贬,就是一种习惯叫法。比如本文所说的这个“余山东子”,就表明他不是本地人,是山东人,姓余,这个称谓有特征,它提供了一个人的基本信息。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是称他为“老余”吧,叫老余也还显得亲切点。
老余既然被称为“余山东子”,那自是打山东过到咱东北地界的,这没的说,我要分辩的是,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老余还是小余。这些前提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现在没有谁会给你讲这些老故事啦,不搞清楚你会听着犯糊涂,好啦,我们开始吧。
说那小余,当初本来是想到东北来找哥哥的。哥哥几年前就去东北了,那时候的东北在山东人眼里可是个好地方——要不咋都来闯关东呢,《闯关东》的电视剧你看了吧?就是写的那时候。
那时候,咱东北人就能忽悠,什么“棒打狍子(也有说獐子的,反正都差不多)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什么“春天插一棍,秋天吃一顿”,听听,多让人眼馋啊,想想都觉得神奇得要命。还有棒槌(人参),还有金矿,还有高大茂密的森林,还有油黑油黑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还有后来歌中唱到的“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什么的,总之是好得不得了。
小余的哥哥走的时候表示,他既不是去弄棒槌,也不是去挖金矿,就是想去那里找个媳妇。你会说,找媳妇在哪里不能找?可是小余家在当地就是穷得没人给介绍对象。哥哥来到东北,听说很快就找到媳妇了。哥哥媳妇是找到了,可人也从此就不回来了。“老话说的好,这娃子,真是‘有了媳妇忘了娘,老话说得一点没错。”“这娃子,就是得了狗头金,也应该回来看看呐,嘁!”四方邻居都这么议论说,可小余不这么想,小余认为肯定是东北那个地方好,要不哥哥怎么会一去就不回来了?哥哥来过几封信,信上写得含含糊糊,没说怎么好,也没说怎么不好,有点闪烁其词的。信上也邀请大家去东北看看,说路费什么的都由他掏。
“来看看就知道了。”哥哥信中写道。
父母是坚决不去,山高水远的,他们担心把自己的老命丢在路上。何况,他们的年龄已经不适宜出远门,已经对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新鲜感了。尽管此前“闯关东”的故事到处流传,到了他们这辈儿,事情已成强弩之末,解放了,山东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父母虽然自己没兴趣,却鼓励小余过去看看。他们希望儿子有出息,“有出息”当然要去远方,没听说谁守家在地有大“出息”的。
备受鼓舞的小余立刻踏上了征程,心里怀着一百个梦想。小余没出过远门,他第一次坐上轮船,肮脏腥臭的四等舱(统舱)并不使他厌烦,他站在风浪飘摇的甲板上,看大海波涛汹涌,看海鸥展翅飞翔,看远处的灯塔的灯光一闪一闪地亮着,大海在夜间像一锅沸水——黑色的永无边际的沸水。
后来,又是汽车,又是火车,小余经历了他人生许多的第一次。车过山海关,就等于是到了关外。路两边的景色与关内大不一样,高山、森林,森林旁边的野花,不知名的河流,或者,一望无际的庄稼,玉米、高粱,在风中摇摆,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这些,都让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蓝天白云之下,太空旷了,太辽远了,几十里地看不到一户人家。
一路上,小余心情愉快,不愉快的只有一件事儿:小余把哥哥的地址给弄丢了。那封信的信皮本来是被娘把它和钱一起缝在内衣里的,可不知怎么掏来掏去,就把那个信皮给掏丢了。小余捶胸顿足,仰天长叹,这件事情足以致命,地址丢了,你扑奔谁去?好在小余年轻,记性好,后来他冷静地回忆了一下,隐约记得,哥哥信上提到的那个古怪的地名叫吉林。哥哥去的那个地方离吉林不远,他想,到了吉林就不愁找不到哥哥了。
小余想错了,出了吉林火车站他才知道,吉林是一座很大的城市,小余根本不知道再去哪里找哥哥。在小余毫无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好心人,那个人也是山东人(小余感觉来到外面,山东人和山东人亲着哩!),听了小余的述说颇为同情,就说,你先别找你哥哥了,反正已经来到这里,先找个工作吧。听说造纸厂正招人哩,你不妨去试试?小余一想,也是,既然找不到哥哥,先找个工作也行啊。于是,就同意去试试。
小余有点文化,写一手好字,报上名就进厂当了工人。那时候我们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哪里都需要人,进工厂比较容易。好像有文化的又比较少,小余的好字很快被发现了,小余就被抽去写黑板报,小余能写会画的才能得到了展示。厂长经常看见这个个子矮小的小伙子站在凳子上画黑板报,厂长就注意了,厂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小余不知道他面对的是厂长,只是觉得这个人像干部,就蹭蹭鼻子,垮垮叽叽地说:俺姓余。厂长饶有兴趣地问:你是山东人啊?小余就说,是哩,俺是登州府的。厂长说,山东人好啊,山东人能干。厂长拍拍小余肩就走了。小余有些愣眉愣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说山东人好,小余的感觉是山东人也有不好的。
不久,小余就被抽到厂部去了,做了团委书记。那
年头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用送礼,也不用溜须,就是厂长一句话。当然,这也不是厂长一个人决定的,开厂务会研究团委书记的角色时,厂长提到了那个姓余的小山东,他特意强调是站在凳子上画画的那个。大家就都有印象,都说那小伙子不错,这件事情就通过了。要不说有点本事和没本事不一样呢,小余从此就是造纸厂的干部了,每天在大楼里进进出出。小余还得帮着出版报,本来这个活是厂宣教科的,自打小余当了团委书记后,就顺理成章地拿到了团委,小余本来也想找个人替他,可是偌大个造纸厂却找不到这样的人才。有一个人画画还行,一写字就完了,蟑螂爬似的。小余就让他画画,自己写字,也还是要站到板凳上。
要说人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小余有了工作之后,很快就打听到了哥哥的下落,真的离得不远,就在城市附近的舒兰县。小余头一次去看哥哥,就很认真,买了四盒礼,给嫂子买了一块花布,给侄子侄女买了一包糖,穿得精精神神的,提着果盒子就去看哥哥。嫂子看见四盒礼,看见花布,就夸小余懂礼节,会来事儿,又听说小余在厂里当干部,就说啥也要给小余介绍对象。提了一个人,是嫂子家的一个远亲,哥哥也不反对,显然哥哥也是见过的,满意的。说办就办,嫂子就领着小余相看去了。小余见了姑娘,挺满意,大高个,比小余还高半头,浓眉大眼的,俩大辫,别看是农村人,小余看着感觉像画上的人似的。小余就眼角眉梢都带笑,嫂子心里就有谱了,问问姑娘,姑娘从辈分上管嫂子叫姨,姑娘就咬着大辫子说,姨,别问我,问我妈吧。当姨的这就啥都明白了,她妈能定啥啊,那就是同意的意思。又走动了几次,哥哥嫂子就帮着把办喜事的日子定下来了。
很快就结婚了,很快就有了孩子,很快小余就变成了老余。变成老余的时候,老余已不是干部了,成了车间的一个焊工。有人说老余娶的老婆虽然漂亮,但这老婆却把老余的运气拐带坏了。倒也是,自从老余结婚以后,他的政治生活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最大的事情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久,老余就被查出家里有历史问题,老余的父母居然是破落地主。小余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家居然有这样的背景,他这才想明白自己家为什么会一下子由富变穷?哥哥为什么当初执意出走?原来是这个原因。大家也哗然,哦,怪不得老余能写一笔好字,是念私塾念出来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念得起书啊。厂长这时候也帮不上老余的忙了,运动正在深入,他让老余到车间去,他说,还是搞点技术吧。老余点了点头,自己选择了焊工。不久厂长自己也成了批斗对象,老余看着挂着牌子的厂长站在厂里的汽车上和厂门前被游斗,就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永远地结束了。
老余乐得自己变成这样的老余,老余就想,本来一切都是拣来的,丢就丢吧,但工作掉了他不怕,党票丢了他有些心疼,给他开除出党他觉得不舒服,老余还是很想在党里的。不过那时,老余的所有想法都没用了,一心一意当他的焊工吧。老余毕竟有点文化,学啥像啥,很快在焊工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了。这时候媳妇一股脑地给老余生了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一顺水似的,都差不了几岁。老余的心思就都在媳妇和孩子身上了。自从自己不是干部之后,老余就觉得对媳妇格外过意不去,这个当初画上的姑娘(老余一直这么看),现在已经被生活的变化给打磨得够呛,大辫子没有了,人也瘦了,连个子好像都跟着变堆碎(东北方言,意为“蜷缩”)了,老余就心疼得够呛。老余只要是自己能干的活就决不让媳妇干,老余学会了打毛衣、做棉裤,老余学会了贴大饼子、摊煎饼、包饺子,可以说家里外头老余都不让媳妇伸手,就是一句话,养着。老余觉得老婆已经够累的了,一气儿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功劳大大的。这么说吧,老余如果自己能生孩子,他恨不得自己生。媳妇总是惦记着乡下的父母,有什么好东西都惦记着乡下,这老余理解。老余就把家里的面攒着,定期换点挂面,然后给老丈母娘送去。
星期天,老余早早把孩子们叫起来,带着大家去看姥姥(姥爷已经去世)。大冬天的,天还没亮,外面黑黢黢的,孩子们赖赖唧唧不愿意起来,老余就挨着个地薅耳朵打屁股,给孩子们穿衣服。孩子起来了,媳妇还在睡,孩子们说,你怎么不打妈妈的屁股?老余说,你妈妈把你们生出来,有功,我怎么敢打她。老余就趴在媳妇耳朵边上小声问,你去不去?媳妇还没睡好,媳妇说困死了。老余就知道媳妇不想去了。老余就不管媳妇,老余用一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前边两个小的,后面两个大的,驮将起来,晃晃悠悠地奔哈达湾火车站去坐火车。老余把自行车寄放在车站,然后领着四个小家伙走出很远,绕进火车站去等火车,老余是从来不买票的。到了晚上,老余照例带着四个叽叽喳喳的小家伙回来,妈妈已经睡好了,有精神了,就问姥姥咋样,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汇报,老余就站在一边慈祥地笑。媳妇就有些不好意思,媳妇说,我给你们做饭去。老余连忙劝住,老余说,我们都不饿。他问孩子,你们饿不饿?孩子们齐声喊,不饿。睡到半夜,孩子们就翻身,把老余鼓捣醒了,老余拉开灯问,干嘛不睡?小丫头就说,我饿。那三个小脑瓜也伸了出来,也说饿。老余说,我还饿呢,就披上衣服下地做饭。媳妇也弄醒了,坐起来,有些披头散发,说你们就跟你爸一起糊弄我吧,不是都不饿么?小的们不说话了,老余在厨房嗞嗞啦啦不知鼓捣什么,香味飘进屋里,孩子们就更饿了。不一会儿,老余进来了,是用荤油煎的粘豆包,焦黄焦黄的,孩子们兴奋得直嚷。老余却是先端到媳妇面前说,你尝一个。媳妇有些不好意思,媳妇说,让孩子们先吃吧,我不饿。
老余说,我知道你不饿,这不是从你家带来的吗,你不吃,你妈能愿意么?媳妇就尝了一个,有些烫嘴,直吸气。孩子们在旁边看着就眼馋,涎水都流出来了。等到端给孩子,孩子已经等不及,就用手去拿,吃了一手一脸的油。四个孩子就像四头小猪,转眼就把一盘子豆包给吃没了,还舔着手。媳妇就说,你爸的呢?孩子们一愣,没想过爸爸,老余说,我在煎的时候就吃了。孩子们就嚷嚷,爸爸偷吃,爸爸偷吃。老余就作势要揍孩子们的意思,老余说,睡觉。孩子们就立即卧倒了。媳妇知道老余是撒谎,就嗔怪地瞪了老余一眼,老余就很知足。
老余对老婆好,对孩子也是出奇的好。所有孩子身上的毛衣(包括媳妇的)都是老余给织的,所有孩子的棉裤(包括媳妇的)都是老余给做的,老余还是显出了能工巧匠的特色,他从别人那里借来纸样试着剪裁,然后往里面一块一块地絮棉花,然后咔哒咔哒地蹬着缝纫机轧线,缝裤钩,锁裤眼,做的棉裤除了腰比别人肥之外,还真像那么回事。为什么裤腰要高一块,肥一块呢,山东老家做裤子就都是这么做的。因此,老余家的孩子冬天的装束就显得和别人稍有不同,裤腰长出一块来,还要挽上,鼓鼓囊囊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像鸭子似的。
老余还定期领着孩子们改善生活——去松江小饭店买浆子、果子吃。早晨四点多钟,老余就领着小小的队伍出发了,他们拿着盆,提着水壶,抱着暖瓶,雄赳赳气昂昂地去小饭店排队了。天还没大亮,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稀稀拉拉地几个,老余就指挥孩子们排在后面。饭店每天早晨发100个铁牌,每个人只能买四根果子,一碗浆子。孩子们能吃,越穷越能吃,老余家一次就得买二十根果子、十碗浆子(也只限买这么些),孩子们回来呼噜呼噜地吃,小猪一样,不一会儿,盆里的果子没了,壶里的豆浆光了。老余本来是给媳妇和自己留两根的,不知道被谁吃了。老余就自己用苞米面做点糊糊,里面放点菜叶子,也是喝得呼噜呼噜响,媳妇喝得就有些艰难。
老余想,这媳妇是富贵命呢。
老余就还想,我一定要让媳妇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老余想是想,日子还是越过越差,不以老余的意志为转移,给孩子姥姥家送挂面已经从一两个星期改为一个月送一次了;买果子、豆浆已经从原来的一个月一次,改为半年一次了。那时候大家都不怎么富裕,秋天买白菜,老余家得买好几千斤。老余家买菜不算多的,邻居还有好几家买上万斤的呢。老余自己吭哧吭哧挖菜窖,他指不上孩子,孩子还小,再说以他对孩子的溺爱劲儿,也不可能用孩子挖菜窖。老余干什么总是富于创造,他在自己家棚子里用砖和水泥砌了一个永久性的菜窖,在里面放上凳子、桌子,用角铁焊了一个坚固的梯子(他是个焊工,焊个结实的梯子还是很容易的)。夏天的时候,孩子们学习热了,老余就让孩子们到菜窖里去学习,孩子们就在小棚子里进进出出,邻居家的孩子就觉得神秘,过去一看,有些眼热,也想让家长给弄一个,拉着家长过来看看,家长一看就傻眼了,乖乖,这哪里是那么好弄的啊?
那时候正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到处都挖防空洞,动不动就拉警报,嗡儿嗡儿的,很恐怖,仿佛随时有不知来自哪里的敌机来轰炸,就都搞得人心惶惶。大街上到处都铺着苞米,说是国家粮库的,家里的粮食那么紧张,却很少有人去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国家备战备荒用的,是早晚有一天要用在老百姓身上的。老余砌那个菜窖的本意也是用来防空的,所以考虑得十分周全,里面有酸菜缸,有粮囤子(虽然最后因为潮湿,也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粮食需要放,堆了杂物,但老余的本意是要用的),就差再弄个厨房和灶台了。棚子里拉上了灯,地上铺着刨花(刨花也是厂里分的),四周用牛皮纸包上,再在上面又铺了很多层的牛皮纸,就成了又暄又软的床,夏天可以在里头睡觉。1973年,正赶上这里闹地震,政府和街道动员大家都住到外面,别人家愁得够呛,许多人就在路上搭起了床铺,老余家的孩子却乐坏了,他们在爸爸铺的床铺上又蹦又跳,把牛皮纸跳坏了好几张。他们高兴啊,他们第一次感到爸爸的伟大和先见之明。
老余呢,也感觉很对得起媳妇和孩子,就坐在边上吧嗒着烟,抿着嘴笑。老三就提醒他,不准在棚子里抽烟。老三是姑娘,老余最喜欢这个老三了,老三额头很大,眼睛也很大,学习又好,老三干什么都细心。老余就把烟掐灭,就在灯下看孩子们蹦,蹦坏好几块牛皮纸也不心疼。
老余家的孩子,不知怎么个顶个地学习好,这可能得益于老余的倒霉。如果是不倒霉,老余的孩子也会和别人一样在外面疯,在外面闹。老余家的孩子开始时也是和别的孩子在外面玩,玩着玩着就觉得不对劲了,他们动不动就被别人骂成狗崽子,骂老余是地主。孩子们就回家问妈妈,我爸怎么是地主呢?媳妇说,大人的事情,不要乱问。孩子们依然不明白,大人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问呢?更让他们不解的是,他们如果在外面被人家欺负,别人家的妈妈来了都是向着自己的孩子,而他们的妈妈过来却是不由分说,把他们领回家去,关上门,让他们站在地下反省,而妈妈自己在那里擦眼泪。这让孩子们很不舒服,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惹恼了妈妈,就有些害怕,就也跟着妈妈呜呜哭,开河了似的,哭成一片。老余回来了,看他们哭过的样子,就问怎么了?孩子们不说,媳妇也不说,好像他们忽然成了同盟,共同隐藏和保守着一个秘密。
打那以后,孩子们就不愿意出去玩了,女孩子不学
习的时候,在家里抓旮旯哈(一种兽骨做的玩具)。男孩子不学习的时候,在自己屋地下弹溜溜,他们变得都很懂事,都不愿意出去。即使有孩子把老余家的门拍得山响,喊破了嗓子,老余家的孩子也是不应。老余就也多少明白一些,老余就用自己的手艺今天给小二做个小飞机,明天给老大做个花瓶,都很精致,但无一例外都是铁的,只能摆着不能玩。孩子们在这种状况下,就只有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学习就都好,比着赛着似的,老余就觉得生活有了奔头。
后来,厂长又是厂长了。厂长依然精神抖擞,重新焕发青春似的,还把白头发染成了黑发,厂长披着一件军大衣来到老余的车间,老余记得厂长已经有好多年不披这件军大衣了,再说厂里是要求穿工作服的。披着军大衣的厂长把当年的小余也就是现在的老余拉到一边,问,让你当车间主任行吗?老余听着隆隆的机器声和感受着脚下的颤动,觉得厂长的声音很遥远,遥远得有些不真实,他虽然心头很热,但老余还是断然谢绝了,他说,我不当,还是让年轻人当吧。厂长说,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我问你们主任了,他说你一直表现很好,我想把他调到别的车间当主任。老余继续坚持说,厂长,你还是让我当工人吧,我已经习惯当工人了。厂长摇了摇头,走了。厂长肯定是觉得这个老余已经不成器了,完了,没前途了。
老余的确已经习惯当工人了,他考虑问题,所作所为都和工人一样,他们总是对车间以及车间以上的领导忿忿不平,总是琢磨如何对付领导。他们还往家里偷纸,他们有的是办法,开始是把纸缠在裤腰上,大摇大摆地往外走。厂里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门卫开始搜查,他们就把纸装在饭盒里往外带。门卫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也是例行公事,但你不能过于明目张胆。
厂里一年不知道有多少纸流失,咱就以老余为例,这么说吧,凡是能用到纸的地方老余家都是用纸,铺床用纸,包东西用纸,盖东西用纸,甚至鞋垫也是用纸做的。这些纸也都是从厂里偷着带出来的纸。老余他们厂主要产新闻纸和做水泥袋子用的牛皮纸,新闻纸他们拿回家给孩子订本子,所以造纸厂学校的孩子都不用买本,即使那些田字格、算草本,也都自己用尺拉出来,没有人去买。用很白很白的新闻纸订的本子多好,大家都在用,就不是秘密了,干部工人的孩子都用,谁也别说谁。牛皮纸——也就是现在说的纸袋纸,使用的就更多了,下雨天你如果在造纸厂旁路过,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每个人都是不打伞,披着一张牛皮纸进进出出,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湿了就一扔。老余是个焊工,除了往家里拿纸之外,还往家里拿管子、弯头、水嘴子什么的,床下已经满满一垛子了,不知道作何用途。老余业务是蛮厉害的,属于技术大拿,考级的时候是八级焊工。他和工人相处得很好,他经常为那些偷东西的人打眼(就是望风的意思)、出主意,别人也帮助过他。老余已经习惯了当工人的感觉,他不知道自己要是再当车间主任还怎么面对那些工人。
因此,老余这辈子就注定当工人了,但老余不甘心自己的孩子也当工人。那时候有接班的政策,老余如果提前退休,不光可以涨工资,还可以让一个子女接班,别的和老余同龄的那些人都乐得让孩子办接班,他们怕政策一变,就办不了了,因为以前的政策历来都是多变的。再加上造纸厂那时候还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一般人想进都费劲,就都办了接班。老余没办,尽管那时候老二因病没下乡,正在家里待业,姐姐已经下乡,老余就让老二成天在家学习,老二看不出这学习还有啥希望,老二的同学大都是造纸厂的子弟,大都办了接班,上班后还请客,都穿着崭新的工作服,谈吐也不一样了,都大大咧咧,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互相谈起化浆、原木、纸机什么的,都好像很懂似的。老二就有些羡慕,就和老余表达想要接班的愿望,老余就是不让,为这个老余还和儿子弄了个半红脸。老余说,我一个人当工人就行了。那意思好像只能牺牲自己一个人,很壮烈,有舍身炸碉堡的意思。
老余也算有眼光,有点高瞻远瞩,过了年的十月就传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对所有念过书的人都是好消息。可是,那些接班的同学已经上了半年的班了,已经把书本扔掉,沾上了工人阶级的一些习气,虽然还有心思,但真正再让拿起书本就有些挠头。同时,毕竟已经有了个班,轻易都舍不得放弃。
老余家的孩子就不同了。老大在乡下,必须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回城是最大的动力。老二在家待业,一直就没荒废学业。老三正赶上高考,一直是造纸厂子弟中学的尖子生。三个人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进了考场,后来三个人的通知书就陆续来了,老大考上了一个中专,老二考上了一个省里的名牌大学,属老三最有出息,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这可是造纸厂中学的一个意外,整个造纸厂都轰动了。厂里决定对老三进行表彰,老邻居们都知道,老三就是那个有着俩酒窝、扎着俩抓鬏的小姑娘,当初谁一欺负她就哭,现在笑得比谁都甜,都灿烂。厂长也过来表示祝贺,厂长握着老余的手说:你给咱们厂争光啦,我听说全吉林市这些所中学,考上清华的没几个。老余就知道傻乎乎地笑,已经不会说什么话了。后来,让他上台讲话,他憋哧半天才蹦出来一句话:感谢厂长,感谢车间的大高大李,感谢二号楼的老邻居们。
大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不对,还觉得挺全面,连邻居都感谢到了,这老余也够周全的了。感谢厂长是真的,感谢大高大李也是真的,大高大李都是在他困难时期把他当师傅的人,他们对孩子的成长也给予了帮助,那些飞机、花瓶,老余没说,都是大高大李他们孝敬他的。感谢邻居就有些开玩笑了,但老余其实说的也是心里话。他后来私下里和孩子们解释说,没有邻居的孩子对你们的歧视,你们能乖乖地听我的话么?老余的泪就流了下来,老余这些年一直在孩子们面前笑嘻嘻的,真的流起泪来,竟是泪如雨下。
媳妇走过来安慰他说,从今以后,这不是好了么?
老余就破涕为笑了,孩子似的。是啊,生活曾经是那么的不如意,大家的经历又是那么的坎坷,那么的相同,可谁会料到,那个被他们不怎么瞧得上眼,被他们称作“余山东子”的老余,居然会是笑到了最后呢。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