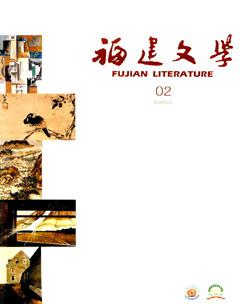雾之春(外一篇)
崖虎
在春山烟雨里,漫芜是心情的落脚。车子穿过贵新隧道便一下子陷于这样的境地。油门也入了烟雨,渐停于便道。山上山下雾的流动,象是拥车而行。
我不动,思想也不动,让这雾更好的迷动。我知道,雾的到来是为了给春天长脸,它是春的另一个弟子,比春风现实一点,比春雨空泛一些,在风前作雨状,在雨前列成风的阵势。
我和山地都是旁观者,雾似乎把山拥得更紧一些。雾的动作也有些节律,完全脱离于我的心情之外,在漫过山坡处有了些散慢与张扬,还有一些顽皮的向上腾起,接着慢慢消散,进入我大脑的某个角落。
我努力安抚那样的躁动,让目光从雾的缝隙里潜入,查找迷黛的山野留给我的注解。山野仍留恋它原本的清静,与流雾开开合合,或把头露将点出来,有一脸的自得。
我知道眼前暂无村落,我要去的地方正冒着温泉,那里的雾是春的私生,只从池底里溢出,有些曼妙和婉转且不易开散,从雾里露出的却是人的头颅,有点潮潮的笑。
人在一定的温度的水里也可以不思想,甚至可以拉过些雾来盖在身上睡一觉,让梦渐入仙境。一枕黄粱无何不可。
其实这里的山形地势并不陌生,雾可以任性的缭来绕去,那山形却在心中渐渐地明晰回来。目光入雾之初也曾有些幻想,那毕竟是个朦胧的场景,这样的美景是春天赠予,只属于春天,是春光在人间的肌理,长在山野之间,呈现些柔润的暗潮,我可以很轻易地用目光在里面播种些暗愁,随着山形流放、弥延。
只是感觉自己少了点什么,被排除在雾的总局之外,被阻隔于山形之外。灰色的天空还在飘洒纷扬的雨毛,雨刮器不情愿地被支使着,每次都在雨水的尽头发出可以听得见的报怨。
我们的日常总是在雾中穿行,迷雾让生活变得朦胧,让目标显得高远。雾还时常包装成命运,使感觉神奇,不一定灵验,却很让自我相信。出于雾的视角,清醒中的盲目是必要的,这样,人的灵魂才能找到机会,做巧合状,所谓的机缘,融合一些梦境,有了抽象,有了具体。
雾在四围随着山形涌动,我的周边反显得清晰。我没有介入山地的生活,或说雾把我隔于山地之外。高速公路在前方渐失,我知道温泉在几座山的后头等待着淹没我的肉体,在那里我可以成为雾的一个部分。车灯狂啸着杀入雾中。
其实我原本是雾,人人都不是明示着的。有时把目的当作出发,在雾中寻找些信号。如果信号被卡断了,又意味什么样的场景,温泉里在蒸腾什么样的雾。雾也是可以入心的,它在那里一次一次累积,却沉淀不了,也咳不出来。
春天,多雾的季节,雾不在等待中消退,不在行进中消退,季节没有消退。春天没有原点,雾没有根。也许在没有雾的日子又想念着雾,也许雾只宜远观才视为美景,也许给别人多一些雾才成为魅力。活于困顿与纷扰,也是生活的雾状态。
雾锁黄昏的日子最是焦心,暮野四合中,仿佛与世隔绝,孤零的心理自视成就着孤独的心态。人的一生最落没的不过于黄昏时节的孤独与寂寞,阅尽铅华的回忆也添不得如雾般汩流的愁絮。
我把车子泊在雾的边缘,步入温泉的雾中,温馨的浸透等待着消解与灭失。这样的雾,没有一生的等待,春天在迫不急待的消逝。于今,不会有人用等待的方式应对生命原生的焦渴,不因无望,没有执着,只要寂寞能暂时回避。
没入温泉,连同张望的头颅。发现雾与梦是不一样的。
石头城,灵魂之隐
一个女人带我走到河边,指了指水中的石头,在我细看石头时悄然远去。
我在石头边找到我现世的影子,那一刻它正与石头耳语什么,至今我都没听见。是否该抛弃影子,以便没有任何障碍地干我的事情?我的影子一直躲藏在石头的背后与另一些影子悄悄地跟踪着。我从背后看见了他们,心里暗暗好笑,也罢!
在河里摸着石头,可能触及灵魂。跳出水之外,石头成堆成堆,辗转于河滩,明摆着干枯。在干枯里寻到墙,那里的石头都因挺挺地站立而风化。在风的缝隙里,曾有过太多的摸索。那便是城的一部分吧!
其实我们从未认真看过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那都是真真实实的文字。它们喘息着路过的每一口风,几百千年,而不需要忏悔。从我把手伸入水中触摸开始,石头里的线条就开始切割,就象桃花逃离春的现场,那些难以思议的变迁。我在切割,还是被切割呢?墙把所有可能的答案立在你面前,尽管分成块状,和那些日益消逝的泥巴。
可以确立一个假想的城门吗?我应该看到怎样的市井,在融入其中之后。唯一能确认的念头是在夜里不需要任何一盏灯,有,也别说出声来。因为我想与石头有个约会,不管是河里的、滩上的,还是挤在墙里的。只想说:让我看看你的背面。我知道那里的细节是影子生活过的地方。石头和石头在那里偷着什么。
把城门与墙越续越长,能关住一些魂灵,就可能恢复过往的烟尘。戏楼子对着烟花三月,西湖里笑声咯咯,水袖包裹着风眼,石头在水面上一荡一漾。我的前身在这样的地方入住,我的今生才会抱着石头细数黄花。呵,店小二唱了个喏,捧出一盘的凉拌。
我不可能等到夜晚才遁出城外,心里有无数条线路,无怪城墙的每一只眼都能看见。如果守着距离,或被距离切成无数的部分,潜伏或是绝好的选择,就象心隐于我,我隐于心。或在塑像阴影里站成一块曾经拾得的石头。
不要说话!我在风里听到断喝:你夺走了我的睡眠。黑暗里所有的眼睛哔哔剥剥睁开将来。石头从未有过真正的睡眠。对不住,我也没有。
我象风一般转过所有的街市,找寻一颗存有心律的石头。把它嵌回城墙才能回归城的生命。它仍躲在黑地里,收缩着原生。我在风眼里也有了些乐子。
僵持,我的城向河水倾去,干枯后的焦渴,所有隐遁的痕迹也一并干枯。石头伸出唯一的草尖。我无力挽回我的石头们的倾泻。
不如随便找块石头,在墙角蹲下,孵出些想说的话语。抚摸石头就象抚摸自己的灵魂,看不到尽头的队伍扛着阿拉伯数字随意组合着我未曾有过的刻意。
谁隐入了我的城、我的石子、我的经年?
我突然明白,石子就是城,那些存在于虚无的意义。那些切割的等式在不对称里寻觅石头与石头之间的轻与重。我便是穿衣行走的石子,等待城或城墙一轮又一轮的荒芜。没有人说出荒芜的意义,而现在,我正掂量着自己的手,该如何配合石头的节奏?退与站都不是想要的答案。石头带着它的城池迁移。
旱季还是随着想像来临,如果你与墙里的石头一样瞪着眼,便不会感到突然,你可以捏一颗作久违状的心来,等待河床的呈现,等着嘲笑那些半干的石头,象曾经的你。尽管曾经的你据说与河床无关。河是你母亲淌过的泪,濡湿你日后风干的脸。
便是那座城么?可以随便启闭,用你黯熟的手势。石头的故事在那里累以万计,却被一一关押在纸竹灯笼的光照里。提着灯笼的手在光之外,和我一样站成距离。手象城一样延伸,在我的围周,石头作势准备呑咂我。对于我这样的不以为然,一定得有个仪式:摘除人类的灵魂。
我只有用不停的说话抵抗,我不惧怕死亡,却不愿失去灵魂。没有了灵魂,做石头干什么?我的话语推开一浪又一浪的石阵。你们为何想要一个没有灵魂的石头。我发现所有的石头都怕语言特别是有声音的语言。他们躲闪着我的话语,他们在离我不远处沉默着,变幻着形体,越积越厚,直到足以让你失望为止。
没有了灵魂,灵魂看着你,象即将被风干的石头。
我必须捍卫灵魂,我的、石头的,就象我曾经的涉水而过。涉过水的人不会焦渴,还会有些石头的追随,那些未入城的蛮野,也曾和城有一样的血统,尽管它们的灵魂糊涂得不如没有。
不对,不是灵魂。我想是我想错了。我在河里摸到的不是灵魂,也不是石头,那只是我自己,以自己触摸自己。那座城也只是我家后院。城与后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生活和生活之外的东西,可以触摸的不可以触摸的,有形的无形的,都免不了与石头出出入入。
那些失去水份的生活被一份一份收起,打印成石子,各种异样的棱面,寻找某些光的反射。最初的阶段总能熠熠。这时,水就该来了,就象城里的每一个水流,都漂浮过石头,让石头接受惬意的抚摸,石子日益光滑,再也离不开水的润滋。那样的灵魂总是无法烘干,象发了酶的春色挣扎着无数斑点。你可以无数次地歪着大脑,也看不出原来的质地。
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后院并没有大脑,是些形似的石头,它们是城的中坚,经营着一轮又一轮的繁华,直到一轮再一轮的荒芜。它们没有恐慌的表情,它们既没有恐慌也没有表情。
结局本身并不是结局,与石头的交往如同成为石头,结果都关系城的生命兴奋。兴奋是城的耗散,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不依不挠的指责,并不曾造成城的溃散。石头的兴奋有着原生的爆裂,象是制造新鲜生命的过程,只是这样的创作只能存在于耗散之中,直到成为一粒可能昂贵的砂。
我们不称砂为石头,甚至不称其为石子。
想找一块裂而未断的石头,在那里寻一些隔世的痕迹,或一口未曾出世的口味,或石头的干枯的遗言。也许灵魂的前生就在那一条窄窄的缝隙里摆着,等待你用眼睛触摸,或在你用双手捧起时得缘你的体温孵化。这样的感觉是否会转化,在我结识了许多石头之后?在我寻到那条等待的裂缝前,我得认真地摆出几个智慧体姿,让我的心神无限地接近一个点,或无限地接近一个存在的虚无。我得浓缩所有的已知,并积极地吸收路过的空气里的所有水份,在蒸发的前奏里加热所有存留的运气。当然不必与石头签约,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与石头有个约会,我的来生注定要进入一块石头,伪装成灵魂,在城门边的第三排第四或第七个位置站成一个吻风啜雨的遗迹。与荒芜一起等待我的来临。
此时,我的手上没有任何的工具,也许有过的叮嘱都被河水浸湿了。除了本能,只剩下可以扫射的目光,在城池中寻找同类灵魂的反克,在夏天到冬天被雨撕过的距离里显示一枚印章,附于石头的胎衣里诊断灵魂的体征。
不知是什么让我伸出的手有了些抖动。
责任编辑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