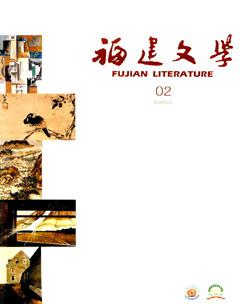时间不复:陌生和忘却
伤水
A.
我现在是在一个陌生的水域给您写信。我绝对不可能第二次站在这片水波上——水的涌动和航线的不确定,更由于我四处浪迹的习性。像那哲学名言讲的,我无法再次伫足。我无法再次感受它的褐色皮肤和普照它的惨忍阳光——这由南方四月的太阳牵出的硬朗的金线。
我在船的甲板上。盘腿席坐。身旁是一堆柳籘筺,几个船员们在专心地修理着。船在专心地航行,从石浦港至椒江港。船微微晃动。
船微微晃动。——唯有这晃动的感觉是我最熟悉的。
一切均是不曾照面。
风掀动我的信笺,使我的书写更艰难。风从陌生的海岸鼓足干劲地拂来。那海岸看起来犬牙交错,支离破碎。船向南航行。指南录。我面南而坐。风打着我的右脸颊,搅乱我的发丝和对你叙谈的语言。
而我的左脸颊和这页信笺充满阳光。我相信您默看这封信时照样会感觉到温暖,持信的手指上沾满阳光。
这些陌生的感觉总使我激动;但更多时候,陌生使我对惯常的漂泊产生感伤,浪子苍凉荒旷的心绪,激动奔放中掺杂忧郁和孤寂。
船的晃动有点激烈起来。我担心这浪波上的文字会变成浪沫。
我总在旅途。总在旅途。英文叫on the way,为什么我总在旅途? Why always on the way?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种味道多么舒服:洒脱里的无奈,放浪中的积极。
你曾讲“跟我流浪”。我总觉得自己过惯了独自漂泊的日子,有了你,会连累的。想想你该是个岸。我依旧漂泊。我累了,我就回来,我轻轻地拢岸。然后你容纳我,好不?北岛这样写:岸,举着一根高高的芦苇/四下眺望/是你/守护着每一个波浪/守护着迷人的泡沫和星星/当呜咽的月亮/吹起古老的船歌/多么忧伤
B.
刚才在船上用过了中餐,浪突然猛起来,船晃得厉害。我仰在甲板上躺了一下,继续给您写信。
你定不知道这石浦港在何位。它属象山县,在浙江省中上部。
旦门,又一个陌生地。我四处流浪,猎奇一样涉足一个个陌生地。那举目无亲、举足无故的处境,给人一种莫名的情绪。我常常体味这种无穷的恍惚。星期四中午12点,天空阴霾,午时和傍晚没什么区别;一辆乒里乓啦、东晃西摆的长途车一个劲地摇了我五、六个小时后,突然在一个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荒凉的海涂边停下,车门哐啷一声关上,车又叽哩咔啦地蹦走,——抛下一个恍恍惚惚的我。我定睛看完那辆公共汽车在海岬拐弯处消失,晃晃脑袋,擦擦眼镜,找到一个残缺的指示路碑,步向叫旦门的村庄,打听叫某某名的冷冻厂。而多年后,我肯定会完全忘却我曾经来过这里,和一个企业签过将履行或不履行的合约。合约,好像也不是用来履行,而是专门用来忘却的。
陌生地,陌生人。当时陌生,以后继续陌生。
这世界对我们永远是陌生的。即使你无时不刻地流浪,也因生命的有限,终究觉得和这世界不曾结识。我们只能自我安慰:在这世界上我们也曾走过一遭。
果真走过吗?谁能在时间中留下痕迹?而“时间”,这太过哲学的时间,使我时时对“生命”产生怀疑。柏格森将时间分成两种,一种是用钟表可以度量的时间,也就是物理时间,一种是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即“绵延”。柏格森认为物理时间受到了空间的侵略,忽视了瞬间与瞬间的不同,还忽略了时间的流动性,而“绵延”是不同质的、流动的、不可分割的,各个阶段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柏格森认为只有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而这“绵延”又能使我抓住什么呢?熟悉的舍弃或陌生的把玩,还是经历后的忘却?
纳博科夫说“未来并不存在”。过去,总在时间中消失;而未来,是目前的“时间”尙未到达的事物。人唯一能够把握的,只有“现在”,我们面对的也仅仅是“现在”。晚上我上岸后的时间在哪里呢?它只降临在我上岸以后,现在它不存在。我右边隔水相望的山坳里的清风,还一缕缕地正在途中,它现在无法吹拂我。我中餐前的时光没有遗留在我前面几页信笺上,文字不是对时间的凝固,只能是记忆。但记忆或许就是时间的一种?那么,陌生就肯定在记忆之外了。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试图追回失去的时间,最终却发现,要重现往事,要现实和过去在“感觉”上的契合。感觉,包括味觉、嗅觉、触觉、听觉。是的,他还认识到,人们只能在精神上追回失去的时间,艺术作品或许就是人们在时间中留下痕迹的精神工具。纳博科夫在普鲁斯特观念上有所发展,在他看来,除非精神,人们不能在物质层面追回失去的时间;艺术的作用也是有局限的,它无法使我们多层次地超越“现在”……
我们失去的都是时间。时间使事物在熟悉后陌生,也使另外一些事物在陌生中熟悉。我喜欢的博尔赫斯正是在小说中(比如《小径分岔的花园》)营造的时间迷宫让人深深着迷,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是由记忆构成的”,又说“一切都会消失”,——那么当时间也消失了,我们在哪里?
船在剧烈地抖动。你看,连“抖动”两字也剧烈地抖动了。我的时间在即时即刻,抖动。
C.
此刻,我已住宿在熟悉的椒江市椒江大酒店。在船上写到抖动时,海与船激烈相抗,晃得厉害。我停下来了。续写时墨水凝结,仿佛时间的停滞(它有过停滞吗?),无法书写。记忆消失了,时间没有存在,我们在时间之外的深渊,一片黑暗。
那么现在继续,“卡尤廷特阿近”——你能听懂这话,电子游戏机“打枪”中那老外对他的枪手的命令。
我把以上在船上书写的文字嗅了嗅,有一股咸腥味。是否气味的感觉让我找回了白天的光阴?有一点肯定是,这在浪上颠簸的文字只属于你,属于阿庄,属于阿庄的时间。这时间在忘却之外。
我说我已在熟悉的椒江市住下,意味着离开了陌生。也许“熟悉”不一定就说明我在我的“时间”内。也许“陌生”才能证明着我的抵达和我的存在。一生中我们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你想得起相同的这句话是谁讲过的?在一首诗中,女诗人,题目叫《母亲》,翟永明)。
面对陌生的重重障碍,总有一刻我会选择放弃而相守相偎,在心里说:归来了,亲爱的,一切都很完好。我知道此时你的眼里定是一片夕光(或者曦光),从那里流出醇厚的柔情和无限依赖,你侧头将脑袋靠在我的胸膛,你双手环抱着我,默默无言。还有什么可言呢?你的充分归附和默契,使语言多余和累赘。
而我想我在拥着你时,会习惯地抬起双眼,望着海、望着海,望着这不曾征服且永远无法征服的桀骜的敌手,望着这教我懂得爱和永恒、教我熟悉陌生、教我体味生命内在的苦痛和激情的友人。我明白我离不开和我同生同长的海和水,我明白我生来就注定要流浪的命运,我明白召唤我的涛声意味了什么又会对我赋予什么。我爱你,无牵无挂地爱你,阿庄。而我必须在爱你的同时也爱海——爱短暂的一生中与生俱来的渴望、爱失败中不断开始的抗争。无论我面对的是怎样的海。让我涉及一片片陌生又诡谲、神秘又险峻的海域,让我熟悉它们然后玩忽于掌腕之间地贯穿其中。最后就让它按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喜新厌旧习性而最终丢弃它吧。我再去步入另一个陌生——我想起《百万富翁》中介绍的“遍地撒种式”的美国奇人休斯,你记得他吗?那家伙从经营休斯工具公司开始,然后逐步建立休斯电影公司、制片公司、休斯飞机制造公司、国际航空公司、休斯电子公司等。我知道,我或任何一位中国人不可能成为休斯,但至少我会干得出色,干得潇洒。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机会。
我讲“必须”。我记得今年正月初二,里岙白沙滩。我的阿庄和海面对面,远远地站着,拾起沙滩上一块又一块石子奋力掷向海,掷向不停地卷上又退下的潮汐。可是,一块也达不到海浪,看不到石子掷入海水激起的细碎的浪花,那乍开就谢的浪花。可你不断地掷着,一块接一块。我用石子在沙滩上划下:阿庄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我是说你自不量力,你已经发挥到极点了,除非你练好了臂力和投掷技巧。那天晚上你悄悄流泪了,你说是因为掷不到海。你说你就是达不到你欲达到的目标。你说你常常就是这样。你说你就是不相信,可你就是达不到。
……我会烙下对这个下午的记忆。有一天那该死的石子会在空中划一个抛物线,远远地落入海水,溅起一串哗笑。
那石子它“必须”达到。
现在让我再次拭去那晚你流的泪。多苦多咸的泪呀。
D.
又一个熟悉的春天。不知道阿庄在这春天里理了怎样的发型。你南方家乡的春天已春得很可以了。最讨人喜欢的是满坡满坡的油菜花,黄得不行,热烈得不行。
哦,油菜花。那仿佛是为你写的诗,仿佛那时就知道会有一个你。我是怀着多么深远久积的感情来等待着你。
在春天流浪。流到哪儿都是一坡一坡的黄。还有,绿和红。记得周四早晨坐车从宁波至象山旦门途上,路旁山坡上青草绿树中,杂着血一样艳俏的杜鹃花。阴霾天,间或淅淅沥沥地落起雨来。可那杜鹃花依旧。依旧以她的血,染山坡一派壮丽。一年一度她都这么顽强,谢了就谢了,萎了就萎了,可该开的时候她照样开。一座又一座陌生的山在车旁转过,一滩又一滩的杜鹃花在车旁红着。山色迷蒙,我脑中却闪起“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豪语来,这恐怕与杜鹃花啼血般的牺牲态势不无关联吧。
你该去看看北方的春色。不知那些money是否够去看看绿和红。红肥绿瘦。不知阿庄在京城由于苦苦地用功瘦了几许。
春天和阿庄怎么老是缠绕在一块儿?想去年的春天,我曾突然地在杭州挂电话给在玉环的您,让你听听杭州春天的一首歌,记得吗?
你、我、春天有缘份。我们和春天已不再陌生。
E.
此时,我在椒江发往玉环长途车中,车将启程。这是一段我熟悉的路程。每次出发或归来大都得打此经过。路象一条蛇,游在每个浪子的征程之中。一个人的生命有无数时间浪费在旅途。我闭上眼休息。我记起昨天在船上也曾躺在甲板上,眯起眼用烟头对准蓝天上的太阳,我想宝贝太阳会替我点燃这支烟的。船在身下晃着。这下你全然感觉不到是在航行。和儿时躺在山坡上晒太阳的感觉没什么两样。一条船,汪洋上的一条船,我躺在船上,眯眼瞧太阳——多么奇妙啊:上是蓝天(昨天天气特好),下是莽海,中间是我。
四周的海皮肤一样完美。
于是我极想能赤足在海水上面溜达而不沉没下去,就象在陆地上一样随意,跑一下,蹦一下,躺一下,多么惬意。高兴起来了,就潜入海中和鱼一样翔游,我和鱼平等相处,签订和平相处五项原则,决不捕捞、加工它们并出口到日本或台湾。当然我还不能将自己的残酷和罪恶,暴露给可爱的鱼类。哪怕我和鱼相对无言,恍如存有芥蒂偶然相逢的旧情人,也不能让可爱的水族们明晓我成吨成吨地贩卖它们的罪行。我们和鱼类一样同属水中居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用不着回头是岸,尽管苦海无边。
F.
我知道您一直在等我来信。明日该打电话告知您。我已欠你许多封信了,这封将是最长的,我分几个信封同时发出,然后你一口气连起来读。让熟悉的潦草的字体和专属于我个人的句子习惯——再次列队走过你的视野。在一周之后。
有蛙声如鼓在田野,有灯光如蜜桔黄在陋室。你熟悉的玉潭路179号,崔健和高明骏的歌声刚熄,托友人从厦门带来的CAMEL烟燃在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桌头散乱的书籍和背后平展于床的棉被,一个人坐在塑料椅上伏在白色的书桌用银色的圆珠笔倾吐对另一个人的思念——
在四月深得即将没顶到天亮的春夜。
我听见了远处几声依稀的鸡啼。
我可能五月份会去北京,届时我们一块儿手拉手在北京逛胡同——晚上听一台商讲他在北京经常通宵步行,大街小巷,胡同四合院,味道好极了。
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声音。我该休息4个小时,然后上班。
此刻您定在梦中见到了潦草的我。
责任编辑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