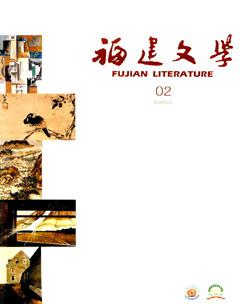海中的守望(外二篇)
禾源
有时会想,我能否如一块礁石,扎根岛屿之上,迎一股股浪潮劈头盖脸地袭来,又送一波波汐水哗啦啦地退去;若有幸能顶个灯塔,借光成为航标,所有的孤独也会幻化成如磐的骄傲。有时又想,还不如像一滴水,融在潮汐中,有我而又不是我,安安然然地生活着。
地里活着草根,得适宜气候就会萌出草尖,我那些不断冒出的想法是不是也如这些草尖,总有一条根盘活在我的记忆里。闭上眼,居然感觉到曾经的海,不变的潮,一浪浪地推着我。少年时在海边滩涂上踩过一串脚印,捕过单鳌蟹;青年时和同学站在船头扬起几分意气;成熟了拥抱着爱人坐在海堤边听着浪潮,看着浪花,想着哪一朵是自己心海里绵绵的思念,看着搁浅在海边的小舟想着哪一艘是爱人心中折下的纸船……
不能再这样想下去,我还不甘愿整天深耕着回忆,毕竟还没到只活在回忆家园里的时候,生活中还有许多可以延伸的空间,记忆之根还可以延长,会把若干年后回忆的家园营造得更大更大。
我曾以为最值得信任的是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可如今我觉得最值得信任的应该是感觉,特别是第一感觉。就凭这种感觉,我把再去三都澳看海的愿望托付给一个文友,一次宴席上偶遇的文友。就这么一个酒后的托付,居然成了一次约定,她选定了时间,安排好行程,邀好同行,便开车起程。路上,我静静地思索着耳闻与目睹,若说对这位文友的耳闻,只听过她明晰的声音,还没听过她别的传闻;若说目睹,也只见过她舒朗的身材和大方的举止,没见过任何关于她的鉴定文字,更没有看到她乐于助人的简介。只不过是感觉告诉我可以托付,我就托付。还是古之圣人说的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感觉可信耶。
一股浓郁的海腥味告诉我码头就要到了,这股味虽嗅得次数不多,可有一着,就够深刻。世间诸事无常,水可易道,人可易容,可最难改变的就是本质里透出的气息。就如刚才嗅到的气味,就是蕴涵在海里的鱼、虾、蟹等万种生物体味的汇聚,借海浪翻起,随海风吹来;或一网网打捞,一篓篓汇聚,把浓郁的海气息集中到码头,停泊在码头。这气息是别的地方能有的吗?
我如同一个缺氧的人,大口地吸着这里的气息,这味道和牛的腥味一样,不仅能诱发我的食欲,还能激发出驱舰斩浪的快感。坐在冲锋艇上看前方的水被劈得唏哩哗啦让出道来,势不可挡的感觉真好。我以为吸足的海腥味,能给自己输入海的气息,这样上岛就石不绊脚狗不吠,可没想到岛上的狗依然吠得狂,异味的入侵激起了它的愤慨,不仅把锁住它的铁链挣得铛铛响,还把它脚下的土抠出了坑,这狗比人更在乎自己地盘的气味纯正。
穿过街道向岛上的高处行走。我记得岛上有天主教堂、修道院,还有兵营、炮台。可看到的炮台只是遗址,兵营也是雁去楼空,只有天主教堂依旧安祥地耸立在岛上,修道院的修女把院内打扫得干干净净。看着这历经兵燹与世事变革岿然不动的教堂和修道院,又不自觉地走进老道智慧中去——想起坚硬的牙齿总比舌头更快离开身体。这三都海岛,海上的军舰、岛上的兵营,高处的炮台,大概都是牙齿,教堂,修道院则是那柔弱的舌头。虽然说不太确切,但是同理。安宁的环境,一定要有坚强的守护,高飞的灵魂一定要有血肉的炼狱。
修道院前是一块大空地,长满荒草,荒草任其枯黄,并没有人打理它。一根大概是失效的有线电视光缆耷拉在院前十几米的地方,两端都还没脱离电杆而落地,像是牵着的一根黑色警示线。我一脚跨入,一位文友说:修道静地,这是警戒线,你怎能跨入。惊回首,我立即抽回脚。走到修道院的侧门,看到文物保护的牌子之外,还看到了开放时间,修道静地可以参观,那条线只是废弃的电缆,并非是警示线。
我轻轻地敲门,静静地等待。门打开了,一个年纪与我相仿佛修女侍在门边。白衣黑裤,浑身洁净,一个不染尘的人。见到她,我有点拘束,觉得自己像是刚从草灰中掏出的地瓜。她轻声细语,轻移脚步把我们引进修道院,院中四围走廊,中间天井,每间房门从不同方向朝天井开着,天井中栽种着花草,这些花草也一尘不染,虽然花草绿得有些脆弱,可洁净得让人怜爱。也许今天是阴天,或因楼有三层,这天井能引进的阳光不会太满,花草大概也缺了点什么。
我与修女面对面交谈着,这种没有准备,没有主题,没有目的谈话,只能是道外人对道中人的一种探询。她十几岁出来修道,在修道院也度过三十多年,非常适应这种生活。我想她能从老姆姆身上看到自己年老时的处境,还能从圣经中找到许多修行的真谛,再加上还有神父的开导,她们并不是迷茫地活着。她看着老姆姆推着轮椅助走的目光关切中没有担心;她听见躺在床上的老姆姆呱呱地叫,也没有吃惊。我说那位老姆姆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疼痛在叫,她说:她在念经。生活中的感觉要沉积多少才能成为经验?我不太清楚,但这位修女从从容容仿佛有了许多经验。她带我参观展览室后,还告诉了我,还有几位年轻修女上山活动,到了时间她们就会回到院里。我问她所谓年轻,到底最小有几岁?二十几岁,也修道几年了。
三都澳是个岛镇,几百户人家生活其中,炊烟飘着家的气息,灯火点着温馨。同守在这岛上的还有海军官兵,他们军歌嘹亮,他们浑身是劲。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这岛上的姑娘偷偷会见她们心上的兵哥哥。一个个成了军嫂后,就在岛上开个军嫂店,照料着后面又应征到这里的兵弟弟。文友说她家的姑姑等好几个女人都嫁给兵哥哥。我曾以为这岛四周是海水,多孤单;曾以为这岛上人少车稀,多寂寥。其实,就是因为孤与寂的碰撞,把岛上的情字燃烧了起来,让许多岛上阿妹为兵营里的阿哥缝着军衣领子……岛!可谓是一个多情的岛。岛上人醉在这个情理中,把船摇得浪来浪去,岛上的白鹭也醉在这情理之中,一代代扇动多情的翅膀。
那满载着多情的小舟,修道院的修女们看得真真切切;翔飞的白鹭停栖在教堂之上,成双成对影子一样成了修女们的风景。岛上的情天恨海修女们并不是熟视无睹,也不是无动于衷。她们一样热爱着这一切,只是她们有自己的认可,有自己应当要承受的一切。生活简单,简单到只余下四个字,那就是认可与承受。
修道院的修女,猎潜艇上的官兵,三都澳的乡亲。我在胸前划个十字架,道声“阿门”,向他们作别,我不知道这个举动的深刻含义,就像身处他乡学了一句土话一样,说着亲切,说着享受。
三月的乌镇
三月,在家乡是个潮湿的时节,山野遇潮,小草含露,树叶新萌,展露着新生的气象;村子遇潮,磨石路边爬上青苔,老屋壁板出现霉斑,有着一股腐去的气息。三月,三月的乌镇会是怎样?你可是镶在江南水乡名片中的乌镇。
三月的乌镇,是种一觉初醒,梦境犹在的状态。和煦的阳光照得乌镇温馨如室,老屋、水街、小舟、柳树,……享受着这一温情。树不想动,水不想流,老屋的门不想打开,还有许多的许多都想静静地躺在这个大温床上,把三月温存。
然而春风总爱撩拔情芽,哪怕很轻很轻,所触之处便有痒痒的感觉。柳条儿轻摆,柳絮轻盈,若有若无地飘扬;舟橹轻摇,桨儿轻划,水街有了荡漾的涟漪。醒来的柳条、醒来的水街先把老屋摇醒,老屋再把熟睡的人泛醒,刚醒来的一切回味着睡时的梦,把梦呓复述在三月的阳光下和春风中。情景里我如入梦境,小桥、流水、磨石街弄,这一切我都似曾相识,一拔拔的人流我也似曾相识。我向街边小店哼着小调拉麦芽糖的伙计打招呼,向卖花纸伞的姑娘打招呼,向挂满纸扇的店里老板打招呼,还向……可还没等到他们回应,自己则随人流匆匆而逝,只有梦境才是这样,一定是梦里江南,梦里乌镇。
小舟在水街徜徉,人流在石街流动,三月的乌镇,就在这些律动里传递着古老回音,振动着当下游人踩出的节奏。老街两边的木板楼,以千百年来民房的高度相挨相对,谁也不敢突兀高起,我知道这是民风俚俗所至,在天地间,上苍所赐的福份如同阳光雨露一样,每家每户一样平均,敬畏天地一样情怀,天机地福同等享受。只是因为每个人的福报不同,他们的门户有大有小,有尊有卑,有贵有贱。那些成为陈列馆的都是大户人家,那些贴着春联和婚联的都是些小户人家。看着陈列馆件件古物,参观的人流一浪接浪,再看墨香犹在春联与婚联,我感受到自古荣耀,光照千秋,自古百姓生生不息,似乎让人明白了热闹与平静凭什么相守的哲理,体会着世事无常中的有常与和谐。
我深深地作揖,别过沈雁冰的故居,许多的历史回响一直萦绕,矛盾,茅盾多好的笔名,传承与变革就在矛盾中进行,从《幻灭》至《动摇》直到《追求》,轨迹深深的三部曲,是在无常世界中一个有思想的作家轨迹,矛盾永久存在的矛盾,茅盾永远光耀的茅盾。有人说“茅盾某些作品风格沉闷。”或许吧,耸立在历史的隧道里每个标识,它的立定,一定周匝着沉重的气场,如是的气场,沉重与沉闷皆为性然,就如这乌镇的木屋,几百年烟熏,重重地染下了铁质一样的岁月,当年门前纳凉的阿爷,把酒话桑麻的场景挥之不去;阿婆秉灯养蚕的背景深深沉壁。年年三月风,吹来的是记忆,是重读。看,那些二十出头小女生们戴的青花头巾,楚楚动人,多看几眼,仿佛见到当年浣纱的阿妹,白居易的诗句在心中默诵“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十足江南味的阿妹!三月的乌镇,就是这样处处让人追古抚今,暗发着幽古思今的情怀。
邂逅永远与美妙同行,三月的江南处处美妙,再有邂逅确实能让美妙生花,让人陶然其中。有的,只要有纯洁浪漫的情怀,就会有美丽的邂逅。曾经我游周庄就值世界选美颁奖活动在那举行,便有了与许多美人邂逅的机缘,这次到乌镇一样也有,有的称叔——帮我拍张照,有的叫大哥帮个忙,不管她来自何方,不管她姓氏与职业,瞬息之间照相机留下她们的靓影,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当我走进乌镇染坊的展馆里,激动着染布如瀑的情景,那垂天而挂凉晒的青花布随风起波,想象中这是从大地流向天空的碧波,这是一截无根的青色瀑布,许多美人走进那竖直的碧波中,摆着万千姿态,进进出出,如同仙子出隐瀑中,足以叫人留连忘返。就在这时,一位姑娘笑盈盈走来,亲切一声大哥,才让我清醒,我接过她递来的相机,她展风情,我找聚焦,拍下了一组片片,其中有一张正值一阵风起,青花布一波传一波直向天上流去,她扯上一缕,此时定格,画面中她如立波中随波升腾,她激动得一定要请我美食乌镇的“东波肉”,我没接受,她不谦让,这个美丽开始也就在美好的AA制中分别。
有人说时光短暂,美好短暂,三月过去,乌镇别过,可我想记忆长久,历史长久,只要我有记忆,乌镇的美妙就会在我记忆里,就会在许多人记忆中,也就会在历史的记忆中。
弯弯的稻穗
那是一片稻谷,一片金黄的稻谷。它们一串串弯腰俯首,一式背负的姿势把沉甸甸的成熟扛起,稻谷的一生在谢幕前用虔诚膜拜定格。我的双脚踩过田埂,让草儿贴地,让自己情怀贴地,仰视着一串串稻穗。悬在稻穗末梢的谷粒,特别地饱满,以身相许,回报稻田,仿佛是最盈实的愿望;稻秆上还有许多谷粒昴首向天,让太阳晒去成长中欲望的水份,感恩原来只需是一粒粒晒干的大米。
阳光照在金黄稻谷上的场景,本是一幅自然的秋意画面,可今天我怎么把她看作是一个肃穆的朝圣仪式,是不是生命的轮回观在我脑子里作祟,自己也琢磨不透,但我确实想到此中的稻谷就要从稻秆脱离,就要进入另一种的存在方式,朝圣该是生命转折的最好准备。这么说我的想法也许有合理的地方。
一阵风,所有的稻谷向一个方向朝拜,一拜、二拜、三拜,随着风向的改变,稻谷拜过四面八方。站在稻田中的我该不能闲成一个异类,或成为影响这盛大仪式的痴呆,我一定要做点什么。击掌当作木鱼,不行!朝圣不是诵经,不必击拍敲点;合十祝福,好像也不适当,一辈子养我的稻谷,我的祝福是为她还是为自己呢?也像别的采风者一样,照下一张张片片,这个虽然可以,但毕竟把自己与稻谷拉开距离,不尽我意。风,田野的风,她一阵一善举,一缕一情怀,不但引领着稻谷参天拜地,还借来蒲公英当使者,轻轻把稻谷头顶上的季节信息吹落到他们中间。我也吹起了蒲公英,嘟着嘴聚气吹上,接着便托咐给风把它吹远,我一直注目相送,第一朵看不见了,再吹第二朵,第三朵,第五朵,我的心就如蒲公英一样,落到稻谷间。
心留守在稻谷间,脚却随田埂牵引走过田野,我来到了穿过田间的溪流边。溪岸的芦苇,花尽秆枯,折的横斜,竖着孑立。败草、溪边树再添这些苇秆,把我投进溪中的目光滤得斑斑驳驳,看浅水轻流,见水落石出。我收拾起零碎的目光,举目搜寻溪流的来龙去脉。溪流弯弯曲曲,我喜欢着,这是活着的姿态,溪流活着不仅要有水,还要有曲折的流线。活着的溪流让我睡过的遐思又一次被漾醒过来,漂浮在溪水上,感受溪水流来的是日子,流走了是时光,且这些日子就长在水田里,历经春夏,在秋日结成串串稻穗。春天的日子稻禾长的是种田人一家的梦,夏日稻禾嗅着这家人的汗味,秋日稻穗和种田的人一样向天地弯腰参拜,这就是溪水流进水田的日子。种地人一家的梦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梦则是能像大人一样地生活。插秧种地,娶媳妇生儿育女。小时候我们常常会在稻田边,采来掰爿草,两个伙伴各执一端掰开,口中念念有词:“村里的‘小芳能成为我老婆吗?结婚后是生男还是生女,掰爿草,请告诉我”。对掰后,若是一丝相牵,便说是生男,若是丝牵棱形,便断为生女,若无丝相连,就说明与这姑娘没有姻缘。这些做梦的日子,稻田里的水明镜着,稻田里的稻谷见证着。明镜的水流到溪里,随时光流走,把这梦流到更远的地方,也许是替这梦寻找归宿;见证的稻谷则结满谷粒,让日子不饿,让我们吃饱长大,去圆种田人的梦。
我在溪边坐下,稻穗就在身后,溪水就在面前,一根根苇秆像是我下的钓杆。我要钓回什么?是溪里的鱼,还是流走在远方的梦?或者是刚刚还在回味的新梦呢?梦与溪里的鱼一样可爱,但被钓起的鱼活下的能有几条?被晒在太阳下的梦还是我的吗?我轻轻用脚拨动苇秆,惊走想要上钩的鱼和梦,让鱼儿快乐地游在溪水中,让我的梦依然长在稻田里。
触动苇秆,仿佛是我做了一件得意的事,在几分满足中,瞧过自己的双脚便拾起脚步走向那座清乾隆年间修建的石拱廊桥——劝农桥。廊桥的青瓦把秋天的阳光遮挡,桥里的风少了阳气,桥中的色泽更见古朴,就连神龛上的神偶也和耕夫一般,满面尘灰,土里土气。歇在其中的我,左顾右盼自己的影子,才知我的身影借古色点灯,随风而行,为寻觅那段历史而去,怪不得我找不到自己的身影。影子能邂逅影子,我的影子遇到了当年知县的影子,知县在吟咏《春日东郊劝农》的诗句:“载酒春山自劝耕,官亭杂沓共欢迎。溪回树绕青旗转,风定花随翠盖轻。已荷恩纶蠲宿赋,史占丰穰报秋成。太平乐事原多众,野老休夸长吏清。”呵呵!又苦又累的农活,活出诗意,虽说这不是农事的本意,但农事不仅仅能产出稻谷,也能育出诗心,这个不足为怪,劳动创造一切。但我有些不解,稻谷农家人早就奉为至宝,同时民以食为天,这种粮之活是产宝之活,是关天大事,还得知县来劝吗?诗经中“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该不是指这些耕种者吧。知县劝农,劝的是什么?知县吧:知民,知事,知己、知君。劝的该就是诗中的最后两句:“太平乐事原多众,野老休夸长吏清。”原来为官之道也要借物阜年丰来当盘缠。
稻谷啊!你弯下腰,原来不仅仅只是在参天拜地,还得感谢浩荡皇恩,清明长吏;稻谷啊!在田时你是农家人的日子,离开了水田,脱离了稻秆,农夫不敢说他是你唯一的主人,稻秆再也认不出哪些谷粒是从它身上掉下。农家人只能在春来时,再一次次弯腰朝拜,恭请着新一年自己的日子。
责任编辑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