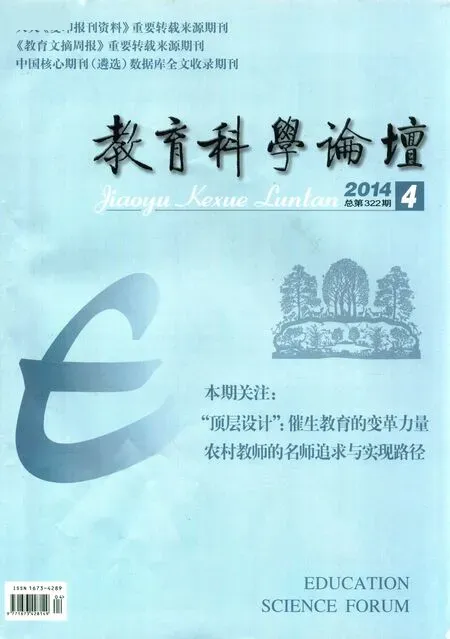关注语言,实现语文阅读教学的价值
●贾卉
《语文课程标准》对阅读和语言的关系给予了明确的表述:“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这两句话的阐述都用到了同一个词“运用”,阅读就是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阅读只有通过运用语言文字才能获得它的价值和生命。关注语言,是指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要有关注语言的意识,要善于挖掘文本中的语言因素,要积极引导学生感受文本中的语言之美,并能不断创造语言实践的机会,让学生在适宜的实践运用中习得语言。
一、用教学目标强化师生关注语言的意识
细心的老师会发现《教参》的目标一般“老”三条:朗读——字词——情感。朗读和字词的学习,是语文的基础性目标,有普适价值。但是除此之外呢?是不是就只有情感目标呢?我们随便来看两三课《教参》上的“教学目标”之第三条:《师恩难忘》要体会作者对老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装满昆虫的衣袋》从小养成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的志趣,《小草和大树》领悟在逆境中只有具备坚强的意志和聪明智慧的人才可能拥有精彩人生,如此等等。人物精神品质感受当然是要的,人文性当然也是要的!但是怎么要?是概念的获取,还是学习文本如何运用语言来表现人物精神品质呢?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会简单地将目标浅表为人物的精神品质,陷入人物精神分析的泥沼中。语文课,语言文字课,言义兼得的语言文字课。教学目标是一堂课,一个文本学习的航向,语言的意识只有转化落实在目标之中,关注语言才能很好地落地生根。
例如:《诚实和信任》一课的目标设计
甲老师:引导学生领悟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的道理。
乙老师:了解故事内容,明白诚实和信任是我们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
丙老师:学习按事情发展的顺序,用对话的形式阐述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的道理。
我想在三个不同目标的纵向比较中,我们都会有意识的选择丙老师所设定的目标。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目标指向了语言,有对谋篇布局的关注,也有对具体表达方式的关注,在语言的指向下通过阅读,理解故事内容,揣摩人物内心从而体会主人公的精神品质。工具性与人文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在执教《水上飞机》(科普童话)一文时,开始的教学目标制定为“让学生在朗读中理解、品味、感受水上飞机的神奇本领及其作用。激发学生从小爱科学,学科学,长大用科学为人类造福的志趣。”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课堂中师生津津乐道的是水上飞机的神奇本领和作用,个别词汇、语句的品味指向的不是语言运用的妙处,而是为了体会神奇,激发志趣。至于文本用什么形式,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这些内容的都没有涉及。这堂语文课科学满溢,人文过甚,唯独没有语言实践。在听课专家的指点下,第二次执教时我重新制定了目标:“学习用对话写出水上飞机种类及性能的表达方式,仿照文章第七自然段的言语形式读写结合:你还能设计出什么样的水上飞机呢?”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课堂上我借助对话朗读既让学生感受了语言的情趣,同时也感受着作者用对话的形式写水上飞机种类与性能的表达方式。在读写结合时,因为有言语形式可供模仿,学生的语言表达清晰干净,而这正是科普类文章的语言特色。对比前后两次的不同目标制定,第二次教学正是有了关注语言的教学目标,课堂上有了语言关注的意识,因此教学才显得丰满,言意兼得。
二、用文本形式觅得谋篇布局的途径
关注语言应注意对文本形式的把握,因为文本的形式影响着语言存在的方式。歌德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之,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从歌德的这句话中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研读文本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关注语言:内容、涵义、形式。内容和涵义我们总会有意识地去思考,尤其是涵义,在细读文本时我们会以批注的形式品评语言,但是文本的表达形式却常常被我们忽略。而所谓形式可以指谋篇布局的独到之处,比如文章的写作顺序,写作方法等,也可以指文本的语言风格。
比如《少年王冕》一课,我在第一次执教这一课时只关注了王冕孝顺母亲和学画两件事情中的语言品读,但是没有去探究文本的表达形式,缺少了一个整体架构的高度,因此就无法感受文本以时间为序,通过典型选材而达到的简练准确的语言描写的魅力所在。第二次执教该文时,我在重新细读文本中发现文章有这样几个表明时间的提示性语言:王冕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眼看三个年头过去了,王冕已经十岁了——不知不觉三四年过去了——到了十七八岁,王冕就离开了秦家。一旦找到这些暗示性句子,你会很轻易发现文章就是以时间为序用简练的语言浓缩了王冕生活的经历。因为这一发现我顺理成章地引导学生认识了文章在描写王冕十一年成长的时间跨度里是如何选取典型事件,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写的。对文本形式的关注让文章、让课堂因为这份理性关注而因此清晰,因为这份清晰让课堂对语言的品评有了支撑,有了意义,也有了高度,因此也让课堂能拥有了一份情智之乐。
因为有了这个意识,在执教《二泉映月》一课时,我敏锐地发现了它的文本表达顺序:又一年中秋之夜,小阿炳跟着师父来到泉边赏月。——十多年过去了,师父早已离开了人世,阿炳也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又是一个中秋夜,阿炳在邻家少年的搀扶下,来到了二泉。
发现了文本以时间为序,以听泉为由来组织材料后,你会很容易发现文章其实写的是一个艺术家时隔十多年的两次听泉那种完全不同的心情。而交待这种心情变化的起因放在了这两次听泉的中间,以一个看似简单的过渡既弥合了时间的跨度,更是写出了阿炳前后两次听泉所产生的不同心境的缘由:阿炳在这十多年间所经历的生活磨难。艺术源于生活,这样在利于学生理解两次听泉不同心情的同时,也顺理成章的渗透了这种大跨度时间内围绕主题选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通过对文本形式有意识的关注,学生可以很快习得如何在大跨度时间内来谋篇布局,来组织材料,来表现一个人。当然,以时间为序只是文本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够不断地来关注文本形式,我们就会为学生带来更加丰富的谋篇布局的途径。
三、用语言范式发现具体表达的精妙
我们在批改作文时常常为学生作文描写的泛化而大伤脑筋。反复思考,我想原因之一应该是我们在阅读教学中,一遇到这些具体描写的句段就在挖掘其思想内涵,而忽视了语言表达的本身,忽视了语文课程的本质性任务是学习运用语言文字,因此也就忽视了引导孩子结合语境体味语言具体描写的精妙。没有具体可感的语言范式引导,没有具体可感的语言范式背后的情趣体味,学生对具体描写可能也只是流于概念吧。我在教学中总会有意识的引导孩子们在品读中关注语言的范式,感受文本具体描写的动人。
比如《李时珍夜宿古寺》一文中关于对寺庙“破败”的具体描写:“李时珍轻轻推开门,只见里面到处是灰尘,断垣残壁上长满了青苔,中间的神像蒙上了厚厚的蜘蛛网。”真可谓不言破败,却何处不破败。于是我设计了这样的流程:(1)出示这段话,读一读,古寺给你什么感觉?(2)交流,主要说清你是通过哪些关键性词语读出这种感受的。(3)看看书中用了一个什么词语来概括这座古寺的?与自己概括的词语进行比较,品读“破败”。(4)根据提示读。形式一:这座破败的寺庙里(随机指名朗读有关句子)。形式二:,这就是破败。在这样看似随意的品读中学生首先领会到了“破败”一词概括的精妙:残破衰败,既有年久失修,残缺不完整之意,作为寺庙也有香火凋零衰败之意。很微妙,汉字的不可言传之意都在其中。其次学生在我的提示引读中深深体会到了文本是如何具体写出寺庙“破败”的。在感受汉字文化的同时也习得了具体描写的一种语言范式。
再如《石榴》一文的第四自然段:“这时,你摘下一个石榴,剥开外皮,只见玛瑙般的子儿一颗颗紧偎在一起,红白相间,晶莹透亮。取几粒放入口中嚼嚼,酸溜溜、甜津津的,顿时感到清爽无比。”从剥开石榴到吃到嘴里,很多时候学生就一句话“好吃极了”写完了所有的感受,既没有细致的观察,也没有细腻的味觉体验。在教学中,我利用文本的这一语言范式引导学生去观察,去体会。基于此我有了如下的设计:(1)轻声读读,小作者看到了什么?品出了什么滋味?(读后交流)(2)小作者看得非常清楚,品得也很真切,这是他的感受呀。现在老师发给每个小组一个桔子,大家可以看一看、摸一摸、尝一尝,然后用下面的句式说一说(出示句式):桔子圆圆的,像,它的外皮有的是,有的是,剥开外皮,只见般的瓣儿。取几瓣放入口中,、的,顿时感到。(读后交流)(3)小结:从外形到剥开外皮后样子的观察、描写再到用心品尝,细腻捕捉自己的感受,你就能写出和他一样具体漂亮的文字。吃过柚子吗?你来写一写,试试看吧(学生练写、交流)。
这个利用语言范式进行的读写训练中我从看到什么,品出什么开始交流,唤醒孩子自己生活中看石榴,吃石榴的经历,充分调动起了孩子的兴趣,让他们自觉将每一个感官都兴奋地参与进来。此时,再不失时机地拿出孩子们都比较熟悉的桔子,带着孩子一起看看、尝尝、然后利用文本语言的范式,仿照课文的样子说说,水到渠成,孩子们轻轻松松在仿写中习得了写法,积累了语言。并随即创造了另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实践机会:写一写柚子。如此,习得语言,运用语言得到了有机的融合,真正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语言。
四、用特别语言唤醒孩子的言语智慧
一个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有着高度的语言敏感性的老师。王崧舟老师说:“敏感就是见微知著,就是洞察一切,就是窥斑见豹,就是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唯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作者隐藏在其中的特别的语言之美。而所谓特别的语言在这里主要是指打破常规的语言表达,比如语序的颠倒,打破常规的修辞或字词的活用等。教学中,汉字的魅力我们既要在平实的叙述中去引导学生感受,也可以通过这些特别的语言表达来引领学生享受,领略汉字的博大精深。品读文本中特别的语言,它特别的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无声的,却充满情感的表达。它一经点拨,就能强烈地撞击着我们语言的神经,触发着内心丰富的体验。
比如王崧舟老师执教《慈母情深》的其中一段:“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为了引导学生发现这一特别语言的表达魅力,他先是引导学生发现片段中“我的母亲”连续三次的语序颠倒,接着通过与正常语序的对比感受这一特别的表达形式所包孕的情感,然后通过慢镜头的回放式引读,来引导学生描述记忆中母亲的背、脸和眼睛的神采,再次通过今昔对比等各种形式让母亲现在的影像无比震撼地在孩子们的头脑中清晰起来,并以此来引导学生感受这一特别表达所蕴含着的作者的震惊和心中瞬间集聚的饱满的母爱。特别的语言形式让这种丰盈的、无私的母爱在无声中直达学生的心灵,在这特别的表达中学生咀嚼出了母爱的味道,语言的味道。我想这样的语言点挖掘只有教师具有强烈的语言意识,对语言高度敏感,才能捕捉到这种独特的写法。
特别的语言在行文中常起到“言已尽意无穷”的独特效果,让我们在阅读之余,在品评之余回味无穷。《月光启蒙》这篇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黄河留给家乡的古道不长五谷,却长歌谣。”我想到学生也许并不能领会这里用词的妙处,而仅仅是觉得奇怪:五谷可长,歌谣如何能长呢?细细去解读,于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五谷长,是生长的本义,是五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幼苗到成熟的过程,由一粒粒种子带来丰盛收获的过程。长歌谣,借用这个意思,歌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不断增多。那它是怎么多起来的?是一代代人的创造,是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特别的用法将黄河两岸歌谣的盛行一下子就描摹了出来。在此基础上,我还启发学生去链接生活,去想想生活中还有哪些这样有趣的用法。学生说出了:“我楼下的哥哥不长个子尽长脑子了。”“妹妹打碎了我心爱的金鱼缸,也打碎了我的心。”如此等等。
关注语言,从目标开始,让形式助力,用范式引领,在特别处揣摩。只有真正走进文本,用心玩味,语言在运用中才能成为我们的一种能力;只有真正关注语言,阅读教学才能彰显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