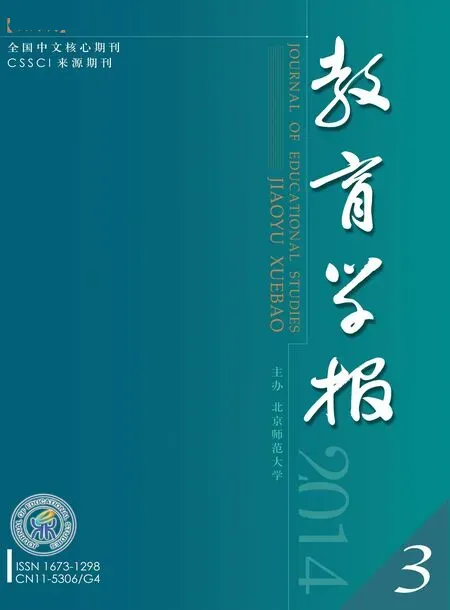教育中的兴趣概念
丁道勇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北京 100875)
兴趣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被注意到了。20世纪早期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们已经普遍认为,兴趣对于学习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是在2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在行为主义及程序教学流行开来以后,兴趣在教育界的重要性才被贬低下去。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再次发现了情绪和情感在教育上的重要性。于是,兴趣再度被认为是影响学习和学业成绩的重要变量。[1]*在心理学上,兴趣往往与好奇心、内部动机等概念一道讨论。但是本文并不涉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相关文献。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Silvia, P. J. (2006). Exploring the psychology of interest.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8]许多研究发现表明,兴趣对于注意过程、注意质量以及学习者的任务组织、目标选择等方面有积极影响。
那么,如何理解对于学习及教育过程如此重要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兴趣”怎样在学习活动中起到助推的作用?教育界对“兴趣”有不同的定义,相应的“兴趣”作用机制也是迥异的。因此,反省“兴趣”概念,在帮助我们明晰兴趣的作用方式的同时,还有助于更新我们对学习活动的认识。本文的概念辩证表明,一些常见的关于兴趣的认识,是肤浅甚至错误的。依据这些的兴趣定义,不但未必能改进学习效果,甚至会让一些对学习过程至关重要的方面,溢出我们的视野,从而忽略学习活动中一些真正值得关注的方面。从这些角度来说,做概念辩证,找到一种更有解释力的兴趣概念是有必要的。
一、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
一种关于兴趣的定义认为,兴趣是某些事物的属性。从该属性的角度来区分,行动的对象当中有的是有趣的,有的就是无趣的或者少趣味的。那些有趣的事物,往往是新异的、稀少的、珍贵的;那些无趣味或者少趣味的事物,则是一般的、常见的、低劣的。不难发现,在做这种描述的时候,这种兴趣概念并未参考学习者的特性。有趣的总是有趣的,无趣的总是无趣的,与学习者是谁没有干系。既然兴趣只是事物的属性,那么兴趣本身将被认为是孤立的、固定的。所谓的“孤立”,是指与行动者无关;所谓“固定”,是指不随情境的转易而变化。在应用这种兴趣概念时,这两种属性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并且,基于一种定义本身的同义反复,人们很容易相信这样的判断:有趣的事物容易唤醒人们的注意,而无趣味或者欠缺趣味的事物则让人感到无聊。根据这一“兴趣”定义,教育中的学习内容也被区分为两类:教育的内容不见得都是有趣的,有一些对儿童来说有趣味,另一些则不是这样。学习有趣味的事物,往往伴随着舒适或者愉悦的体验;学习欠缺趣味的事物,往往伴随着无聊甚至痛苦的体验。有趣味的事物,容易获得学习者的关注,无聊的学习内容则相反。这种“兴趣”定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兴趣的作用机制。
基于这种定义和描述,教师在实务工作上该如何选择就十分明确了。教师得要选择有趣味的学习内容,或者设法让无趣味的内容变得不那么无聊。这种“选择”和“润饰”的观念,在教育实际中十分盛行,但是在理论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意见认为,“短期的唤起兴趣,同在更为广博的意义上长期地建立兴趣不同。[2]”随着短期兴趣的结束,相继的往往是更严重的冷漠。通过种种补救的办法,让本来无趣的内容,变得容易接受。用种种取悦儿童的技巧,让儿童忍受甚至乐意完成原本可能放弃的活动。这种“加入甜味剂”式的“糖衣”策略,败坏了学习的本质,使得兴趣概念在教育上获得了种种恶名。
另外一种选择,也是基于上述兴趣定义和对教育事实的描述。这种选择与关于“努力”的理论相关,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虽然学习有趣味的事物较为愉悦,但并不是每项学习内容都有趣味。习于有趣味的事物,会让人对无趣味的事物产生更强烈的抵触。并且,在更广大的现实生活中,也不是时时刻刻充满着娱乐。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充满了各种无奈,生活本身不是一场游戏或者享乐。因此,让学习者及早适应种种无奈甚至痛苦,让意志得到训练,也应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努力”在这种教育选择当中有重要位置。总是让学习者处在精致化的、遴选过的、有趣的人工环境中,会让学习者丧失努力。趣味本身会败坏学习者努力向学的品性。因此,根据这种观点,兴趣在学习过程中应当禁绝。反而是那些沉闷、无聊的训练本身,最适于塑造努力学习的品格。
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教育选择,都已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实际上,无论是教育上的苦学传统,还是乐学传统,都可以在杜威那里找到对应的批评意见。[3]*对“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的批评,可参考《民主主义与教育》第10章《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9]。另外,杜威在来华讲学时,对于第一种兴趣定义的教育应用,即所谓的“‘软的’教学法”和“‘施粥所’的教育理论”[4]134有这样的批评:“做教师者若是误解兴趣为娱乐,在教授时极力使学生直接得着快乐,如用音乐、游戏、宴会等,以引起儿童之注意。但是结果不过供给他们片时的娱乐,不能达到较高远的目的。[10]142”这些批评与赫尔巴特的评论,颇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反对肤浅的兴趣。在赫尔巴特那里,肤浅的兴趣是一种“分心”,“所以我们必须防止草率的逗留,想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有所作为。[11]61”赫尔巴特关于教学阶段的整个设计,甚至都是以兴趣的发展为目标的。在现在的舆论环境中,几乎没有谁公开地承认自己认可其中某一项。但是,这些教育传统所基于的兴趣概念并不总是能得到反省,反而是不断获得新人的投诚。此种兴趣概念与彼种教育处置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总是十分清晰。实际上,认为兴趣是事物的孤立、固定属性的看法与日常生活中的见闻十分一致。似乎,有一些事物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而另一些事物总是让人厌弃。因此,要抗衡这种兴趣定义和相应的教育处置,还需要找到更有解释力的兴趣概念才行。
二、作为目的的兴趣
在杜威看来,将兴趣定义为事物的一种属性,最重要的错误是将事物与心灵割裂开来。他提出的兴趣理论的重点,就是重新将这两个方面建立联系。在杜威那里,心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正是通过活动的目的来实现的:“把学习的对象和课题与推动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联系起来,乃是教育上真正的兴趣理论的最重要的定论。[4]”根据杜威的兴趣定义,外部环境是否有趣味,要看这个环境与个人目的的关系如何。这样,环境中各个事物是否有趣味,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因人、因境而异。另外,这些事物的趣味程度,与行动者的目的密切联络,不再是孤立的。杜威曾经比较过“旁观者”和“参与者”。其中,是否带有相关的目的,是两类人群的关键区别。正因为“有关”、“无关”的不同判断,让旁观者与参与者对于外界事物的关注出现明显不同。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外界的天气变化在不同人那里,就有“有趣”或者“无趣”的分歧。杜威意义上的兴趣的有无,在这个例子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
旁观者对正在进行的事情漠不关心;一种结果和另一种结果分不出好坏,因为每一种结果只是供人看的。代理人或参与者和正在进行的事情休戚与共,事情的结果和他息息相关。他的命运或多或少和事件的结果攸关。因此,他就要尽其所能,影响这件事情的取向。旁观者就像一个身在监狱,注视着窗外下雨的囚徒,对他来说,窗外下不下雨都是一样。参与者就像一个计划着第二天要去郊游的人,下雨不停会挫败他的郊游。[4]132
参与者在判断外界事物的过程中,始终参考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对于未来的结果有着某种关心或渴望,并且愿意参考外界事物调整自己的目的,避免较坏的结果。这时候,行动者的心灵不是孤立的内部世界,外界环境中的事物是否有趣味也不再是这些事物本身的属性。一个事物是否符合人们的趣味,要看这个事物是否处在一个目的性的活动当中。譬如,那些与当下目的没有关联的事物,就处在个人的兴趣范围之外。此时,个人对这些外界事物漠不关心,好像囚徒对于天气的态度一样。
将兴趣定义为一种目的,这个定义要求相应的教育上的选择。基于这种兴趣定义,学习者发生兴趣的事物,总是在他们的目的性活动当中。与学习者的目的无关的事物,则被定义为“不感兴趣”。这一处理与日常生活所见也颇为匹配。一个最不爱听课的孩子,也会醉心于自己中意的小玩意。对他来说,老师的课是无趣的,课桌底下进行的事,才是趣味盎然的。根据杜威的兴趣定义,教师的任务不是用动画、色调、声音等等与所学内容无关的特征去引诱儿童(例如“乐学”传统),也不是刻意地排除学习过程中的乐趣(例如“苦学”传统),而是提供兴趣发生的条件。更明确地说,这些条件就是能够迎合“儿童的急切需求和能力”的那些。教师如果能够发现儿童的这些需求和能力,并为他们提供各种资源、对儿童的活动进行充分指导,那么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学习就总是有趣的。经过此种目的化的学习内容,在学习者看来都是有趣味的。[3]更进一步来说,因为个人的心灵总有满足自身目的的趋势。所以,在满足自身目的的过程中,总会有发生兴趣的事物。教师的任务,只是如何让将要学习的内容与学习者的兴趣中心相互匹配。更确切地说,在这个理论中,“需求”在前,“学习”在后。“教师的作用莫如是提供材料和条件,通过它们儿童的生物性的好奇心被导向有目的、可以增加知识的研究上。[5]”这样的设计,与上述第一种“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概念的设计,有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教师主要的工作被认为是研究儿童,而不是研究教学素材。
在将兴趣目的化的这个理论中,仍然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容易成为各种冲突观念的宿主。当学生追问“为什么做这个而不做那个”的问题时,实际上往往是在质疑“谁的兴趣得到了关照”。杜威的兴趣概念,正确地意识到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兴趣。但是在师生共同生活的范围内,到底学生的兴趣是什么?这个难题还是留待教师去解答。根据教育田野的实际所见来看,这就是把迈出去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一个关心儿童兴趣的教师,未必按照儿童实际想要的、他们感兴趣的或者心理学意义上的儿童的爱好来做。[6]”一个最粗暴的、无视儿童需求的教师,也可能认为坚持己见恰恰是在保护儿童的成长。把界定儿童需求这项工作交付给教师,让杜威的“兴趣”概念,在教育上埋藏了祸根。教师可能在一句“我是为你好”的名义下,做出各种与杜威的“兴趣”概念背道而驰的事情来。
三、兴趣状态是紧张而非愉悦
对自己的运动能力尚缺乏控制的婴儿,会有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当他发现自己感到趣味的事物时,会欢叫着用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向成人发出指示。接着,当他想要的东西真地在其掌控下之后,小宝宝又可能因为自己无法自如地操纵而发脾气、哭泣。婴儿的这些表现,告诉我们关于兴趣的一项事实,表现了处在兴趣状态时人们的心理感受:小宝宝想要某物时,感受到的不是愉悦,而是紧张。他通过发脾气、哭泣来表达这种需要,也表达了这种心理体验。在获得想要的物品而感到满足时,他已经不再处于一种兴趣状态了。换句话说,感到满足之时,就是兴趣消失之刻。
阿诺德(Felix Arnold)的兴趣理论[7],可以对这种日常观察进行理论化。他认为兴趣是针对某种情境的态度,包含动力和认知两个方面。其中,兴趣的动力方面是指,兴趣总是朝向某些事物的努力、意向、欲求或趋势。兴趣的认知方面,是指对将来有待实现的时刻的模糊认识。这种模糊的认识可以在兴趣的动力作用下逐步发生变化,逐步清晰、丰满起来。在兴趣发生时,个人感受到了某种冲动;个人认为在自己的欲求和某些外部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还没完成。这种未完成的状态带来的紧张、压力或者要求进一步控制的趋势,描述了兴趣状态下的个人感受。总的来说,这种兴趣定义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兴趣不是指向当下的,而总是指向未来。其二、兴趣的标志不是愉悦、放松、满足或宁静的感受,而是某种紧张、冲动、意向等。与兴趣相伴随的是紧张而不是愉悦。兴趣也因此可以定义为一种指向未来的紧张状态。
一个人品尝水果的滋味,或者享受花朵的芬芳,或者鉴赏画作、雕塑的美感而感到愉悦。这种愉悦是当下的。这个人会停滞不前,只为吸收这种愉悦。但是,如果这种满足或者愉悦没有出现,只有通过对注意中心的某些情境的控制才能得到,那么这个情境中的兴趣就会存在,并激发动力的态度和倾向。这些倾向将被感知为兴趣,并指导进一步的控制。[7]
愉悦不是指向未来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当下的情感。只有当这种愉悦的体验还未实现的时候,它才能指导行动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愉悦还不是现实的,个人感受到的还是紧张。这种紧张指向了未来的愉悦。更直接地说,感受到愉悦,恰恰表明了兴趣的消失。这个理论,很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判断:兴趣不等同于娱乐;兴趣甚至总是和紧张、焦灼乃至痛苦等体验联系在一起。兴趣的动力方面的这些特征,使其能够推动个人认知的发展。这个道理很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作为兴趣的对象,会更持久地保持在注意力的中心,因此也会得到更充分的认识。
在教育上,无论是“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还是“作为目的的兴趣”,都没有正面回答兴趣到底意味着紧张还是满足。这两种关于兴趣的概念,几乎都不假质疑地认为,兴趣一定有助于学习。兴趣可以让学习变得更加愉悦、更加自然或者更有目的性。将兴趣与紧张建立联系,这就取消了个人对于兴趣的天然爱好。兴趣并不总是人们乐意发生的。换句话说,当发生兴趣的时候,个人的心理感受并不愉悦。因此,利用兴趣来改善师生关系,利用兴趣让学习过程变得轻松愉快,这样的愿望在阿诺德的理论中,就都是难以实现的了。更甚者,根据这个理论,愉悦、满足本身就是完成了的情感,本身并不是积极推动、指向未来的,而是鼓励行动者停留在当下去享用,因此并不值得教育者追求。兴趣虽然可能以愉悦和满足为终点,但是到达这个终点恰恰意味着兴趣的终结。因此,在教育中应用兴趣,恰恰不应以学生的愉悦、满足、放松或宁静等状态为标志。拿教育田野所见来说,一节充满欢歌笑语的课未必是好课,一节让学生皱着眉头结束的课反而更可能是。
根据阿诺德的理论,兴趣在儿童身上的表现,和在其他年龄段、其他领域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差异。尽管在那些年龄段、那些领域,兴趣发生时的紧张情绪可能不会以“孩子气”的形式来表现,而是表现为调用更多的注意力、体力等资源来实现目标,在认知方面也表现得更加专注。但是,人们在兴趣状态下感受到的主要是紧张,这一点是与婴儿在兴趣状态时的感受相一致的。我们在收藏爱好者身上可以看到紧张、满足种种情绪体验的变化历程。回到前面的例子,在小宝宝对某些事物感到兴趣时,同时伴随着一种紧张、焦灼的情绪。当他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咯咯笑起来的时候,兴趣也就终结了。此时,他已经得到了满足。紧接着,他希望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来操作物体。但是,年幼的他并不总能如愿。于是,在拿到东西以后不久,就因为无法自如地操纵物体而尖叫、哭泣起来了。这时候,一些指向未来的张力,再次出现了。这标志着新的兴趣的发生。对于小宝宝来说,兴趣成为推动其接触事物、探索事物的动力。也可以换句话说,兴趣是推动他学习的动力。相反,把任何他想要的事物很快提供给他,只是让他感到满足、感到惬意,并不会推动他学到什么。这种满足,对于学习的助力是很有限的。这是阿诺德的兴趣定义对于兴趣作用方式的独特解释。这也将是在教育上应用兴趣原理的新的基础。
四、阿诺德与杜威的兴趣概念的比较
在介绍杜威的兴趣概念时,笔者曾经引述过一段话,对“旁观者”和“参与者”进行了对比。在那段引文中,杜威所说的“参与”可以换算成“感兴趣”的意思,“不参与”或“旁观”就是“不感兴趣”。杜威在应用“参与者”这个概念时,强调外部条件与个人目标的联系。发生了联系,就是“参与”;不发生联系,就是“不参与”。有联系的时候,行动者是一个“参与者”,会高度关切外界条件;没有联系的时候,行动者是一个“旁观者”,对外界条件表示冷漠。应该说,行动者的目的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这一点是杜威的兴趣概念与阿诺德的兴趣概念的共同点。但是,这两个兴趣定义之间,还是存在很多深刻的歧异。(鉴于“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定义在杜威那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批评。这里只对“作为目的的兴趣”和“作为紧张状态的兴趣”这两个兴趣定义作比较。)实际上,正是这些关键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学习的独特解释,进而在原则上要求教育实务工作者做出调整。
差异一:成员身份还是学徒身份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学习一种新技能的一开始,个人还不能很好地完成它,更不用说十分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活动了。此时的学习者,还不能十分确定地知道何种外部条件,最能够帮助自己完成预期的目的。表现为,新手的注意力总是分散和低效率的;只有专家才能够迅速筛选外部对象,将这些外部对象目的化。但是,此时的专家已经不再是一名学习者了,他早已经成为一名拥有完全资格的成员。在杜威的“兴趣”概念中,学习者本身就是这类专家级别的合格成员。杜威假设这些学习者已经能够明确地知晓外部环境中的那些事物,知道什么与自己的目的相关、什么与自己的目的无关。笔者相信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许多学生在求学期间,并不特别清楚自己从事的活动与长远生活目标之间的联系。因此,作为学生就特别需要导师的干预:是导师代表我们遴选学习内容,帮助我们确定什么值得学、什么不值得学;是导师为我们规划了向目标进发的路径,也可以称之为“课程”。
杜威兴趣定义的这一缺憾,在阿诺德那里得到了纠正。按照阿诺德的兴趣定义,成为合格成员的学习者,其兴趣已经完结了,学习活动也完成了。恰恰是在作为学徒的时候,学习者会格外渴望得到认可,渴望成为正式成员。但是,这时候的他们,还只会笨拙的模仿或者正处在反复的试错当中无法自拔。因此,从兴趣定义的角度来理解学习过程,则学习者还只有一种类似学徒的身份,还不能像一名合格成员那样,对“目的——手段”做出清晰、准确的判断。但正是这一点,确保她拥有旺盛的学习兴趣。
差异二:个人选择还是实践传统
在杜威的兴趣概念中,学习内容的选择要与学习者的需要联系起来。教师的重要工作,就是发掘这些需要,并为满足它们提供条件。杜威的兴趣定义,确保了教师提供的这一类支持条件,总是会自然而然地让学生发生兴趣(定义本身的同义反复)。问题是,杜威尽管也强调对学生兴趣的引导,但是并没有明言标准的问题。如何规避外界强加给学生的目的?这仍是杜威兴趣概念无法解答的实务难题。学生的什么需要是正当的?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产生什么样的需要?这样的问题,在杜威那里都没有明确的回答。
实际上,杜威理论对于个人选择的看重,早已经受人诟病。毕竟,我们都是生活在传统之中。个人的反省,在大多数时间、大多数场合都是罕见的、高成本的事情。*对杜威的反省思维的讨论,参见丁道勇:《我们怎样思维:信念结构理论及其应用》,载《全球教育展望》,2013年第1期。在其中,“反省思维”被认为是对“我们怎样思维”的一种规范性的回答,其缺陷是未照顾个体的实际心理需求。反省思维理论偏爱的是科学思维,只刻画了人类认识的一面。该文在一系列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用信念结构理论替代反省思维,作为对“我们怎样思维”这个问题的回答,进一步讨论了杜威所鄙弃的各类有缺陷思维的价值。那么,按照阿诺德的兴趣概念,个人会在什么时候对事物发生兴趣、渴望掌握它?一定是在学习者还未充分掌握的阶段。或者用刚刚使用过的概念来说,是在学习者尚且作为“学徒”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将要学习的东西,认识不清、了解不明,但有一种模模糊糊、莫名所以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学习者愿意忍受漫漫学徒期的煎熬。吸引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阿诺德本身没有明言。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兴趣定义中的学习对象是先于个人的存在,是一种卓越的、有吸引力的东西。用一般政治学概念来说,可以用“实践传统”来概括。例如,一名立志从教的学生该学什么?答案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他一定要寻求教师群体中的卓越者所代表的实践传统。正是这些传统本身,让新一代的教师心生向往,并立志成为其中一员。在这个例子当中,该学什么既不是学习者个人的选择,也不是教师教育者能干预和摆布的。
差异三:目的化的环境与目标群体
在杜威那里,“环境”是经过重新定义的诸多概念之一。理想的“环境”强调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信息沟通。这样的“环境”,能让行动者获得更充分的信息基础、远离偏见,因此具备教育性。在杜威的兴趣概念中,兴趣的对象是原子式的。各种外部条件,以一种各个林立的方式,接受个人的甄选、判断。我们很难相信,这种“原子”状态下的外部对象构成的环境,一旦与个人目的发生了联系(在杜威看来,就是个人感到有趣),就具备了教育性。这时候的外部条件,尽管在个人看来是清晰的、明确的,但同时也失去了因为距离和陌生带来的诱惑。更重要的是,在没有目标群体作为参照物的时候,对于外界条件的理解是纯粹个人的。缺乏意义架构,诸如崇高、庄严等价值在个人身上都难以实现,所剩下的不过实用罢了。
用阿诺德的概念来说,“目的化的环境”概念,混淆了“享用”和“期盼”两种状态。环境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事物,虽然与行动者的目的相关,但并没有指向未来的动力特征。相反的,它们往往在牵绊着我们,让我们裹足不前,停留在当下。因此,这些事物尽管与我们的目的相关,但是并不会对我们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按照这个观点来说,譬如,“红袖添香”就不是一种很好的学习状态。学习过程本身的愉悦、温馨,让人流连。真正高效的学习状态是“废寝忘食”。一个“废”和一个“忘”,描述了学习者对于加快学习进程的迫切愿望。这种状态本身不是温柔陷阱。总之一句话,环境中的那些目的对象,并不总是有教育性的,并不总是能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我们大多数时候不是作为学习者,而是作为各类群体的合格成员。只是在我们作为学徒的时候,我们开始处于一种学习渴望当中。这时候的环境要素,标志了我们要进入的目标群体,尽管不能享用,但是富有教育性。这段讨论实际上是要把杜威的“环境”概念进行细分。总之,外界事物与个人目的相关,还不能确保个人对其发生兴趣。
五、结论:更新兴趣概念以后的学习观
基于上述比较,更新后的兴趣定义描述了学习活动发生时,个人的一系列状态:受到目标群体中卓越标准与实践传统的感召,从学徒身份转变到成员身份的过程中,个人感受到的某种紧张体验,即兴趣。这个兴趣概念在教育上的应用是:行动者在发生兴趣时,各外部事物之间并没有有趣、无趣的质性区分,也不再是个人目的性活动的操纵对象,而是转变为个人渴望进入的目标群体的表征。对于学习者来说,这个群体充满了魅力和感召力。在学习成为其成员的过程中,学习者学会与那个将要进入的目标群体成员之间,分享某些共同的东西,也就是该群体中的特定实践传统。举例来说,同一所学校的师生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之中。一名转校生,经历最初的陌生、排斥,到最终的熟悉、融合。在这个融入新团体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兴趣。兴趣推动着这名转校生,关注该校的各项传统。但是,兴趣的维持,是以学徒身份作为条件的。一旦他被接纳为成员之一,兴趣也就终结了。我们可以想象,曾经的转校生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他很快就会与大多数本地的学生一样,每天上学、放学,有自己的朋友,有与自己的朋友类似的爱好和苦恼,不再思考自己与这间学校的关系问题,不再对校内传统给予特殊关注。兴趣所能起到的动力作用,也就是推动学习者学习的使命,至此宣告结束。
我们已经看到,在更新了兴趣概念以后,关于学习活动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更新。譬如,个人选择开始让位于历史传统。正是目标群体所代表的卓越标准,启动了学习的过程。这个判断赋予教师工作以合法性。教师作为成人社会的代表,意思是说教师应当是各种卓越传统在学校内的代理人。又譬如,挖掘目标群体的魅力,看来要比满足学生的需求更重要。在教育田野中,我们有时会见到痴迷于自己工作的教师。这类教师往往会教出痴迷学问的学生来。这就是因为,这些教师有意无意地更充分地挖掘了自己所教的内容,是自己学科的更合格的代理人。最后,在学习活动过程中,学生还只有学徒身份。换句话说,即使是在最理想的兴趣状态下,学生对于所要学习的东西,也只有模糊、片面的认识。因此,教师更有责任给予他们更适当的课程。尽量准确地呈现所要学习的目标群体的传统和魅力。这应是针对教师的一项最重要的教学伦理标准。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本文对“教育中的兴趣概念”的辩证,以及相应的学习观方面的认识更新,都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实务工作要求:如果说,“作为事物属性的兴趣”及其学习观,要求教师研究学习的素材;杜威的“作为目的的兴趣”及其学习观,要求教师研究学生;那么,在更新的兴趣概念及其学习观的指导下,教师应该开展对“课程”的研究。这里的“课程”,是从课程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代表了人成长的“目标”和“路径”。一位只关注教学法的教师,未必能理解自己执教的课程的魅力所在。表现为,他可能并不清楚,自己所教的学科为什么值得他人学习?这个学科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人心生景慕甚至激动不已?研究“课程”,把课程作为自己的工作对象,用课程自身的魅力吸引学生。这是更新后的兴趣定义,给教师的原则性建议。笔者的几项研究工作也表明,即使是小学课程,也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Hidi, S. Interest: A unique motivational variable [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06(1): 69-82.
[2] 布鲁纳. 教育过程[M].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50.
[3] Dewey, J. Interest and effort in education[M]. Cambridge, MA: Riverside, 1913:95-96.
[4]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143.
[5] Dewey, J. How we think: A restatement of the relation of reflective thinking to the educative process[M]. 2nded. Boston, MA: Heath, 1933:40.
[6] Peters, R. S. Ethics and education[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6:168.
[7] Arnold, F. Attention and interest: A study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M]. New York, NY: Macmillan, 1910:186.
[8] Silvia, P. J. Exploring the psychology of interest[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杜威. 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G] 任钟印,译. // 杜威.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167-213.
[10] 杜威. 平民主义与教育[M]. 常道直,编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2:142.
[11] 赫尔巴特. 普通教育学 教育学讲授纲要[M]. 李其龙,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