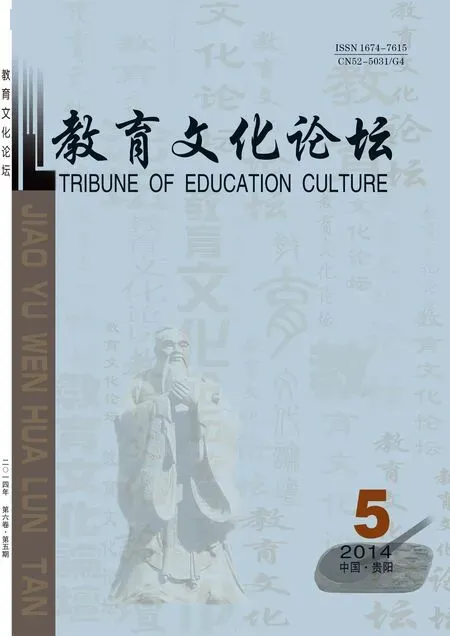沙滩黎氏与地域文化
黎 洌
(1.遵义师范学院 学科办,贵州 遵义 563002;2.遵义师范学院 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2)
“沙滩文化主体是黎氏家族,……黎氏家族沾溉及于郑氏、莫氏两家以及邻里戚友。郑珍和莫友芝接受黎氏家学且有所拓展,郑莫二氏之学也是沙滩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1]黄万机《沙滩文化志》对黎氏与沙滩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作了高度评价。任何一个文化现象都是在时间和空间交错中呈现出它的特征,沙滩文化同样,作为一种具有很强地域特色的家族文化,它与特定的时空密不可分。
一、沙滩文化形成前的地域文化时空特征
在汉文化圈,贵州可谓开发较晚,至明代始成为十三行省之一,朝廷控制范围,多集中在由卫、所构成的交通沿线,甚至连布政使司也与土司宣慰府同城而设。少数民族环伺的社会环境和崇山峻岭的自然环境,使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传播较为迟缓,正如莫友芝在《黔诗纪略》卷一按语所言:“黔自元上而五季皆土官世有,至汉唐郡县,几不可寻。莫流鲜闻,安问风雅。”[2]
沙滩文化的发源地,今属黔北,清雍正前属四川,亦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但开发较早,秦定黔中郡,改鄨国为鄨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设犍为郡和牂柯郡,犍为郡的郡治即在鄨,但实施 “郡国并存”政策,即流官与土官并治。同时开辟五尺道,徙豪民屯田,汉文化进入,今天,在务川、仁怀等地发现的汉墓中,就有大量的汉文化元素的遗物出土。但两晋时期,中原纷乱,黔中沦入大姓之手,汉民夷化,据《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记载,汉文化已廖如晨星。虽今黔北地区多为经制州,但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中,所见皆为“开山峒、招豪长”所置。这一时期的播州文化,受地理环境、民族习俗、历史传统等因素影响,决定了夷僚混杂、尚鬼信巫等特点。杨氏统领播州后,沙滩由于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而被杨氏土司看中,“沙滩者,宣慰使杨应龙官庄也。”
南宋时,播州杨氏开始仰慕汉文化,从杨轸到杨文数代,大力招贤纳士,设置官学,建孔子庙,以取播士请于朝,而每岁贡三人,在短短数十年间,“土俗为之一变”。出现“破荒冉家”,产生了八位进士,涌现了冉琎、冉璞等军事人才,并产生了杨汉英这一学养深厚、精通汉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仅创作了诗文集《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还撰写了哲学著作《明哲要览》九十卷。但此时汉文化的流播主要局限于上层,是以“官学”身份出现,土官“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而下层民众参与学习的机会则非常之少。为此,汉文化对播州文化整体结构影响不大。
明代,贵州的改土归流引起杨代土司的警惕,兼之长期的内部纷争,封闭保守成为播州的主流。直至万历二十八年平播之役的结束,将播州分置遵义和平越二府,结束了长达725年的土官统治。随着府、县等行政建制的设立,大批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流官进入黔北地区,开始了他们以汉化夷的文化管理,开设学馆,充任塾师,执教授徒,兴办书院,将杨氏土司点燃的汉学星星之火,推向燎原之势。天启元年,黄平、湄潭的生员要求开科入试,表现出当地生员在汉文化教养下的濡化进程。同时,大量汉移民的进入,对播州文化及民风民俗的改变有极大的促动。随着汉文化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确立,“椎结之服,劲悍之性,靡然变易矣”,少数民族强劲野性的文化被温文尔雅的柔性的汉文化所取代,而过去的“土司之民”也转而为“朝廷之民”,人们社会文化的认知随之改变。到雍正五年,将遵义划入贵州,成为黔之北。
明末的战乱,遵义相对安稳的环境,使大批文士趋之若骛,南明永历王朝移驻贵州,更使部分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进入贵州。明亡后,由于“滇黔犹保冠带之俗,”大批明遗民滞留或迁移贵州,一时间,黔北乡间文人雅士云集,或隐居明志,或遁入空门,“避于浮屠,以贞厥志。”最具代表的是钱邦芑和陈启相。钱邦芑,号大错,明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南明永历中,以御史巡按四川。永历六年(1652),受任抚黔。翌年,张献忠起义军余部孙可望率众进入贵州,他隐退于余庆蒲村。以后便削发为僧,潜心诗文,以授徒为业,从学者甚众。陈启相,四川富顺县人,官河南道御史,明末因甲申之变弃官来遵义,隐于平水里掌台山寺为僧,号大友,设书院讲学著书,谈亮、罗兆甡等名士皆出其门下。“遵义人才之开,掌山功最钜。”黎氏家族的黎怀智,明未任黄冈知县。明亡后薙发为僧,号策眉,“与明遗老大友、大错辈讲味禅悦,藉以韬光。”[2]遵义明末清初由流亡文人形成的人文汇萃的历史语境,为汉文化在沙滩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态,也为沙滩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二、黎氏家族与沙滩
据《遵义沙滩黎氏家谱》,黎氏原 “家广安军渠江之金山里。”后因兄弟争田水,黎朝帮“令怀仁祖择邻,初徙贵州之龙里,”“厥后二十九年而播州杨氏平,地入遵义、平越两府,分属川贵。更徙卜遵义治东八十里乐安水上之沙滩居焉。”“始吾祖自蜀迁黔之龙里,己着籍为黔人,居十九年而徙遵义,还入于蜀。”“越百有二十六载,而当我朝雍正五年,世宗皇帝丁未之岁割遵义隶贵州,故又复为黔人也。”[3]
家谱记述了黎氏家族迁入贵州的历程,还附记了唐、宋时黎氏先祖的宦游情况,说明其家族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如果说家谱中关于先祖的记载有许多不确定因素,那么,对入黔始祖的记载则是清晰无疑的。始祖“朝邦,明廩膳生,兼力農。”与明初大规模移民不同,黎氏不是作为军屯或民屯进入贵州,而是主动离开熟悉而又令人伤心的兄弟相争的环境,选择陌生的他乡重起炉灶,入籍贵州。龙里是在“洪武二十三年四月置龙里卫于龙里长官司”,康熙十一年(1672)始改县,黎氏入迁时,周边是平伐、把平长官司等少数民族政权[4]。作为一个读书人,黎氏入黔始祖朝邦进入贵州前,已有功名在身,汉文化的教养使他渴望回归于主流文化之中。因此,十多年后播州平定,改土归流,黎氏家族选择迁回蜀地,固然有战争使少数民族人口十去其九,留下大量无主土地,更有从“夷蛮之地”回归故里,从少数民族与卫所杂错的环境中回归熟悉的巴蜀文化和汉文化环境的念想。虽然雍正五年,黔北并入贵州,黎氏家族再次入籍贵州。但此时的贵州,与当日不同,已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区域行政属性的改变,并未改变文化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家族的文化血脉里,一直就流淌着汉文化的血液。由蜀而黔,由黔而蜀,再由蜀到黔,改变的是地域身份,没有改变的是对汉文化的依附与坚守。正是由此,一个家族的文化行为,才能带动一方,最终形成享誉一方的文化景观。
黎氏定居沙滩后,“其所卜居之业,治家之法,饶有古儒风焉。”[3]将儒家文化用于家庭管理,使文化传承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这就使家族繁衍与汉文化紧密相连,不绝如缕。“黎氏自迁遵义以来,累代耕读为业。”耕读传家,是农耕时代汉文化圈理想的生活模式,在经济收入较为稳定的环境下,将谋求生存与读书做人合二为一。同时在科考中获取功名,“读书成才”,最终成为书香门第。黎氏家族从始迁沙滩起,就自觉以儒家思想规范自身的行为,即使在“三代不应清朝科举”的束缚下,仕途无望,仍坚持读书明理的原则,以儒家思想作为行动的准绳,通过读书以陶冶情操。其意义在于,在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背景下,坚持儒家的伦理道德,就是坚守汉文化的传承,守住汉文化之根,也即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与“存天下”。因此,四世黎耀才能以一介农夫做到“躬领家政,事亲有道,温凊定省,率家人以礼法,每遇元旦、庆节、生辰,鸡鸣时子妇孙曾即起,拜跪称觞,无敢惰慢,若迟至曙则有罚。”[3]五世黎天明,“生平忠直自处,仁厚待人。上事先白祖,下友诸弟,庭无闲言。”[3]虽读书天资不高,仍追求“以诗书垂后”。六世黎国士举止言谈自觉以宋儒为典范。“葬祭必依于礼”。“治家有道,内外必肃。以耕读、勤俭、孝友垂训后人”。生活俭朴、不崇奢华,“饮食衣服、一缕一粟、必爱惜。遇喜筵,寿节,岁时,伏腊,毋糜费,毋奢华、闺门之内、秩秩如也”。“率族人以礼法”。子侄辈时群聚笑语,见其至,“辄拱立以俟。既尊长,行亦循循规矩。毋敢箕距喧哗。”[3]同时刻苦攻读,“家计艰难,教读以资衣食,昼则训诲生徒,夜则然膏课诵。亦时而经营交易,家以织布为业。每负往郑场出售,挟所抄文艺册及笔砚以随,甫出门,即口占一四书题,途次构思,寂无一语,及至场入店,腹稿己成,辄伸纸录之。或时在店,未及买卖,即取抄册熟诵,其苦志如此。”[3]弟黎国柄幼读书悉通章句,尤熟古文辞及三国志。又便弓马,初欲应武试以图进取,及兄黎国士考中举人,“见门户有庇,乃弃儒业,躬耕自给。产不甚丰,终岁勤动食指而外,家无长物,处之泊如。稼穑之余,亲操纺织以供裳服,布素萧然。”耕是为了生存,使家族能够繁衍生息;读是为了传承文化,陶冶情操。正是不离不弃地对儒家礼仪的自觉遵守和对诗书的不断追求,使黎氏家族在沉寂数十年后,重新成为簪缨之家,并成就一方文化。
对汉文化的恪守,具体化就是对“忠”、“孝”、“仁”、“义”等儒家道德文化观念的恪守,二世祖黎怀仁曾这样教育子孙:“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帅子弟,在朝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党不可一日不以正直化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己。”[3]“忠”、“孝”、“慎”、“勤”等儒家文化观,始终贯穿于黎氏家族的行为和著述之中,体现出一个移民家族对文化之根的记忆和坚守,这种坚守,对平播后汉人移民聚居的黔北,既是良好的示范,也是有益的带动。
三、沙滩文化的地域特色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自然环境和风俗民情,文学创作更是如此。改土归流有效地改变了西南边陲土司割据称雄的局面,推动了民族间的交流和发展,但万山之中的自然条件并没有改变。位于我国地势第二级阶梯边缘的黔北,是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和湘西丘陵的过渡地带,山峦起伏,地势陡峻,交通梗阻,信息蔽塞。在清乾隆年间,贵州人口也才五百余万。雄奇诡伟的群山,蚕丛鸟道的交通,地广人稀的环境,对沙滩文人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程千帆先生在论及文学与环境关系时说:“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犹有先天后天之异。所谓先天者,即班氏所谓风,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谓后天者,即班氏所谓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为其根本,后者有多翻遍,盖虽山川风气为其大齐,而政教习俗时有熏染,山川自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也。”[5]先天的自然地理,对生活于兹的沙滩作家群心理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如郑珍《巢经巢诗钞》,“有三百多首出现过‘山’这一意象近四百次,如果计入词序中出现的‘山’,以及其他一些代称山的字眼,如峰、峦、岭、岩、石、厓等,则远远超过四百次。”[6]黎兆铨“蚕丛通一线,鸟道入重岩,山半成云海,舆前只石巉。难于经蜀道,险倍越崤函。间有人生出,依稀类黑猿。”[7]极力地描摹出黔北的峭山险道,成为作家外在的、易于指认的地域性界标;黎庶昌《丁亥入都记程》所记娄山同样:“娄山即汉志之不狼山,山极高大,群峯崱屴,连延不断。横亘数十百里,皆娄山也,实不能指属何峰。自黑神庙上至关门,非甚陡峻。惟立关门下瞰,则深壑中线路如蛇,阴森可畏。”[8]不管是沙滩文人吟咏的诗还是文,在取材和内容上,都打上了鲜明的黔北山地烙印。生于斯长于斯的沙滩文人,在这特有的自然景观中,不自知地受到客观环境及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的规范,将地域文化作为逻辑思考与审美表达的起点,其中不乏柔软的爱的温情。在郑珍的诗文中,哪怕是用奇字辟语,渲染了黔北山水的险峻雄奇,也很少使人感到凶险恐怖,相反,恰好有一种“历尽万山不觉险”的见惯不惊和随意自然,传达的就是这种爱和特定地域丰富多姿的生命丰采。正是这种爱,郑珍辑《播雅》,莫友芝、黎兆勋等编辑《黔诗纪略》,黎庶昌编《全黔国故颂》、《牂柯故事》、《黔文萃》,刻《黎氏家集》,莫庭芝、黎汝谦编《黔诗纪略后编》,希望通过收集黔中散佚文献,存留地域文化,建立“地方性知识”。
山川的风骨造就了沙滩文人不甘沉沦,勇于进取的精神。他们辑丛书,编方志,是为了彰显贵州的特色,强调贵州并不落后,“亦有儒风”。正是这种文化自信,使他们有极强的文化自觉,敢于与中原人士一争短长。如《遵义府志》,明确的以地域标准采录地方事像,对遵义历史沿革、山川河流、物产木政、职官宦绩、古迹名胜,风土人情等地域空间及历史文化作了大量的考证研究,将之记录在案,成为人们认识黔北地域文化的教科书;而且,为了突显地域特色,在体例上敢于创新,成就了“天下第一府志”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说,《遵义府志》实际上就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正如杨芝光言:“文辞典雅,堪追遗范于方姚,考据淹通,足绍绝学于顾、李,不特山川辉耀,亦闾里增其声价焉”。[9]让人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沙滩文化的产生,是移民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完美交融。一方面,他们是移民迁居沙滩,骨子深处有一种移民前文化的优越感和对汉文化的自觉认同;另一方面,黔北艰难的生存环境,狭窄的文化空间,使他们踏实地选择耕读方式。荷锄耕作、吸水破柴是生存所需,读书著述、教化乡土是精神所系,这就使他们的耕读与其他地方的耕读多了一份沉重和使命感。因此,尽管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功名都不高,但他们仍然潜心著述,就如耕作一样,特别关注脚下给与他们安身立命的土地。体现在文化心理上,就使他们一只眼睛盯住眼前,关注当下;另一只眼睛却始终关注外界,以博大的胸怀吸纳外来文化,如郑珍拜程恩泽为师,学习文字学,入程恩泽幕府;黎庶昌在西欧任参赞期间,广泛参观学习,对欧洲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认真观察,并详加记录,撰成《西洋杂志》,被誉为“西洋十九世纪的风俗画卷”[10];黎汝谦任日本神户领事,与蔡国昭一起,翻译了中国第一部《华盛顿传》,在《时务报》发表,向国人介绍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的事迹。这种文化心理,不仅是沙滩文人的文化心理,也是所有贵州移民共有的文化心理。正是在这种心理下,他们踏实做人,执着坚定,同时又敢作敢为,以自身对文化的追求,参与构建了地域文化。
四、沙滩文化对地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如前所述,从汉到明,黔北就一直没有停下与汉文化交融的步伐。但总体来说,沙滩文化形成之前,黔北对汉文化是一种学习,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来说,是一种转轨和融合;这种学习,虽然在土官上层是一种积极主动,但范围有限,这从思州田氏后裔从田佑恭后就寂然无闻可见。遵义虽然在南宋时就儒学勃兴,但在明代,杨氏土司出于个人利益对汉文化持疏离和抵制态度,汉文化兴盛的大潮便瞬息消退,在明代近二百年的时间,播州考中进士的仅一人,而且还是从朱元璋始明廷在各地区大力兴学的历史背景之下。因而,汉文化在黔北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没能形成民间思潮,下层群众未能形成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故而影响不大,持续时间不长。整体来看,仍然是巫风盛行,“不学子弟泰然安行,无或至稍觉其非者”。
黎氏迁至沙滩后,不仅倡导耕读传家,更将汉文化视为生活、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具有秀才功名的黎氏两代入黔初祖,其文化身份意识应该非常清晰,他们是“朝廷之民”而非“土司之民”,执着于汉文化就是执着于移民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身份又必须和生存环境适应。这就使黎氏家族所倡导的汉文化打上了浓郁的地域印记。始迁祖的秀才身份,使他具备了知识分子的资格,有别一般群众;而仅具秀才的身份,离上层社会毕竟还非常遥远,甚至连跻身官僚阶层的资格都没有。即使是黎怀智,虽任过黄冈知县,也不过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因此,介于簪缨世族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文化地位,其汉文化的意识和追求,实际上是所有中下层移民能寻找到的精神支撑,也易于赢得广大移民的响应。黎氏家族将这种意识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以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人格感召来提升民间精神生活,表达了偏远地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在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背景下,他们能以“救天下”为己任,规定“三世不应清朝科举”,自觉断掉了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却始终不懈的以读书务本为业,在谋求生存的同时,追求崇高的品性,为周边的汉民族儒生家庭树立了道德典范,也从精神上产生了巨大冲击,为今后沙滩文化的崛起奠定了良好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康熙年间,清廷对儒家文化的大力吸纳,消解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疑虑心态。到乾隆时,陈玉引入山蚕,使黔北经济日臻富裕,成为贵州首富之区。但在嘉庆、道光年间,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腐朽,士子大都缺乏理想,只知埋头时文,科考封爵,以鲜衣美食为宗,以高官厚禄、光宗耀祖为旨;或者科考无望,凭借所学讦讼乡里,以饱其私欲,没有仁爱廉耻之心;或者良心未泯,以课塾弟子为生,以求温饱,无学术进取之意,无立德立功立言之志。儒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并未真正确立。在这样的背景下,黎氏家族一方面积极参加科举,以求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宋学,强调道德义理,强调个体的修身养性与道德完善,并以此教学授徒,对提升黔北儒生的思想境界有着积极意义。由于宋学缺乏干预现实的路径,也缺乏展示立功立言的国家平台,因此,沙滩学人又自觉地选择汉学。一因汉学是实学,从乾嘉始,在全国即为显学,要进入国家层面的学术话语体系,跻身全国大师之列,汉学是必由之路;二因洪亮吉、程恩泽等汉学大师先后视学黔中,奠定了汉学发展的基础,莫与俦、郑珍即先后出于门下;三是作为汉学先师的舍人、尹珍本为黔产,与黔中学术有深厚的历史、地域渊源。莫与俦“教人崇笃学,去浮靡,从学者言考据,言义理,言诗古文辞,悉各就其性之所近,不拘拘焉以门户相强。”郑珍“其治经宗汉,析理尊宋,专精三礼,经术所不能尽者,发为诗古文辞以昌大之。” 正是这种融汉宋为一炉的学术思路,既承接了文化主流,赶上了时代演变的步伐;又打开了黔北文士的视野,为逐鹿中原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黎氏家族重视文化,重视读书,当他们走出封闭的大山,外界优厚的读书环境使他们倍加珍惜,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黎雪楼曾说:“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吾以进士为读书之始。”在浙江桐乡任知县,所有的积蓄不是买田买地,而是用于购置书籍。锄经堂近三万卷的图书,既是沙滩子弟读书治学的基本工具,也打开了他们的视界,为沙滩文化崛起奠定的物质基础。沙滩藏书作为黔北乃至贵州最大的“图书馆”,不仅哺育了郑、莫、黎家族的沙滩文人,对蹇、宦、赵家族及桐梓赵旭、黎平胡长新等人的成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是沙滩文人身处下层、在艰难的环境中发自内心的向学,将读书治学成为生存、生命中一种自觉自为的生活方式,才能使“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 改变了汉文化“传入”边远地区的文化流动方式,以一种新质的地域文化整体形象冲出大山,展示出辉煌的成绩。
[1] 黄万机.沙滩文化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2] (清)黎兆勋采诗,莫友芝传证.黔诗纪略[M].关贤柱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3] (清)黎庶昌.遵义沙滩黎氏家谱[Z] 光緒十五年南京刊本。
[4] (清)周作辑.贵阳府志[M].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校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5] 程千帆.文论十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6] 罗筱娟.郑珍笔下的山意象[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9(6).
[7] 刘作会.黎氏家集续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8] 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Z]//《黎氏家集》,日本使署活字版本,1888.
[9] 杨芝光.民国桐梓县志序[Z].1930年民国刊本.
[10] 黎庶昌.西洋杂志[M].钟叔河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2.
[11] (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Z].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1986重印本.
[12] 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遵义新志[Z].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1986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