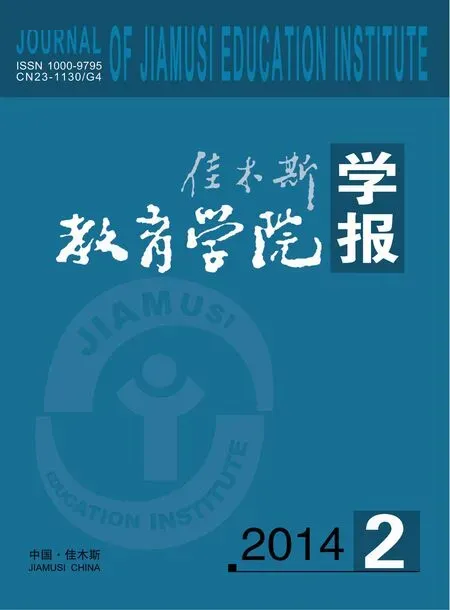弗吉尼亚·伍尔夫《飞蛾之死》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解读
何转红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弗吉尼亚·伍尔夫《飞蛾之死》的生态女性主义的解读
何转红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文章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散文《飞蛾之死》。通过分析文中的“自然”,“感性”和“女权”等元素,文章撅取她去中心化的生态女性主义的整体意识和对自然、自由、尊严、权利、命运、死亡和存在的思考。
生态女性主义;自然;感性;女权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二十世纪英国“传统散文最后的大师和新散文的首创者”[1],与詹姆斯·乔伊斯同为开创意识流文学的巨匠。她擅长藉女性视角描写人、物细腻的内心世界和活动,诠释对女性、自然和世界的深度和广度。
一、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发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揉和了生态学和女性主义[2]。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权制对自然的压迫与女性的压迫有直接联系[3]。在男性制社会,女性、自然、动物、感性、身体和主观被等同,被当作是男权、人类、理性、心灵和客观的对立面,是被统治、被征服和被压制的对象。在男权社会,男权优于女权,人类高于自然,理性胜于感性,心灵统治身体,客观压过主观。因此,废除具有压制的、物化的、等级优劣逻辑的反生态整体发展的二元体系,去中心化,尊重自然内在规律,约束人类企图干预、控制、征服自然的行为[4],才能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男女平等和多元化的生态整体。
二、自然:一间自己的屋子
伍尔夫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先驱[5]。她研读过诸多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和作品,如简·奥斯丁,勃朗台姐妹。在《两位女性》中,她道出了当时女性的生存状况:缺乏独处空间、无收入来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种种不平等[1]。她也十分关注自然。她推崇以自然主义和宿命论闻名的文学家托马斯·哈代,对远离喧嚣的田园气息非常神往。可以说她是一位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中的作家”[1]。
她曾说过,一个女人要写作的话,必须要有钱和一间屋子[1]。在当时的社会,男性制渗透各个领域,而女性被驱逐出这个中心,处于边缘境地[5]。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生动诠释了游走在男性制社会中被边缘化了的女性的写作实践状况:写作时“思考”就是条“小鱼”,微小但具有“独特的神秘性质”,令人心潮澎湃。她的这间“屋子”是河边的一片“草地”,被男性“压了300年之久”。草地由专人把守,他们为女性专设了“砾石路”。当她大胆闯入“草地”时,一个面带恐惧和愤怒的男人开始拦截她,把她带到了专属女性的道路,又把“鱼”吓得不知藏到哪儿去了。
(一)人与自然:和谐并存。二十世纪早期,英国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革命,人类不断违背自然规律,改造和征服自然,人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打破了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自然生态和谐,引发世界秩序的混乱和人类精神的裂变。自然不再是浪漫主义文学家所描述的令人敬畏的力量,唯美的存在和精神的向往,而是充满欲望的、腐化了的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寓所。
伍尔夫是时代的叛逆者。她延续了十九世纪的人们对自然的热情、赞美、敬畏和神往。散文中,自然这间“屋子”柔美、和谐、充满生机。窗外,气温和风景舒适宜人,农夫辕马掌犁,劳作耕田,白嘴鸦在树林中欢腾、盘旋、栖落枝头;屋内,她也乐于和飞蛾共处一室,因为这种藏在帷幕幽暗处的飞蛾仿佛是她思绪深处的隐匿的“小鱼”。飞蛾突然出现在她眼前,无疑给她惊喜,使她无法专注于书本,激发起她对沉沉秋夜和青藤小花的欣快联想。此时,自然成了她灵感的来源,给她鼓舞和启示。因此,死神降临时,她不能置飞蛾的命运于不顾。落座于“屋”中,她敏锐地洞察世界的变化。人与动物、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没有破坏自然生态,似乎又回溯到浪漫主义时代的田园生活。
其次,相对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物化,伍尔夫对有别于人类的生命形式表现出人性的关怀和尊重。散文中,作者用“他”而不用“它”来指代飞蛾。这和男性制社会中动物低于人类,应被人统治的观念相悖。尼采认为,人不是万物之主,人和自然界的生物是平等的[4]。她认为,飞蛾和白嘴鸦虽不足以道,却“也是生灵”[6]下同,并不是没有思想、对生活没有热情和目标、没有乐趣、不会痛苦的低等物种。散文中,飞蛾似乎是有灵魂和意识的。他和人类有相同的存在主题---死亡和命运 ---同样的勇敢和顽强。飞蛾和“小鱼”一样,似乎是女性觉醒的思想意识,有血有肉,和男性的思想同样重要和有意义,并不低劣。
然而,自然和谐的背后也蕴藏着冲突:贫瘠的山丘,成片的白嘴鸦如命运之网,黑压压地罩住天空,透露出浓重的不安和压抑,预示死亡即将来临。它们“像是在欢庆某一次年会”,飞蛾似乎就是它们的祭品。海德格尔曾言,人是向死而生的,人无法逃避死亡。死亡是自然保持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必然规律。在自然规律面前,与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相比,人无能为力,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者,干预和控制不了自然。叔本华认为,人应当考虑到动物有人类无法干预的基本权利,重新建立对自然的尊重[4]。伍尔夫虽然同情飞蛾“命运不济”,“机遇不堪”,几欲用铅笔帮助飞蛾摆脱困境,最终还是选择遵循自然规律。自然是强大的,不可抗横的,飞蛾逃不过他的终极命运。
(二)理性与感性:感应身体的呼唤。伍尔夫是感性的、主观的。她主张作家要自然地表达出意识的流动和内心的感受[1]。她响应身体流动意识的呼唤,感性地呈现出飞蛾的立体面。“他”“心满意足”地出场,“背负重荷”“翩翩起舞”。面对死神,“他”拼力搏斗。作者被飞蛾对生命的热情和奋力挣扎所感染:从对飞蛾感到“欣快”,到很快便把“他”忘了; 随着飞蛾动作频率的增加,她再次被飞蛾牵引,两次提笔要参与到飞蛾和死神的搏斗中,想帮助飞蛾翻身。然而,死神却一如既往的冷漠超然,不被感动,无视飞蛾的生命热情和挣扎。
面对死神的理性,伍尔夫总屈服于身体的感性,她“充满了惊异”。事实上,她一生中多次亲历死亡,对死亡和存在深有体悟。她的母亲、同母异父的姐姐Stella、父亲和哥哥Thoby相继离世使她几度精神崩溃,精神疾病多次复发。1905年,父亲去世后不久她试图跳窗自杀未遂。她生前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伤害和影响,1940年,她的家在战争中被纳粹飞机炸毁。由于丈夫是犹太人,她一度担心万一纳粹胜利丈夫的安危问题。1941年,她预感自己精神病将复发,担心再次拖累丈夫,留下遗书后用石头填满衣袋自沉于河中自杀。她的自杀不是出于对死亡的屈服,而是出于存在的尊严和意义。她一生都在和病抗争,长期在常人无法忍受的精神疾病的折磨下笔耕不辍,活跃于文学圈子。这都归功于其丈夫对其悉心的照顾。她因此心存感激,想让丈夫的生活更有意义,不愿再拖累他。对她来说,感性永远不受理性的拘束,身体永远不受精神的压制。
(三)男权与女权:自由、存在和尊严的抗争。伍尔夫在《女人的职业》写道,“屋子是你们的”,“要和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进行斗争”[1]。她生于家庭关系复杂的大家庭,很少有自己的空间,曾被同母异父的哥哥性侵, 这些特殊的经历激发了她为女权、自由、存在和尊严的抗争。散文中飞蛾和死神的搏斗似作者人生的写照。
伍尔夫没有描写色彩鲜艳生物,而写了一只枯黄色双翼的、躲在窗帘阴影里的“只有一天生命”的飞蛾。一方面,“他”是被边缘化了的女性意识的化身,是“既无人重视又无人意欲保存的生命”。在能轻而易举夺去千万人性命、毁灭城池的伟力---男权的化身---面前,“他”实在太渺小太微弱,似乎映射着作者以一己之力和强大的反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作斗争。另一方面,蛾是变态昆虫,由卵孵化成幼虫或毛虫,脱皮成蛹后做茧把自己缠绕起来,蛹在茧里发育成飞蛾,寿命很短。换言之,蛾是此昆虫生命的最后形态和阶段,离死亡最近。这让人无法不悲悯和珍惜这微小的“瞬间”的存在---无论是作为自然生命体的飞蛾,还是作为作者头脑中的女性意识。正是这样挣脱不了死亡阴影的生命体对存在充满热忱,用弱小的身躯抗争应有尊严,“展示着生命的真谛”。在强大而冷漠无情的死亡和命运面前,飞蛾奋力挣扎和反抗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但对于飞蛾本身而言,这是有意义的,飞蛾证明了自己,绽放了生命的光彩,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生命的尊严,体面地、毫无怨言地死去。
三、结语
《飞蛾之死》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态的、女性的人生、世界和思考。她如飞蛾一般勇敢地为自己的“屋子”而抗争,绽放存在瞬间的精彩。
[1]乔继堂,等主编.伍尔夫随笔全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Mac Gregor, Sherilyn. Beyond Mothering Earth: Ecological Citizen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Care [M].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286.
[3]Merchant, Carolyn. In 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2,184.
[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4-47.
[5]柏棣,主编.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32-245.
[6]沃尔夫,弗吉尼亚.飞蛾之死[J].陆谷孙,译.中国翻译,2001, 22(6):72-74.
Interpretation of ecological feminist of Virginia Woolf "the death of the moth"
He Zhuan-ho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China)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to interpret Virginia Woolf's essay "the death of the mot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emotion" and "feminist" and other elements, the overall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feminist articles take her with decentralized with nature, freedom, dignity, rights, fate, death and the presence of thinking.
ecofeminism; nature; emotion; feminism
I106
A
1000-9795(2014)02-0108-02
[责任编辑:董 维]
2013-12-24
何转红(1983-),女,广西南宁人,讲师,从事英美文学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