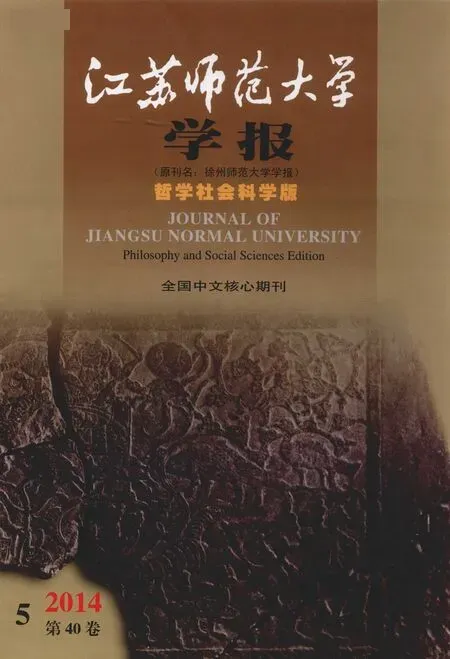大学德性迷失的现象解读与原因分析
朱景坤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大学是公众心目中圣洁的象牙之塔,一个充满道德优越感的德性组织,“学院和大学应该表现出远远超过最低道德要求的道德敏感性,因为高深的学问使这些机构具有较为敏锐的洞察社会不平等的能力”[1]。大学应与贪污腐败、道德失却等社会丑恶现象距离遥远,“即使社会的其他部分出现了道德滑坡、衰退,大学也应该独自坚守道德高地的角色定位,不能随波逐流”[2]。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与大学自主权的扩大,以及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后的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繁荣的表象之下也乱象丛生,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现象屡屡发生,德性的迷失使大学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人们对大学的不满与诘难、困惑与担忧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一、大学德性的内涵解析
希腊语中的德性(arete),“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指事物的特性、品格、特长、功能,亦即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是指一种‘无与伦比的卓越境界’,一种从心底发出来的、宽阔的伟大”[3]。柏拉图把德性作为与人的天赋相适应的品位,将德性分为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一种内在于人类活动本身的、用来使个性达至善福的性质,包括理智的德性和品质的德性。在《欧洲伦理生活史》中,莱基将德性分为严肃的德性,如庄敬、虔诚、贞操、刚正等;壮烈的德性,如勇敢、牺牲、忠烈、义侠、坚毅等;温和的德性,如仁慈、谦虚、礼貌、宽和等;实用的德性,如勤劳、节俭、信用、坚韧等[4]。英语中的德性(moral character)是指道德存在的组成部分,是道德存在的表现形式,是道德存在转化为道德行为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力。与德性紧密联系的一个词是德行(moral caliber),是指出于义务而遵守道德律,是道德支配下的行动。德性“包含着道德律与敬重两个要点,意味着把握理性中的法则并因敬重而使法则成为意志的唯一动因,因而德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精神品质(对道德法则的认识和敬重)。因而,‘德性’是决定意志是否善良的意志的唯一因素,并决定一个行为是否称之为‘德行’”[5]。无论对德性作何种划分,都存在一个显见的事实,“即把德性确定为人的一种本性,确定为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智慧实践”[6]。即是说,德性是一种体现道德主体卓越品质的崇高道德境界和善行习惯与趋势。
尽管对于德性问题存在许多概述,但何为“大学德性”,中外思想史上鲜有学者给予专门性的概念界定。的确,相对于大学和道德关系问题的浩繁阐释,“大学德性”一词的解释则显得相对“贫乏”得多。不过古今中外先贤大儒的有关思想为其阐释提供了金钥匙,通过对先贤思想的解读、分析和概括,不仅可以了解大学德性范畴的认知历史和全景图,而且可以给予大学德性以现代意义上的界定和厘清。教育基本理论认为,教育组织至少有三个要素:教育者的有目的活动,教育资料,教育对象。由于教育者有目的活动产生于对社会需求的选择,教育资料源于文化,教育对象是有待培养的人,因此,大学德性体现在其组织自身、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所具有的德性和所表现的德行。首先,大学本身是一个德性的组织。大学是西方文明中最古老的组织,除了完成其明确提出的使命如创造、传播和保存知识外,还履行了一系列其他重要的职能,代表着社会良知、提供了人文关怀和可以坚守的精神家园。大学通过提供博雅教育训练人的智力,造就社会的绅士,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明确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个人生活之间交往的文雅化。英国诗人约翰·曼斯菲尔德曾经写道:“世间再无堪与大学相媲美的事物。在国破家亡、价值沦丧之时,在大坝坍塌、洪水肆虐之时,在前途暗淡、了无依赖之时,不论何地,只要有大学存在,它就巍然屹立,光芒四射。只要有大学存在,人的自由思想、全面公正探索的冲动仍能将智慧注入人们的行为之中。”[7]其次,教师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无论从历史的考察还是从现实的观照来看,大学都是教师——学者的集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果没有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教师,不仅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成功,也不可能开展任何有效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活动。哈罗德·J·珀金明确地指出,时至20世纪后半叶,在一个日益为各种专家所支配的世界上,“大学教师已经成为其他专业的教育者和选拔者”。大学通过它的教师提供了艺术、科学和技术方面“新知识的生长点,理智文化的主流和革新的制度化”[8]。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所承担的学术责任几乎可以转换为教师所担负的责任,大学职能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教师职能的发挥,亦即大师的德性决定了大学的德性。第三,学生具有良好社会道德。美国学者德海特·艾伦指出:“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9]培养学生成才,是大学教育的题中之义。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拥有的,不单是智慧、勇敢、节制这样的古典德性,而是“培养具有德性而非甘于卑俗的人,追求真知而非听命于意见摆布的人,践行伦理而非恣意而为的人,能够面对世间那些根本的冲突,担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后果的人,而不是寻觅教条的避难所来推卸和逃避责任的人”[10]。
二、大学德性迷失的现象解读
麦金太尔指出,近代以来由于功利主义的膨胀等原因,传统德性已从以往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沦为实现外在利益——功利的工具,人类社会呈现出道德危机的征候[11]。经过近代以来急风暴雨式的洗礼,我国传统德性虽不至荡然无存,但也所剩无几。身处社会场域中的大学难以独善其身,中国大学出现德性的迷失,表现为精神层面上的价值观危机和行为层面上的德行堕落。
1.大学的价值观危机
随着人们对权力、地位和金钱等功利目标的推崇,大学逐渐放弃传统价值的职守,越来越随波逐流,“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市场化了”[12]。首先,学术活动商业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学越来越以市场的机制为基础,按照市场竞争规则和产业逻辑运行,为了追求卓越的学术成就和市场影响力,教学和科研变得不再是一个教育的和道德的过程,而达成的仅是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大学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将研究知识转化为智力资本和财产,使教育异化成为一种“可以凭借权力和金钱随意兑换的商品,大学成为交易的焦点的同时,却也成了社会败坏的焦点,大学不再是能够批评和对抗社会不义的力量,而成了这种不义的具体化身”[13]。其次,价值取向功利化。以创新和传授知识为使命的大学,其价值取向本应是公益性的,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对大学的强力渗透,使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出现了功利化倾向,以至于有悖于大学的本质”[14]。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个人和组织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政府重高等教育的规模而超过重质量,大学重学校的声誉而超过重绩效,教师重个人的名利而超过重自己的责任,学生重获得的技能而超过重习得的学问。这种功利化倾向忽视了为大学注入价值观与它们的特色和身份的发展,“使得大学师德师风、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学校管理、办学行为、学术风气发生了深刻而又令人焦虑的变化”[15]。再次,大学精神庸俗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但在工具理性的侵蚀和实用主义的浸淫下,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式微,大学传统的理想追求逐步让位于商业价值、犬儒主义和市侩作风等,大学降格为一庸俗教育的场所,“大学取向非规范、非道德、非健康、非自律,甚至偏离大学组织本质属性的不良现象、不良行为,且有‘蔚然成风’之势”[16]。庸俗化使大学难以坚守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必需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难以肩负起应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和历史担当,严重损害了大学思想文化高地、社会大众良心、人类道德楷模、时代精神风标的形象,大学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象牙塔”。
2.大学德行的堕落
首先,教育质量下降。1990年代,中国“‘大跃进’式高等教育扩招是在大学思想准备尚不充分,教育资源短缺、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准备不够,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熏陶和生存技能训练力不从心等情况下进行的”[17],由于没有遵循教育发展的外部关系规律,高等教育未能实现量的扩张与质的同步提高。就进入大众化阶段、向高等教育强国进军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教育经费虽然实现了较快增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虽然已达到4%的目标,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以上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6%的平均水平,特别是持续增长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稀释了原本就不充裕的教育资源。高等教育质量逐渐成为显问题,正如彼得·斯科特所言:“大众化过程中和大众化之后,随着数量的扩张,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十分关键的、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问题。”[18]其次,人文关怀的缺失。随着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雄居大学殿堂,大学出现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承载着道德教化作用的人文学科领地日渐狭小且备受冷落,人文精神式微。“科学技术成为强势学科,占有了大学的主要资源,人的培养变成一个‘制器’的过程。教育的功能已从培养健全之国民,偏向过分充实学生‘何以为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放弃了‘为何而生’的内在目的。”[19]这种人才培养中的重科技轻人文、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人格的养成和精神境界的提升,道德逐渐成为大学教育目标中可有可无的装饰。学生被模塑成充满竞争意识和实用技能的单向度的人,而作为人之为人的那种心灵的自由与内在的禀赋被褫夺了,成为嵌入市场竞争格局中的一种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而非开物成务之博雅君子。再次,学术腐败的滋生。有网络批评者指出:“学术腐败是九十年代之后风靡中国大陆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后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不仅如此,学术腐败已经从学者的个体行为发展成集体、集团行为,并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趋势。”[20]知识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离开了学者的独立创新,学术就丧失了它存在的价值。学术乃天下公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伤害的不仅是学术的声誉,更是学术的根本。学术不端挑战的是科学的根本精神和学界的学术责任和道德规范。而大学集中的是社会精英群体,担负着传承文化、开启民智的社会职责,承载的是社会良知和道德寄托,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是不能退守的道德底线。
三、大学德性迷失之原因分析
中国大学德性的迷失,既与大学同外部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错位相关,也与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失衡有关,是外在压力挟迫和自我放逐的结果。
1.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失衡
从国际情况看,欧洲大陆国家主要采用政府集中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较多的约束;美洲国家主要采用政府分权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英国和原英联邦国家,主要采用政府借助中间机构实行分散管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的约束往往以间接方式体现[21]。尽管各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表现形式并不同,但在本质上却存在相通之处:就政府而言,政府总是力图保有对大学的最终控制权,但“所幸的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这种权力没有被无限地行使”[22];就大学而言,大学自治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大学也从来没有完全自治过,但“大学自治的基本信念并没有动摇,它仍然是政府干预或控制大学的边界”[23]。正是大学与政府间这种适度的张力,使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作为大学最根本的理念得以保留,达成国家与大学目标利益长远意义上的一致。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被置于国家控制下的、科层制的官僚体制之中,缺乏学术共同体所特有的价值准则和学术规范,形成一个政府直接管理、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学的学术组织特性逐渐削弱。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之后的今天,大学虽然在形式上成为法人实体,“但现实中的大学其行政附属机构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法律规定的办学自主权并没有真正落实”[24],高校自主办学空间依然十分狭窄,学术根本没有独立地位。在对国家的依附下,“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在方式、范围和程度上挤压了大学自治,使大学丧失了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25]。
2.象牙塔精神与服务站职能的较力
随着知识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心地位的确立,处于知识产业中心的大学,也正在从为精英服务转身为社会大众服务,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大学开始“走出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服务站”,其边界开始延伸至整个社会,更少地与社会分离。但大学自中世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有其应有的边界和固有的‘象牙塔’精神传统,它作为大学组织所特有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成员淡漠名利,拒斥外界干扰,恪守‘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的学术价值准则,把研究‘高深学问’视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26]。也正因如此,大学充分发挥“服务站”的社会服务功能而不忘其“象牙塔”本色,人类才能不断拓展和深化对未知领域的认识,大学深层次的社会服务也才不会流于浮泛和庸俗。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虽是舶来品,但更多地只是移植其外在的形,而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为表征的大学精神并没有很好地在中国扎根,中国大学始终在政治、经济的闹市上被牵来牵去。没有“象牙塔”精神的涵养,“服务站”成为中国大学的流行和时尚,深陷市场社会的漩涡,“大学与外界间的一道有形或无形之墙已经撤销了。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一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大学与社会间的一个保持清静思维的距离也消失了”[27]。这种实用主义和商业化催生了大学功利浮躁的学风,校园变成“喧嚣”的集市,唯有知识商贩的叫卖声而无学子的朗朗书声。可以想见,如果大学不能保持自身的宁静、不能坚守大学应有的理性和学术价值、不能坚持对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追求,何以成为德性组织,何以培养德性人才。
3.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错位
具有学者行会传统的大学首先是一个学术组织,学术性是其本质属性,学术权力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而作为一个结构复杂、目标多元的社会组织,行政权力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布鲁贝克指出:“没有任何一所学院和大学是纯粹的学者团体,……为了生存并继续发展,这种团体需要一个在管理不动产和取得经费并进行大笔投资方面拥有广泛的知识和经验的补充性的组织成分。正如高深学问的发展需要专门化一样,在学院或大学的日常事务方面也需要职能的专门化。事务工作和学术工作必须区别开,因为每方面都有它自己的一套专门的知识体系。”[28]针对大学组织的特点,西方大学往往“采用科层组织与学者行会组织交织,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共存的‘双重组织模式’,即围绕资源管理和行政事务形成的、由非学术人员控制和管理的科层组织结构;围绕知识体系和学术事务形成的、由教授控制和管理的传统组织结构”[29]。这种相对健全的保护学术权力及学术自由的治理模式,较好地保持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必要的张力,保障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遵循教育规律发展。
以此观照我国大学,民国时期,大学深受外国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所设置的评议会、教授会在学术管理中是发挥决定作用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全面的行政体制,企业、学校、银行、医院,甚至各类行业协会,都被纳入国家的行政体制。在大学内部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力居于主导地位,大学管理染上了浓厚的行政色彩。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和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强化,导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严重错位,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主导各种学术资源的配置,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不高,科层制成为学术组织的基础,管理主义侵蚀着学术文化,等等。而当“以利益判断为基准的行政权力大大盖过了以学术判断为基准的学术权力,所损害的绝对是弱势的学术事业”[30]。
总之,在我国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旨的大学,如今却弥漫着浓重的官气,唯上是从,跑“部”前进,充满了大跃进式的豪迈和各种各样的高指标;弥漫着厚重的商气,金钱至上、成功主义之风盛行,运行着官、产、学、商各不相同的机制。学术自由源于学术职业的行会传统和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化特征,只有一个具有独立精神和品格的大学,才会有独立人格的大师,才会培育出有独立人格和独特价值观的德性人才。“灵魂已经出壳”的中国大学必须回归象牙塔精神,由“衙门和学店”恢复到作为教育和学术机构的“大学之身”。确立基于正确认识之上的大学理念、大学价值观,遵照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发展规律和逻辑,在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时不忘自己的使命。再就是要让学术本位尽快回归校园,建立由学者实行学术自治的组织,让行政权力为学术权力服务。大学的美好在于它们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唯有回归到学术优先的原则上,才能把大学办成一个道德高尚的杰出大学、使大学教师成为道德高尚的杰出学者、使大学生成为道德高尚的杰出人才。
[1][28][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37页。
[2]高德胜:《论大学德性的遗失》,《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12期。
[3]张东:《论大学教学管理的伦理诉求》,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4][6]戴木才:《论德性养成教育》,《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5]郁乐:《康德“德性“概念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经济社会发展》,2008年第11期。
[7][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别敦荣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第6-7页。
[8]Har old J.Per kin.Key Profession:The History of t 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
[9][美]德怀特·艾伦:《高等教育的基石》,《新华文摘》,2005年第22期。
[10][13]李猛:《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自由教育》,http://www.zhlzw.com/qx/xxl n/96452.ht ml。
[11][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12][27]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增订版,第21、21页。
[14]张乐农:《大学文化建设困局探究》,《文化学刊》,2012年第3期。
[15]廖志坤:《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非教育性倾向探析》,《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
[16]眭依凡:《大学庸俗化批判》,《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第3期。
[17][19]朱景坤:《社会转型期中国大学的危机》,《现代教育管理》,2013年第1期。
[18]Peter,S. The Post moder n University?in Smit h, A.&Wester,F.(Ed.),The Post moder n University—Contest Vi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ciety.Brist ol,PA:SRHE 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7:37.
[20]亦明:《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http://www.cpeer.or g/ht ml/guandianyusuibi/guandian/2004/0521/2641.ht ml.
[21][24]朱景坤:《大学“被行政化”的制度分析与“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2][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3]许杰:《彰显、复归学术权力: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根基》,《高教探索》,2011年第1期。
[25]韩水法:《大学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26]王作权:《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改革的四维张力探析——基于西方大学理念的视角》,《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9]朱景坤:《构建巨型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应注意的问题与理想取向》,《辽宁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
[30]张家:《大学去行政化的困难何在》,《大学教育科学》,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