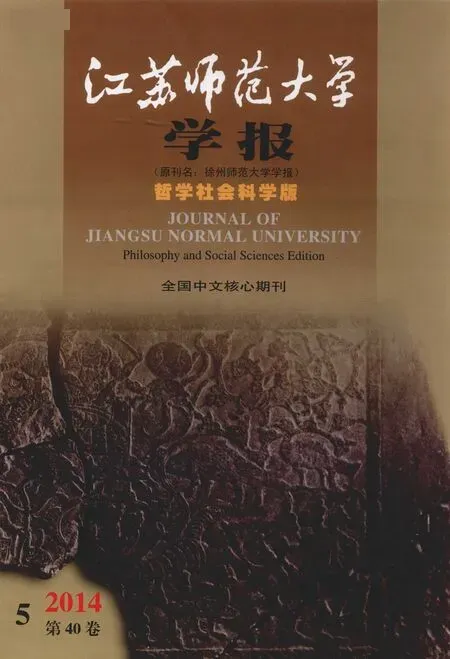简析媒介文本中的符号暴力与权力编码
——以剩女话语为例
孙金波范红霞
(1.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2.《当代传播》杂志社,新疆乌鲁木齐 830051)
简析媒介文本中的符号暴力与权力编码
——以剩女话语为例
孙金波1范红霞2
(1.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2.《当代传播》杂志社,新疆乌鲁木齐 830051)
剩女;编码/解码;符号权力;刻板印象;性别秩序
“剩女话语”是由媒介制造出来的,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下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剩女”话语刻画出的女性刻板印象和污名化想象,体现了男性中心的性别视角,因而具有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的标示意义。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既生产了知识,同时也生产了权力。通过对“剩女”的命名和定义,这一话语旨在贬低女性的性别形象和社会价值,并将其整合进官方认定的正式话语体系中,从而构成一种既定的话语秩序,以迎合传统观念中男性主导的性别霸权,因而成为一种符号暴力。关于“剩女”标签的制造和权力编码,以及在此称谓上附加的形象建构、道德想象和社会评价,反映了男性对现代独立女性的恐惧和排斥,以及女性自身在传统角色规范和现代身份认知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语言能够生产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各种符号(包括文字、声音、音符和各种影像、图片和物品)来表达概念、观念和感情。媒介文本的生产就是对意义进行编码从而建构意义的过程。霍尔认为,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1]。然而,具有意义的话语并非是在一个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里被“编码”,这个过程中蕴含矛盾冲突。基于某种社会情境,受众解读的意义与媒介机构生产的意义并非完全一致。这个“编码/解码”模式的关键特征是媒介话语受制于媒介机构和受众双方的共同生产,而不是成因于单一的机构与个人的活动,而且植根于现有的权力与话语构成之中[2]。通过编码/解码过程,在媒介与受众之间完成信息的传播和意义的循环。有鉴于此,在社会性别和媒介研究的语境当中,研究人员往往重点考察社会性别话语如何在媒介文本中被编码,性别权力如何借助“话语”得以体现、弥散并形成“霸权”。本文拟以近年来媒介中出现的“剩女”话语为例,着重分析媒介文本中话语权力的生成与抗争。
一、“剩女”话语的制造
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是一个符号语言,更是服从某些规律的话语实践。我们不应再将话语当作符号的总体来研究(把能指成分归结于内容或者表达),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3]。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是构成知识的方式,各种话语不仅是思考、产生意义的方式,更是构成它们试图控制的那些主体的身体的本质、无意识与意识的心智活动以及情感生活的要素,无论身体、思想或情感,它们只有在话语的实践中才有意义[4]。
“剩女”一词最初是在网络上出现的,在坊间作为私人化的词语流传。而它正式进入社会语言体系,源于教育部2007年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将“剩女”等171个新词汇收录进去,这个词语从而成为一个正规的汉语词语。而它的含义,最初是指那些具有高学历、高收入、高要求的大龄未婚女性。也被称为3S女性,即单身(single)、70后(seventies)、被卡住了(stuck)——嫁不掉。不过,随着80后也跨过具有标示意义的30岁“大关”,那些80后的大龄单身女性也被归入“剩女”的行列。并且,“剩女”的年龄下限也不断下调,现在过了25岁、还没有固定男友的年轻单身女孩也开始自称“剩女”了。
这个词语具有极大的现实投射性,它昭示着婚姻市场上极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权力问题。中国自古就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说法,并且成为约定俗成的社会礼法。但是对于大龄单身男女来说,其社会评价并不均等。在传统观念里,男人的成功在于功成名就,在社会上建功立业,而女人的成功在于嫁得如意郎君,相夫教子。从空间上来说,男人的功业在公共领域,而女人的职责是归属家庭,照顾家人,属于私人领域。空间也是权力的象征。外部空间能够获得荣誉、地位、财富和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也渗透于家庭。对于女性的贬抑,是从婚姻带给女性的身份改变开始的。从其身份来讲,适龄未嫁的时候地位最尊贵,而对于久居娘家迟迟不嫁的女子,往往在财产继承方面受到限制。新中国建立后,移风易俗,在法律上实现了男女平权,包括在婚姻家庭上的自主权和平等权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知青返城,城市大龄男女未婚问题逐渐凸显。在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上,男女本来是一视同仁的。然而,对大龄未婚女性的社会评价从与男性一视同仁到逐渐沦落,也是近些年来的事情。从“剩女”一词的出现就可见一斑。
人们对于“剩女”的刻板印象主要围绕其道德上的“不洁”(非处女)和与其年龄身份不相称的择偶条件而展开的。当这两点汇聚在一起时,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剩女”,就充满了恶意的嘲讽和歧视,并伴有幸灾乐祸的心理。在百度“剩女吧”里,一些帖子常以“非处”、“二手车”、“二手筷子”、“剩饭剩菜”等隐喻式语言,对“剩女”群体进行嘲弄和侮辱。这些带有人身攻击和道德污名的表述,已经构成赤裸裸的语言暴力。在“剩女”的话语建构里,最多的就是认为“剩女”具有丰富的性经历和对婚姻“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借助男性之口,这些话语以充满歧视和暴力强制的标签,刻画出一个道德污名、性格暴戾、行为乖张、大龄未婚的女性群体,她们是女性中的贱民群体。这个群体因其年龄的增长,没能因循文化预设完成婚姻而饱受诟病。她们的地位和形象低于已婚女子,低于青少年女子,甚至低于离婚女子[5]。
由于网络上的流传,以及传统媒体的介入而形成的对于高职高薪独立女性的负面评价与形象贬损,形成一种男性中心和突出男性优越感的“话语秩序”。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曾深刻指出: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的。这些程序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处理偶然事件,避开它沉重而恐怖的物质性[6]。如此一来,话语就被放置到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因而也必然受到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子必须嫁人,通过丈夫家族的接纳来完成社会身份的转换,以赢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今天的现代女性自立自强,能够掌控个人命运,并因其经济上的独立和择偶的自主权方面而被“剩下”——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明明是出于个人的选择,但是在男性视角下,她们却成为“被人挑剩下”的人,并被这种男性中心的文化冠之以“剩女”的称号,并将其整合进官方认定的正式话语体系中,因而成为一种“既定”的“话语秩序”。如布尔迪厄所言,既定的秩序,连同它的统治关系,它的权利和破格优待,它的特权和不公正,如此轻易地被永久延续下去,而最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常常以可接受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出现[7]。布尔迪厄将这种对男性统治秩序的承认和接受,即服从于既定的“话语秩序”,称之为“象征性暴力”。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媒介)来实施的,它反映的是一种“既被统治者又被被统治者所认识和承认的象征原则的名义所实施的统治逻辑”[8]。如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剩女,该将就还是要讲究?》作者以貌似客观忠告的口吻,一方面说着“幸福不能将就”的陈词滥调,一方面又劝告剩女们要“放下身段”,“懂得将就”[9]。通过媒介表述出来的社会态度与舆论压力,直接将剩女定义为婚姻市场的一件“商品”,如果不能迎合男性需求,“适销对路”,就只有“积压”下来不断贬值了。媒介的象征性暴力借助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往往会产生一种制度化的力量,即把媒介所宣扬的信息、思想和价值观转化为被大众视作理所当然而接纳的“合理存在”。权力往往与话语相连,通过建构“知识”与“话语”,并通过对知识及话语的真理化,话语就转化为一种权力。在此,“剩女”话语体现了一种具有压制性的性别权力观念。
按照这种逻辑,作为结果,“剩女”话语原本是男人制造出来的,但是后来逐渐也被女性自身所接纳、认可,尽管她们对此也充满矛盾心理。许多大龄未婚女青年现在也不得不接受了“剩女”称谓,甚至刚刚过了25、26岁就开始自称“剩女”,仿佛是屈从于这种“象征性暴力”了。象征性暴力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统治,导致女人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判定她们的状况,推断她们的自我贬值[10]。有研究者指出:这个具有歧视意义的、给人负面印象的词语,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性别危机,或者可以将之界定为未婚女性的自我认知危机。这场危机的背后,若隐若现地潜藏着男权性别统治的幽灵,这个幽灵在正规媒体中被掩藏,但在自由的甚至放纵的网络论坛中横行无忌,毒害了男女性别间的平和关系,挑起了性别统治和反统治、女权平等和反平等的斗争[11]。
二、女性神话的破灭与厌女症的流行
剩女话语的流行,恰恰也说明了女性神话的破灭和当前社会中“厌女症”的泛滥。东西方的文化中都有关于女性神话的记载。在中国,有“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的传说,西方有地母盖亚,以及司婚姻与生育、丰收与平安、美与爱、人类命运的各位女神。在人类学家和文学家眼里,这些既是人类历史中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也反映了自古以来对女性在生育、生产、爱情和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及地位的崇拜。即使在今天,“贤妻良母”仍然是各种文化中不断加以强调、提倡和赞美歌颂的形象,反映了社会对女性普遍的角色期待。不同于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勤俭持家、慈爱可亲的“母亲”,侍奉公婆、相夫教子、履行家庭使命的“贤内助”等符合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女性形象,则构成了一种“世俗神话”。
但是,在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女性崇拜逐渐衰落,甚至完全逆转,导致最后形成一种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女性的地位逐渐降低,被贬低至次等的群体,即西蒙·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甚至男人的堕落也被说成是女人的过错。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就是因为夏娃被蛇引诱偷吃了禁果(蛇也是女性的象征)。而宙斯造出美女潘多拉,就是为了让她把灾难带到人间,以惩罚人类的过失。古代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美女海伦和帕里斯私奔挑起的。在中国文学中,褒姒、妲己是亡国的“祸水”。女人从“女神”的位置上跌落,成为“祸水”和灾难的代名词。这是厌女主义意识的源头。
所谓“厌女症/厌女主义”是广泛存在于文学、艺术和种种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中的“病症”,表现为对女性化、女性倾向以及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物和意义的厌恶,并把妇女,尤其是妇女的性,当作死亡与痛苦,而不是当作生命和快乐的象征[12]。厌女症其实反映了一种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这种话语极力贬低女性的人格,在道德和伦理层面上表现出对女性的蔑视。在一些文学作品和哲学专著中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女性被描绘成轻浮虚荣、愚蠢、贪婪、情感幼稚、喜怒无常、容易堕落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也否定了女性的才华与能力。似乎女性天生就比男人低一等,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上,从而为男尊女卑的社会等级秩序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的权利义务条款,但父权制文化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男孩偏好”“养儿防老”的思想仍然左右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就业市场上,女性求职屡屡遭遇歧视、碰壁和各种借口的拒绝,即使入职后在薪酬、福利、培训和职场晋升等方面也难以与男性员工平起平坐。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时代,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女性的“物化”观念也逐渐流行,商业文化催生和精心打造的“物质女郎”,将女性作为欲望的主体和客体,进一步削弱了女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主体性。
梁巧娜比较了中西方神话中女性的地位变化,从性别文化的视角上,深刻剖析了人们对女性的一些观念和看法是如何出现并定型的。梁巧娜认为,中国的神话故事在流传和演变的过程中逐渐被政治化和伦理化,神话的整理者和叙述者根据自己的政治标准和伦理标准对故事进行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改造。在这个整理并改造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呈现下滑的趋势[13]。她将这种女性地位沦落的原因归结为男性掌握了“叙述权”。由于男性掌握了叙述历史和制定标准的权力,是他们规定了男尊女卑、男主女次、“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历史也就成为男性“帝王将相”的历史,女性的声音被湮灭以致不闻。
而在大众传播时代,传播媒介的发达把历史语境以及人与环境的物质关系转变为文化关系。媒介文化也成为主要的叙述文本。在文化媒介化的背景下,人们对社会文化的参与更多是通过大众文化的投射,日常生活的理想和兴趣得到了更细致更平常的回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媒介文化也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表象[14]。凯特·米勒特在《性政治》一书中,研究了男性强权的表现。历史上绝大多数男权制社会通过法律把男性强权制度化,为维护对女性的财产性占有,对女性的通奸等出轨行为予以残酷惩罚,以及强迫女性堕胎、强奸等性暴力活动[15]。另外,男权制社会中人们常常把残酷的情感与性相联系,比如色情文学中以男性为施虐者而以女性为受虐者,以及某些男性观众对于性暴力和大屠杀的幻想性认同等等。随着消费主义观念的流行,围绕女性的相关产品和服务逐渐形成了有利可图的产业,女性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日益被商品化、物质化,厌女主义有再次抬头的迹象。比如,在各类新闻报道和犯罪文学中,女性往往成为各级贪官弄权索贿、贪污腐败的借口。
即使在依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女性身上,也无法摆脱这种男性思维的定势:女性的成功不是靠个人能力,而是靠与之有特殊关系的某个掌握权力或资本的男人“提携”起来的,在人们关于官场、娱乐圈、名利场上各种“潜规则”的想象和讨论中,女性往往被视作“潜规则”的对象。按照这种逻辑,女性的成功一定是实施“潜规则”的结果,她们不是靠才智、实力和奋斗,而是凭借美貌和身体资本而“上位”的。社会上把这些独立自主、追求男女平等,甚至在职场上与男性对手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女性称之为“女强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贬损和否定的意味)。她们中的一些人因为不肯降格以求,不愿随俗草草嫁人,就被打入“剩女”的行列,受到百般嘲弄和污蔑。这种对女性成功者进行污名化想象和道德谴责的“叙述”,恰恰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厌女症”余毒未靖。
三、符号权力与性别秩序
(一)语言和命名是权力之源
据《圣经·创世纪》所载:“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第1页)此后,上帝又造出了空气、大海和陆地,日月星辰,动植物,飞禽走兽以及人类,并分别为之命名、归类。人类的第一个祖先亚当也是上帝造出来的,并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女人,作为他的伴侣。在这里,借助神(上帝)无所不能的能力创造了世界,通过命名展示其全知全能的权威。这个关于“创世纪”的神话,也成为标示男性话语权力的隐喻。正如玛丽·克劳福德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和命名是权力之源[16]。她认为,对语言的批判性思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以性别名义的社会分类体系授予男性的权力要远远多于女性。
语言和命名是权力之源,而给事物作出判断、归类及确定属性正体现了这种命名的权力。采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命名或者作为修辞策略,往往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并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日常生活中,我们给事物的分类定性(贴标签)的做法也是实施命名权力的过程。关于“剩女”这一话语的生产,是基于男性视角对某一女性群体的命名。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莲娜·西克苏在分析父权社会如何遮蔽和消除女性话语时,着重指出,因为男性(父亲)掌握对事物的命名权与裁判权,而女性“言说”的权力被剥夺了,她无法表达自己。而知识往往是基于语言的,掌握语言就必须要经历“阉割”女性自主权与自主意识的过程,因此女性也就被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被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就是排除在语言之外,排除在律法之外,排除在同文化和文化秩序之间任何可能的关系之外”[17]。我们在各种文化中,在一个象征权力的舞台上只能看到女性“缺席的在场”。她们被剥夺了表达的能力,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西克苏主张重建“女性在语言中的作用”[18]。她认为,女性一方面要学会“表达”,创作关于女性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要改变父权话语中心的“元语言”。如此一来,抵制“剩女”话语,打破语言与文化中的男性话语霸权,就具有了性别革命的意义。
(二)词与物——知识与权力秩序的再生产
福柯曾经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考古学》中将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以及医学话语的演变揭示为一种“词与物关系的重组、话语的变更”,因为语言和目光的重新分配,身体内部的疾病被重新赋予了一种可见的形式,医学话语的变化并非医学技术的问题,而是构成知识生产的“词语”发生了变化,词与物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识因而成为一种话语的生产。关于“剩女”的话语,虽然肇始于网络,但随着传统媒介的传播介入与扩散,原本用于描述某一少数群体的一种暂时状态的词语,逐渐演变为具有污名意义的身份名词,其内涵的“异化”,也正是体现了“词与物”的关系变化。由话语所构成的象征秩序,即话语秩序,建立了一种社会权威,并使社会主体不得不屈从于这种权威。“词”与“物”的关系既是不可见的微观权力载体,同时,也作为一种符号暴力,将一种权威深深植入我们的话语、情感和观念之中。
对事物命名,有助于我们对其体验和分享,并能够谈论它。而未经命名的事物则鲜为人知,或易被遗忘。但是,由于我们的语言中固有的包含性别歧视的词汇和语法规则,使得语言成为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在现有的语言和词汇中,存在许多贬低女性,包含性别偏见的词语。玛丽·克劳福德归纳了性别词汇在语言上的几种歪曲方式:1.冠以被人们认为有违常规的标签;2.采用具有轻视性的女性性别词汇;3.“在他是优点,在她却是缺陷”;4.排斥,这是一种最普遍采用的方式[19]。“标签”的作用在于制造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型化。语言使用中对女性的贬低,以及“贴标签”式的命名方式,建构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弱化了女性作为社会主体的作用,同时彰显了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性别文化。
四、结语
关于“剩女”标签的制造,以及在此称谓上附加的种种道德想象、形象建构和社会评价,反映出男性对现代独立女性的恐惧、厌恶和排斥,以及女性自身面临传统角色规范与现代身份认知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以至于她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这种混乱与惶惑,既是话语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也凸显了大众传媒的符号权力对话语秩序的控制力量,它在构建性别政治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并体现了对话语主体——享有“命名”权力的男性以及“无声”女性的控制。
[1][英]斯图亚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2][荷]L.van Zoonen:《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曹晋、曹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3][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页。
[4]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5][11]周松青:《“剩女”与性别统治》,《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5期。
[6]Foucault,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appendix of The Archaeology of K nowledge,P.216.
[7][8][10][1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59、3页。
[9]钱伟:《剩女,该将就还是要讲究》,http://www.ah.xinhuanet. com/2013-01/23/c_114470117.htm。
[12]“厌女症”的词源解释见百度百科释义。
[13]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1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15]Kate Millet(2000).Sexual Politics,U u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pp43-44.
[16][19][美]玛丽·克劳福德、罗达·昂格尔:《妇女与性别——一本女性主义心理学著作》,许敏敏、宋婧、李岩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2、103-104页。
[18]H élène Cìxous,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trans.A nnette K uhn,Signs:Journal of W o 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1(1981),p.42.转引自刘岩、邱晓轻、詹俊峰编著:《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The Symbolic Violence and Code of Power in Media Texts——An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s about Spinster
SUN Jin-bo1FAN Hong-xia2
(1.Foreign Language College,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6,China;
2.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Xinjiang Daily,Urumqi 830000,China)
spinster;coding/decoding;symbolic power;stereotype;gender’s order
"Spinster discourse",coined by media,has play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urrent gender ideology and gender order in China.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stereotypes about women shaped by spinster discourse and the phenomenon of stigma,and reveals the dimension of thinking from gender in the discourse,which embodies androcentrism,thus the discourse becomes a label of inequality of gender.Michel Foucault thinks discourse produces both knowledge and power. Spinster discourse aims to debase women's social image and value by nomination and definition.It tries to embed itself in the official discourse order and become an established one.It caters to male-dominated supremacy in the conventional ideology.In this sense,it becomes a symbolic violence.Male's fear and rejection of modern independent female is revealed by the production of the label"spinster",the coding of power,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s image,the association from the angle of moral and social evaluation,which also mirror 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 in women's cogni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role and modern identity.This question deserves our further consideration.
G210
A
2095-5170(2014)05-0156-05
[责任编辑:邱 健]
2014-07-1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疆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传媒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3X X W 00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由怀疑到信任:信息时代媒介与受众新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2JC X W 04 Y B)的部分研究成果。
孙金波,男,江苏泗阳人,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范红霞,女,山东东明人,《当代传播》杂志社编辑,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