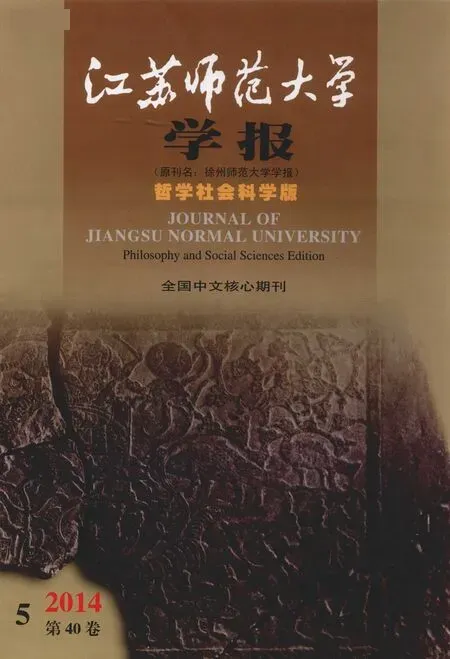论晚清厘金与印花税
杨华山
(韶关学院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了解决军饷问题,清政府被迫抽征厘金以充军饷。而厘金的功用也没有辜负清廷的“厚望”,正是在厘金的襄助之下,清政府才实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同治中兴”。按最初的计划,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厘金即应裁撤。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需款更巨,厘金不仅未能裁撤,反而推广到全国。同时,厘金的诸多积弊也日益加重,如直接提高了商品的成本和价格,造成贸易受阻,市场萧条;地方官绅、局卡吏役等肆意勒索商旅,祸国殃民;加剧了中外货物的不公平竞争,有利于洋货的倾销,损害了民族利权。因此,对厘金的改革成为晚清社会关注的一大问题,如“裁厘加税”、“裁厘统捐”、“裁厘认捐”等都是对厘金的改革方式[1]。除此之外,改征印花税以取代厘金的尝试也是晚清厘金改革的重大举措。学术界对晚清厘金及印花税均有阐述,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研究,本文拟对晚清厘金与印花税的转换及其失败作一初步探讨。
一
时人在指斥厘金的积弊时,或主张尽裁,或主张转换。由于厘金占清政府岁入近1/5,加之大清帝国财政拮据的困境一直有增无减,因此不可能裁撤厘金,只能转换取代。开征印花税即是转换取代厘金的方式之一。
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在论及改革厘金之弊的诸多措施中,即曾提到“或仿外国行印花税之法”,并介绍了两种印花和两种征税办法。“譬如商家合同及地契、租契、揭单、汇票、公司股票等项,一经输纳印花,即作奉准在案”,倘遇纠纷,必为按律判断,如无印花,则为私告官不理。在郑观应看来,印花税至少有三利,一是不需勉强,自愿输纳,二是无巡丁、委员勒索等费,三是税虽轻而征税多。他说,英国本土印花税每年收数一千数百万磅,“中国地广人繁,所收当不亚此数”[2]。为了顺利推广印花税,他还建议饬总税务司先从通商口岸试行,以兴利除弊而纾民积困。
就笔者目前所见,官方最早明确提出举办印花税的应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欲重整海军,但苦于经费不充,詹事府詹事志锐认为各省厘税杂捐,户部无籍可稽者不少,可令沿海省份年筹若干、非沿海省份年筹若干。李鸿章则以为因近年肆意搜括,各省已无有报之款,即使按照志锐所议饬行,恐怕也是一纸空文,回复必无实济。“万不得已,拟仿东西洋印花税一项,令各口试行,或可渐集成数。”但李鸿章同时也意识到印花税“事关创举,闻者以为烦扰,推行或有窒碍,只可姑存是说”,“仍声明恐与中国政体不合,如不谓然,即请删去”[3]。这一最早开征印花税的提议者本身就不自信,清政府更未仔细斟酌,当然被束之高阁了。甲午战败后,因筹款维艰,又有人奏请开设印花税。光绪二十二年(1896),御史陈璧即奏请开印花税。印花税创自荷兰,盛于英国,遍行各洲,简便易行,有利无弊,连日本每年亦征得二千余万,以中国之大,若仿而行之,“总计每岁所集,当不下一万万两,则不特洋债易于清还,从此罢抽厘停捐纳,举数十年欲除而未能之弊,一旦廓清,全局转机必在于此矣”[4]。这是晚清政府官员较早以印花税替代厘金的提议。总理衙门奏复也认为印花税利国便民,应该可以仿办,令出使各国使臣考察汇报各国施行印花税的情形,张之洞也电请驻俄、德、法大臣收集各印花税章程及式样,成为其后来主张行印花税的蓝本。
此后,官方和民间陆续有开征印花税以替代厘金之说者。各驻外使臣遵旨搜集的泰西各国的印花税情形陆续抄报给清政府,其中驻美使臣伍廷芳1896年的《请仿行各国印花税折》最为详备。他深感中外多故,筹款万难,“参考外邦理财之书,为中华自强之计,惟印花税一事,可以试办”,并胪列出印花税的“十便”:
富商大贾出入巨万,所征之税不过毫芒,揆之群情,当所不吝。其便一。债券地租无征不信,印花既贴,昭然若揭,民必乐从。其便二。懋迁交易,此税出于买者,而卖者不与,于穷民无所耗损,不致以厉民为词。其便三。关税、厘金皆征于货物未销以前,此则收之于交易既成之后,千百取一,何嫌何疑。其便四。户部总其成,各省下其法,或设总局督销,或发殷商代售,随时随地皆可分购,无委员检核之繁,无胥吏假手之患。其便五。他项厘税,名目不同,多寡不一,侵渔者众,漏匿者多。此税价值列于纸上,一目了然,无从隐匿,中饱之弊,不祛自绝。其便六。凡开局设卡取材于民,创办之始,必多怨谤。今听民间领购,无所用其抑勒,商民相信,必多购印纸以备用,预缴印税以纳官,奉上急公,自然而致。其便七。外洋之法,凡契券不贴印花纸者,即以废纸。单据已用,不涂销而再用者罚。贸易之人,必不吝小费而罹惩罚,互相稽考,可杜奸欺。其便八。各国通例,此项为内地税,与关税无涉,外人无从借口,他国民人经商我国,我既任保护之责,即有征税之权。通商之埠愈多,印花之数愈旺,不劳口舌,利赖无穷。其便九。欧洲此税,岁数千万。我亦渐次推广,库储既足,应办诸务,均可次第举行。其便十。
在中外多故、筹款维艰之时,印花税有此十便,下不病民上可利国,应饬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妥筹办法。为避免立即推广导致纷扰,“请饬令总税务司各关监督,于通商口岸先行试办”,“俟成效既著,逐渐通行,以顺民心,自无窒碍”[5]。
民间也多有倡议开办印花税者,尤其是有游历、经商海外经历的学者和商人,对国外的印花税有较多了解,将实行印花税作为自强之道,“今能仿此法附邮政而行之,一年小效,三年大效,其入款必有过于厘税者,其利孰甚,可惜当代之主持其事者,不能急其所急,为可慨也”[6]。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奏请坚决裁厘,但他也认识到惟千余万之巨款,非有以抵之,势难高议裁撤,“臣既奏陈印花税纸钞银行,计岁骤增入款四万万,比今五倍”[7]。谭嗣同借外人之语“谓中国之厘金,为呛商务喉咙之石灰气”,认为西方税法取于坐贾,不取于行商,最合中国古法,而印花税尤为便利商人,并具“八利”:无抑勒冤辱;局员、司巡无中饱;自买印花税票于行店,无交纳轇轕之弊;货无隐匿;沿途省去立局卡之劳费;惟于出口及到埠一查验而已,事简易办;无留难阻滞,时速而商利自捷;票轻于携带,无补水补数诸挑剔之弊。“八利具而厘金之弊去,弊去而上下交足焉”[8]。他建议先在一地一时试行,如在湖南岳州试办一月,然后渐推渐广,由岳州而湖南,由湖南而至全国各省。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关于开征印花税的提议,都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而中断。
二
庚子事变后,面对西方列强的空前压力,慈禧太后被迫改革,实行新政,在胁持光绪皇帝一路西逃的路上发布变法上谕,宣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还总结说晚近学习西法者,不过是其语言文字、制造器械等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变法上谕号召各部官员、出使各国大臣及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9]。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慈禧太后不仅拾起了两年前被自己无情镇压的戊戌变法,而且在舆论和效果上甚至超越了戊戌变法本身。慈禧太后的变法既有讨好列强的心理,更有筹措巨款赔付巨额外债的压力。面对四百五十兆的空前赔款,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各就地方情形,悉心筹议,以期凑集抵偿,迅速电奏。因此,在所有关于变法的奏折中,如何筹款都是核心内容之一,于是开征印花税便被更多的清廷官员提及。
在内外大臣纷纷响应慈禧的变法号召而上书言事中,最著名的当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会衔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变法三折”之三《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第八即为“行印花税”。张、刘二人认为,印花税的大意在“抽银不抽货,抽已卖之货不抽未卖之货,抽四民百业凡有进项之人,不仅抽商贾贸易之人”。现在变法筹款,印花税可以仿行;而且新商约谈判正在商议增加关税,西方列强必定要求裁撤内地厘金,如果开征印花税,正好可以借资抵补。张、刘还比较了英国和日本的印花税章程,认为英国的最为详密,日本的具有东方特色。“但中外情形略有不同,外国商富民饶,产业价值贵,银钱往来多,故所抽巨;中国商贫民苦,本业既微,转移亦少”,所抽有限;至于遗产税,英国最多,每年可收八兆余镑。但中国产业本廉,又子孙相继,虽然不能多征,即使得英国二十分之一也可征得五六百万元。英法等国开征印花税之初也多有梗阻,后经改革始得畅行。因此,“中国初办之时,隐匿必多,推敲过细,不免纷扰,只可稍微从宽,不求算无遗策,必须十年八年以后,稽核之法渐周,自然日臻畅旺”,故应“敕查各国章程,斟酌妥议举办”[10]。
除张之洞、刘坤一之外,署理浙江巡抚余联沅致电军机处“请行印花税”;江西巡抚李兴税致电军机处请设银行、制银纸、饬圆法、办保险四事之外,尚有印花税,“若各省一律举行,不难骤盈千万巨款”;两广总督也致电军机处仿行印花税,“约略计算,每年可得千万之谱,有裨时局匪浅。如钧处谓然,请旨饬下户部,查照各国印税章程,参酌妥善通行照办”[11]。
此外,张謇在响应清廷变法上谕而作的《变法评议》中列举户部应办十二事,“行印税而裁厘金”即是其一。根据统计,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各省厘金收入总数约为1500万两,裁厘之后的印花税须与此数相当。张謇的办法是:“令各省列表,开列五年各物进出(进则落地,出即产地),及经过所收之厘数而汇于部;部为析之,取其中数,匀经过厘于产地、落地,加收三成,寓于每张印花之内;产地、落地,各收其半。分令各府州县赋税官饬各业立税会承领总数,行用印花,犹江浙包捐之法。稽查检视,责之警察。”[12]这样下省一切船头查舱红钱黑费,上省一切局卡员司丁役薪费。1906年,张謇在答张之洞书中进一步主张“尽裁中国厘捐,改行西洋印花”。尽裁中国厘捐,则可以回已去之人心,留未去之人心;改行西洋印花,则可以保中国之利权,揽各国在中国之利权。其具体实行办法,“凡一印花下签说声明,然后由户部斟酌定式。损益价值,发交总督。每一州县,派员设局经理,优给薪水,明示章程。每一业立一会,每一会立一董,董以印花分发同业。各行铺如领捐票,按月稽其已用之数,未用之数;已用者按直缴钱,未用者留待下月”[13]。印花税实行之初,厘捐不必全部裁撤,但严饬捐卡遇有印花者,则立即放行,或者另给一旗帜,作为已完纳印花税的标明。这样三五个月之后,使大家都知道印花税的便利,而后再尽裁厘卡。
上述这些开征印花税的主张者由于其所处地位不同,各有侧重。谭嗣同、伍廷芳主要着眼于开办印花税的好处,一为“八利”,一为“十便”;张之洞、刘坤一位高权重,虽然明白开征印花税的好处,而且借鉴英法日本,但他们深知每一项改革的艰难,欲速则不达,因此并不急于求成,而是寄希望于“十年八年”之后达到“日臻畅旺”的目标;作为状元实业家,张謇对厘金之弊有切身感受,对印花之利期望甚殷。他对工商实业亲历亲为,故对印花税的论述重在具体实行的操作技术层面。他们的共同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以印花税取代厘金,如此既可以免厘金积弊,又可以抵补裁厘之损失,于国于商于民均有利而无弊。应该说,这些各有侧重的述说基本上厘清了开征印花税以替代厘金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但问题的关键还是作为地方督抚大吏的张之洞和刘坤一看得更为清楚。他们本身是大清帝国的洋务派改革者,对改革的艰难曲折有深切体认,所以给予了“十年八年”之期。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的新政全面展开,不知有多少比印花税更重要更急迫的要务亟待清政府处置,最终印花税未及实施,大清帝国便黯然退出历史的舞台,而这正好是张之洞、刘坤一所规划的普遍实行印花税的“十年八年”之期,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讽刺。
因此,开征印花税以取代厘金的建议朝野都有反对的声音,在清政府也未能得到认真的反应。清末新政时期,为筹款赔款练兵,又有人提议开征印花税,清政府以中国警察尚未普办,警学尚未精深,稽核恐难得力为由,诏谕从缓办理。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曾奏请试办印花税,获得清政府同意。袁世凯向日本印刷局订制了四种印花税票纸样,分两期交收,头批印花票纸运交到筹款总局[13]。但试办之初即遭商民的极力反对,不到三个月,清廷又下旨“印花税事属创行,恐滋扰累,著从缓办理”。同时庆亲王奏请举办印花税,清廷令户部妥议,户部仍主张从缓,建议俟各省警察办成之后,仿行各国印花税成法,“再行逐渐推广,以昭慎重而裕饷源”[15]。
巨额赔款之外,新政、练兵等在在需款孔急,而随着清政府禁烟政策的实施,收数颇丰的洋药、土药税厘渐绌,税款抵补问题必须解决。清政府对此问题的认识虽然不及英、日等列强及时与深刻,但如何抵补毕竟是现实而急迫的问题,开征印花税以资抵补的方案还是被提出来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郁生奏请开办印花税,“拟请饬下部臣、疆臣,考察各国新章,或择要先行试办,以为抵补土膏税厘之地”。这一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积极回应。新成立的度支部“以实行禁烟,洋土药税绌,奏请仿行印花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旨谕度支部:“国家岁入洋土两药税厘为数甚巨,均关要需,现既严行禁断,自应预筹的款,以资抵补。前据度支部具奏,研究印花税办法,当经允准。惟烟害必宜速禁,抵款必宜速筹,著度支部详细调查东西各国成法,迅速研究,渐次推广,期于可行。限两个月内条例办法章程,奏明办理,勿得稍涉延宕。”度支部认为现拟印花税办法,应先从宽简入手,疏节阔目,略植初基,但求养成人民贴用印花之习惯,不能骤计国家收入巨款,将来设法推行,逐渐周密,商民既遵循有素,财政自可藉以扩充。“谨就各国成法,参酌中国情形”,拟定了《印花税则十五条》和《印花税办事章程十二条》,同时提到中国幅员广阔,风尚习俗所在不同,此次定章如有未能推行尽利之处,应由臣部体察情形,随时修改,并准各督抚各就地方情势详细体验,分别奏咨变通办理。“至此次办理印花税,系为筹补洋土药税厘起见,将来收有成数,再当由臣部分别酌量拨给各省,以资弥补”[16]。
《印花税则十五条》的第一条规定:“凡人民之财产货物,当授受买卖借贷之时,所有各种契据、帐簿可用为凭证者,均须遵章贴用印花,方为合例之凭证。”第二条将各种契据、帐簿分为二类29种,并规定了每种的税额,如提货单、银钱收据等,价值合制钱十千文以上者,贴印花二十文;汇票、期票、借款字据、田地房屋典押契据、铺户或公司议订合货营业合同等五种纸面银数不满一千两者贴印花二十文,一万两以下贴印花一百文,一万两或一万两以上贴印花一千文。《印花税办事章程十二条》规定由度支部设立印花税局,派员管理印花税事务。各直省藩署、或相当局所附设管理印花税处,专司本省发售印花事宜。发售印花,照票面价值提7%作经售人费用,其中总发人应得3%,分售人应得4%。同时要求各省地方以地方官奉到部发印花后三个月为施行之期。未施行以前,应先由地方官将印花税办法、税则及种类式样、开办日期,于各府州县之城镇、村市详细出示晓谕。印花税则及章程奏定后,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曾就某些条文提出异议,度支部一一回复,认为并无不妥。
度支部的征收印花税方案得到清廷批准,光绪三十四年正月饬令直隶先行试办,并令于宣统元年九月在全国开征印花税。但是,在印花税推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言官、地方政府、士人和商界的抗议与抵制,或群起反对,或恳求缓办。尽管度支部仍极力推行,实际效果却极不如意,不仅鸦片税款的抵补目的未能达到,而且招致了沸沸扬扬的反对风潮,直到清帝退位,印花税的征收并无实效[17]。
三
清政府推行印花税遭到普遍的反对,只有湖北省较有实际举措。
光绪三十四年,湖广总督赵尔巽在湖北试办印花税,筹拟了办法,并设立了印花税总局,计划分四期实行,第一期包括武昌、汉阳两府于宣统元年开办。由于事起仓促,宣传不周,实行无力,武汉商人要求缓办,遭到湖北地方政府拒绝,故前往购买贴用者仅官、学、军各界,真正应该购买贴用的商界响应极少。如一年的印花税收入中,官、学、军缴印花税制钱2万余串,而汉口和武昌商民所缴税款只有1千余串。在此情况下,湖北自第二期以下不得不停办。其他各省或成效不大,或未及认真实行。清政府所编宣统四年的全国岁入岁出总预算表中,印花税收入预算只有银九万三千一百八十七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由此也可见开征印花税的成效之微。
在西方卓有成效的印花税在大清帝国却走向了另一面,其原因很复杂,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此时推行印花税已背弃了先时主张开印花税者的原意。印花税本为替代厘金而设,而清政府却是为了抵补因禁烟而造成的洋药、土药税厘的减少。因此,印花税不仅未能取代厘金,反而成为厘金之外的又一项额外税捐。各地甫一试行,即遭到普遍的反对,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苏州各业如钱业、典业、纱缎业、绸缎业、米业、酱业、珠宝业、肉业等等纷纷具书反对印花税,苏州商会将其汇编为《苏城各业缓办印花税理由书》。江苏谘议局则以为印花税事属创始,商民未尽熟悉,办理又未必得宜,“近年商情凋弊,既苦于旧有捐税未能分别减蠲,又苦于推行新政辄增种种负担,积困生疑,积疑成阻,系必至之势”[18],故议决从缓实行印花税法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天津试办印花税时,天津商务总会多次致函天津县衙,禀陈天津自庚子事变,商业破坏已达极点,旋因举办新政,捐税加征,商民困难,哀恳推缓印花。又禀报农工商部及直隶总督杨士骧,陈述天津商业艰难之状,“拟请将印花税暂行缓办”[19]。杨士骧、农工商部均驳回申请。嗣后各商联合缓办之请纷至沓来。如五月有796家商号、次年八月更多达1877家商号联名上书请求缓办,宣统二年七月各行草拟出津地缓办印花税的十二条理由。常州、保定、成都、正定、汉口等各地商会也为之声援。当广东省实行印花税法时,“商民因而罢市”[20]。不久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清末试办印花税的方案亦告失败。
当人们痛恨清政府腐朽没落、专制独裁、冥顽不化时,客观而论,自太平天国起事,清政府在内外冲击之下其实也一直在筹划改革之中,尤其是清末新政,改革力度之大与步骤之快超出了清政府本身的承受与领导能力。清政府在改良与革命的双重压力之下改革,改革又进一步唤起了国人的参与意识,“人们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的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21]。改革千头万绪,而政府手忙脚乱,捋不清轻重缓急,摸不准主次难易,结果左右遇困,上下难调。印花税对厘金的转换变成了对鸦片税费的抵补,典型地表现了清政府的无能与失措,与其说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不如说是清政府选择了自己的归宿。印花税抵补厘金的失败正是大清帝国灭亡的一个缩影。
[1]杨华山:《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派的“裁厘加税”思想》,《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2]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7-558页。
[3]《李鸿章全集》第7册,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9页。[4]陈璧:《请仿行印税折》,《时务报》第五册,第7页。
[5]丁贤俊等:《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5-57页。
[6]《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354页。
[7]张涛光:《康南海经济科技文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8]《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3页。
[9][10]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1-4602、4765页。
[11]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950-952页。
[12]《张謇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13]《张謇全集》第二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14][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两次试办印花税史料》,《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
[15]《东方杂志》第一年第7期。
[17]刘增合:《清末印花税的筹议与实施》,《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18]章开沅等:《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0页。
[19]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9页。
[20]周秋光:《熊希龄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页。
[2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