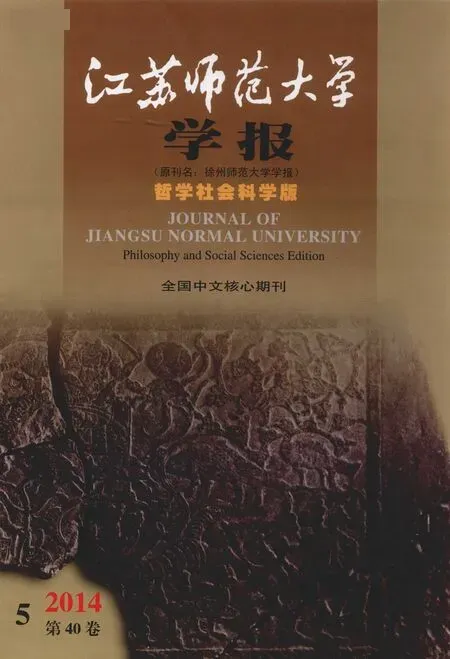唐代讲唱文学的民间性及其文化意义
谢思炜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00)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使一批唐代讲唱文学作品与通俗诗一道重现于世[1]。与其他敦煌文书不同的是,只有这两类作品在传世文献中无所归属,二者一起出现也揭示了它们共有的某种特殊民间性。在上世纪,以《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从语言学角度揭示了讲唱文学的民间性;在表演、文体和其他形式方面开展的探源溯流工作,则揭示了讲唱文学的各种民间、宗教来源和复杂的构成脉理。本文认为,讲唱文学的民间性不同于一般的民间文学或口头传承文学,它属于上层文人创作和民间自发创作之外的第三种文化产品。为此,需要对它的社会功用、生产条件及其作品内容和叙事方式进行更为全面的综合考察。
一、讲唱文学的社会功用和生产条件
唐代讲唱文学与此后的宋元话本、长篇演义类似的是,所提供的都是一种在一个长时期内形成的活动性、生长性文本,无法确定其产生的精确时间。但无论从表演形式还是从作品的选材、叙事技巧来看,唐代讲唱文学又自成一体,与后代的说唱文学、表演艺术明显有别。因此,我们有可能但也只能对它做一种断代的整体性考察。与讲唱文学相比,通俗诗(如王梵志诗)具有鲜明的时事性,说明至少其主体部分有比较确定的创作时间,有可指实的或想象出的一两个作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传统相对单纯,可以由一两个人的思想活动统贯起来。讲唱文学除个别晚出作品(如《张义潮变文》)外,不具有时事性,它也不是某个个人思想活动的表达。它的产生既需要更长时间的培育,也涉及更多方面、更为复杂的思想传统和文化因素。讲唱文学与通俗诗二者的社会功用也因此有明显区别。
对变文语义和讲唱文学表演形式的考察,不可避免地会追溯到佛教的宣教,会导致对俗讲制度和程序的细致探讨。但不可否认,局限于佛教宣教范围内的讲经文,在文体(包括语言和叙事手法)和思想意义两方面都不足以充分代表唐代讲唱文学。事实上,讲唱文学的表演者和表演形式、表演内容都在唐代的某一时期摆脱了佛教宣传的限制,成为一种世俗性、民间性的文学活动,就如通俗诗也具有广阔的民间思想背景一样。且不论讲唱文学中还有说话、词文、俗赋等其他民间伎艺形式和成分,只看从佛教讲经文向变文的发展,其间固然存在着形式的借鉴和挪用,但导致这种发展的并不仅仅是讲说题材和范围的扩展、转移,不仅仅是从佛教题材发展为其他题材。宗教源头确实给讲唱文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它毕竟在唐代的新生产条件下完成了其世俗性转变;在始终保留继承某种宣教性的同时,在某种思想文化动因作用下具有了远比单纯宗教布教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宣教性一方面源自宗教,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中国的一般教化传统有关,使讲唱文学在基本性质上不同于直接感发性、表达性的民歌和民间文学作品。它因而是一种次生的、二次性创作,后者才是初生的、第一次创作。所谓宣教性是指讲唱文学必须以某种经典为据,成为对某种经典的演绎、解说。在这一点上它与通俗诗和戏剧表演形式也有所不同,后者包含很多感发性和原创性内容。讲唱文学的题材就依它所演绎的经典文本的不同而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佛教经典演绎为讲经文和佛教题材变文,第二类和第三类分别由史传和民间故事演绎为历史题材和其他题材的变文、词文、话本等。其中民间故事如孟姜女故事、王昭君故事、韩朋(凭)夫妻故事,原本含有传说因素。它们进入唐代讲唱文学固然可以视为故事本身流传演变的一个阶段,但在宣教性社会功用的规定下,这种演变受到经文演绎和史传演绎的影响、同化,也成为一种具有明显教化意义的演绎。它们与史传故事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有正史来源,而史传故事在进入讲唱文学之前大概也经过类似的民间传说中的演变。演绎性固然是叙事文学流传的一般特征,但其中是否渗入具有反思性的宣教意识和渗入程度如何仍会带来很大区别。讲唱文学在这一点上与所谓口头传承文学(如民歌、民间故事、某些民族的史诗)根本不同,后者始终是一种原创性的创作。讲唱文学的某些题材可以溯源至民间,但就其整体和基本性质而言,则不会像民歌或民间歌舞那样自发地产生于民间。
不过,宣教性也仅仅是讲唱文学社会功用的直接表现和表面化形态,并不足以将其从宗教宣传和一般教化传统中区别出来。宣教性来源并从属于这类文化产品的一种更重要的社会功用,即它的文化认同作用,后代通俗文学在这一点上与唐代讲唱文学具有共同性。它们都不是纯粹的乡土民间或市井社会的产物,也不是单纯的口头文学作品。它们是一些作者(虽然身分、姓名等很难确切考知)有目的地写出来的,或依照某种程式演绎加工出来的。由唐代作者开拓出的这类创作,其历史延续了千年以上。在上层知识分子的文化制作和民间自发的创作之外,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可能与民族的文化需要有关。由于史官文化传统的建立,神话传说早在先秦时代就已被充分信史化。汉民族缺少神话和史诗传承,不仅体现在官方和知识阶层的文化系统中,也深刻影响到民间的文化传承。在缺少民间神话和史诗传承的情况下,民间仍要保持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社会下层民众当然不会自外于这种民族文化认同——就需要向官方和知识阶层记载的民族历史寻求资源。由此可见,正是民间固有的这种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需要,为变文中的历史故事以及后代的讲史、通俗演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当然,原有的民间故事传说只要同样能够满足文化认同的需要,也会成为被加工的资源之一。这种向上层文化经典寻求资源的需要,与佛教向民众宣讲教义的需要不谋而合,它们均需要寻找一种适合向普通民众宣讲的形式,于是形成了变文、讲经文等主要形式。
当然,讲唱文学由于面对民众,在内容上谈不上雅驯,做不到“不语怪力乱神”。但这不过是文化一般特点的反映。六朝至唐有大量志怪传说产生,并且不分上下阶层,覆盖了整个社会,讲唱文学也因而掺杂有大量志怪成分。但讲唱文学就总体而言,不同于单纯的志怪文学,并不以“述异”、“稽神”、记录志怪神异故事为创作动因,也没有提供任何一种稍具系统的民间信仰、神怪谱录。这些志怪成分在作品中基本上仍处于从属地位,附属于作品整体的宣教和文化认同目的,正像大量佛教神异故事和道教法术故事服务于其宗教宣教目的一样。讲唱文学不能背离民族文化的一般状况。在佛教讲经文范围内,讲唱文学仍以宗教教义为思想准则;而一旦进入世俗生活领域,它就必须以世俗社会的道德伦理思想为基本原则,用它来整合统摄各种文化因素、思想因素。
然而,讲唱文学为什么到唐代才出现,且其社会功能才得以发挥?除社会需求外,这显然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有关。敦煌文书用大量作品印证了历史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条件在唐代开始成熟。唐以前既无这种性质的作品,也没有任何有关记载。唐代讲唱文学和通俗诗同样担负着向民间宣教的任务,也就是向目不识丁、没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的下层民众传输某种知识和思想,进行文化输导。承担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接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同时又因社会地位或思想原因与社会下层保持密切联系,与下层民众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符合这种条件的一方面可能是宗教人士,比如像王梵志那样具有佛教教育背景或本身即为下层僧侣。佛教一向比儒家和官方更重视向普通民众宣教,其教义的平等精神也更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它不仅在宣教性和宣教形式上为讲唱文学提供了示范和重要源头,而且也在传教中培养出了一批适合从事通俗宣教的人士。也正是在这些人士的努力下,佛教内容在讲唱文学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
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由于实行科举制度和官私学校的兴办,唐代的教育普及率较之前代有较大提高,由于官员和胥吏需要大量后补者,教育的辐射范围已深入社会基层。《通典》卷十五“选举”提供了有关科举考试的一组数字:唐代“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十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以降,凡十二万馀员。……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这12万馀人只是进入官学及后补官员系统的人数,没有包括通过私学、家学受教育者[2]。此外,《通典》卷四十“职官秩品”还提供了唐代官员和胥吏的定员数,其中内外文武官员总数为18,085人(同上),内外职掌(其中包含一部分品官,也包括仓督、佐史、里正等胥史)总数为349,863人。前者人数不及后者的1/20。官员是科举考试胜出者,受到较好的文化教育。胥吏则至少需要粗通文墨,科举失利者也可能进入这一阶层。在胥吏身后,至少还应有两到三倍的后补者。这样,整个社会中接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人数至少在百万左右,约占人口总数的1~2%[3]。根据以上推算,这部分人中只有百分之一能够通过科举成为官僚—知识阶层的一员,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不得不委身胥吏。可见在唐代由科举主导的教育制度下,绝大部分人不能如愿上升,在胥吏之外至少还有几十万人流落于民间。他们之中身份较卑微者,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寻求与民间需要、民间意愿结合的途径。哪怕其中只有千分之一的机率,就将为讲唱文学提供数量可观的有才情、有思想的作者。世俗题材的讲唱文学作品就应出自他们之手。敦煌作品的内容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舜子变》在叙事段落中反复出现:
舜即归来书堂里,先读《论语》、《孝经》,后读《毛诗》、《礼记》。[4]
唐代明经考试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两中经,《礼记》属大经,《毛诗》属中经,《论语》、《孝经》须兼习[5]。这段叙事反映的即是唐代授学的实际情况。《敦煌变文集》所收《秋胡变文》[6]也开列了一个唐代读书人的书单:《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榖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此外如《伍子胥变文》,其中大量运用诸如“儿闻桑间一食,灵辄为之扶轮;黄雀得药封疮,衔白环而相报”、“刘寄奴是余贱朋,徐长卿为之贵友”等典故成语。又如文中描写伍子胥窜身吴江:
唯见江乌出岸,白鹭争飞,鱼鳖纵横,鸬鸿纷泊。又见长洲浩汗,漠浦波涛,雾气冥昏,云阴靉靆,树摧老岸,月照孤山,龙振鳖惊,江豚作浪。若有失乡之客,登岫岭以思家;乘查之宾,指参辰而为正。[7]
这样优美的文笔在讲唱文学作品中虽不常见,但足以表明其作者身分,说明讲唱文学的特殊文化属性[8]。它们在20世纪重见天日,既是一个偶然事件,又包含某种必然。因为有这些人的写作和抄写,才可能有这些作品的流传收藏。唐以前没有相应条件,也就没有这种性质的作品。宋以后由于文人参与程度进一步加强,通俗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也愈来愈丰富。
二、讲唱文学的伦理主题
如果说以王梵志诗为代表的通俗诗主要体现了佛教向民间文化的输导,讲唱文学则在更大范围内体现了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的输导。但这种输导并不是单向的,与统治者和知识上层的提倡灌输尤其无关,主要是适应民间需要通过下层知识分子的介入而完成的。这种输导之所以通过讲唱文学来完成,自然与它的独特表演和体裁形式有关。这种形式一方面具有当面宣讲的感染力,并提供一种集体性的娱乐形式,不像诗歌那样单纯通过文字载体或简单的口耳相传形式传播;另一方面与戏剧等表演艺术相比,又以语言形式的讲说为主,其他艺术表演元素处于辅助、次要的地位。因此至少在这一阶段,其娱乐因素尚不是十分突出,在总体上不及百戏和其他歌舞伎艺,也少见有著名艺人[9],所满足的主要是民间的知识教育、伦理教育的需要。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讲唱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别适应于这种文化输导的需要而发展繁荣起来的。但正像王梵志诗在宣讲佛教教义的同时并不妨碍它表达下层民众的思想感受,讲唱文学在演绎经文、史传故事和其他题材故事时最重要的作用和特点,就是自觉适应民间伦理教育的需要,表达下层民众的思想意愿。
讲唱文学的这种作用体现在它的题材选择上。讲经文暂且除外,其他讲唱文学作品的最重要主题就是宣扬孝道,这类题材的代表作是《舜子变》(原题《舜子至孝变文》)。除世俗题材外,这一主题也渗入到佛教题材中。作为讲经文附属形式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是后代广泛流传的二十四孝故事的早期文本。被称为“佛教孝经”的《佛说盂兰盆经》,在唐代曾由著名僧人作注疏[10]。在讲唱文学中不但有《盂兰盆经讲经文》,而且出现了据该经改编的《目连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二者在内容上多有一致,使得这一题材成为连接讲经文与变文两种形式的特殊文本。《目连变》在敦煌写本中写卷极多,在当时流传极广,对后代影响极大。此外还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对本来即产自中土、宣扬孝道的“伪经”《父母恩重经》再加敷演宣传。
不难看出,孝道主题在讲唱文学中尤为突出,是由于孝道作为中国社会基本伦理原则除得到统治阶级有意褒奖提倡外,还有更为广泛深厚的民间思想基础,同时在唐代还有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亟待解决,即得到普遍信仰的佛教如何修正其教义、与孝道伦理原则相适应。在唐以前,佛教因其不敬王者、不跪父母的教义,曾一再遭到儒家思想和统治阶层的批判抵制,佛教传教也确实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对中国礼俗的破坏和冲击。唐代统治者曾一再发表诏令,告诫佛教必须“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自今已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至于丧祀轻重及尊属礼数,一准常仪,庶能正此颓俗,用明典则”[11]。此外,前代佛教思想家如慧远,则着重阐述出家修道与在家信佛之别,不反对在家信佛者忠君孝亲,试图以此来兼顾儒释,使各循其规[12]。讲唱文学所反映的民间思想则与上述思路不同,它将抽象的教义和思想讨论抛掷一边,对佛教与世俗礼教明显冲突的部分也不作正面回应,而是直接从佛教的各种故事人物、喻象演说形式中发掘其可被改造的歧义性内容,将孝道思想直接导入佛教,以这种方式来修正佛教教义,使佛教伦理与中土民间伦理逐步融合无间。这种修正既有对《盂兰盆经》等佛经中孝行人物的发掘,又有《父母恩重经》对父母恩德的真切描述和讲唱文学的进一步渲染,以及对佛教人物故事与儒家思想人物的直接大规模比附,如《二十四孝押座文》所说:“目连已救青提母,我佛肩舁净饭王。万代史书歌舜主,千年人口赞王祥”;“如来演说五千卷,孔氏谭论十八章。莫越言言宣孝顺,无非句句述温良。孝心号为真菩萨,孝行名为大道场。……佛道孝为成佛本,事须行孝向耶孃。”[13]这些宣讲演说来自民间,远比儒家经典《孝经》之类的枯燥训诫更贴近民众生活,更能显示亲情恩义,更易打动人心。佛教经过这番改造、伪托和重新解释,其与儒教和世俗伦理的冲突被基本消解,统治阶层和上层知识分子未能很好解决的意识形态矛盾在民间伦理、民众生活中基本得到解决。
佛教经典和教义在这种通俗宣讲中被改造,自然可以视为佛教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的一种姿态。但这种改造是由本身为中国社会伦理观念深深浸润的民间人士完成的,所以不如说是他们代表了中土民间思想和民众力量来进行这种改造。没有这种改造,佛教就不会在中国民间生根。统治者或官方意识形态对佛教的接受或拒斥,都不能代替或抵消这种改造的强大力量。
除对佛教实行改造的意义之外,孝道主题的突出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间伦理在当时对上层社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孝亲与忠君两大伦理原则本来具有伦理的一致性,但在君权专制下又往往相互冲突。唐代上层社会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在观念上和礼法实践中都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唐太宗倡导忠君之义,改变魏晋以来的君父先后观念,“其用意在于辩护自己的玄武门之事”[14]。唐代官员夺情起复、不守丧制,宗室内“贵加于尊”、不拜舅姑等等现象,都一再引发争议[15]。在这些争议背后所反映的,则是宗族势力衰弱、君权加强以及科举官僚制度建立等社会结构的变化。在魏晋以来门阀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礼法观念此时遭受一定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护孝亲原则、理顺忠君与孝亲的关系,是礼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讲唱文学作品宣扬孝道,是民间的自发诉求,与唐代的新社会关系相协调,反映的是以自耕农家庭为代表的广大乡村和社会基层的生活观念和伦理要求。尽管这种宣传在当时不一定有针对上层社会礼制错乱现象的特别意义,但恰恰是唐代这种以普通家庭为核心的社会基层形式成为此后中国下层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这一阶层所表达的伦理要求和思想也必然得到上层社会的遵从和呼应,是统治阶级在进行意识形态调整时不能不重视并必须参照的。唐代讲唱文学以孝为主题,宋元戏曲《赵贞娘》等以贞为主题,讲史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以忠为主题——在这几个历史阶段中,通俗文学中主题的变迁恰好反映了道德意识在社会整体变化和上下阶层互动中的选择和强化。
以宣扬孝道为中心,讲唱文学作品将劝善惩恶的道德主题扩展到与家庭伦理有关的各个方面。如《伍子胥变文》宣扬复仇观念,《汉将王陵变》、《李陵变文》表现男子尽孝与尽忠责任所导致的困境。此外,《孟姜女变文》、《韩朋赋》、《王昭君变文》等作品表现和歌颂夫妻双方纯朴的忠贞之情(当然也有谴责暴政昏君的意义)。就民间观念来看,夫妻关系对他们来讲是相对平等的,一夫多妻、喜新厌旧之类事情很少进入他们的生活经验。因此,同时代文人传奇中的士人风流故事并未进入讲唱文学[16]。尽管讲唱文学本身是一种宣教性而非自发性的创作,但上述各类作品所传达的道德意识却是来自民间、与民众生活自然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与社会结构变动相适应的社会整体道德观念形成和调整的自然过程。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道德意识的形成,所谓“移风俗,美教化”,其中真正来自统治者“化下”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从来恶行败德在贵族和统治者中间发生的概率都远远高于民间,在社会变动时期尤其如此。道德的深厚力量其实来自民间,来自普通民众的生活伦理。正是植根于民间的这种深厚力量,使整个社会具有一种道德的自洁能力。唐代讲唱文学和其他道德宣讲所发挥的就是这样一种功能,它们也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物故事在后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中的发展并不均衡。伍子胥故事仅偶见于戏文,王陵、李陵故事则完全退出通俗文学领域,只有夫妻题材的作品得到较多继承。这可能是由于某些事件不够典型,人物不够有名,如王陵;也可能是由于人物事件的涵义太过含混复杂,引起较多争议,如伍子胥复仇叛国、李陵降敌辱身。通俗文学由其功用、性质决定,要求道德定义更为鲜明,人物定性更为纯粹,上述几个人物故事自然便被淘汰了。这反过来说明唐代讲唱文学在选材上还不够成熟,思考也相对简单,只考虑了其中所包含的孝亲因素。
唐代讲唱文学中最特殊的一篇是《唐太宗入冥记》[17]。它的题材涉及唐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以特殊变形方式讲述了唐代统治者讳莫如深、一般文人亦绝少敢言及的玄武门之变。学者曾诧异于唐人殊少忌惮,竟将此事形诸笔墨[18]。由于题材的敏感性,该故事的产生应当与上层人士或文人没有什么关联[19]。在唐代,官方禁忌从未达到能控制整个社会言论的程度,民间思想自有其表达空间,可以借助某种观念形式正面处理这一题材。初唐张鷟《朝野佥载》曾言及此故事梗概,有“冥官问六月四日事”语[20],说明此故事产生时间很早,可以看作民间舆论对玄武门事变的直接反应。一般来说,民众对宫廷政治斗争并无特殊兴趣,通俗文学作品很少涉及此类题材。唐太宗故事成为例外,除了其中引入的佛教冥间、冤报思想对民众的吸引外,显然与这一事件涉及的伦理内容有关。出于维护政统合法的需要,在唐太宗授意下,唐代官方记载不但对玄武门事件的真相百般掩饰,而且拿出所谓周公诛管蔡之说替夺政者洗脱[21]。根据某种新历史观,权力争夺中手段是否合法似乎也不再是史家关注的焦点。但唐代的民间舆论却不这样看,该作品直接借冥间判官之口,称太宗“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从简单的人伦善恶标准出发,确认了当事者李世民的罪责。这恐怕并非是有某种特殊势力意图挑战统治者权威和官方说法,也不仅仅是在事实认定上对官方说法表达异议。弑兄戮弟的事实本来十分清楚,民间的判断标准也很简单,即便承认所谓周公诛管蔡说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统治者的作为由于与这个简单的人伦标准相冲突,在作品中必然遭到谴责。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深深植根于普通民众的最基本的人伦善恶标准是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哪怕你是权力最大、功业最隆、被称为最圣明的君主!对这一伦理底线的坚持,在知识阶层慑于政治权力均噤声无言时,只有通过民间形式和通俗文学才得到表达的途径。仅此一点,就使我们不能不惊异于讲唱文学的特殊精神力量和思想意义。当然,敦煌作品以及张鷟的记载都加入了其他一些观念因素,使故事具有了多义性;同时作品中还有要太宗抄《大云经》、修功德的情节,适当利用了统治者本人对佛教的崇信和对冤报的恐惧,从而使这种对统治者不道行为的谴责变得不那么触目,这件作品在当时之所以能够产生和流传也就相对容易理解了。
三、讲唱文学的叙事方式
讲唱文学在接受和适应下层世俗社会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同时,其所采用的叙事内容和策略同样体现了民间精神世界的特殊性。从题材来源上看,佛教故事本来具有传说或寓言故事的基本特点,十分适合被讲唱文学吸收。另一类道教神异故事则属于初创性质,在叙事方面尚嫌粗糙,仅以其神异内容吸引群众。民间故事和经过民间流传改编的史传故事因为本来就与讲唱文学的改编机制内在吻合,也很自然地成为讲唱文学的重要题材。只是史传作品的改编在唐代还不够成熟,在选材和叙事表现上都缺少经验积累,仅仅为此后的讲史和历史演义小说传统开了个头。如果将这几类故事与文人创作的唐传奇对比,不难看出差别。文人传奇作品除取材本阶层生活外,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叙事方面基本上不讲虚构,在真实生活经验之外不敢越雷池半步[22]。讲唱文学作品恰恰相反,它们不是个人生活经验的产物,而是依赖于各种来源的经典故事,基本上不需要写实。作品所包含的某些带有现实因素的描写,如《伍子胥变文》写子胥逃亡,《舜子变》写舜子遭杖,顶多是以折射方式将现实情况写入作品。
适应于普通民众的思维习惯和欣赏需要,讲唱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具有前现实主义文学的一般特征,其人物不仅具有明显的类型化特点,而且往往为某一道德理念支配,作为其化身出现于作品中。如作为至孝化身的舜子、目连,作为复仇者的伍子胥。早期叙事作品中的这种理念型、类型化人物,就如通俗文学作品中传播的道德观念一样,不能简单地视为某种道德说教的产物。它们实际上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生活的认知方式,是用来满足他们坚持某种生活信念的需要的。广大群众需要在作品中看到的并非真实生活本身,而是他们理解和需要的一定的生活原则。因此故事内容必须被这些原则整理和贯穿,这样生活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作品才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所以这些作品在产生过程中并不在乎人物性格是否真实,只需要定义鲜明的类型化代表。
与作为道德理念化身的舜子、伍子胥等相对立的,是对其施以迫害的恶继母、暴君、奸邪佞臣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正反面人物对立中,比较多地出现了反面的暴君、昏君形象,如楚王(《伍子胥变文》)、楚霸王(《汉将王陵变》)、汉帝(《李陵变文》)、宋王(《韩朋赋》)等。《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残缺过甚,但据故事内容而言,谴责暴君和昏君的主旨也不会有变。在君权至上的社会结构中,民间创作自然选择了更多的以君主为中心、由君主控制他人命运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合乎逻辑地导向对君主罪恶的谴责。其中尽管不会有任何挑战君权、鼓吹造反的意图,但显然真实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生活的直观感受。这与文人诗文中小心回护君主形象的做法恰好形成鲜明对照,也与后代清官戏盛行的意识形态背景大有不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唐代民间完全不自觉的、集体完成的寓言活动,但这是一个比任何文人的比兴寄托都具有更深刻涵义的寓言现象。佛教把人生痛苦的原因归结于人本能的贪欲,王梵志诗也宣传这种观念。这是一种理智层面的分析,自有其道理。但叙事性作品一旦涉及社会性苦难,便自然将所有责任归于社会主宰者——君主。这是叙事和生活的逻辑使然。与真正的社会批判学说相比,这种逻辑完全是下意识的。君主任何失德和小的过失,如误信画工之图,都会导致人物的悲剧命运。叙事因此相信和依赖各种偶然性和细节,而不太强调本性和必然性。但偶然细节导致的结果总是那么强硬,可见这些故事所暗示的是某种更无法违拗的社会强制性,人生完全受困于这种更难以逃脱的宿命。不管民众对现实的君权如何顺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就是如此,这正是讲说前代历史故事中所包含的寓言意义。
与类型化人物故事相配合,讲唱文学作品常常采用重复回环式情节,这也是通俗叙事文学的一般特征。如《伍子胥变文》写伍子胥逃亡途中先后向拍纱女子、阿姊、其妻、渔人乞食问路,女子和渔人均为避嫌疑或投河或覆船而死。这些重复的相见情节,均属无中生有的虚构,不但太过巧合,有些也明显不合生活常情。但恰恰是这些情节构成作品的主体部分,其作用主要在于加重主人公复仇责任的深重性和事件的悲剧性。换句话说,故事主人公在身陷噩运时决不会只遇到一次考验、一件悲苦,而是要遭遇一连串的考验和悲苦。《舜子变》写舜子遭恶继母陷害,由摘桃、修廫、浚井几段情节组成,所设恶计有变,但展开方式却是大体相似重复的。《八相变》、《目连变》、《降魔变》等作品的重复回环情节,本来即是其所据《佛本行集经》、《盂兰盆经》、《贤愚经》等佛经故事的基本结构方式。在隋唐以前汉土民间原有的各类叙事作品中,这种结构方式尚不多见。由此来看,讲唱文学在结构方式上可能受佛教文学影响较大,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叙事文学由简省走向繁富的一个重要转变阶段。
在具体情节和细节上,讲唱文学作品广泛吸纳采用各种民间生活素材,并在作品中加以程式化运用。如《舜子变》写恶继母以金钗自刺其脚,诬陷舜子树下埋刺,类似情节便屡见于民间权诈故事。当陷害不成,恶继母必要挟其夫,要挟之辞总是:“解事把我离书来,交我离你眼去。”这完全是某种民间生活场景的程式化再现,恶继母类型就这样塑造完成了。将某种真实人物关系、某一生活场景凝固化为某种极具概括性的程式化情节并反复运用,讲唱文学就是借助这样一种手段来提供生活实感。这与同时代文人传奇中所见、也是一般“现实主义”小说所需要的“细节的真实”,显然不同。读者观众从中看到的是他们经验和意料中必定如此的生活,而并不是真实生活本身。对于在观众直接经验之外的生活内容,讲唱文学也会用同样程式化的方法想当然地予以演绎补充。如《王昭君变文》写单于欲使昭君欢心,便“告报诸蕃,非时出猎,围绕烟脂山,用昭君作中心,万里攒军,千兵逐兽”。正如周幽王之于褒姒,观众想象中君主讨妃子欢心的方式就是如此。
然而,程式化同时也意味着观念的扭曲和不真实,例如《伍子胥变文》写拍纱女子和渔人之死。为完成复仇主题,若干次要人物可以自愿牺牲,以极端方式表示忠贞诚信,这无疑显示了集体观念的某种残酷和偏执。为了保证观念的畅快和一致,讲唱文学在这种场合下往往并不考虑是否有违捩生活常情之处。毕竟以完成类型化、理念型人物故事为主旨的文学作品,要以观念为先导,观念的意义远比生活的真实更为重要。
一般来说,讲唱文学中凡与宗教有关的作品,其中宗教宣传的主导性、强制性是不容质疑的,因而观念对生活的扭曲必然十分严重,我们很难企盼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多少真实生活内容。但由于宗教思想本身的歧义性和观念影响生活的复杂性,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在这方面,《唐太宗入冥记》又是一个独特的标本。它恰恰借助特殊宗教观念形式,触及了一个人们在当时讳莫如深、不敢公开谈论的政治话题,由此介入于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它所借助的特殊观念形式,就是佛教的地狱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地狱巡游故事模式。根据佛教观念,在现实的生人世界之外(之后、之下)还有一个死者的地狱世界,人死后必须接受冥间对其生前作为的审判。佛教宣传者就利用这种地狱观念恐吓耸动世人,要其对自己现世行为负责,尽快弃恶从善。在中国佛教徒的发挥中,于是出现了生人巡行地狱、在阴间受审的故事,如南朝齐王琰《冥祥记》中《赵泰》篇曾描写主人公巡行地狱十日。初唐时期这类传说更为流行,唐临《冥报记》中有多篇采用这一故事模式,并有以帝王为主人公者。根据佛教观念,一切人包括帝王,在轮回果报和冥间审判面前均无脱逃特权。而且自南北朝以来,王室权贵之间的政治诛杀异常惨烈,帝王经常成为冤报故事的主角。正是在这种观念背景下,民间传说才可能让唐太宗也进入冥间,接受冥官对其杀兄戮弟行为的审问。传说还运用在同类型故事中已经出现的由生人充当冥官的情节,让冥官运用其权力与受审的唐太宗作交易,换取太宗在阳间为其授予美职。这一情节设置在巧妙利用地狱与人间颠倒对应关系的基础上,为故事进一步增添了喜剧讽刺力量。
然而,就民间传说本身而言,令我们难以分辨的是,所有这些情节安排究竟是由地狱巡游故事模式推衍而来,还是由对玄武门真实事件有意加以改写变形而来?在导致作品产生过程中,究竟哪方面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一件民间作品,不相信民间也有借小说谋政诽谤的企图,那我们最好相信,该作品对统治者恶行的揭露是在佛教观念作用下,由民间“集体无意识”完成的。唐代大量的地狱、报应故事也证明,佛教观念的渗透、与民间伦理观念的融和在民间思想进程中是主要的,对某个具体人物如唐太宗道德行为的谴责,只是在这一过程中附带出现的。不过,尽管如此,地狱观念及其故事模式除了其固有的荒谬和千篇一律之处外,在这个故事中还是充分显示了它的复杂涵义,显示了它所具有的特殊思想力量。由此可见,我们对深入于民间的任何思想观念,都不能简单地因其荒唐、虚幻、“不真实”、源自宗教或巫术,就将其一笔勾销。
[1]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逐步接受用“变文”来概称这些讲唱文学作品。自80年代以来,学者根据敦煌文书中的标识及其形式特征,对所谓“变文”作出更细致的分类,如张鸿勋将其分为词文、故事赋、话本、变文、因缘、讲经文六类,另押座文为附类,见《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载《敦煌学辑刊》总第2期,1981年。周绍良的分法略同,多诗话一类,见周绍良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代序《唐代变文及其它》,中华书局,1987年,并参见周绍良、张涌泉、黄征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周绍良所撰《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王小盾分为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文六类(又曲子辞、诗歌二类不属本文所说的讲唱文学范畴),见《敦煌文学和唐代讲唱艺术》,《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2]《通典》卷十五所提供的是天宝年代以前某一时期的数字,估算方式存在问题。官员定额18,085人与后补人数12万馀人,都是某一规定时间的统计人数。但人的任官年限一般要长于学习和后补年限,二者的比率可大约设定为3∶1。也就是说,18,085人如果按每年1/30更换的话,12万馀人就要按每年1/10更换,因而二者在某一年之比就不是1/8~1/9,而是<1/20。《通典》卷十五提供的另一组数字是:“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开元以后,……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者百才有一。”又卷十七引赵匡《举选议》谓:“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这都是就每年得第人数所做的估算,比例远低于1/8~1/9。此外,这里的“举人”是指获得乡贡进士资格者,不包括在乡贡考试中已被淘汰者。后者的比例由于各地、各时期情况不同,很难加以估算。但据《唐摭言》等文献所载事例,乡贡考试的竞争十分激烈,淘汰率一定相当高。该书卷一载会昌五年(845)格文,限定诸道(州府)所送应举进士人数为10~30人,明经为15~50人,偏远区域更分别只有7人和10人。如果将这两层考试的淘汰率合并计算,比例将是几百分之一或更低。考虑到一个人参加考试的机会可能达到5~10次,最后得出的中举比例或许稍高于百分之一。
[3]姑以《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提供的天宝十四载(755)“国家之极盛”时期人口数52,919,309人为基准数。
[4][7][13]周绍良、张涌泉、黄征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9、1062、1065页。
[5]见《唐六典》卷二吏部员外郎,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45页。
[6]敦煌文书编号为S.133,《敦煌变文集》拟题,从文本形式考察,学者多认为此文与变文形式不同。
[8]佛教宣教作品中的优美文笔则表明,接受良好世俗教育者也加入了佛教宣传写作。如《破魔变》写魔女妆束:“侧抽蝉鬓,斜插凤钗;身挂绮罗,臂缠缨珞。东邻美女,实是不如。南国娉人,灼然不及。玉貌似雪,徒夸洛浦之容;朱脸如花,谩说巫山之貌。行风行雨,倾国倾城。”《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第814页。
[9]赵璘《因话录》卷四所载僧人文溆善于演唱,“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以至吸引“听者填咽”,是记载中最著名的讲唱文学表演者。《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56页。
[10]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大正藏》第39册。
[11]《唐会要》卷四七议释教上显庆二年诏、开元二年敕。
[12]见《弘明集》卷十二慧远《答桓太尉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三章第六节“慧远的佛教思想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31页。
[14]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参见任爽《唐代礼制研究》第七章《唐代的礼制与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200页。
[16]学术界曾根据宋曾慥《类说》以“一枝花”为《李娃传》主人公之名,认为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自注所言“一枝花话”为白行简《李娃传》之蓝本。这一说法已遭受质疑,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节行娼李娃传》条,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敦煌文书S.2630,王国维拟题,《敦煌变文集》收入。此篇一般被归入话本一类,与后代话本小说有渊源关系。
[18]王国维《唐写本残小说跋》,收入《观堂集林》卷二一。
[19]有关《唐太宗入冥记》的文类归属、文本特征等问题,由于该本残损严重,尚缺少细致全面的研究。学者或根据该作品,推测高宗、武后时期曾有为玄武门之变翻案的某种思潮。但根据现有史料,无法证明这一点。陈珏《初唐传奇文钩沉》第七章将该作品归入初唐“准传奇文”范畴,承认其“白话成分更加深入文理”,但认为它出于“当时的某一个有头有脸的文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308页。本文认为讲唱文学在总体上有下层知识分子介入,但与上层文人和宫廷政治斗争没有直接关联。几乎无法想象知名作家在当时会采用这样一种文体写作,而敦煌文书的存留也说明它并非在一个小圈子内流传的作品。
[20]《朝野佥载》卷六,《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第84页。
[21]参见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22]虚构往往被认为是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主要特征。在传记类作品中“向壁虚造”,引入志怪成分,有意淆乱年代、地理、人物,用于“影射时政”或其他目的,是初唐托名和匿名传奇文的特点。参见李鹏飞《从〈梁四公记〉看唐前期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陈珏《初唐传奇文钩沉》第七章《初唐传奇文地图之重绘》。而中唐文人传奇的重要艺术特点恰恰在于,从本阶层真实生活选材,并采用严格的写实手法。讲唱文学既不同于前者的影射虚造,也不同于后者的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