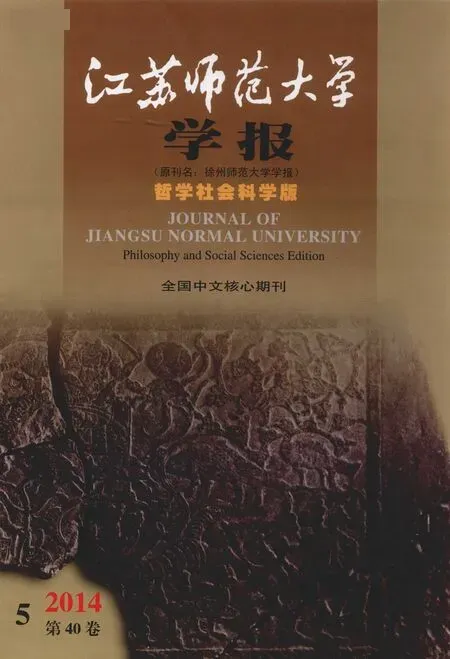伊卡洛斯形象在19世纪的演变
——以歌德笔下的欧福里翁-拜伦、波德莱尔与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几篇诗作为例
杨宏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伊卡洛斯形象在19世纪的演变
——以歌德笔下的欧福里翁-拜伦、波德莱尔与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几篇诗作为例
杨宏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伊卡洛斯;斯特凡·格奥尔格;歌德;拜伦;波德莱尔
在古希腊神话里,伊卡洛斯由于不听父亲的劝告而飞得太高,翅膀被太阳融化,坠海而死。后人将他阐释成各种形象,如追求爱与美的诗人与爱人,追求自由的英雄、革命者、反叛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在19世纪,有三位大诗人——拜伦、波德莱尔、斯特凡·格奥尔格——续写了伊卡洛斯神话。献身希腊战场的英国诗人拜伦在歌德的《浮士德》里以欧福里翁的形象出现,是一个英雄伊卡洛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把追求美的现代诗人比作不幸坠落的伊卡洛斯,德国诗人格奥尔格则塑造了一个作为诗人-先知的伊卡洛斯,他是变革社会的精神领袖。格奥尔格对伊卡洛斯形象的塑造,成熟于他在伦敦漫游中与拜伦的神交、在巴黎参加马拉美主持的星期二聚会以及对波德莱尔诗歌的熟稔,这可视为一种“侨易”现象,同时也造就了格奥尔格的伊卡洛斯形象的独特性。身处不同时代、源自不同民族与国家的这三位诗人对伊卡洛斯的不同感悟与阐释,展现了伊卡洛斯形象在19世纪的一种“侨易”过程。
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根据奥维德在《变形记》卷8第183-235行的讲述,伊卡洛斯的父亲代达洛斯为带他逃离克里特岛,用黄蜡粘合羽毛制作了两双翅膀,可他不听父亲的劝告,鼓动双翼兴奋地向着太阳越飞越高,终因黄蜡融化羽毛散落而坠海死亡。那片大海后以伊卡洛斯命名。
人类文明之初的神话人物,常常作为一种文化原型表达了人类的一些精神诉求,如俄耳甫斯呈现了文学艺术的摄人心魄与改变世界的魔力,普罗米修斯集中体现了反抗强权与启蒙人类的战斗精神,飞向太阳的伊卡洛斯寄托了人类追求自由、光明与美的激情。伟大的生必有伟大的死。俄耳甫斯被疯狂的酒神女撕碎,但他的头与琴在海上漂流,呜咽之音回荡在后世,绵绵不绝;普罗米修斯被绑在高加索山上,肝脏被老鹰啄食又随即复原,普罗米修斯的精神也在几千年的人类精神世界里生生不息;伊卡洛斯坠落大海,但那片大海被称为伊卡洛斯海,无尽的海浪永远吟唱着伊卡洛斯。他们的这种非同凡响的结局,是对他们的歌唱与精神不死的神话表述;一代代后来者的不断阐释,才是他们的歌唱与精神不死的见证;而这些阐释,必定是一代代人从所处时代与自身处境出发的生命实践与感悟。就本文的探讨对象伊卡洛斯来说,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1868-1933)在《伊卡洛斯》一诗中表达得简明扼要:
你曾经驾着命运赐给的羽翼
高高飞翔——远离了大地山丘……但内心的冲动放纵不羁
你飞得太高竟遇到了火球。
你早就离开了大地高高地飞翔
炽热的阳光之吻把你的双翅
融化而你掉进了惊涛骇浪
的大海——救救你自己伊卡洛斯!(SW 1,S.41)[1]
这首小诗写于1886-1887年。第1节的4行与第2节的前3行半全用过去时态,似在描写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但在最后一行,以一个破折号为转折,时态一下变为现在时态,最后的呼唤指向了诗人自己。作为世纪末的一个现代诗人,格奥尔格将如何理解伊卡洛斯?对比同一世纪的拜伦、波德莱尔对伊卡洛斯的展现与阐释,可以窥见伊卡洛斯在19世纪的一种“侨易”过程。
一
在这首《伊卡洛斯》里,有两处传达了格奥尔格对伊卡洛斯神话的改写。一是“阳光之吻”(sonnenkuss),诗情画意中隐含了一种爱欲关系。把伊卡洛斯情爱化,有着悠久的传统。奥维德除了在《变形记》里讲述伊卡洛斯与他父亲的故事,还在《爱的艺术》卷2中简述此故事,意以飞翔的伊卡洛斯比爱神:“轻盈的它有一双羽翼,随性而飞,双翼难被管束。”[2]到了近代,爱情诗人也喜自比伊卡洛斯,把爱人比太阳,爱神给他插上飞翔的翅膀,他“如伊卡洛斯被神圣之美即爱人吸引,爱人的目光如太阳光一样置他于死命……”[3],另一处改写是伊卡洛斯的翅膀由“命运赐予”。命运赐予的翅膀可认为是命中注定或与生俱来,如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让苏格拉底讲述的人的灵魂的羽翼,其本性是让人从尘世升上天界去凝视神圣的美。但就在同一篇对话里,柏拉图认为爱可以滋润培育灵魂的羽翼,凭翼而飞的爱若斯同样可以让恋爱中的人心灵飞翔关照神圣之美。联系起来看,格奥尔格的这两处改写是一致的,准确地说,这个伊卡洛斯的翅膀是爱神给予,爱的渴望让他展翅高飞,情爱之吻却让他折翅坠落。由于这两处改写,格奥尔格在这首诗里以过去时态描写的就不尽是神话中的伊卡洛斯,而是一个“旧”伊卡洛斯,因为在一个神话人物的流传过程中,后人的理解必然建立在前人的阐释之上或受其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首诗在最后半行的转折与现在时态的呼唤,同样指向格奥尔格自己[4]。
格奥尔格写作这首《伊卡洛斯》是他在达姆施塔特上中学时的1886-1887年。1888年3月,格奥尔格中学毕业,开始游历伦敦、米兰、马德里、巴黎等地。8月,他从伦敦写信给中学同学斯塔尔,自比伊卡洛斯写信道:
我请你务必好好地保存这些信。你想想,如果将来还有别人记得这些信,那多丢脸!!!读过这些信的人日后想起,那个家伙,夸夸其谈诗歌与戏剧,被一种诗人的幻想折磨着,翅膀七零八落如——啊——写不下
去了——[5]
初出茅庐的他感叹写诗的自己如一个折翼的伊卡洛斯,就在同时,他开始感到了情欲之美:
你想想看,人们总是偏爱灵魂,不爱肉体……我首先想到的是身体……单单身体的美就能让你发狂……[6]
他迷醉的不是肉体,而是“身体的美”。这已然预示了情欲的升华与一个欲飞的“新”伊卡洛斯。而爱的迷狂与诗的迷狂被柏拉图在《费德若篇》中并列,似也说明两者可以互为映照。
将情欲升华为诗,正是《伊卡洛斯》的两组押韵所隐含的“新”伊卡洛斯诞生之径。这首诗的两组纯韵flügeln-zügeln,weggeflogen-meeresw ogen暗示翼与羁、飞翔与骇浪之间的内在关联。水一般是生命力或无意识的象征,“深藏在海面之下的东西,显得神秘而恐怖,此外,大海深处也象征心灵的创造力,在弗洛伊德之前就被认为是储存无意识的容器”[7]。现代精神分析学认为,各种原始欲望与本能深藏在无意识中,因此大海的惊涛骇浪可以象征人的原欲,即一种原始的、没有被任何理性束缚和压抑的激情,具有破坏与创造的双重性。“旧”伊卡洛斯断送于情爱之吻,可以说呈现了原始情欲的破坏力;但原始情欲如果被升华,就会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就是力比多的升华,虽然有些绝对,还是颇有启发性的,许多诗人的缪斯女神就是他们深爱而未能拥抱入怀的女人,如贝雅特丽齐之于但丁,劳拉之于彼特拉克,毛特·岗之于叶芝。就这两组纯韵所隐含的内容来说,那就是:将狄奥尼索斯似的原始情欲升华为展翅高飞的力量,约束高飞远举的翅膀,以便创作出美的诗歌。“新”伊卡洛斯的飞翔即诗歌创作,而诗是用语言与形式表达思想的一种艺术,需要约束。格奥尔格创作诗歌,不是象牙塔内的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与其生命血肉相连的一种生命活动。
二
不听父亲的劝告而冲向太阳的伊卡洛斯虽然任性、鲁莽、倨傲,但更让人看到的是勇敢与冒险、追求自由与一种真正的革命激情[8]。伊卡洛斯因此不乏被阐释成英雄、革命者或反叛者。热爱希腊、一生追求正义与自由的诗人拜伦为希腊的独立而献身沙场,歌德在《浮士德》第2部所描写的精灵欧福里翁,就隐含了他对这个伊卡洛斯般的英雄的歌颂。拜伦的诗无不充满了反抗与战斗的激情,1824年他在战场上的死将他的生命定格在那辉煌的一刻。英勇无畏、灵魂高贵、追求自由、激情四射、壮烈牺牲、英名永存的拜伦,简直就是神话人物伊卡洛斯的现代版本。1888年8月,格奥尔格感到情欲之美、即将创造一个“新”伊卡洛斯之时,他正在拜伦的出生地——伦敦。虽然在格奥尔格的作品与一些重要谈话中未曾出现拜伦之名,就连详尽展现了格奥尔格生活与创作的《格奥尔格年表》上对拜伦也只字未提,但这并不意味着格奥尔格那时对拜伦一无所知或毫无兴趣[9]。不过格奥尔格对行动与革命确实有他自己的理解。在《伊卡洛斯》一诗里,海浪所象征的人的原欲,也会外化为客观的社会活动,如各种战争或反社会体制与社会秩序的革命,在中外象征文化里,潮水或洪流即可象征变革或革命[10]。格奥尔格两次感叹伊卡洛斯飞得太高而离开了大地,也寄托了他对这个具有神圣追求的伊卡洛斯能够作用于现实的殷切期望。革命与性爱都可认为是非理性原欲的爆发或宣泄,有时还会呈现出一致性,如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但在这首《伊卡洛斯》里,原欲之升华与飞翔之被约束,都暗示了格奥尔格对“行动”的一种新理解:诗歌创作即“行动”,诗将是改变现实的理想工具。
在伦敦,格奥尔格完成了剧本《马努埃尔》第2稿[11],这是与翻译易卜生的《喀提林》同时进行的一项工作,从易卜生笔下的使用暴力的起义领袖喀提林到他自己创造的精神领袖马努埃尔,伊卡洛斯似的革命激情让位给了一种更高贵的精神追求。
喀提林(Catilina公元前108年-前62年)是古罗马的一个历史人物,企图颠覆腐朽的共和制,“喀提林阴谋”是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风云中的一次叛变。格奥尔格在1884/1885年上中学时,就学过西塞罗的著名演说《反喀提林》[12]。西塞罗发表过四篇《反喀提林》,抨击喀提林是一个“用剑和火”威胁罗马的“罪大恶极”的阴谋家[13]。易卜生这部处女作写于1848-1849年,他不同意历史学家和西塞罗对喀提林的判决,塑造了一个拜伦似的高贵的革命英雄,对历史人物的这种再塑造应和了19世纪上半叶的挪威民族解放运动[14]。1888年,德国政坛风云变幻[15],年轻的格奥尔格内心里充满了骚动与反叛情绪,他曾说:“如果我在20岁有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我会把全欧洲的统治者都赶出去。”还说,如果不是在19世纪,在其他任何时代他都会进监狱[16]。这种反叛精神迅速领悟到了“喀提林阴谋”的伟大,他特意自学挪威语来翻译这个剧本。收入《格奥尔格全集》之《终卷》的有他翻译的两个片段,一是第1幕中一些年轻的罗马贵族提议让喀提林领导他们造反,因为他“确实具有非凡的天赋,——/不但有无畏的勇气,而且思想高尚”[17]。二是第2幕中喀提林和那些年轻贵族对峙:他们造反只是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可喀提林要重现古罗马的光辉,他梦想“自己拴上了伊卡洛斯的翅膀,/在高高的苍穹下不停地盘旋飞翔”,梦想自己获取神灵的雷火闪电将腐朽堕落的罗马城化为灰烬,让古罗马复活[18]。好一个革命英雄伊卡洛斯!伊卡洛斯的勇敢、冒险与革命激情都体现在喀提林的梦想中,伊卡洛斯的坠落也是他的命运。
如果说翻译《喀提林》应和、疏解了格奥尔格的反叛与革命激情,喀提林的惨败却也是一个警示。像是在回应拜伦与喀提林,格奥尔格创作《马努埃尔》第2稿,设想了一种变革社会的理想方案。
马努埃尔是一个王子,梦想和平、自由、平等,相信自己被上天赋予了建立“和平之国”的神圣使命;门内斯是叛乱领袖,惊叹马努埃尔的高贵,又亲眼看见他奋不顾身跳进大火救人,被他的英勇折服,自愿让位,甘当助手。当马努埃尔因深爱的女子莱娜被他父亲抓进修道院而无助绝望时,门内斯提议武力解救莱娜:“大伙都会跟随你/只要你站出来领导。”马努埃尔却断然拒绝:“即便如你所说我能成功/我杀戮,逼迫,然后统治——/可是,门内斯,和平之国在哪儿/只有它能永久地保证和平……”(SW 18,S.27-28)马努埃尔反对以暴制暴,渴望奇迹的出现;但现实是残酷的,莱娜割腕自杀后,他也自杀。此举似乎不像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精神领袖之作为,但一如那首小诗《伊卡洛斯》里爱欲升华为诗,马努埃尔的爱与他的事业也是唇齿相依:“你不知道我多么感谢这份爱/它激励我去行动/赐我力量挺过大风大浪/成就了我最美好的人生……”(SW 18,S.26)马努埃尔死了,可他的理想由门内斯继承下来:“我看见了一场巨大的战斗/我要用新精神激发民众/我启蒙吸引迷醉他们/一切虚伪的坏势力/就将化为乌有/一如尸骨遇上空气。”(SW 18,S.33)
比较两个剧本,两个主人翁都渴望变革社会,喀提林倾向先破后立,马努埃尔倾向先立后破,以新精神塑造新人、把新人比喻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这样的理想具有一种先知色彩,为人类的未来指出了一个光明的方向。在格奥尔格对马努埃尔与门内斯的关系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反叛的革命激情如何归顺并服务于崇高的精神追求:
门内斯:……你让我无比钦佩/(不管你是谁)我曾想/你要是我们的人该多好。/我常常跟踪你/想和你说话争取你/但从未成功。/当我听从大伙的建议/举剑冲向你·我认识了你/我心头忽然一亮:/一个比我更伟大的人/出现,命运变了。/心碎的我不再领导起义/当大伙犹疑地看着我/我劝他们放弃我的行动/去相信你的话。
马努埃尔:你那时让我很惊讶。
门内斯:现在我自愿/当你的助手。
马努埃尔:门内斯,我的朋友!/完成艰巨任务/——上苍交付我的——我需要你。……(SW 18,S.18-19)
面对高贵的马努埃尔,门内斯感到自己的“命运变了”,因为他原以为自己领导大伙翻身闹革命就是救世主。在那首《伊卡洛斯》里,伊卡洛斯的羽翼由“命运”赐予,与其同组的一首诗里说:“能力是神赐予的……/自己无能——痛苦啊——/马不停蹄又有何用?”(SW 1,S.18)格奥尔格相信命定论,在命定的责任与使命中,他相信崇高的理想高于暴力革命。门内斯皈依马努埃尔,似乎可以看成是对格奥尔格的内心转变——从当统帅领导起义到成为一个精神领袖——的一个文学描写,但变革现实的梦想没有变:“‘行动’成为格奥尔格创作的一个关键隐喻。对笔迹学颇有研究的克拉格斯没有错,当他多年后写到,格奥尔格的字展示了‘一种进入到——如果不说是脱轨到——艺术中去的行动者天性。’”[19]
马努埃尔是精神领袖,门内斯是忠诚的下属,这种关系的塑造除了受到格奥尔格自幼耳濡目染的天主教仪式中的等级制度的影响之外,易卜生所描写的喀提林对他的启发性也不可忽视。喀提林雄心勃勃,但跟随他的那些人只谋求卑鄙私利而无崇高追求,被他称为“下流胚子”,他不止一次痛心疾首[20]。就在收入《格奥尔格全集》之《终卷》的第2个片段中,喀提林对着那些人“痛苦地”说到:“我真是一个傻瓜!竟想依靠你们获得成功!/在这群懦夫的心中哪里还能找到半点热情?”[21]卓越的领袖没有优秀的士兵,注定是要失败的。但马努埃尔与门内斯的关系完全相反。马努埃尔在世时,助手门内斯出于“嫉妒”要“看管他的一举一动”;马努埃尔死后,门内斯以“忠诚地继承他的遗产”来表达对他的“尊敬与爱”。(SW 18,S.16,S.33)如此尽职尽责、勇敢忠诚的门内斯才能用马努埃尔的精神去启蒙民众,马努埃尔的“和平之国”才有望实现。
三
格奥尔格对伊卡洛斯形象的塑造,与他游历欧洲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达姆施塔特上中学时就已经阅读易卜生的戏剧《喀提林》。在当时的德国有一股易卜生热。1887年6月,易卜生的《群鬼》在柏林秘密上演,而在达姆施塔特,1886年10月就上演了易卜生的戏剧《社会支柱》。不过,格奥尔格喜欢的不是当时风靡大众的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而是他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如《喀提林》等,这些戏剧的主人公多为历史或传说中的英雄,心灵的高贵和精神的反叛是戏剧的中心主题,为此,他特意自学挪威语翻译了《喀提林》中的一些片段。但是,只有当他在游历中面对生气勃勃的自然与生活感受了情欲之美,又在拜伦的出生地对拜伦的精神心领神会之后,他才会塑造一个比反叛英雄更伟大的引领社会变革的精神领袖。格奥尔格在伦敦完成《马努埃尔》第2稿,好像与拜伦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他对马努埃尔与门内斯的塑造可以看成是他向拜伦表达的纪念与敬意。门内斯曾是叛乱领袖,格奥尔格曾渴望领导起义,上中学时还写讽刺诗,具有“特别的讽刺天分”(SW 1,S.98),他们与拜伦一样,内心燃烧着反叛的烈火;拜伦为理想而驰骋疆场,但他们刚好相反。格奥尔格不久就完全放弃了讽刺诗的写作,没有一首讽刺诗被他收入《格奥尔格全集》,他描写门内斯皈依马努埃尔,让反叛的激情服务于更高贵的精神追求,改变现实的方式也从破坏转向了建构。格奥尔格的这种趋向“保守”[22]的态度,与歌德对拜伦的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歌德在1825年2月24日与艾克曼的谈话中,认为拜伦的恶魔性格对其创作与人生都是有害的,他说:“要想真正地有所作用,就不要谴责,不要去想扭转乾坤,应该一直做有益的事。因为关键不是破坏而是建构,人类在建构中才能感到真正的快乐。”[23]歌德认为拜伦倾向破坏,而他觉得应该建构,他放弃狂飙突进时代所追求的叛逆的普罗米修斯英雄,去魏玛宫廷参与实事,从浪漫向启蒙的转变与这一思想是有关的[24];欧福里翁-拜伦也是年老的歌德对自己的青年时代的一次深情回眸。
在《伊卡洛斯神话:从奥维德到W.毕尔曼》[25]这部文本汇编中,编者汇总了从古到今的作家诗人如奥维德、贺拉斯、J.桑那扎罗(Jacopo Sannazaro)、歌德、波德莱尔、格奥尔格、奥登、E.扬德尔(Ernst Jandl)、W.毕尔曼(Wolf Biermann)等创作的伊卡洛斯形象,分为五大类:1.父与子: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代达洛斯与伊卡洛斯;2.罪人、英雄、爱人: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的伊卡洛斯;3.艺术家与殉难者:从古典到古典现代的伊卡洛斯;4.反叛者与革新者:从表现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伊卡洛斯们;5.乌托邦主义者:当代德语文学创作中的伊卡洛斯。这个编排按时间顺序同时又分门别类,显示伊卡洛斯在各个时代的流传与演变并不与某些具体作家具有必然的关联,而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这也说明一个文化原型在时空位移中的“侨易”自有其相对独立的特性,如伊卡洛斯的英雄化契合了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文艺复兴精神,狂飙突进及其之后的天才崇拜又重新让伊卡洛斯成为诗人的象征,20世纪的文学艺术从表现主义这一先锋运动开始重新介入社会,伊卡洛斯于是成了充满激情的文学与革命的急先锋与空想家。第三类有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10位作家诗人创作的12篇诗文[26],其中波德莱尔的《一个伊卡洛斯的悲叹》被称为伊卡洛斯神话在这个时期的“关键文本”[27],格奥尔格、茨威格与里尔克都翻译过这首诗,但只有格奥尔格在翻译时做了很特别的改动,比较其译诗与原诗,可以清楚地看出两位诗人对伊卡洛斯形象的不同阐释。
去做妓女们的情人/都很幸福、舒适、满意;/而我,却折断了手臂,/为了曾去拥抱白云。
多亏那些在天空里/照耀的无比的群星,/使我这衰耗的眼睛,/还留着太阳的回忆。
宇宙的中心和终极,/我徒然妄想去发现,/碰上不知名的火眼,/我感觉到翅膀碎裂;
为了爱美而被焚烧,/我无此崇高的光彩/给我这葬身的大海/冠以我自己的名号。[28]
这是波德莱尔的原诗。波德莱尔自比伊卡洛斯,他反抗丑恶的世界,追求美与光明,却没有伊卡洛斯那样的光环与名声;诗人不仅不被认可不被传颂,反而还被人嘲笑,他在《信天翁》一诗中这样感叹:“诗人啊就好像这位云中之君,/出没于暴风雨,敢把弓手笑看;/一旦落地,就被嘘声围得紧紧,/长羽大翼,反而使它步履艰难。”[29]1861年,波德莱尔编订出版《恶之花》第2版,大获成功,自信的他乘机向法兰西学院提出申请当学院候选人,这当然是徒劳之举,生活中的他也是贫病交加。这首“悲叹”诗最初发表于1862年12月28日。1867年8月31日,波德莱尔凄凉离世,次年,戈蒂叶把这首诗增补进《恶之花》,与其他24首诗作为增补遗诗。
波德莱尔欣赏拜伦的“反抗与自由的精神”[30]。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的商品化与物质化压抑异化了现代人的精神,被本雅明称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波德莱尔,以一种浪荡子的叛逆去对抗这个社会,他自比伊卡洛斯的悲叹既有浪荡子的“忍受尘世的苦难而赎罪的宗教色彩”,又有浪荡子的“面对痛苦而不动声色的英雄气概”[31],而后者根本上也属于文人叛逆者。本雅明在论述波德莱尔的专题论文的最后,把波德莱尔与密谋反叛者布朗基并列,认为“布朗基的行动是波德莱尔的梦想的姐妹”[32]。
格奥尔格大概在1893年翻译波德莱尔的这首《一个伊卡洛斯的悲叹》,晚于他自己写作的《伊卡洛斯》。比较译诗与原诗,最大的改动是格奥尔格把原诗最后一节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这一改动不仅凸显了格奥尔格的自我意识,而且暗示他对现代诗人的命运有着与波德莱尔不一样的理解。这首诗的标题Les plaintes d’un Icare用的是一个不定冠词,而不定冠词表示泛指,因此,波德莱尔在诗中使用的第一人称“我”不单指他自己,也代表了现代诗人这一类人,也就是说,他作为现代诗人的一个典型,其个人命运能够代表现代诗人的命运。当格奥尔格翻译这首诗时,如果考虑到他把翻译当成自己的创作,那他也加入了波德莱尔等现代诗人的行列,这首译诗可以看成是《伊卡洛斯》的后续。诗的前三节描写诗人的崇高追求,格奥尔格保留了第一人称,声明自己也是一个伊卡洛斯;诗的最后一节描写诗人不被认可的一种受难者的悲哀,格奥尔格改成了第三人称“他”,由此把自己与忧郁的伊卡洛斯们分开了,这个“他”尤其让人想到是指原诗作者波德莱尔。格奥尔格与波德莱尔一样挣脱世俗羁绊去追求美与光明,但他不分享波德莱尔的悲叹与忧郁,他在自己5年前创作的《马努埃尔》第2稿就已经展现了一个自信的启蒙民众的精神领袖伊卡洛斯。此种态度也决定了格奥尔格与马拉美等象征主义诗人的异同。法国诗人的匠心独运与尽善尽美的诗作、马拉美献身诗歌的执着与虔诚,满足了格奥尔格如伊卡洛斯追求美的渴望与梦想,但“唯美主义之于格奥尔格,以完全具体的、政治-社会的方式,是‘美学的对抗’”[33]。格奥尔格以他的诗对抗现实并进而改变现实,这也是马努埃尔之为精神领袖的意义。
四
格奥尔格对伊卡洛斯形象的塑造过程,清楚地展现了一种“侨易”现象。《伊卡洛斯》写于他在达姆施塔特上中学时的1886-1887年,他对伊卡洛斯形象的所有朦胧预感都隐含在那句“救救你自己”的呼唤中。1888年3月,格奥尔格中学毕业,开始游历伦敦、米兰、马德里、巴黎等地。虽然他在达姆施塔特就已经阅读易卜生的戏剧《喀提林》,但只有当他在游历中感受了情欲之美,在伦敦对拜伦的精神心领神会,他才塑造了一个比反叛英雄伊卡洛斯更伟大的“新”伊卡洛斯来担当新时代的精神领袖。1889年4月格奥尔格到达巴黎,遇见马拉美并参加他主持的“罗马街星期二聚会”,格奥尔格的这次游历终于到达了终点,马拉美追求美的献身精神,一如波德莱尔所描写的伊卡洛斯,让格奥尔格对“新”伊卡洛斯之为诗人的理想与追求得到了确认,于是翻译并改写了波德莱尔的《一个伊卡洛斯的悲叹》。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构成格奥尔格的伊卡洛斯形象的关键因素尽管都隐含在那首《伊卡洛斯》里,但格奥尔格在游历中的经历才让它们发芽开花,正如梁漱溟所说:“学术出自人类的智慧而育成于社会交流之上。所谓人类智慧者非他,人心内蕴之自觉是已。”[34]格奥尔格以他自己创作的《伊卡洛斯》、马努埃尔-门内斯组合以及他改写的波德莱尔的《一个伊卡洛斯的悲叹》,为19世纪的伊卡洛斯神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书写。
拜伦、波德莱尔、格奥尔格在19世纪的前期、中期与晚期以各自的方式续写了伊卡洛斯神话。这三位诗人身处不同的时代,又源自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他们对伊卡洛斯的阐释,是他们从所处时代与自身处境出发的生命实践与感悟,让这个神话人物在时空的位移中呈现出丰富的内涵。这可以视为伊卡洛斯在19世纪的一种“侨易”过程[35]。虽然以这三位大诗人为例,但他们所展现或阐释的伊卡洛斯形象——反叛的革命英雄、追求美的悲伤诗人、领导社会变革的诗人-先知——却是具有某种独立性的。19世纪前期,在法国大革命的鼓舞下,欧洲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英雄的反叛者伊卡洛斯是那一时代精神的体现之一,无论其表现者是拜伦还是易卜生笔下的喀提林;1870年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突飞猛进的经济增长,发达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外扩张与殖民地开发,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与经济矛盾,追求自由的精神被弥漫社会的庸俗物质主义所压抑,再加上社会体制的健全,艺术家感到不再有力量参与社会的进步与改造,即便他们还有密谋反叛的革命梦想,但他们是被诅咒的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伊卡洛斯是整整一代诗人的写照;到了19世纪末,大诗人魏尔伦、马拉美等逐渐走进艺术的象牙塔,故意忽略对社会的批判性介入,与法国相比,德国的资本主义程度是落后的,但随着1871年的民族统一大业完成而如虎添翼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同样使人异化与精神变得庸俗,格奥尔格虽然在1890年前后把马拉美、魏尔伦等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与诗歌当成他的精神导师与精神家园,但他自己的德国精神传统却起着主导作用,不同于法国19世纪中后期文学把诗人-先知称为被诅咒的诗人,诗人-先知在德国文学中却是“毫无嘲讽意味的一条直线”[36],从克洛卜施托克、诺瓦利斯、经由格奥尔格,直到彼得·汉特克,格奥尔格,只是这一传统在世纪末的最杰出代表。可以说,伊卡洛斯形象在19世纪的演变,是与各个时代的精神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其形象如何随时空变化,伊卡洛斯神话所讲述的对光明的勇敢追求,始终是伊卡洛斯形象的精髓。
[1]本文引用的格奥尔格诗歌均出自Stefan George:Sä mtliche Werke in 18 Bänden,bearbeitet von Georg Peter Land mann und Ute Oelmann,Stuttgart,Klett-Cott 1982ff.此处的缩写表示:《格奥尔格全集》第1卷第41页,下文类推,不再一一加注。
[2]Ovid:Ars amatoria II,Achim Aurnhammer und Dieter Martin, Mythos Ikarus.Texte von Ovid bis Wolf Biermann,Leipzig,Reclam Verlag 1998,S.19.
[3]Achim Aurnhammer:Zum Deutungsspielraum der Ikarus-Figurin der Frühen Neuzeit,Martin V öhler und Bernd Seidensticker,Mythenkorrekturen.Zu einer paradoxalen Form der Mythe-nrezeption,Berlin·NewYork,W alter deGruyter 2005,S.158.
[4]“他受到的严格的天主教教育使他只知道两种女性:危险的性尤物与圣母般的纯爱化身的女神。他渴望一个能燃起他内心‘伟大’激情的女人,但在寻找这一个她的过程中,越来越失望。漂亮女人总是现形为邪恶的毁灭男人的荡妇。”(Thomas Karlauf:Stefan George.Die Entdeckung des Charisma,München,Karl Blessing Verlag 2007,S.64.)
[5]转引自Robert Boehringer:Mein Bild von Stefan George,2. ergänzte Auflage,Düsseldorf und München,Helmut Küpper vormals Georg Bondi 1968,S.28.
[6]出自格奥尔格在1888年8/9月写给中学同学C.鲁格的一封信,转引自Robert Boehringer:Mein Bild von Stefan George,S. 27.斜体字在原文中也是特殊的印刷体。
[7]Uwe Schneider:Meer,Günter Butzer und Joachim Jacob,Metzler Lexikon literarischer Symbole,Stuttgart·Weimar,Metzler Verlag 2008,S.228.
[8][8]参见Volker Rieder:"Er flog zu hoch hinaus.Er sah die welt wie nie".Aspekte der Ikaros-Rezeption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des 20.Jahrhunderts,Volker Rieder,Literarische Antikerezeption zwischen Kritik und Idealisierung. Aufsätze und Vorträge,Band 3,Jena,Verlag Dr.Bussert& Stadeler 2009,S.297.
[9]且不说格奥尔格中学毕业后游历欧洲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学习语言与文学以满足他对文学的渴望与追求,他在伦敦对拜伦的诗不应该不有所涉猎;就他从小表现出来的语言天赋与文学热情来说,他也可以通过歌德的《浮士德》知道拜伦,《格奥尔格年表》上记载,他所上的中学“有一些小圈子,大家一起读歌德”,他也曾参与。(H.-J.Seeka m p,R.C.Ockenden,M.Keilson:Stefan George.Leben und W erk.Eine Zeittafel,A msterdam,Castru m Peregrini Presse 1972,S.4.)
[10]Carsten Würmann:Flut/Dammbruch,Metzler Lexikon literarischer Symbole,S.111f.
[11]剧本《马努埃尔》第1稿大约写于1886年,格奥尔格自己后来说,这一稿是“根据前歌德的田园诗形式,很幼稚地描绘了最单纯、最原始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SW 18,S.6)收入《格奥尔格全集》之《终卷》的只有11行蒂蒙(即马努埃尔所爱的女孩莱娜的父亲)的心理描写,未出现第2稿的两个关键人物马努埃尔与门内斯。
[12][12]Günter Hennecke:Stefan Georges Beziehung zur antiken Literatur und Mythologie,Diss.,Köln 1964,S.9.
[13]引自西塞罗的第2篇《反喀提林》演说,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王以铸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8页。
[14]挪威从1397年到1814年一直是丹麦的附庸国,1814年被丹麦割让给瑞典,直到1905年才独立。1848年,在欧洲革命运动的推动下,挪威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喀提林》一剧正写于此时。具体可参见《凯蒂琳》“第二版作者序”,黄雨石译,收《易卜生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5-6页。译者把Catilina翻译成凯蒂琳,但现在更常见的是译为喀提林,本文从俗,为行文一致,引文中相关之处也加以改动。但书名除外。
[15]1888年,德国相继出现了三个皇帝。3月,实现了德国统一大业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去世,其子弗里德里希三世继承皇位,这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统治者只统治了99天就溘然长逝,他的儿子,年仅29岁的威廉二世,在6月15日登上王位。
[16]转引自Robert Boehringer:Mein Bild von Stefan George,S.152.
[17]易卜生:《凯蒂琳》,黄雨石译,收《易卜生文集》第1卷,第21页。
[18]易卜生:《凯蒂琳》,黄雨石译,收《易卜生文集》第1卷,第72-73页。为行文一致,将引文中的依卡鲁斯改成伊卡洛斯。
[19][19]Thomas Karlauf:Stefan George.Die Entdeckung des Charisma,S.56.
[20]引文见易卜生:《凯蒂琳》,黄雨石译,收《易卜生文集》第1卷,第91页。比如:“啊,这是无望的挣扎——想一想要靠这帮/懦夫和饭桶去消灭罗马,那如何可能!/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们?他们已经坦白承认——/他们的唯一动机是大捞一把——是他们的贪心。”(第86页)在临战斗前,喀提林自语:“这便是我赖以建立我的希望的信任和忠诚!/就这样,他们一个个抛弃了我。噢,神灵啊!/在他们的无比卑下的心灵中,看来永远是/只有叛卖和怯懦才能引起一点波澜的一滩死水。/哦,我多么愚蠢,竟抱着那么多空幻的希望!/我一定要毁灭罗马城,这个毒蛇窝——/其实它早已变成了堆满废物垃圾的场所。”(第109页)
[21]易卜生:《凯蒂琳》,黄雨石译,收《易卜生文集》第1卷,第72页。
[22]Claude David:Stefan George.Sein dichterisches Werk,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 1967,S.24.
[23]Franz Deibel:Goethes Gespräche mit J.P.Eckermann,Band 1,Leipzip,Insel Verlag 1908,S.191.
[24]1774年,歌德创作著名的诗歌《普罗米修斯》,歌颂这个盗火的叛逆英雄,而在与此同时写作的一个同名诗剧断片中,歌德却开始解构普罗米修斯的叛逆意义,随即在第二年,歌德进入魏玛宫廷,这标志着他“开始了自己生命中另一段历程,而放弃了青年时代以感情冲动为标志的‘浪漫时代’,这当然也包括放弃了追寻强力英雄、尝试彻底叛逆的道路”。(叶隽《歌德思想之形成——经典文本体现的古典和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本书第35-53页有对《普罗米修斯》与同名诗剧断片的详细分析。)
[25]Achim Aurnhammer und Dieter Martin:Mythos Ikarus. Texte von Ovid bis Wolf Biermann,Leipzig,Reclam Verlag 1998.
[26]它们是歌德在《浮士德》第2部描写的欧福里翁、W·缪勒(WilhelmM üller)的诗《酒徒的自足自满》与《新伊卡洛斯》、波德莱尔的《一个伊卡洛斯的悲叹》、格奥尔格的《伊卡洛斯》、冯塔纳的《伊卡洛斯》、邓南遮的《大海上的羽翼》与《Altius egit iter》,等等。除他们的12篇作品外,还收了格奥尔格、茨威格、里尔克翻译的波德莱尔的《一个伊卡洛斯的悲叹》。
[27]Achim Aurnhammer und Dieter Martin:Mythos Ikarus. Texte von Ovid bis Wolf Biermann,"Nachwort",S.256.
[28]钱春绮译,收波德莱尔《恶之花》,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368页。钱译标题是《伊卡洛斯的悲叹》,但原诗标题Les plaintes d'un Icare中用的是一个不定冠词,为与伊卡洛斯神话相区别,最好翻译为《一个伊卡洛斯的悲叹》,因为波德莱尔描写的是现代诗人的命运。
[29]郭宏安译,收波德莱尔《恶之花》(插图本),郭宏安评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30][31]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评,代译序“论《恶之花》”,第129、14页。
[32]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张旭东校订,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21页。
[33]WolfgangBraungart:ÄsthetischerKatholizism us.Stefan Georges Rituale der Literatur,Tübingen,M axNiemeyer Verlag 1997,S.14.
[34]转引自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167页。关于“游历”之为侨易现象一种,参见叶隽在本书第114-115页的分析。
[35]关于“侨易”的概念,见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36]Wolfgang Braungart:Ritual und Literatur,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 1996,S.205.
The change of the image of Ikarus in the 19thcentury————Euphorion-Byron in Goethe’s Faust,several poems of Baudelaire and Stefan George as examples
YANG Hong-qin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CASS,Beijing 100732,China)
Ikarus;Stefan George;Goethe;Byron;Baudelaire
The mythical figure of IkaruSWho ignored his father's advice and flew too close to the sun and then fell into the sea where he drowned was interpreted as poet and lover in pursuit of beauty and love,as hero,revolutionist,rebel and utopian longing for freedom.In the 19th century three famous poets Byron,Baudelaire and Stefan George showed their conceptions of Ikarus.While Goethe depicted English poet Byron as a hero Ikarus in the mythical figure of Euphorion in Faust and French poet Baudelaire composed a lament to the modern poet who soars up into heaven longing for beauty like Ikarus and falls but more unfortunately than Ikarus,German poet Stefan George gave an image of Ikarus as poet-prophet who is the spiritual leader of changing society.George's mature image of Ikarus grew out of his admiration for Byron in London,his attendance at the Tuesday evening held by Mallarméand his familiarity with Baudelaire's poetry in Paris during hiSWander,this development can be regarded as a"Kiao-I"process of the poet George and marks the special feature of his image of Ikarus.Bor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ived in different times,these three poets depicted varied figures of Ikarus,which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Kiao-I"process of the figure of Ikarus in the 19th century.
I106.2
A
2095-5170(2014)05-0020-08
[责任编辑:林晓雯]
2014-04-15
杨宏芹,女,湖北宜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