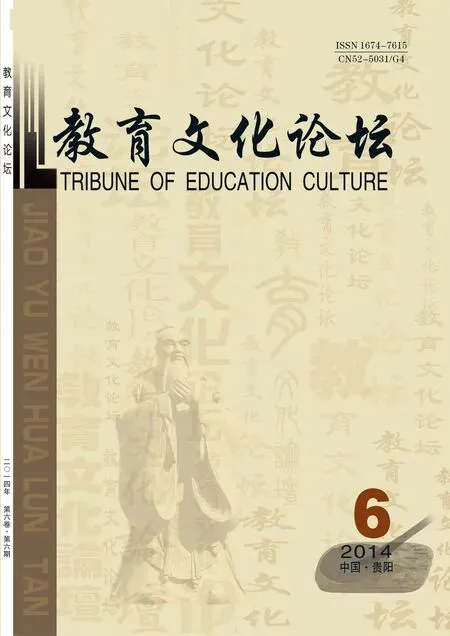香在无心处
——我的儒学情怀
吴 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5)
我的儒学情缘,或许可以追溯到童蒙时代。我并非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普通的农家子弟,模糊记忆中祖父还认识几个字,比父亲有文化,但他什么也没传给我。我的父亲只读过一年半书,因为家境困难辍学了。但父亲写的毛笔字是正宗楷体,比我现在写得还要好。他还能够熟练背诵《三字经》,并传给我未曾谋面的哥哥,我哥哥是在我出生那年病死的。于是家里仅有的四本书——《三字经》《百家姓》及另外两本中医手抄本便传到我手里,成了我的启蒙读本。我母亲出身于外村的破产地主家庭。原本家境不错,但都给我舅舅赌博败光了,所以正式成分是贫农。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儒家的一套做人道理却懂得很多,什么“做人要仁义”“要讲信用”呀“要穷得有志气”“唯有读书高”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呀,简直比文化人还有文化。我想,这也许是外公、外婆教育的结果,也许是当地文化氛围所潜移默化,以至“百姓日用而不知”吧? 母亲在我出生那年因为两个哥哥相继去世而悲伤过度,并染上了肺结核,终其一生也没有治愈,但她那慈爱善良、坚忍不拔的性格始终是我人生的榜样、力量的源泉。
然而,在那个全面批判儒家“旧道德”的年代,我接受到的家庭儒学教育难以抵消社会上和正规学校里的反儒、批儒教育。所以青少年时代的我,对孔孟之道并无好感,尤其是当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之类“反封建”作品以后,对所谓“封建礼教”十分反感,并且误以为那“吃人”的礼教便是儒家的全部了。所以直到大学时期乃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思想上基本是反封建、反儒家的。
“文革”初期,我积极响应伟大领袖“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号召,参加了造反派的队伍,但我没有打人骂人,而只是随大流参加批斗会。然而,1967年到处发生的夺权、武斗、停产的形势教育了我,使我开始怀疑文革的正当性,使我思想上变得“右倾”而走向反对“极左”的一面,于是我参加了调查文革红人戚本禹的“大批判组”,并在1968年初戚本禹垮台时公开写了一张批左大字报,定名《戚本禹的垮台说明什么——论“极左机会主义”的破产》。从此以后,我自觉走上了反左的路线,并在林彪灭亡、四人帮倒台时始终坚持批判极左的立场。这也是我在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真理讨论中能够自觉拥护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路线的内在思想原因。
1978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以后,开始系统阅读诸子百家之书,虽然我的论文选题是《道家黄老之学》,但我还是写下了批评老庄贬斥儒墨的“消极无为”主义、赞赏黄老“采儒墨之善”的“积极无为”主义的文章,并写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辩——论董仲舒“王道”观的进步性》《王充学说的根本特点——实事疾妄》等肯定儒家思想的文章,这可能是我“崇儒兼道”思想的起点。另一方面,我在中学时代,开始读王充的《论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鲁迅的杂文集,颇受其批判精神与民本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己出身农民、又是新安江移民,我的家人和乡人深受当时“共产风”之苦,几乎处于饿死边缘,因此能真切感受民众疾苦,自然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社会批判精神以及民本、民主思想。这也是我能够提出并坚持“民主仁学”的原始根源。
1988年,我由于刘述先先生的推荐、杜维明先生的认同而被聘任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就任“专任研究员”,我认真思考了新加坡经济腾飞的原因,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奥秘在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中华美德”三大法宝,并且真切感受到一个“多元社会”、“多元文化”的力量之伟大,所以在1988年9月1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漫说多元胜一元》的读史随笔,回国后又发表了《东西方礼仪交互作用的新加坡》(载张敏杰编著《当代国际礼仪指南》,长春出版社1994年版8月版),这又是我“多元和谐文化观”之滥觞。
当然,我之所以能够形成比较系统化的儒家思想,主要还是得益于我在研究生时期通读了《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古史辨》等古书,得益于1988-89年在新加坡做研究时阅读了大量宋明理学家和现代新儒家的著作,尤其得益于我们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世界和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起阶段的时代思潮。这使我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地走上了当代新儒家的思路,从而建立了我的《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的理论论述。
诚然,比起哪些现当代儒学大师来,我的儒学史与儒学理论的论述还是很不系统、很不完善的。从我主观自觉而言,并没有存想建立一个什么新儒学哲学体系,而且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和学养去建构一个哲学体系,充其量只是提出若干经我思考、自觉有些创见的新观点、新命题罢了,只能算是一偏之论、一得之见,绝不敢自称是什么哲学家或思想家,也不敢奢望我的观点会有多少拥趸(粉丝)。但我很喜欢山野中绽放的兰花那种品格,很欣赏古人吟咏兰花的诗句。20年前,我在写于1995年4月21日而发表于10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散文《寻兰》一文中写道:“世间繁花似锦,品类万千。而我最爱的却是初春盛开的山兰,是山野间那吸纳天地精华自然开放的野兰,那默默无言毫无矫饰的素兰,那散发幽香激励追求的幽兰。屈原《九歌·礼魂》中的‘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以兰菊芳香长继的品格,比喻诗人始终不渝、千古不移的情操。宋代曹组的咏兰词有“著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的名句,则借兰花的幽香表达词人淡薄名利独善其身的志趣。”我在文中还介绍了清初浙东抗清名将兵部侍郎冯京第仿照《周易》而编著的《兰易》与《兰史》,指出“著者虽然写的是兰,而所寄托的却是性情志趣,隐含的是国家兴亡、政治变革。”“我真希望那些治史而有闲情者,为政而有逸致者,也能读读冯侍郎的《兰易》和《兰史》,庶几从中汲取一点修身养性、治国安民的教益,使人格如兰之清,期德业似兰之馨。所谓开卷有益,岂虚言哉!岂虚言哉!”这是我当初著文的感触,也符合今天写书的心情。也许,拙著中某些有新意的观点,就像山野默默开放的兰花,会被进山观景的人们在无心中发现其可爱而予以欣赏的。
下附:
吴光先生新著《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吴光说儒》,于2014年7月由孔学堂书局出版,此书属《大众儒学书系·名家说儒》丛书之一,题下共分五篇。
第一篇,题曰“以仁贯道的儒学发展史”,下设九小节。系著者对中国儒学史的回顾与展望,梳理了从孔子到当代儒家仁学的发生、发展、演变简史。指出:儒学自问世以来经历了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近现代儒学和当代新儒学等六种形态变化,但不同时期的儒学在本质上都是仁学的不同表现形态而已,它在先秦时期是“仁本礼用”的道德仁学,在汉唐时代是“德主刑辅”的经典仁学,在宋明时代是“修己治人”的经世仁学,在清代中前期是“经世致用”的力行仁学,在清末近代是“中体西用”的维新仁学,在现代是“开新外王”的心性仁学,在当代则是“新体新用”的创新仁学。
第二篇,题曰 “儒学的智慧与现代价值”,下设十四小节,系著者关于儒学的基本特质、核心价值观、发展方向、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提出了著者本人不同于前人论述的一些原创性观点。如把儒学定位为东方型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论说了儒学的五大基本特征、儒学的政治观、历史观、知行观,儒家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表述等,还对儒家生态观的思想模式、儒家廉政文化的内涵与实践方向,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变与当代论述及其现代性与普世性,“中国梦”的思想解读与及其核心价值观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说。
第三篇,题曰“儒学的创新:新体新用的民主仁学”,下设六小节,著者在简述当代中国儒学复兴十大标志与新儒学主要形态的背景下,论说了著者的新儒学理论即“民主仁学”论。民主仁学的基本思想架构,可以概括为“民主仁爱为体,礼法科技为用”的体用论,“一元主导,多元和谐”的文化观和以“仁”为根本之道、以“义礼信和敬”为常用大德的“一道五德”核心价值观。“民主仁学”为确立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充沛的思想资源,在政治实践上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多元化。它在建立民主仁政、提升公民道德人文素质、辅助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业中将起到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第四篇,题曰“治学方法经验谈”,下设六小节,系著者30年来的治学心得。著者以为:治学方法不在于“求同存异”,而应是“存同求异”;学问之道,贵在“独立思考”,反对空谈与抄袭;提倡分析与综合兼备,坚持经世致用,并提倡“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学术视野、“实事疾妄”的批判精神、“兼采众长,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学者情怀。
第五篇,题曰“弘道兴儒,身体力行”,下设四小节。主要追记了著者30年来弘道兴儒、身体力行的儒学实践,诸如主编《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马一浮全集》,主持《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等资料整理工作,为学界提供了宝贵可靠的原始资料,可谓嘉惠士林之善举;又如筹办三次黄宗羲国际研讨会,筹办国际儒学、国学研讨会、发起成立浙江省儒学学会和发起全国省级以上儒学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中国儒学年会),以及奔波各地进行讲学弘道活动,为儒学的传承、推广贡献了一份心力。
书末“附录”,题曰“吴光儒学论著目录(1979—2014)”,以便读者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