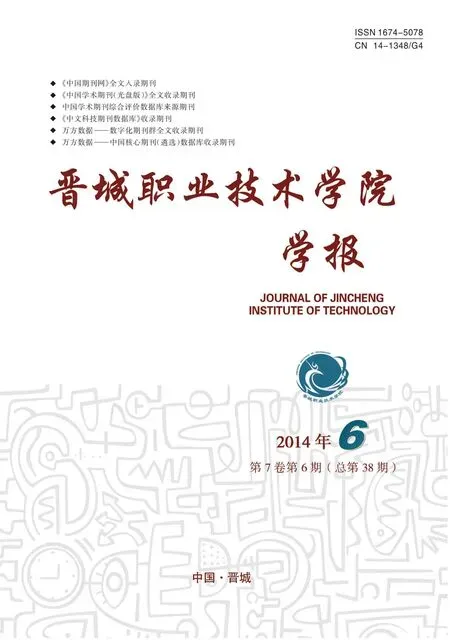试论孟子的“反经行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苗新莉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23)
试论孟子的“反经行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苗新莉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23)
孟子的经权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超越,孟子明确提出“反经行权”,而且理论更加系统化,对“经”“权”提出了度的限制。本文在分析孟子“经”“权”思想内涵的基础上,阐释了孟子的“反经行权”思想,并归纳总结了其思想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度。最后,分析了孟子“反经行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孟子;反经行权;现实意义
经权思想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系统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孔子,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经权”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其思想,并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体会,使孟子的思想体现了灵活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深刻理解孟子的“经权”思想还可以对孟子的“仁义”之说有新的认识。
一、“经权”思想的内涵和渊源
(一)“经”的内涵
“经”本义是指织物上纵向的纱或线,与“纬”相对,后来引申为南北纵向的路。现在常用“经”来指为人处世或选择时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原则。在传统的儒学范围之内,“经”实际上指的是以“仁”作为内在根据的礼。如:“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经,常有,万世不易之道也”(《四书集注》)。
(二)“权”的内涵
“权”本义是指秤砣,如:“权,然后知轻重”,朱熹《四书集注》也讲“权,秤锤也,所以称物之轻重而取中也”。后来引申为两种含义:一是法家所倡导的,指的是权势、权谋;二是儒家所主张的,指的是权变,有权宜、变通之意,指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进行道德选择时应该有所变通和权衡。
(三)理论渊源
在历史上,孔子第一个注意到道德选择的两难问题,也是他首先提出“经权”之说的,但孔子并没有明确讲到“经”。“经”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在孔子看来,“经”就是礼,合礼就是“经”之本,而“权”是对“经”的补充。对此,孔子也曾说过,“可以共学,未可适道;可以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由于孔子明白如何处理“立于礼”和通权达变二者的关系,所以孔子在面对生活或仕途方面的问题时才显得游刃有余,懂得变通,才能做到如孟子所说的“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才能成为“时之圣者”。
二、孟子“经权”思想的阐述
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随着时代的变化,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经权”思想,还对其进行了发展,带有时代的印记。
(一)孟子的“经权”思想
孔子的“经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仁”,而孟子的思想是以“仁政”思想为核心的,因此,孟子的“经权”思想在政治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就是说在施仁政以实现王道的过程中,社会环境和现实的条件是不断变化的,要想有所作为,就要学会适当地舍弃,有所不为,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对客观情况进行变通,这就充分体现了孟子所主张的“反经行权”的思想。
孟子曾借孔子之口来表明自己对“经”的态度,曰:“非之无常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这是说,孔子把人分成四种:中道者、狂者(有进取之心)、狷者(有所不为)、乡愿(同流合污的伪善者),并对其进行了比较:中道者是最可取也是最难得的;紧接着是狂者;狷者又不如狂者;乡愿最为不可取,孟子称之为“德之贼”也。要想杜绝与这样的人交往,只有“反经”。“反”就是反归,“反经”就是返回到做人最根本的道德标准、道德原则。
同时,孟子也提倡“行权”,比如孟子曾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谓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在孟子看来,扬子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墨子又是极端的利他主义者,孟子显然不赞成扬子与墨子的做法,认为要避开这两种极端而采取中间立场。子莫恰好采取中间的态度,这是可取的。“执中”就是要去除两端,而取其中合适的中,适度、中道就是这个道理。这里的“中”也就是“经”,是原则。同时,孟子还说过,“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意思是,中道并不是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和调整,即孟子说的“行权”。“经”和“权”是相互依存,可以变通的,可以说“经”是“行权”的根本原则,而“行权”是“反经”的具体方法,不应只知道抓住原则而不知变通。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根据现实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调整,才能真正的做到遵守道德原则。
(二)孟子“经权”思想的分析
1.“礼”与“非礼”中的“反经行权”思想
淳于髡曾问过孟子“嫂溺”救与不救的问题:“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与孟子观点不和,提出“嫂溺”难题以刁难,希望其陷入困境中。“嫂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伦理难题。一方面“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礼,是“经”;另一方面,“嫂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理应援救,但是伸以援手似乎又违背了礼,孟子指出,这就应该有所变通,不能一味地遵守所谓的“礼”。因此,淳于髡是想在政治上或者说“援天下”的问题上要孟子做出变通,“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孟子立即回击到:“子欲手援天下乎”,这就把问题又推给了淳于髡。孟子认为“援天下”与“嫂溺”是不同的情况,“嫂溺”属于特殊情况,而“援天下”只能以道,是依靠的手段与政策,不能以手。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立场上孟子表现得非常坚决,绝对不会让步,认为必须“反经”,回到道德本质问题。在这里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孟子是如何处理“反经”与“行权”的度的问题了,天下只能施行王道,这是根本,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把这个根都去了,那“援天下”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和必要性了。
2.“孝”与“不孝”中的“反经行权”思想
孟子在“孝”与“不孝”的问题上也涉及了“反经行权”的思想。以舜娶妻告与不告为例:万章问孟子:“《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怨父母,是以不告也。”孟子也还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按照一般的立法,娶妻应该要向父母禀告,征得父母的意见,而舜作为孝的楷模,却不告就娶妻,这似乎有点儿不合道理,是不孝的,仔细想来,舜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思量后的决定。这里的“经”是“娶妻必告父母”,舜的选择是“不告而娶”,这是“行权”的结果。当时摆在舜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娶妻必告父母,二是告父母必废人之大伦,在中国传统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看来,舜前者为不孝,后者为大不孝。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严重,遇到人的大伦问题可以不拘小节,因此而成就大孝。不告而娶虽然有些不符合礼法,但符合孝道,可以体现道德的根本和原则。由此看来,“行权”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定的情况下“行权”,反而能更有效地维护道德,从而也体现了行权也就是反经。
(三)孟子“经权”思想体现的原则
1.以行王道、施仁政为最高准则
孟子以王道、仁政思想贯彻始终,并把这一思想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也就是“经”,这是孟子不可让步的。孟子主张“行权”,但是“行权”不能与“反经”相背离,可以说“行权”的最终归宿也是“反经”,就像孟子在与淳于髡的对话中一样,“天下溺”只能援之以道,不能援之以手,可见孟子施行王道思想的决心。
2.以仁、义为原则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信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信条,儒家一方面讲究要有“信”,比如孔子就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是另一方面,讲“信”要学会变通,不能拘泥固执于“信”。比如,对你的敌人就不能讲“信”,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变通、改变。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惟义所在”。
3.行权之人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孟子与公孙丑有一段对话,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太甲是君主,伊尹是臣子。按照礼制,臣子是不可以放逐君主的,这是违背“经”的。对于普通的臣子来说,这样做就意味着篡夺王位,然而对于伊尹这样一个有能力、为国家安定和长治久安着想的人来说,孟子并不觉得这是篡夺王位。这里孟子为我们指出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行权。他认为那些圣人,有仁义之德的,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丝毫利己之心的人才可以行权,这样的人他们不仅可以心系万民,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握行权的度。
三、孟子“经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经权关系体现的是在原则性的问题面前如何变通的问题,既要体现原则性又要体现规范性。学会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孟子主张“行权有道”,做任何事都要抓住事物本身的道德原则,最高原则。也就是说变通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就是“道义”,不能“违道害人”,做出有损于道义的事,这就体现了“礼义”的规范性特征。“权”既保证了主体行为者的灵活性,同时又保证了主体行为的道德秉性。这为汉代以后“经权一体”的思想以及“常则守经变则行权”等思想的扩充提供了理论来源。
第二,孟子的“反经行权”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主要是引导现实,不过最终目的是要行仁政。孟子在“嫂溺”救与不救中的“权”说,就是解决现实生活中道德冲突的很好的例子,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的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其实孟子的“经权”学说的根本是要教给人们在生活实际中的一些道德实践的智慧,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
第三,孟子对“行权”做了诸多限制,其目的是要遵从人的理性标准。孟子对“经”的态度是反经,孟子对“行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任何社会都必须要有必要的理性,而不能都是完全洋溢着感性冲动,规则的制定是一个社会正常发展必要且必须的。规范和准则是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的保证。人在社会中属于同类,是平等的,因此这个社会便有相同的价值选择标准、道德原则,这样行权才不会造成行权的随心所欲。
第四,孟子的“反经行权”思想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看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懂得变通,不能拘泥于教条。“经”是一个社会稳定的保证,但不能拘泥于“经”,这样一个社会会失去它原有的活力与生命力,显得十分呆板。孟子“反经行权”的思想恰当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既有原则性又不失灵活性,可谓处理问题的典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孟子的“反经行权”思想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于处理我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傅佩荣.傅佩荣解读孟子[M].北京:线装书局,2006.
[3]杨泽波.孟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On Mencius“Anti Norm and Right”Thoughts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MIAO Xin-l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B222
A
1674-5078(2014)06-0064-03
10.3969/j.issn.1674-5078.2014.06.021
2014-05-27
苗新莉(1988-),女,山西太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伦理。
——基于SZH的案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