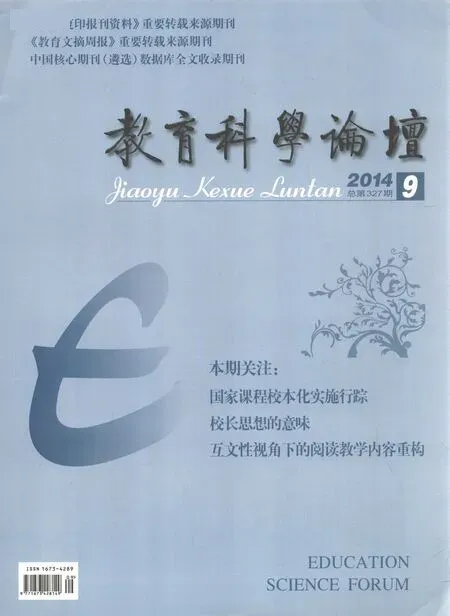互文性视角下的阅读教学内容重构
●毕美娟
王荣生教授曾指出当前阅读教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教师引导学生从事低层次、低水平的“扫读”,而不是高层次、高水平的“理解”。他将广西观课的印象总结为教师阅读教学的“三部曲”:指示性寻找——胡乱地谈论——激情式号召[1]。这种“扫读”“三部曲”使得阅读教学呈现出视野封闭、 互动肤浅和意义虚无特征。这种阅读教学内容被预设且固化为某几点,简单的线性思维封杀了学生基于文本内容的丰富思想感情, 阅读教学创新以及教师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相应淡失。
一、互文性及其对阅读教学的重要规限
互文,在中国古代,多指一种修辞现象;互文性,是指文本之间的意义关涉,属舶来品。有学者对二者的区分曾专门探讨[2]。 文本也取其广义,不仅指书面的文字文本,也包括口头的话语文本。《论语》中孔子对弟子问“仁”、问“政”、问“孝”等同一问题的不同答语,就体现出一种极为鲜明的互文性。互文性即文本间性,“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3]。一篇课文不是孤立的作品, 而是和其他作品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 阅读教学虽然不能也不必穷尽由这篇课文所延展开来的文本“森林”,但是总可以发现和这篇课文距离相近的几棵“树”,进而引导学生管窥到相对较大的问题视域与意义空间。 教师引导学生关注的,绝不仅仅是单篇课文这棵孤立的“树”,而是由这棵“树”所引起的书面文本和口头文本的丰富关联,进而领会到意义寻求的由此及彼与触类旁通。我国古人强调的“神与物游”,便是建基于互文性文本的阔大视野与自由想象。
互文性对阅读教学就因此具有了种种规限,上述“扫读”式阅读教学显然是严重违规。 互文性阅读教学的目的,在于提升师生的语用能力和自我心性,突破复制教学模式和记忆式学习牢笼。
(一)阅读教学要从单篇视域走向多篇视域
关联性文本选择使得特定文本意义的视域扩大,给读者带来想象张力和思辨空间。思辨睿智和审美兴味, 是互文性阅读必然会带给人的思想情感福利。
(二)阅读教学要从还原再现走向创造生成
互文性理论注重多部作品的叠合与互渗, 彼此映衬与相互折射。 这种文本上的互文性正好印证了思维上的共通脉络。 文本作为一种选择性记忆和书写,存在许多意义空白点。读者自然会受到作者思维图景和逻辑思路的某种指引和牵制,但是读者的思想旁逸与思维变异也会存在。
(三)阅读教学要从教控制学走向教解放学
新语文课改提倡“个性化阅读”,个性化阅读其实就是一种互文性阅读。 阅读教学不能引导学生追求同一性阅读,而是追求和而不同的互文性,体现文本意义阐释的“多声部交响”。 此时的互文性主要是指课文文本与师生话语文本之间的意义关涉, 交织着课文文本与其他书面文本之间的意义关联。
二、互文性视角下阅读教学内容重构的三个层次
王荣生教授曾指出:语文教学内容既包括在教学中对现成教材内容的沿用,也包括教师对教材内容的“重构”——处理、加工、改编乃至增删、更换;既包括对课程内容的执行, 也包括在课程实施中教师对课程内容的创生[4]。课程内容的创生既有教师视角的文本理解和教学处理,也有学生视角的文本思考。学生或对或错或不足或困惑的文本理解, 是课程内容创生的重要基石。 于是,课程内容、教学内容和教材内容三者,就构成极为鲜明的互文性。从互文性视角看,阅读教学内容重构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一)文本意义发现的知觉建构
此系师生对课文文本与关联文本的对象性实践。文本符号作为共享的集体记忆和文化通道,其意义能够被群体中的个体所感知与发现。 作为受教育儿童,由于知识经验的不足,必然会存在集体记忆上的缺损与文化通道上的障碍, 其关于文本意义的主动建构自然会出现某种不足, 师生的文本意义发现就会存在认知落差。认知落差的存在,正是新语文课程改革强调要“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与理解”的缘由,是教师实施教学的重要依据。
(二)思想认识交流的经验互构
此系师生围绕课文文本与关联文本的意义建构而发生的沟通性实践。阅读教学要求学生课前预习,也就是要求学生带着对课文文本意义的某种发现与困惑到课堂上来,与人分享或寻求支援。实施了这一环节,教师就是将学生主动建构出的或对或错或不足或困惑的文本理解,转变成重要教学资源,同伴之间的相互学习就成为阅读教学内容重构的重要手段;缺失了这一环节,阅读教学内容就是教师对学生思想认识的简单外部强加,阅读教学于是就成为教师的霸道施教。
(三)文本自我理解的反思重构
此系师生由认识分歧和认知困惑而诱逼出的伦理性实践。 教师有义务与责任帮助学生意识到课文文本理解或对或错或不足或困惑背后的逻辑推理,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思维递进与认识攀升。学生的文本理解和学生自我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关系,见证着学生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过程。应试背景下的阅读教学大多引导学生关注文本意义本身,所以才会推崇与复制名家的文本理解,却让学生自我淹没与迷失。 其实,主体和文本的关系、主体和主体的关系都是中介, 最终都要回到主体与自己的关系上来。“理解他人就必须在自己身上设身处地地‘重构’他人的经验。理解作为一种再体验,意味着体验他人之人生与体验自己之人生的一致性, 其实也就是理解自我、发现自我。 ”[5]
三、互文性视角下阅读教学内容重构的主要策略
由上述三个层次所决定, 阅读教学内容因为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经验和语境、 时间上的变化和他人经验和语境的刺激等而出现微妙变异。 阅读教学要摆脱对文本理解现成结论的先在性控制, 教师要学会虚心倾听学生的看法, 使得语文课堂教学成为一个“时机化的”、“境域发生式的”和“相互构成着的”[6]意义生成场域, 师生的课前准备都会因为课堂情境中的互动机变而出现调整和变化。 经历上述三个层次,文本对象的自我认知,文本对象的他者认知,以及基于自我与他者文本对象认知辨析的自我认知三者,就内在地包含着因为时间变化,所带来的学生思维转变。这就是佐藤学教授提及的,学习即三种对话性实践的有机统一体:学习不再是学生单纯掌握知识的认知性、文化性实践,还是协调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政治性实践以及致力于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伦理性、存在性实践[7]。那么,互文性视角下阅读教学内容重构该如何操作? 下面以陈钟樑老师的 《合欢树》课堂教学[8]为例加以解释。
(一)多角度文本关联策略
《合欢树》是作者对母亲的温暖回忆与深切怀念,瘫痪对母子的创痛与母亲对儿子的至爱,以及理解母爱的渐进心路历程,是苦难中溢满温情的生命书写。合欢树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苦难生命历程中的母爱所昭示的人格品质和所孕育的精神果实, 感人肺腑。陈老师的教学中出现三次横联,便显示出三个角度的互文性:一是主题。教学起始阶段引入史铁生《我与地坛》中的一段文字:“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 她那艰难的命运, 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后面又联系王安忆对史铁生散文的评价:“在叙述中流露原初面目的情感”,“情感经过历练逐步趋向理性”,“理性最终孕育着哲学的果实”,并借“意蕴”一词再次将《合欢树》与《我与地坛》相联系。 “地坛”与“合欢树”具有某种对应关系,都是一种精神象征。二是写作手法。教学过程中,陈老师为了引发学生思考作者写母亲为何还要写一群老人,联系《故乡》中作者写闰土还写杨二嫂, 谈人物写作关涉到文章主题的深度与厚度, 一种极其重要的折射作用。 三是句义。陈老师在引导学生理解“悲伤也成享受”一句时,联想到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即一个小孩走进森林深处的恐惧与走出困境的喜悦, 并引入茨威格的《世界最美的坟墓》,向学生传达“时间距离产生心理美感”信息,母亲对儿子倾心付出的温情元素与作者对母亲愈来愈深刻的理解,这种心灵的呼应与叠合,使得母亲离去的悲伤中也和着许多感动和美好。
(二)高质量对话互动策略
从“灌输”走向“对话”,对话教学是新课程改革以来极力提倡的重要策略。 对话教学的两个要素在于问题设计的精准性与答案寻求的思辨性,它体现出教师“让学生学”的教学策略。 对话式阅读教学的关键在于寻求差异,催生学生的个性化阅读,这与一些老师将教学导向一个预定答案不同。 陈老师注意用问题引发对话,如第一自然段中“母亲什么性格”,学生依次道出“活泼”、“开朗”、“好强”、“爱美”;第二自然段的母亲变老表现,学生指出“头上开始有了白发”, 老师补充 “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怎么会烫了呢? ”);如引导学生理解母亲为什么挖含羞草(后来变成合欢树)回家? 理解含羞草和母亲的相似处,便有一个逐步深入的师生互动过程, 将学生从母亲爱美、 含羞草生命力顽强过渡到对母亲与含羞草的一体化认识:温柔而坚强。 后来让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多次提到那个小孩儿和树影儿?”学生提到“折射”与“生命的循环”,耐人寻味。整个教学过程存在一个对话互动的互文性格局。
(三)深层次语言咀嚼策略
作品语言的深层次意义是需要咀嚼的, 是需要结合具体语境来理解的, 作品阅读和阐释就会存在文本语境与读者语境的复杂交互。 陈老师在引导学生理解老太太们和史铁生在一起时从 “聊天喝茶从不提起母亲”到“终于提起母亲”,指出“终于”一词包含三层意思: 时间的等待、 头脑的酝酿和行动的努力,并先让学生理解这个词的具体语境:老太太们害怕提起母亲会让史铁生伤心难过, 但更害怕史铁生会忘了他的母亲, 母亲在老太太们心中是挥之不去的永远惦念, 那棵茂盛的合欢树便是一路风雨兼程母亲的最好见证。显然,“终于”是要和“提起母亲”联系起来理解,是“老太太们”、“母亲”和“我”三者之间关系性复杂心理活动的结果。因此,“终于”和“最终”截然不同,不能随意调换。还有像“时间”、“悲伤也成享受”、“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和那个小孩儿” 等,“母亲”的那种顽强抗争生命意识、“合欢树”所沉淀的伟大母爱和“我”的生命觉醒,成为理解这些语言的具有感染力与引导力的渲染性文本语境, 构成参差多态的互文性。 文本内的人与物、人与人之间,以及基于文本理解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都存在某种共通和感应。
由上述三种策略所决定, 互文性视角下的阅读教学内容重构是师生语文经验参与文本意义建构,进而发生语文经验互构, 并跃升到文本意义的反思重构,隐含着师生的语文思维和心性变化。文本意义建构、互构和重构本身,都是一种时间性和境域化理解。教师要超越课本知识传递的传统做法,转而通过关联性的文字符号文本、 生活经验文本和生命体验文本,引发学生的趣味性沟通和创造性转换,并大力关注和不断完善学生的话语表达, 从而活化学生的语文思维。如有学者指出,“如果不通过表达展现,我们如何去确证,如何去验证,又如何知道从哪里着手去修正、补充、完善他们?如果儿童仅仅是充当‘听话者’的角色,作为被规训者,作为教育者‘语言讲述的对象’,而没有表达自我感受和意愿的机会与意识,其自我意识、求知欲望如何培养,其进取、探索、开拓品质又如何形成? ”[9]这样看来,互文性视角下的阅读教学内容重构,教师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文本意义理解理所当然,但是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自我意识、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同样重要,教师也要注意培植。后者是学习的额外福利,虽然隐蔽,但更为重要。
[1]王荣生.当前阅读教学的问题在哪里:广西观课印象及讨论[J].语文学习,2012,(3):12-17.
[2]周流溪.互文与“互文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37-141.
[3]转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4]王荣生等.语文教学内容重构[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
[5]张文喜.自我的建构和解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4-115.
[6]张祥龙.现象学视野中的孔子[J].哲学研究.1999,(6):67-71.
[7][日]佐藤学著.课程与教师[J].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23.
[8]陈钟樑,余映潮.陈钟樑老师<合欢树>课堂教学实录评点[J].语文教学通讯.2012,(2):15-19.
[9]和学新,焦燕灵.试论表达的教育学意义及其实现[J].教育研究.2006,(9):2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