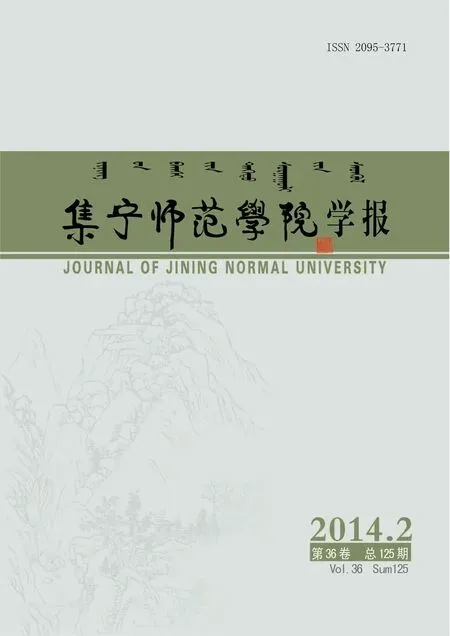论王安忆《众声喧哗》的边缘化叙事
匡妙妙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阶段,王安忆总能以风格多变的作品走在时代的前沿,获得读者的瞩目与欢迎。可是,评论者们却为此头疼,因很难对其作品进行归类和总结,无法判断其下一里程碑是什么,故称之为难“追踪”的作家。实质上,这是由王安忆独特的写作姿态和文学叙事的方式所造就的。王安忆曾说,“小说的创作者是边缘人,处于边缘化立场,与主流保持距离。”①而“边缘”一词的被提起、被关注实际上是生命个体自我独立意识的确立,作家开始远离主流话语的大众立场,拾起边缘生活碎片,获得新的文学价值和心灵境界。谈及王安忆新推出的短篇小说《众声喧哗》,就立足于“边缘处叙述”,着眼于现世安稳的日常生活,诗意地观察着被遮蔽的边缘人物,以普通大众的生存观照着整座城市的变迁,书写着“自我”的精神本真,表达着生命的独特感悟和理解。
一 对边缘人物的诗意关怀
从“雯雯系列”开始,王安忆小说中塑造的形象往往都是远离社会中心的小人物,诸如打工者、乡下人、小市民等弱势群体。这些形色各异的小人物处于城市的一角,艰难地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斑斓生活,凸显着个体生命的价值。之所以选择这些叙述对象,与王安忆的个人经历是有联系的。一直以来,作者不断提及自己的“外来户”身份,强烈的外来户体验在她生命中的感觉似乎已经沁入骨髓,她曾坦言,“在这座城市外来人之感几乎全来自于我本人。”②同时,身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王安忆敏锐地察觉到乡土与城市之间二元对立状态下所呈现的尴尬态势,而作为一位力图写“人民”,反映真切生活、有良知的作家,有义务对城市生活边缘的群体——草根阶层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进行着不懈地开拓与挖掘。在《众生喧哗》中,欧阳伯伯——作为从宁波迁徙到上海的城市异乡人,是以一个城市变迁亲历者的姿态进入了城市。丧偶后,为了排遣孤独,在繁华的大都市中选择开一家纽扣店,惬意地享受着子女的关爱和照顾;年轻保安——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青年男人,在家人的宠溺之下成长,身无一技之长,徒有一张女性化的好看脸蛋,心安理得地游走于社会的底层;六叶——一位进城务工的外来者,满身粗鄙俗气,却携有冒险精神,只身闯荡上海追求梦想。这三位人物可以说各成体系,各自代表城市某一种文化或生活状态,他们之间并无联系,只是恰巧进入王安忆的创作视野中。她为此变成讲故事的人,贴近群体的生活,追踪每一位底层人物的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愿意倾听所有的声音。
王安忆对边缘人物的刻画没有执着在苦难叙述的层面上,而是从“人”的意义上观察这些小人物,因为小人物的生活并不拘束于社会硬性的规定之中,他们可能潜藏着某种活力和民间的独特力量,他们常常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王安忆就《众声喧哗》中为何选择如此在社会上“不起眼”的主人公,曾说:“其实他们生活得很有诗意。他们之间有一种邂逅,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抒情,而一些老板一样的 ‘主流’我倒觉得生活得像机器一样的,和员工、下属的关系是一种决定性的关系。”欧阳伯伯经营着小小的纽扣店,即使没有生意,也尽力将柜台上的电话擦得干干净净,年轻的保安下班之后定时前来报道,兀自拿些粮食去喂养天上的鸟儿,有时跟着伯伯借着午后柔暖的阳光进入到梦乡。他们一个口吃,一个话语叙述不清,却在孤独的漩涡中,有着类似相濡以沫的暖意涌出,抑或相视一笑便能弥补彼此精神上的空虚。作者用理想的眼光观照着大众的日常生活,提炼出自由惬意的生活态度和诗意享受的生活乐趣,奠定了其温存美好的日常叙述基调。在叙述六叶艰难地拼搏时,更多的是用轻快自在的笔调。处在基层的六叶能口若悬河地向欧阳伯伯和保安介绍着世界市场的走向和金融经济的发展,甚似一场宏大的事业蓝图的筹谋。面对一场城市洪水的袭击,并未浇灭她的梦想,转而借钱批发大量货物。后来,凶悍的丈夫带着孩子出现暂时中断了这场“伟大”事业的进行,可她仍然想方设法地改变自己生活的处境,追求着梦想。王安忆用温润的眼光注视着芸芸众生,以诗意关怀的姿态融入小人物的生活史中,目的只为挖掘出背后潜藏的一种对市民阶层生命力顽强的感动与赞叹。
二 以“小”窥“大”的历史观
在全球化入侵中国的背景下,城市的急遽演变导致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新生代”作家群体以 “边缘化”的写作姿态观望着社会变迁,从最初注重倾诉个人体验、彰显个体情感,逐渐演变成欲望苦闷的肆意宣泄,媚俗地迎合大众的文化需求。而王安忆选择将目光转移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跳脱出“情感宣泄”、“欲望骚动”的个人化写作。她认为,“边缘化”的叙事更要强调的是生活对于文学无可替代的价值,从大众生活中投影出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她笔下记载的都市历史不是灯红酒绿、放纵不堪的夜生活,不是惊天动地、响彻寰宇的重大事件,而是平凡琐碎、真实质朴的日常生活。她曾直言:“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无论多大的问题,到小说中都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日常生活。”③她所要表达的不是凝重宏大的主流历史,而是厚实韧劲的民间小事,于此同时让我们自然地从这些边缘事件之“小”中窥视到时代之“大”来,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边缘”精神。“这种‘边缘’精神正是‘小说’之‘小’的重要体现;也是‘小说’具备‘大气’的必要条件。”④
王安忆在慵懒阳光照射的路南老公寓着手创造的这部短篇小说《众声喧哗》,叙述着老商业街上门铺的更换,对比着雄伟壮丽的新建筑,转而提及欧阳伯伯的纽扣店,在数度岁月中内部构造不断演化。欧阳伯伯在痛失老伴后,日复一日地数着纽扣,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只知道守着自己的纽扣店,自我陶醉在狭隘的生活经验中,无关紧要地看着身边世界的改变。只用简单的两句,要么采用否定句式“不可能的啊”、要么采用肯定句式“就是讲呀”,应对着喧哗的人生。欧阳伯伯的处事哲学代表着昔日上海文化的市民保守心理,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传统。在六叶上门与其探讨商业社会如何运筹,希望与其一起做生意,可欧阳伯伯任万物风云变幻也仅是回答六叶“不可能的啊”,另一人物保安在姐姐们“囡囡”的呼唤声中促成软弱无能、毫无主张的性格特点,他悠然自得的接受着欧阳伯伯的市侩文化,潜移默化地受制于欧阳伯伯看似深刻莫测实则一无是处的“人生经验”。王安忆借欧阳伯伯、年轻保安的生活理论牵动着历史的神经末梢,实际是作者在寻找“旧上海的灵魂”,用固步自封、无所作为的形象消解了上海神话书写的迷思蛊惑,更加真实地描摹出城市化进程中的细节变化。相比较而言,外乡人六叶的生活是热闹喧腾的,她无所畏惧地规划着自己的宏伟事业,尤其是作者描述她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地带着欧阳伯伯和保安,指挥着他们快速地穿梭在批发市场中。六叶这种自由奔放、生机勃勃的冒险精神极具上海“新”文化的内涵,这种“新”逐渐对抗着“旧”,也成功加速着“旧”的消解。而这块“旧”的寒冰在欧阳伯伯借钱给六叶时就开始逐渐消融,小说最后结尾说到,欧阳伯伯主动携着保安走向众生喧哗的自由市场,在零碎混乱的街巷中看到了六叶的身影,他们感受到了醒目的光线,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并深深地陶醉其中。王安忆用边缘人物精神生活——“陈旧保守”与“创新活力”的对比,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小事中,融进上海文化的种种变迁,打开了一扇通往上海回忆和上海叙述的新大门。
三 “自我”的本真书写
王安忆认为,“小说的理想是,以语言为材料的故事形态,建设一个心灵的世界。”⑤而在《众声喧哗》中,她巧妙地通过边缘人物的当下世俗生活中窥探出整个城市的真实纹理所在,为的就是“使小说文本在直面世俗生活的同时,也直接逼近了作家的内心真实。”⑥她深知那些琐碎的、世俗的、庸常的人性情感,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的内在真实性,完成对“自我”的本真书写。王安忆作为上海都市“外来户”的代表,强烈的孤独漂泊感始终围绕在她的身旁。而后将之沉重的情感带入笔下的人物,年迈的欧阳伯伯,除了昏睡在躺椅上,只剩下不知疲倦地数着纽扣,保持着最后一分清醒。城市飞速运转的节奏,即使被吸引,也再没有力气承受这份喧哗,只能慢慢容纳着这样的“蒸腾”;被嘲讽的保安,无论在白天黑夜总戴着墨镜,如生活中的怪胎,看起来十分可笑,但是在笑的背后却有着隐隐的哀痛。他无情地被社会淘汰,企图用墨镜躲避一切世间纷杂,过滤掉那些次要的、庞杂的、零碎的,留下能够与之沟通的精髓;标榜跟随时代潮流的六叶,虽然张嘴即是来自国际都市的高级服装,其实自己不过是批发市场里的常客。脱口而出的商品时代、知识产权等专有名词,也不过是游走于城市之中获得的概念印象。当她回到夜市生存,离开都市的繁华镜像,“时间变成一条无边无岸的河,没有来路,没有去路,人在其中就不是漂,而是浮。”
“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色彩强烈的醒目的奇骏的东西,现在人到中年,慢慢安静下来,喜欢蕴涵很深的戏剧性,在底部的像潜流的东西,看上去面目特别安静,但里面有一种演变动力,由很小的东西一点点积累起来,最后形成一个大动作。”⑦王安忆将这样的写作启发完美地实践在这部新作中,文中两个主人公都是有语言障碍的,而她却为小说命名为“众声喧哗”,戏剧性地将两者衔接起来。实际上,小说人物的无声或寡言彰显的就是“沉默者”的情态,他们成功地在喧哗城市的底层边缘安稳地讨着生活。作者“滑稽”地设计欧阳伯伯在闹腾的情境中用数纽扣来保持心中的宁静,而这数纽扣的行为也被看作一种特殊的人生修炼方式,其中渗透着生活的禅机。在保安因赌博欠债后,欧阳伯伯一眼便洞穿他的心思,采用一种淡然处之的传统文化策略——静静地数纽扣,来点醒这位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摆脱了现实困境和心理困境。在文章最后一段结尾说,“这一个夜市,就好像从七浦路切下来的零碎,散落至此,离乡背井似的,于是压抑住了声气,人们都在悄然中速速地动作。沉静中,却有一股子广大的喧嚣,从水泥地路面下升起,布满,天地间都是嘁喳声。”王安忆饶有意味地将“沉静”与“喧嚣”发生冲突,实则更凸显出“蒸腾”的生活中丰富的声音和光线的机理。虽然漂泊的生存状态让这些边缘人孤独落寞,但是并未抑制住他们领悟到生命另一处的禅机,继续奋力地朝着既定的方向迈进。
在《众声喧哗》中,王安忆秉持着“边缘立场”,用“边缘”视野来关注文学内在的“边缘”人物,而“强调‘边缘立场’是为了发现中心和主流话语背后被遮蔽和覆盖的看不见的东西,在主流之后看到一些新的东西。”⑧毋庸置疑,王安忆的坚守是正确的,诗意关怀下的草根阶层各有自己的处事哲学,都拥有个体坚韧的求生力。作家细致地深入他们日常生活的样貌和情态,思考当下城市精神文化的种种变迁,从而真实面对“自我”的心灵世界,在喧嚣的尘世中寻得一份净土,安抚落寞无根的一众灵魂,最终诗意浪漫地呈现小人物们该有的生命价值。
注释:
①王安忆,《歌星日本来》、《香港的情和爱》,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②王安忆,《纪实和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③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文学报》,2000年第11期。
④何永康,《二十世纪中西小说比较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9页。
⑤⑦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分别引自第290页,第112页。
⑥管宁,《从文本体验到欲望书写—对先锋小说新生代写作叙事方式的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第77页。
⑧南帆,《本土的话语》,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