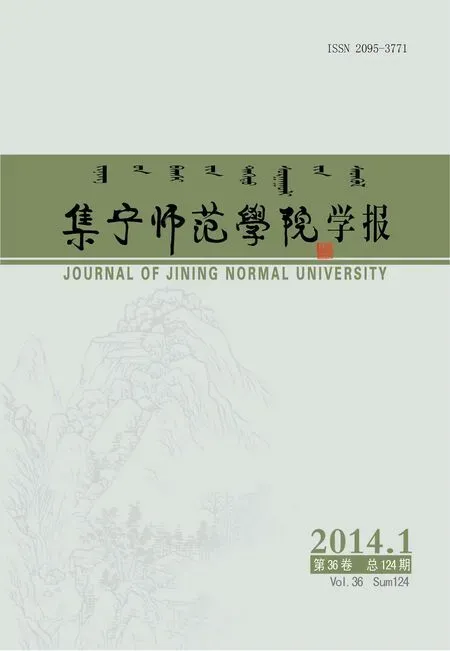《十日谈》伦理叙事的重新阐释
韩 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10)
一 教会淫乱的真实再现
基督教深受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浸润,它的律法道德观念来自于犹太教,它的基本精神孕育于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摇篮,说到底就是唯灵主义的浪漫精神,即灵魂或理想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彼岸世界的追求。①人要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必须克制肉体上的种种欲望,把一切奉献给神。②奥古斯丁认为,性欲是人类邪恶中最肮脏、最不洁的,最能体现人对上帝旨意的不遵从,它能彻底摧毁理性和自由意志,是人所驾驭不了的最基本、最普遍的邪恶。③所以基督徒只有完全否定性,过着不受玷污的贞洁生活,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11世纪教会改革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取消教士的婚姻,建立教士独身制度,使禁止性欲从早先的被少数人追求的理想变为后来对基督教教会人士的绝对要求而强制实施开来。④世俗大众作为一般信徒,虽然可以结婚,但性只是为了生殖而不是为了求欢。婚前性行为、通奸、乱伦、性变态等行为是对神的大不敬,必须一律火焚处死。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更多的政治权力,有意识地用“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封建制度,用人欲来对抗神权。人文主义者们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着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他们用各种方式去赞扬人生的伟大,歌颂人生的价值和提倡人的尊严;大力鼓吹人的意志自由和个性解放,并把这种观点作为同教会禁欲主义进行斗争的手段;针对教会的蒙昧主义,大力宣扬知识的作用和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肯定人、注意人性,要求把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⑥
自中世纪以来教会就兼具了精神领袖和世俗领导人的双重职能,他注定有着理论超越性和行为世俗性的双重特征。在海外贸易繁荣促使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拥有特权的教会的世俗性特征显得尤为明显,而过分的世俗化,导致了教会精神领袖地位的变质。⑦《十日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抨击了当时政府的腐败和教士的堕落,讽刺了教会的罪恶和黑暗,批判了僧侣的奸诈和伪善,表达了当时平民阶级挣脱教会和宗教枷锁的要求。⑧实际上,《十日谈》关于教会腐朽与淫乱生活的批判都是中世纪教会真实生活的写照,并不仅仅是作家出于文艺复兴的时代需求而刻意夸张的结果。
14世纪以来,教皇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名目繁多而又花样翻新的税收、贡赋、费用为教皇赢得了“敛财机”的口碑。教会其他人员在教皇的榜样之下有过之而无不及,肆无忌惮敲诈勒索,兜售赎罪券。⑨教会还设置了一套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教会人员进一步垄断文化,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权,肆意歪曲、篡改《圣经》。中世纪强烈鼓吹禁欲主义造成的结果是纵欲的强烈反弹。在中世纪的晚期,有些教士公然供养姘妇,甚至娶有妻室,全然不顾教士理应独身的教规。⑩一些修女开始穿时髦的衣服,参加宴会,随意会见来访的男客,甚至留客人过夜,修道院成为神职人员半公开的妓院。在1166年吉尔博蒂尼修道院里甚至发现一个修女怀孕。[11]以至于,人们普遍怀疑,在男女双修的修女院,神职人员是否能够严守修道规程和道德准则。到了13世纪,许多双修的修道院都解体了。14世纪的教会,上至教廷下至低级教士修士的腐朽堕落已经无法遏制。人们对教会非常失望,从而引起了对宗教信仰的普遍怀疑,于是意大利不信宗教的风气盛行,教会面临着严重的信仰危机,教会人员的价值观念在这个大潮中不可避免地与俗世趋于一致。[12]
以薄伽丘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所反对的主要是,基督教教会僧侣对不合时宜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清规戒律的固守,反对他们利用基督教来实现个人的邪恶目的,并不反对基督教本身。作家本人就是天主教徒,他相信基督教本身是个伟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作家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大肆宣扬人的情欲价值,但这种表达又是在反对现实教会和教士们的丑恶行径中生发出来的。他一方面要坚持基督教真正的价值观,一方面又要恢复被宗教戒律扼杀的人性。[13]
二 欲望化的典雅爱情
骑士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不仅直接作用于当时社会,而且对后来的社会也产生深远的影响。[14]在11世纪末以前,骑士对妇女的态度冷漠,行为粗暴甚至残忍。从反映骑士早期生活的史诗中可看到,他们不仅强暴领主的妻子,甚至还强奸和杀害修女。[15]骑士文学中的典雅爱情观产生于11世纪末的法国南部地区,最初主要是以新型的普罗旺斯抒情诗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此类诗歌在法国北部、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地区和国家的传唱,这种爱情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6]骑士文学中的典雅爱情,往往是社会地位比较低的骑士与出身高贵的“已婚”女性之间的爱情,这种爱情以忠诚为基础,往往表现为婚外情的方式,不以最终的婚姻为目的,通常会得到贵妇丈夫的赞赏,同时它以勇敢的战斗、彬彬有礼的举止和多才多艺的展现为表达方式。[17]女性作为父权私有财产的“第二性”,一直深受其压迫和奴役,并且早已被其规范了行为准则和性别角色,他们必须忠于丈夫,保持贞洁,女性贞洁作为一种道德义务甚至高于生命本身的价值。而典雅爱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两性关系,男女两性之间是平等的,甚至表面上女性权利要高于男性权利,骑士甚至愿意为贵妇肝脑涂地。骑士与贵妇之间也可能是一种通奸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典雅爱情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少,大部分典雅爱情都是精神恋爱,以追求绝对圣洁的理想化爱情为目标。典雅爱情符合并顺应了基督教的思想,得到了教会的默许,并最终成为基督教义所倡导的贞洁崇拜的典范。[18]
古代社会对通奸的惩罚是非常严苛的。古代雅典的刑法规定:当男子发现其妻、姐、妹、女儿与人通奸,他有权将对方男子当场处死。[19]恩格斯说:“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时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20]《十日谈》中的通奸叙事正是对典雅爱情中的柏拉图之爱的一种补偿,市民伦理从理想主义的精神之爱升华为理性主义的性欲之爱。[2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的教会仍然把性爱列为七宗罪之一,婚姻中的性爱通过赎罪还可以得救,但是通奸则是该入地狱的重罪。有记载说法国的两名骑士由于被指控与王妃有染而被阉割,然后用马拖至绞刑架处死。[22]所以说,薄伽丘的通奸叙事仍然具有向传统秩序挑战的强烈意味。
三 女性异端运动的影响
在基督教神学家眼里,女性作为男性肉体欲望的载体,应该对男性由于性而导致的神圣性的丧失负全部责任。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认为:“女人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她是死亡之门,是毒蛇的信徒,是魔鬼的帮凶,是陷阱,是信徒们的灾星。”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传说更加确认了女性作为男性的从属地位。在基督教这一权威观念的笼罩下,中世纪的女性不仅被普遍地排除在教育和文艺创作之外,她们的基本生存权利也得不到保障。[23]虽然,12世纪随着十字军的东征,在西欧各地出现了对玛利亚的崇拜,但是这对整个社会女性地位的提高没有根本的作用,因为玛利亚是童贞女,社会上绝大部分女性都不是童贞女,与其说人们崇拜女性,不如说人们崇拜的是贞洁。另外,在欧洲中世纪文学作品中,似乎将女性推到了一个无上的地位,“人们应该把她们视为世间最有价值的珍宝,并永远赞美她们!”[24]而现实生活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却恰恰相反。而且,在文学作品中鄙薄的言辞也常常穿插其中,文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游走于赞颂与谴责的双重立场当中。无论是赞扬还是责骂,被写入作品中的言辞都是针对所有的女性,这便可以看出欧洲中世纪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重视与轻视这两种态度的对立。[25]
男权的压制必然激起广大女性的不满,表现之一就是大量妇女加入新兴的各种异端运动,如贝居因运动和古列尔迈教派的大众异端运动,在异端运动中,女性获得了以前不曾拥有的某些权利。贝居因妇女被称为 “第一批女权主义者”。而古列尔迈派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兴起,女基督、女教皇、女性写作的福音书、女性宗教等思想无疑是女性极度自我认同的完美展现,她们指出,女性之所以能救赎就因为她是女性,是与男性同等的性别,与圣洁、谦卑、脆弱等修饰词无关。[26]薄伽丘说:“多情善感的女性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她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为了多少弥补这份缺憾,我才打算写一部书,给苦于相思的少女少妇一点安慰和帮助。”[27]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利用大量篇幅对女性美德大加褒扬。
《十日谈》的一部分作品歌颂了女性的智慧和坚韧。第1天的“菲亚美达的故事”中,法兰西的独眼龙国王爱上了蒙费拉托侯爵的妻子,他派遣侯爵的队伍先行出发,自己却来侯爵家作客。侯爵的妻子一下子就猜出了国王想调戏自己的心思。她给国王端上来的每一道菜都是母鸡做的,暗示所有的女人都是很贞洁的。第2天的“菲罗美娜的故事”中,意大利热那亚商人贝纳卜称赞自己妻子忠贞,安勃洛乔与之打赌,赌他可以勾搭上贝的妻子。实际上,安并未勾引成功,但他却使计窥视了太太的裸体,同时偷窃了一些东西,他利用这些所谓的证据获得胜利。信以为真的贝命令仆人杀死妻子,仆人心软放过太太。太太女扮男装,辗转进宫伺候苏丹,后来被提拔为大臣。她使计将安与贝两个人都带到苏丹面前,命令安说出真相。真相大白后,夫妻二人重修旧好。第9天的“菲罗美娜的故事”中,两个男子爱上了有夫之妇,女人使计拒绝他们的追求。
《十日谈》还有一部分作品歌颂了女性对爱情的忠贞。第5天的“爱米莉亚的故事”和第4天的“斐洛特拉多的故事”,都是私通殉情的故事。第4天的“潘斐洛的故事”中,小姐与一位平民相爱,情人暴死在小姐的怀中。当她和女仆一起把情人的尸体抬到街上的时候被巡警抓到。知事想趁机占小姐的便宜,小姐拼死不从。后来她到修道院做了修女,一直过着贞洁的生活。第4天的“菲罗美娜的故事”中,小姐与仆人私通,小姐的三个兄长知道后秘密地处死了仆人,小姐抑郁而死。第四天的“菲亚美达的故事”中。郡主婚后成了寡妇,与一个侍从相爱。王爷知道女儿的私情后非常气愤,郡主与侍从两个人都是宁死不屈。侍从纪斯卡说:“爱情的力量不是你我所管束得了的。”[28]郡主说,“假使人死后还会爱,那我死了之后还要继续爱他。”[29]亲王杀死仆人,小姐凛然殉情。亲王最后遵照女儿的遗嘱将这对苦命的有情人合葬。这些性灵飞动的女性,仅仅是男性世界的一个点缀,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女性社会和家庭地位的卑微,她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道路漫长而艰难。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研究论文中,研究者总是把“好感”称为“爱情”。比如关于西蒙被启蒙的故事,有些研究者就将其称为爱情。在欧洲中世纪,人们还是普遍实行包办婚姻,男女双方没有婚姻自主权,所以“灵肉一致”,“互相爱慕”就是人文主义者世俗情怀的一种渴望。同时,那个时候两性关系是一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模式,所以“两性平等”也是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突破。而且人们长期在父权和神权的压迫下,个体意识消失所以“个人本位”的个体意识的复苏也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在当今社会,人们对爱情的定义除了以上几点之外,还必须具有排他性、持久性和责任感。爱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状态下,两性之间以共同的生活理想为基础,以平等互爱和自愿承担相应的义务为前提,以渴求结成终身伴侣为目的,而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自主结成一种具有排他性和持久性的特殊社会关系。[30]所以说,在《十日谈》的很多故事中,所描绘的男女二人之间的密切吸引,从当下的视角来看仅仅是一种好感,还没有上升到爱情的高度,而上面这几个女性故事中,男女双方的真挚情感则是一种美好的爱情。
四 人格平等思想
《十日谈》包蕴着两性平等的人格平等思想,在第四天的“菲亚美达的故事”中,郡主勇敢地与一个侍从相爱,她高呼“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样的机能、同样的效用、同样的德性”[31]。这种人格平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并不是横空出世,多少也是受基督精神的影响。
基督教教义和教会与人文主义者的关系十分复杂,人文主义不是建立在沙漠之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之中。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传统和精神,不是由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直接加以继承的,古代及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在其间所进行的传递工作也不容忽视。人文主义新文化摒弃了基督教的封建神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添加了新的内容,把目光更多地投在人的身上,注重世俗生活和人的存在,更充分体现近代社会的特征。[32]
从斯多葛学派开始,出现了普遍的人格平等的思想,基督教吸收了斯多葛学派的平等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强化,即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不平等仅涉及人的肉体,而不涉及人的精神。[33]14世纪出现了像约翰·威克里夫这样的对罗马教会进行抨击的宗教改革家。他所倡导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打响了欧洲宗教改革的第一炮。他从教会守贫理论出发,提炼出一种社会平等理论,不仅切中时弊,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也体现了要求人人平等的思想。[34]
人的发现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民主意识和人道情怀。在《十日谈》中,突破等级制度的人格平等作为全新的伦理内涵被大书特书。在第3天的“妮菲尔的故事”中,医生的女儿芝莱特爱上了伯爵的儿子贝特兰。伯爵死后,贝特兰承袭父荫前往巴黎伺候国王。国王得了重病,芝莱特趁机前往巴黎给国王治好了病,并请求国王将她嫁给贝特兰,贝特兰嫌芝莱特地位卑微,婚礼后他就离家出走。芝莱特邀请丈夫回家,并说明如果丈夫不愿意与自己一起,她可以离开,但是丈夫却说,他决不跟她一起回去,除非是“我这个戒指会套在她的手指上,她的胸怀里会抱着我亲生的儿子”。芝莱特只身来到丈夫所在地,了解到丈夫正在热烈追求一位破败名门的小姐,她与小姐母女沟通好,许给她们一笔酬劳,让她以小姐的身份与伯爵同房,并想法要到了伯爵的戒指。伯爵知道真相后,觉得她非常坚忍和智慧,同意与她百年好合。在这个故事中男女两个人物形象是截然对立的,丈夫特别重视门第观念,为女方设置了重重障碍,而妻子作为一个平民女子,则无视等级观念,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并使用智慧最终达成所愿。第4天的“妮菲尔的故事”中,商人的儿子纪洛拉摩与裁缝的女儿相爱。母亲为了断绝这对恋人之间的关系,派儿子去巴黎学习。两年后当公子回到家乡,发现心爱的人已经另嫁。公子潜入往日恋人的房间,见恋人已经不再接纳他,心灰意冷,在床边窒息而死。裁缝的女儿有感于往日恋人的忠贞,扑倒在死尸身上立时毙命。两个人用生命与封建等级制度做出最激烈的抗争。另外,第4天的“菲罗美娜的故事”,第4天的“潘斐洛的故事”,第5天的“爱米莉亚的故事”,讲诉的都是身份高贵的小姐无视等级藩篱与平民相爱的故事。第5天的“爱莉莎的故事”中,身份高贵的公子爱上了平民的女子,两个人为了爱情私奔,经历一番曲折后终于结为连理。以上这些都是男女双方突破等级制度的规范追求美好爱情的故事。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强调了人的自然本性,强调了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意志以及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复兴作为一场文化运动表现出应有的平民化立场。[35]
五 异质同构
以往的研究中,经常拿来与《十日谈》做比较的是《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拍案惊奇》、《金瓶梅》等作品,其实这些作品与《十日谈》内容的相似性并不是特别突出,而如下几个故事则是被以往的比较研究所忽略的,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作品。
首先,《十日谈》第4天的前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父子两个离群寡居,父亲不让儿子知道世俗之事,唯恐扰乱了他侍奉天主的心。儿子年满18岁了,老人看他平时侍奉天主十分勤谨,认为即使让他到那浮华世界里去走一遭,大致也不会迷失本性。在路上,他们遇到一些年轻女性,儿子问父亲这是什么?父亲说,不要看她们,她们都是祸水,她们叫“绿鹅”,儿子说“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这个故事与中国广为流传的《女人是老虎》的歌谣如出一辙。石顺义作词的歌曲:“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待,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小和尚暗思揣,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的老虎最呀最厉害,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傅呀!呀呀呀呀,坏坏坏,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来心里来。”这个流行歌曲,实际上是源于清代文学家袁枚的散文《子不语·沙弥思老虎》。“五台山某禅师,收一沙弥,年甫三岁。五台山最高,师徒在山顶修行,从不下山。后十余年,禅师同弟子下山。沙弥见牛马鸡犬,皆不识也。师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马也,可以骑。此鸡犬也,可以报晓、可以守门。’沙弥唯唯。少倾,一少年女子走过,沙弥惊问:‘此又是何物?’师虑其动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无存。’沙弥唯唯。晚间上山,师问:‘汝今日在山下所见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在这些故事中,作家想表达的一个共同思想就是,即使是一个未经历过“社会化”的“自然”男性,看到女性后仍然会心生爱慕,即使生命中唯一的“权威”警告他,女人是极其危险的,他仍然对异性无法抗拒。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反对压抑人性的传统观念。虽然中国与欧洲具有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和民族文化,但是这几个故事却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表达了相同的主题内涵。
5世纪初罗马的灭亡标志着历史进入了中世纪。15世纪中期,以人文主义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取代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成为西欧社会的主流文化预示着中世纪的结束。当中世纪的黑暗还在弥漫,文艺复兴的曙光已经初露。[36]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人文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端于14世纪创作《十日谈》的作家薄伽丘的家乡意大利,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达到鼎盛。《十日谈》正是创作于14世纪50年代文艺复兴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因此说这个故事表现出强烈的反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时代内涵。文艺复兴时期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刺激了人们对现世享乐的追求,勤奋劳动并不是为了灵魂的得救和来世的幸福,而是为了现世的利益和享乐。[37]人文主义思想将“人”从中世纪的封建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把那种在封建主义束缚下没有生命力的人,还原为充满活力、自由意志和理性的人。[38]
清初统治者为钳制人民思想,巩固统治,大力推行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封建伦理纲常,扼杀人的自然天性。康乾时期,政局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一度销声匿迹的启蒙思潮逐渐兴起。徐渭、李贽、公安派及汤显祖等一批富于反叛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有识之士,以性灵为武器向假道学与复古的形式主义文风宣战。其中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的观点最为突出。[39]袁枚充分肯定人欲:“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於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 ”“‘好货’,‘好色’,人之欲也;……使众人无情欲,则人类久绝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无情欲,则漠不相关,而亦不肯治天下。”[40]一个没有情欲的世界,是一个生命枯竭的世界,一个没有情欲的圣人,也就是一个对世事漠不关心的人。[41]袁枚把情欲上升到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认为“情欲”乃圣人治国安邦的动力。[42]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明末清初,广泛传播出现于清朝末年,其高潮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美国学者格里德所说:“除了启蒙运动外,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提供了一种‘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的灵感。”[43]因此说,《十日谈》应该对中国现代作家的部分创作也产生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十日谈》第9天的“劳丽达的故事”中,绅士金第·卡利生蒂爱上了有夫之妇卡塔琳娜。卡塔琳娜怀孕后患病昏迷,家人以为她已经死亡,将其下葬。金第得知非常心痛,想偷偷亲吻她的尸体以解夙愿,当他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卡塔琳娜的乳房时,感知到了她的微弱心跳,他将其抬回自己家中救活。这个有恋尸情节的短文与沈从文的 《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作品有相似之处。小说中,两个士兵和一个豆腐房里的老板同时爱上了商会会长15岁的女儿。女孩吞金自杀后,他们听说吞金死去的人,如果不过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便可以重新复活。豆腐房的老板偷偷将姑娘从坟中挖出来,背到一个山洞里。女尸赤裸着睡在山洞的石床上,地下身上各处撒满了蓝色野菊花。中外这两个原本具有变态意味的奸尸情节在作家的描绘中充满了神奇的诗意。这两个故事本质上都是,一个男性的利比多长期遭到压抑,外来的突发事件导致这种压抑将永远没有释放的机会,于是被压抑的利比多向一个畸形的方向释放的情欲故事。
《十日谈》第4天的“潘斐洛的故事”中,小姐梦到她的情人被一个妖怪拉到地底下去了。同一天,情人也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在一片树林里打猎,突然出现一只猎狗,把他的心叼走了。结果情人真的就死在小姐的怀中,小姐把一个玫瑰花冠戴在他头上,又把采摘来的玫瑰花瓣都撒在他身上。《十日谈》第9天的“劳丽达的故事”和第4天的“潘斐洛的故事”,使人联想到沈从文的作品《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和《医生》。《医生》讲述一个汉子将一具新丧的女尸从坟墓中挖出来放到山洞中,请医生帮她起死回生的故事。沈从文这两篇小说中都有在尸体周围撒满花瓣的浪漫情节。死亡是人类最为永恒的话题,中外作品都在死亡的惊悚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中世纪的死亡原本具有狰狞恐怖的面孔,而14世纪中叶创作的《十日谈》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浪漫主义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美化死亡的浪漫主义运动。沈从文本人更自称是“30年代最后一个浪漫派”。
《十日谈》第4天的“菲亚美达的故事”中,郡主成了寡妇后,勇敢地与一个侍从相爱。王爷知道了女儿的私情后,叫人用一只精美的金杯盛放侍从的心脏,送给郡主。郡主一面流泪,一面亲吻那颗心脏,并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毒汁倒在心脏上一饮而尽。第四天的“菲罗美娜的故事”中,小姐与仆人私通,小姐的兄长知道后秘密地处死了仆人,把他的尸体埋在郊外。仆人托梦给小姐,小姐来到埋葬尸体的地方,将他的头颅割下来,带回家中,亲吻了一千来遍后,将头颅埋葬在花盆里,上面种上罗勒,用眼泪、玫瑰水或者香橙水来灌溉。花长得枝叶茂盛,香气四溢。兄长们偷走花盆,逃亡异地,小姐则抑郁而死。这两个故事所渲染的惊悚、死亡、畸恋和浪漫的氛围,不禁使人联想到《莎乐美》,堪称唯美主义“恶之花”的先声。
独幕剧《莎乐美》是王尔德的代表作,写于1892年,首演于1894年。剧本取材于《圣经·新约全书》中施洗者约翰之死的故事。希律王害死兄长,夺走他的妻子希罗底。约翰谴责这桩罪行,被希律王囚禁在土井里。希罗底的女儿莎乐美走过土井,发现了约翰,为其美貌所动,深深地爱上了他。但约翰看不起莎乐美,认为她是乱伦者的女儿,拒绝了她的求爱。莎乐美要求把约翰的头割下来,用银盘献给她,国王照办。莎乐美接过银盘,亲吻了那曾经拒绝过她的嘴唇,希律王气急败坏,让卫兵处死了她。该剧描写一种无所顾忌地追求情爱的疯狂行为,以超乎常情的情节冲突展示主人公独特的心境和性格,从痛苦、恐怖、残暴与瞬间感觉中表现美,是一部典型的唯美主义作品。“恶”曾经是唯美主义者反叛社会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注释:
① 卢肃霜,《浅析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灵肉对立及其主要影响》,《海外英语》,2011年第1期,第209页。
②[23]彭佳、李园,《浅谈西欧中世纪的女性观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S1期,均引自第83页。
③詹姆斯·A.布伦德茨,《中世纪欧洲的法律、性和基督教社会》,芝加哥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④薄洁萍,《试论中世纪基督教婚姻思想中的矛盾性》,《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第74页。
⑤贺璋瑢,《西欧中世纪的女性观浅探》,《学术研究》,2004年第9期,第90页。
⑥朱兴存、丁红军,《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比较》,《中学政史地》(九年级),2007年第11期,第14页。
⑦⑨[12]邓婷,《文艺复兴运动与教会》,《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均引自第348页。
⑧谢荣贵,《人文主义的经典之作:〈十日谈>》,《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9期,第101页。
⑩〔美〕C·沃伦·霍莱斯特著,陶松寿翻译,《欧洲中世纪简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9页。
[11]刘锋,《论西欧中世纪修道院的衰落》,《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44页。
[13]刘建军,《基督教与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欧洲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148页。
[14][16]倪世光,《中世纪骑士行为变化与爱情观念》,《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分别引自第84页,第87页。
[15]F.S.舍伊斯,《法国的骑士制度》,E.波利斯迪兹编,《骑士制度》,纽约出版社1928年版,第66页。
[17][18]周景洪,《论中世纪典雅爱情的产生原因》,《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分别引自第73页,第74页。
[19]唐东楚,《现代社会中通奸行为的 “非罪化”》,《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第4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21]李明超、徐善伟,《中世纪西欧城市文学对女性爱情的表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88页。
[22]约瑟夫、f.吉丝,《一座中世纪城堡中的生活》,纽约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
[24]〔意〕但丁·阿利吉耶里,《多么优雅多么信诚》,1283年。
[25]李嗣茉,《浅析欧洲中世纪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双重性》,《文学评论》,2011年第9期,第16—17页。
[26]李桂芝,《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异端运动与妇女权利》,《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第59—60页。
[27][28][29][31]〔意〕薄伽丘著,方平、王科一翻译,《十日谈》,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分别引自第 3页,第265页,第266页,第267页。
[30]汤汇道、陈绪新、曹成付,《爱情认知兼论当代青年恋爱观》,《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75页。
[32][34]夏笑娟,《二元文化表征的解构——试论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分别引自第104页,102页。
[33][36]曹和修,《西欧中世纪意识形态人本蕴含探析》,《文史哲》,2011年第4期,均引自第192页。
[35][38]周海波,《两次伟大的 “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五四新文学》,《东方论坛》,2000年第1期,均引自第71页。
[37]庄锡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意义》,《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4期,第16页。
[39]聂广桥,《论袁枚“性灵说”之流变》,《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65页。
[40]袁枚,《清说》,《小仓山房文集》卷 22。
[41]李祥林,《随园门下红粉多——闲话袁枚及其妇女观》,《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第27页。
[42]晏萌芳、裴香玉,《论袁枚性灵说情感理论的自然主义偏向》,《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53页。
[43]邓宏艺、白青,《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聊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120页。
———对话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