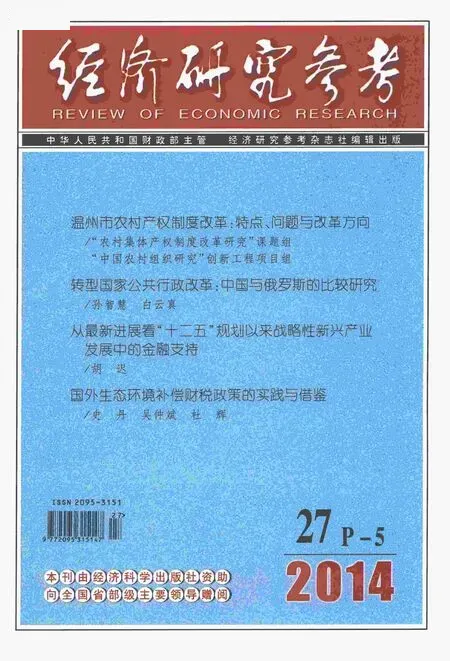国外生态环境补偿财税政策的实践与借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史 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 吴仲斌
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科学学院 杜 辉
一、国外生态环境补偿财税政策的实践
(一)森林生态补偿。
1.补偿原则。国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一般采取公共负担原则。绝大多数国家以政府作为一般补偿主体,通过征税或收费获得补偿资金,再经由财政支出实施补偿。如德国的生态税征收工作刚启动时,采取污染者负担原则,渐进提高标准,从燃油与电力工业设备设施中征税;而美国森林多数为私有林,强调政府与经营者责任分担,采用受益人承担原则;日本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立法,基于国家负担与受益人负担相结合原则,明确要求受益者承担部分补偿责任。
2.补偿主体。国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主体仍是政府。德国在国有林投入和管护部分由公共财政支付;在私有林生态效益补偿上,采取征收生态税方式,由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补偿;在生态横向转移支付上,体现一定市场补偿特征,但仍具有较强的政府干预色彩。日本无论是直接动用财政预算推行保安林制度,还是通过收取水源税实施森林生态补偿,政府都以补偿主体身份出现,且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严格按照4∶1的比例承担补偿责任。
3.补偿资金来源。政府公共财政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美国长期选择“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的政策手段来提高生态效益。德国主要来自征收生态税,首先针对污染者,然后及于社会公众;其次采取横向转移支付策略,或者通过州际财政平衡基金,由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横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金,或者由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承担补偿责任。日本将公共财政预算作为补偿资金重要来源,并征收水源税以获得部分资金,及从公益林划定中受益的地方公共团体等处征收有限补偿资金。
4.补偿对象。虽然国有林是生态效益供给主体,发挥生态主体调整功能,私有林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生态效益供给能力较差。但无论是否实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国有林也全部由政府投入并专门管护。设计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目的在于对私有林因为管护及限制经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补偿。从补偿对象结构看,多数国家补偿对象均为私有林。美国大部分森林在私有林业主手中,德国有约46%的私有林,日本保安林50%以上为民有林。
5.补偿标准。不同国家由于经济水平和补偿内容差异,其补偿标准也不同。美国不采取统一固定标准,依据环境指标或公共团体评定,采取成本分摊法,当前补偿标准大致为每公顷116美元;同时,美国森林生态补偿标准极具弹性,通过引入竞标机制来确定与当地自然经济条件相适的补偿标准。德国森林生态补偿采取机会成本法核算,补偿标准较高。日本在保安林制度中,采用了损失补偿、税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性贷款和项目支持五种补偿形式,各种形式补偿标准独立且多层次,其中对于保安林管护采取了高于一般造林1倍的财政补贴。
(二)流域生态补偿。
1.水资源利用补偿主要依靠政府转移支付。一是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包括国家财政投入和地方政府财政配套。在政府进行财政补贴、资金投入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补偿的“输血”和“造血”功能的不同,在补偿实施过程中按照“把握域情,因地制宜”的原则,合理有序地开展一系列补偿工作。建立促进跨行政区的流域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流域上游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恢复,并考虑流域内可能出现的突发性污染事件赔偿。建立中央和地方相统一、协调的基金是建立流域生态补偿体系的有力保证。二是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所谓“横向转移”,就是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计算及确定转移支付的数额标准,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最早将生态补偿应用于实践的是德国,自1976年来就以“补偿原则”方法作为评估环境影响的主要工具,目前已逐步建立“横向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制度,其最大特点是资金到位,核算公平。横向转移支付基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扣除划归各州的销售税的25%后,余下的75%按各州居民人数直接分配给各州;二是财政较富裕的州按照统一标准计算拨给穷州的补助金。德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易北河生态补偿政策。在易北河流域整治过程中,德国多方筹集资金和经费,目前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贷款、研究津贴、排污费、下游对上游经济补偿。美国生态补偿实践的典型代表是纽约市与上游Catskills流域之间的清洁供水交易。纽约市约90%的用水来自上游Catskills和特拉华河。1989年美国环保局要求,所有来自于地表水的城市供水都要建立水的过滤净化设施。此背景下,纽约市经过估算,若建立新的过滤净化设施,需要投资60亿~80亿美元,加上每年3亿~5亿美元的运行费用,总费用至少要63亿美元。而若对上游Catskills流域在10年内投入10亿~15亿美元以改善流域内的土地利用和生产方式,水质就可以达到要求。纽约市经过比较权衡后,决定通过投资购买上游Catskills流域的生态环境服务。在政府决策得以确定后,水务局通过协商确定流域上下游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的责任与补偿标准,通过对水用户征收附加税、发行纽约市公债及信托基金等方式筹集补偿资金,以补贴上游地区环境保护主体,激励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友好型生产方式,从而改善Catskills流域水质。
2.水质污染防治补偿主要依靠建立多元补偿基金。主要涉及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国外各级财政非常注重加强排污收费制度管理,将排污收费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综合管理,重点用于流域水环境的污染防治、生态补偿,坚持专款专用原则,提高征收资金使用效率。此外,积极探索征收水资源生态税,以满足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能力需要,保证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财力需要。例如,日本很早就认识到建立水源区利益补偿制度的必要性,依据《水源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建立水源地区对策基金。1998年,基多水资源保护基金在 Nature Conservancy,USAID和 Fundacion Antisana的支持下开始启动,它是厄瓜多尔通过建立信用基金补偿制度促进流域保护的首次尝试。除受益者直接支付费用外,基金也可通过国家、国际渠道得以补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为管理“减盐”信用交易,设立环境服务投资基金。该基金会从减排盐分的农场主那里购买“减盐”信用,同时向买主出售该“减盐”信用。该基金会充当减盐信用交易所作用。减盐信用出售采用拍卖形式。在流域生态补偿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还包括哥斯达黎加的生态补偿实践。其国内的Energia Global(简称EG)是一家位于Sarapiqui流域、为四万多人提供电力服务的私营水电公司,按照每公顷土地18美元标准向国家林业基金提交资金,国家政府基金则在此基础上按每公顷土地另外添加30美元,以现金形式支付给上游私有土地主,同时要求其必须同意将土地用于造林、从事可持续林业生产或保护有林地,而对于那些刚刚采伐过林地或计划用人工林来取代天然林的土地主将没有资格获得补助。
(三)资源消耗和污染生态补偿。
1.资源消耗税。该类税为各国普遍开征的税种,可通过限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速度来影响环境,如自然资源开发税、森林资源开发税、矿产资源开发税、地下水资源税等。德国为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自1999年起便实施生态税改革,主要包括引入电税;在原矿物油税适用税率基础上加征生态税率,对每升汽油、柴油增征生态税3.07欧分,分别由原来的每升30.70欧分、50.11欧分提高为每升34.77欧分、53.18欧分;贯彻税收中性原则,削减企业0.8%的年金缴纳比例。波兰从1970年开始设立生态税与资源税,当时是为了激励污染者调整其行为。但由于开征时税率较低,特别是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消费对价格信号的反应都很不敏感,生态税并不能通过价格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更多的是发挥为生态投资和污染削减项目筹集资金的作用。其后,在1989年、1990年和1992年,波兰又对生态税进行改革,税率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征收系统也得以加强。
2.污染生态补偿。一是对排放工业污染物征收税。该类税是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三废”实行课税,如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等。目前,美国主要有对损害臭氧层化学品的征税、汽油税、与汽车使用相关的税收和费用、开采税、固体废弃物处理税、二氧化硫税、生态收入税等。美国的生态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直接税收减免、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等税式支出措施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对研究污染控制新技术和生产污染替代品予以减免所得税。1986年,国会又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所得给予减免所得税优惠。从1991年起,23个州对循环利用投资给予税收抵免扣除,对购买循环利用设备免征销售税。目前,波兰对几百种污染物征收污染税,主要针对二氧化硫、NOx和含盐的采煤用水。税率根据污染物有害性大小制定,并按一定比例适时调增,同时参照已有污染物税率水平确定新污染物税率。二是对造成其他公害征收的税,如噪音税、拥挤税。荷兰特别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种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铀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超额粪便税、狗税等。瑞典的生态税收包括对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税,对能源征收的增值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电力税以及对化肥、电池等的征税等,已经成为税收体系重要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保护了该国环境。法国生态税收入实行专款专用,并由法国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掌握。每年各项环保支出都要编制专门预算,并由审计院负责监督预算执行与资金使用情况,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税、氮氧化物税、水污染税、废物垃圾税、轮胎税、润滑油税、汽车税、地方设备税、伐木税以及犬税等。
二、国外生态环境补偿财税政策的经验借鉴
1.完善森林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支持体系。我国的森林质量较差,平均单位面积蓄积只有85.88立方米/公顷,仅为德国320立方米/公顷的26.84%;德国森林平均生长量达10立方米/公顷,我国乔木林平均生长量也只有3.85平方米/公顷,而且人工纯林较多,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差。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完善的林业公共财政支持保护体系,从森林经营、森林保护到森林利用全过程给予稳定、有效的资金支持,对我国林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为实现到2020年再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13亿立方米蓄积的林业奋斗目标,我国应当借鉴先进国家经验,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林业公共财政支持保护体系,包括造林、抚育、保护、管理投入补贴制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森林保险、林业金融、财税支持制度,对林权保护管理体系建设、林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民林业合作组织、科技服务等林业一般公共服务支持制度等,并建立健全完整、周密、科学的操作和管理办法。
2.多元化筹措水流域生态补偿基金。借鉴国外经验,充分利用各种财税手段来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多元筹资模式。具体而言,一是征收水资源开发使用费。对于直接开发、占用、利用和使用水资源的单位及个人收缴一定标准费用,并拿出一定比例资金作为生态补偿资金。该部分费用直接来源于水资源使用价值,而不以是否有人类劳动的凝结或管理投入为转移。其费用多少,通常根据开发使用的水量、水质以及紧缺程度、所获利益大小来确定。征收的水资源开发使用费主要用于水源区生态服务功能的保护和管理,促进我国生态补偿工作开展。二是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应逐步扩大排污收费范围,严格执行新的排污收费制度,将各种污染源纳入收费范围。进一步提高排污收费标准,以激励企业加大对污染控制投资,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同时,各级财政应加强排污收费制度管理,将排污收费资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综合管理,重点用于流域水环境的污染防治及生态补偿,坚持专款专用原则,提高征收资金使用效率。此外,在征收排污费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征收水资源生态税,获取流域生态补偿基金。三是建立促进跨行政区流域水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流域上游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恢复,并考虑流域内可能出现的突发性污染事件赔偿。四是积极争取国际社会补偿资金,多方面加强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绿色团体、研究机构和大型企业的交流与合作。
3.优化生态税收体系以治理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中国现行税制在某些税种中直接或间接地含有环保性质的税收优惠,但较之其他国家,以直接优惠为主,优惠形式单一,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有些优惠措施在扶持或保护一些产业或部门利益的同时,对生态环境起了破坏作用。据此,有必要优化现行生态税收体系。生态税改革重点在于开征污染排放税种和完善现行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和所得税等税种,使税收制度更加具有生态功能。污染排放税是最能体现生态税收本质的税种,其计税依据是污染量或造成污染的产品数量,其课税对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立足国情,开征初期课税范围不宜过宽,在税基选择上,可采取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和数量双重标准。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采取差别税率。降低环保产品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增值税,对节能设备、环保设施等环保项目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额,拉大各档税额间差额,调整计税依据为开采量。建议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等有关税种合并到资源税中,统一管理,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合并内外企业所得税,统一内外资企业在生态环保方面优惠政策,对企业从事环保产业的所得采取低税率征收所得税。
4.理顺各级政府生态补偿关系。根据国际经验,国外发达国家在生态补偿中,有非常清晰的各级政府职责范围,做到各司其责,形成合力。然而,当前财税体制与行政体制下,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生态补偿的规模、范围、形式上界定相对模糊。从可行性角度出发,与其寄望于先通过厘清存有争议的政府间边界来强制性推动生态补偿中财权与事权的重新配置,再后续安排对应事责;不如先着眼于实现各级政府权责合拍,消除生态补偿中事责“缺口”,保障执行力,再渐进摸索各种权力在政府间最优配置。更进一步讲,财权与事权在理论上如何划分可适当搁置,关键是实践中每份“权”要对应每份“责”,并有每份“财力”来支撑,否则便是纸面空谈,无助于现实。简言之,在每级政府内都要实现权责力三者间均衡,避免“越位”、“缺位”、“失位”、“空位”情况。根据国际经验,中央政府财政投入是生态补偿主要力量。我国中央政府掌握了多数财权与事权,理应承担相应事责。更重要的是,针对基层政府“权小责大,力有不逮”的局面,要积极增加其财力,减少其事责,真正建立财政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1]樊万选、方珺:《国外流域生态补偿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启示与借鉴》,载于《创新科技》2013年第10期。
[2]朱桂香:《国外流域生态补偿对我国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启示与借鉴》,载于《中州学刊》2008年第5期。
[3]王世进、焦艳:《国外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及其借鉴》,载于《生态经济》2011年第1期。
[4]陈曦:《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生态税收体系》,载于《今日南国》2009年第1期。
[5]常瑛、李绍平:《国外生态税收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载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6]陈岩:《国外的生态税收实践与我国生态税收政策选择》,载于《经济问题》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