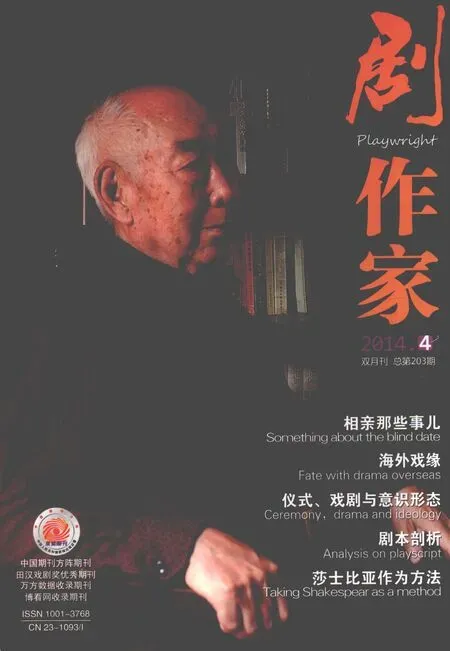二人转是一种民俗艺术
杨 朴
二人转是一种民俗艺术
杨 朴
【摘要】有学者认为二人转是从说唱到戏曲的过渡形式。然而,为什么经过了三百多年,还没有完成过渡?因为二人转是一种不同于说唱和戏曲的艺术。二人转是从古代仪式那里演变而来的,是仪式的原型框架和意象。二人转造型和舞蹈方式来源于东北大秧歌,东北大秧歌又来源于东北民间祭祀舞,而东北民间祭祀舞又是植根于东北古代圣婚仪式的。二人转是古代东北圣婚仪式的形式化抽象——去掉了性交媾舞而留下“二人转”,这样,就把民俗的圣婚仪式内容包容在了自身形式之中,而观众在观看这原始意象的抽象化形式时也必然无意识地体验了这种民俗心理。
【关键词】二人转 东北民俗 东北大秧歌 民间祭祀 仪式原型
属性难辨的秘密
二人转究竟是一种什么艺术品种呢?是曲艺?是戏曲?是舞蹈?还是戏剧?根据它的说唱特点,有人将其归于曲艺类;根据它丑旦行当,有人将其归于戏曲类;根据它的秧歌性,有人将其归于舞蹈类;根据它的故事性,有人将其归于戏剧类。在这场讨论中王肯先生的《论“我”》[1]、吕树坤先生的《从歌舞、说唱向戏曲演变的活化石》[2]是两篇最重要的文章,他们的观点为我们重新思考二人转艺术种类属性,提供了极有学术价值的见解和思路。
王肯先生认为:“咱俩”是从民间说唱、秧歌向戏剧发展的独特的产物——民间说唱,秧歌与一旦一丑行当因素有机结合的两个彩扮的演员;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我认为它是从说唱到戏曲的过渡形式,但过渡多年,仍独立成章,并形成自己的一套词、曲、表演特点。叫走唱类,有些道理,因确实有说唱特点,归民间小戏,亦无不可,但要说明它是独具一格的两小戏,变成戏仍可二人多角,仍可叙述兼代言。”[3]
王肯在精辟地揭示出二人转“过渡”形态的同时,又深刻地指出:“二人转这种独特的形态,从戏曲的发生发展来看,可说是从民间歌舞,民间说唱向戏曲过渡的‘活化石’,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过渡形式,过渡了一百五六十年,依然是活的,而且活得有声有色。”[4]
吕树坤先生从广义二人转的“单出头”基本上都做人物扮的特点,把“单出头”视做“独角戏”,“独角戏虽仍属戏剧的雏形,但它毕竟是戏剧了”,“拉场戏”的由演员扮角色表演故事情节的特点就比单出头“更有资格进入戏剧的行列”;而吕先生又认为单出头、拉场戏和狭义的二人转是“构成二人转这一艺术形式的密不可分的有机的整体”,因而,在吕先生看来,二人转与单出头和拉场戏一样应该是有戏剧的属性的。但吕先生并未据此就片面地认为二人转就是戏剧,他同时又强调了二人转的其它特性:“在二人转这一艺术形式中,演员虽不做人物扮,但已有小丑与小旦这两个行当,特别是在叙事与代言这两种表现手法比重上,后者已明显地超过了前者,这些代表着质的因素的特点,说明了二人转已不完全属于曲艺,在很大部分上属于戏曲了。然而,它终究还不是戏曲,或者说还不完全是戏曲。它的行当的划分和代言式的表演,与戏曲还存在很大的差别”;二人转的“跳出跳入”还没有完全摆脱曲艺的“一人多角”的这一本质特征。至于当演员跳出人物时的叙述,与情节和人物没有必然联系的舞蹈等,更属于歌舞和说唱这一方面的东西了。因而,吕先生认为:二人转是从歌舞和说唱向戏曲演变的“活化石”。但吕先生又认为这种演变的“过渡类型”是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它的寿命不会比曲艺或戏曲的寿命短,“甚至还会比某些曲种或剧种的寿命长”。
王肯先生和吕树坤先生对二人转的属性的见解之所以是极有价值的,我以为:一、在以往的以主流戏剧形态为话语霸权的语境中,他们并没有以主流戏剧形态为尺度去框正、贬抑和鄙薄边缘的来自民间的土野艺术;二、他们的研究是辩证的综合的动态的。正是这种研究弃绝了片面的绝对化之嫌,从而为人们揭示了二人转这种艺术的独特性——一种不同于曲艺不同于戏曲,不同于戏剧,不同于舞蹈,但又综合曲艺,戏曲,舞蹈和戏剧因素的特点的艺术。正是他们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了东北二人转在各类艺术中的独特性和独特价值,也正是他们的研究为后人拓开了研究的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观点、思路,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但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对研究对象的不断探索不断发现、不断理解的过程。学术研究没有绝对、终极、惟一的观点。二人转研究也一样,我们说,王肯等人对二人转譬如说二人转属性问题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并不是说,这一研究已经完结已经有了最科学、最缜密、最全面的认识,已经取得了不可更易的结论。事实上,王肯先生、吕树坤先生对二人转属性的研究还留有一些思考的余地,我们完全可以顺着他们的思路继续探索这一问题。王肯先生曾经思考:二人转这种“过渡形式”,为什么“过渡了一百五六十年,依然是活的,而且活得有声有色”?
吕树坤先生曾经探讨: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过渡形式”逐渐衰微下去乃至消亡了,“为什么惟独二人转这一艺术形式在拉场戏出现之后,特别是在吉剧、龙江戏创建之后,仍然能孑然独立,并且呈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对此,王肯先生的结论是:“在从民间说唱,民间歌舞向戏曲演变的过程中,又保留与发扬民间说唱与民间歌舞的表现方法与特长,从不变掉二人转——双玩艺儿的独特的形态”,“从不变掉二人转民间艺术的特色”[5]。
吕树坤先生的结论是:二人转深受群众喜爱的特点,“是不是与二人转是一种过渡类型的艺术形式有关?是不是因为二人转兼备了歌舞说唱和戏曲之所长才更深受到群众的喜爱?在有限的时间里,可以得到秧歌,民歌、杂技,曲艺和戏曲多种艺术享受”[6]。我们能不能有另外的思考,另外的探索呢?
远古仪式的“活化石”
王肯先生和吕树坤先生都相当充分地注意到了二人转受到群众的特别喜爱,就是因为二人转从不变掉二人转——双玩艺的独特形态和大秧歌等因素。我以为,这是触到了问题的根本。双玩艺是从古代仪式哪里演变而来的,是仪式的原型性意象。
所谓大秧歌实际上就是古代仪式舞的变形。二人转无论增加什么和减少什么,都没有变掉双玩艺和大秧歌,其实就是没有变掉原型;观众喜欢双玩艺和大秧歌,其实喜欢的就是原型;没有说唱向戏曲实现所谓的过渡,所起作用的是双玩艺和大秧歌其实也是原型。
沿着这个思路探索,我以为,所谓“过渡形式”是不确切的:因为二人转不是从说唱类起源的,而是从“二人转”——大秧歌起源的,保留了二人转和大秧歌其实是保留了二人转的原始形态,而其它因素则是附属的因素,后加的因素,是不重要的特征因素,不起最大审美感受作用的因素。因而二人转其实是一种原始戏剧、民俗戏剧,没有被“戏剧化”的戏剧,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二人转的形态与原始巫术形态做一比较就会有明朗化的认识。
二人转是一种民俗戏剧。它起源于民俗,是民俗的一种转换变形。我这里所说二人转的民俗性不是指那种二人转剧本中譬如《蓝桥》所表现的诸如结婚的种种风俗,而是指二人转艺术形式本身,它犹如一朵奇葩,就生长在民俗的文化土壤中,就是民俗原型祖先繁殖的后代,就是由原始意象规定的原始戏剧形式。它来自远古民俗的仪式和舞蹈。王肯等二人转研究专家所几乎一致强调的二人转形式及其秧歌舞蹈是二人转的最根本特征和最重要的审美因素,其实这种二人的构型和舞蹈形式是植根于史前的民俗信仰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二人转放在东北民俗文化的长河中去考察,就会发现,二人转的形成史其实就是一部东北民俗的演化史。一个二人转意象牵系出一部丰富的东北民俗史。二人转构型和舞蹈方式是来源于东北大秧歌,这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东北大秧歌又是来源于于东北民间祭祀舞的,而东北民间祭祀舞又是植根于牛河梁女神祭祀的圣婚仪式舞的。圣婚仪式是通过牛河梁女神遗址的考古发现及与世界各民族的女神祭祀仪式的比较能够基本得到推测的[7]。如果我们这个研究思路和基本看法大致不错的话,就会说明:二人转确实是由原始民俗转化而来的。原始民俗即牛河梁女神的“圣婚仪式”是东北先民最初的“民俗精神”、“民俗情感”、“民俗心理”,而这最初的精神、情感、心理就是一种心理结构、一种心理愿望:以愿望的理想形式如男女二祭司模仿男女二神的圣婚仪式去控制影响生命创造,大自然的循环,以补偿生命的缺憾。如果参照其它民俗的远古圣婚仪式,牛河梁女神的圣婚仪式应该是有一个表现这种圣婚仪式的原始戏剧形式的。这种原始戏剧既有场面和观众:男女祭司表现神的圣婚的场面和参加仪式的“观众”;又有角色装扮和情节故事:男女祭司对神的装扮和以一个基本情节表示神的恋爱与结合,同时,这个原始戏剧的进一步发展,是在舞的同时又增加了歌唱的。因而就形成了男女祭司载歌载舞又模拟人物又表演情节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后世的曲艺和说唱的特点,戏曲行当的因素,舞蹈的形体表现符号,戏剧的基本情节特性是都兼容在一身之中的。我猜想,东北的这种表现民俗心理的原始戏剧方式肯定是存在的,并且是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是由于东北文化的早出和东北文化的晚被文字记载,我们难窥其貌了。
可能由于文化相对落后的原因,东北的这种原始戏剧并没有获得大的发展。但文化落后又使原始戏剧有某种程度的保留,比如萨满跳神。萨满跳神虽然也有“圣婚仪式”的戏剧性演示和转换形式,但它毕竟离原始意象较远而不能真切地表现强烈的原始心理欲望了。如前所述圣婚仪式是东北先民原初的生命欲望和心理结构。这种生命欲望和心理结构构成一种集体无意识,通过生理心理遗传被保留在后代心理结构之中,也成为他们强烈的生命欲望,时时要求表现。正是在这种心理驱动下,他们先是选择了大秧歌,继而又在大秧歌丑旦构型基础上表现故事,于是,他们即从大秧歌的“一副架”形式上构成了二人转构型,又从牛河梁圣婚仪式原型扩展的神话结构那里获得原型故事;既从大秧歌上下装那里获得行当角色,又从萨满跳神那里吸取跳进跳出的模拟化表演;既从民歌和其它形式中获得歌唱,又从大秧歌中获得舞形。二人转就这样形成了。二人转形成的是一种原始戏剧方式,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种原始戏剧方式。之所以要恢复原始方式,就是因为要表现原始心理愿望——恢复原始意象。史前戏剧方式是由史前愿望决定的。至此,我们终于理解了王肯先生和吕树坤先生所说的,与其它剧种比较,它虽然像是一个“过渡形式”,但又始终又没有完成过渡,二人转变来变去但始终变不掉“二人转”和秧歌舞的内含的隐秘的意义,二人转既以恢复原始意象的方式恢复原始心理,又以维护二人转原始戏剧特性的形式维持原始意象的表现。
当然在二人转这种戏剧方式中,已经不能明确看到原始仪式的民俗比如圣婚仪式的具体内容。它本身的确已经不是纯粹的民俗形式和民俗行为,然而,由于二人转的形式是从民俗心理生成的,是从民俗土壤中繁殖成的大树,而二人转形式又是原始圣婚仪式原始意象的形式化抽象——去掉了性交媾舞而留下“二人转”即性互舞,这样,就把民俗的圣婚仪式内容包容在了形式之中,成为形式的必然意味,而观众在观看这原始意象的抽象化形式时也必然无意识地体验了这种民俗心理。李泽厚曾充分地论述艺术的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正因为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意义)已积淀(溶化)在其中,于是,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也正是由于对它的感受有特定的观念、想象的积淀(溶化),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成为特定的‘审美感情'。原始巫术礼仪中的社会情感是强烈炽热而含混多义的,它包含大量的观念,想象,却又不是用理智、逻辑、概念所能诠释清楚,当它演化和积淀为感官感受时,便自然变成了一种不可用概念言说和穷尽表达的和深层情绪反应。某些心理学家(如Jung)企图用人类集体下意识‘原型'来神秘地解说。实际上,它并不神秘,它正是这种积淀、溶化在形式、感受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感情。”[8]
二人转是一种积淀着仪式原型的独特的艺术。因而,它才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歌德曾经深刻论述说:“艺术早在其成为美之前,就已经是构形的了,然而在那时候就已经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往往比美的艺术本身更真实、更伟大些。原因是,人有一种构形的本性。”“而这种独特的艺术正是唯一的真正艺术。当它出于内在的、单一的、个别的、独立的情感,对一切异于它的东西全然不管、甚至不知,而向周围的事物起作用时,那么这种艺术不管是粗鄙的蛮性的产物,抑是文明的感性的产物,它都是完整的、活的。”[9]牛河梁女神圣婚仪式的民俗内容积淀在二人转形式中,而东北农民在欣赏二人转形式时也就这样无意识地体验着圣婚仪式的民俗性内容。由于那种圣婚仪式是民众强烈的心理原型,一种不可磨灭的种族记忆,一种在种族遗传中形成的“先在形式”原始意象,因而,一当积淀着这种内容的形式、意象出现时,心理原型,种族记忆,原始意象就即刻被唤醒被激活了。
“原始”戏剧
二人转文化的谜底终于破译了。二人转之所以生成并常演不衰,原来是民俗心理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几乎不露任何痕迹,但却是极其重要的。露丝·本尼迪克特曾敏锐地指出:“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每个出生于他那个群体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10]如果说荣格的原型理论,使我们看清了圣婚仪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遗传,那么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的理论又使我们看清了文化习俗对种族个体的重大影响和塑造。二人转的本质性内容是文化习俗的,因而,二人转的影响其实就是文化习俗的“文化模式”的影响。
二人转这种艺术既然是一种“原始”艺术,它就必然带有原始艺术“混沌性”的特点。原始戏剧即原始民俗的表现方式在现代艺术眼光看来是一种混沌性的表现方式,其中既有舞又有歌,古时歌舞是不分的;既有角色装扮又有故事表演,装扮与表演又是合二而一的。这些都源于他们的民俗心理动机即他们生命愿望的表现。原始先民没有现代艺术家的明确界线和清规戒律,只要能够表现他们生命感受的东西他们都要创作和利用。东北最早的民俗牛河梁女神的“圣婚仪式”即是东北艺术的内容原型,几乎所有的东北民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戏剧等都是这一原型的转换变型,同时,牛河梁女神圣婚仪式又是东北艺术的形式的原型,几乎所有的东北舞、东北民间戏剧等都是这一混沌原始艺术的分化和发展。
东北的原始民俗艺术虽然是混沌的,但戏剧性表现毕竟是它的最主要特征。二人转在恢复原始艺术混沌性的同时,也同样保留了原始戏剧表现的突出特点。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二人转可以称之是一种“戏剧”。只是二人转是一种原始的,古朴的,未被现代戏剧观分化的戏剧。
对二人转属性的理解,其根据主要不应是戏剧观念或其它戏剧样式,而只能根据二人转自身的特性理解二人转。根据其它戏剧观念或戏剧戏曲样式理解二人转,就可能发生教条化的错误。这种错误的结果我们可以在一个假设的艺术试验中得到观察:当我们强调二人转的说唱性曲艺属性时,如果丢掉了二人转的二人构型和二人舞时,二人转还是二人转吗?当我们强调二人转丑旦行当的戏曲属性时,如果丢掉了“三场舞”、上下场舞,二人转还会是二人转吗?当我们强调二人转的舞蹈属性,如果丢掉了二人转的具有二人转形式结构的原型故事,二人转还会是二人转吗?当我们强调了二人转文学剧本的戏剧性的角色化的表演,如果丢掉了歌与舞等,二人转还会是二人转吗?
二人转是一种“原始”的戏剧,因而我们也就只能用“原始”戏剧的标准来衡量二人转。不能用统一的,现代的戏剧标准来衡量二人转。二人转的潜在内容是表现民俗心理的,因而我们不能把二人转这种原始性戏剧同现代戏曲或曲艺等相衡量。谁这样衡量谁也就从根本上误解了二人转。我们不能用京剧、黄梅戏、晋剧等来衡量二人转。这些艺术虽也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文化来源,但它或者是从原始戏剧中分化出来,或者是经过了几代人的艺术加工,成为了一种现代的戏剧或戏曲形式。相对来说,二人转却仍然是“原始”的,它虽然具有其它戏曲、戏剧等样式的属性因素,但是它不是从其它样式学来的,而是从东北远古仪式生长出来的。它的混沌性和“原始性”充分说明:在中国,其它任何戏曲、戏剧都没有二人转这样强烈的民俗背景,这样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这样来自遥远古代的仪式原型,这样保持了巫术仪式戏剧的原始性、质朴性和民俗性。
注释:
[1]王肯:《士野的美学》,时代文艺出版社,l989年版,第21页。
[2]吕树坤:《关东剧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l988年版,第l-7页。
[3]王兆一:《关于“谈戏”的通讯》,见吉林省地方戏曲研究室编印《二人转史料》第3集。
[4]王肯:《独特的“我·你·他”》《土野的美学》,时代文艺出版社,l989年版,第ll页。
[5]王肯:《少见的流变与形态》《土野的美学》,时代文艺出版社,l989年版,第5页。
[6]吕树坤:《从歌舞、说唱向戏曲演变的活化石》
[7]参见杨朴《二人转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27页。
[8]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l982年版,第27页;并参见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25页。
[9][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79页。
[10][美]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