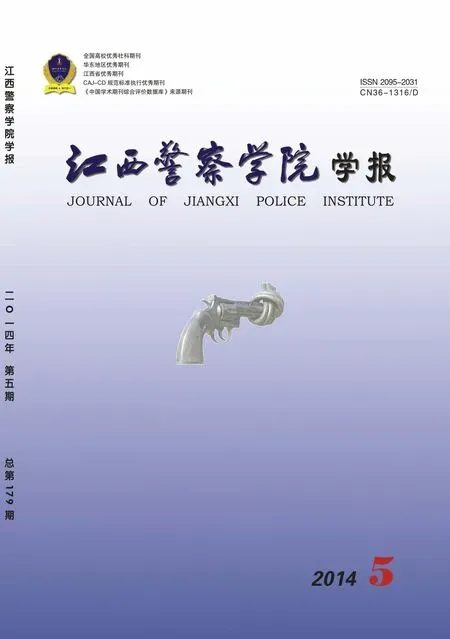诉讼诈骗罪司法适用
李 红 ,马荣春
(1.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上海 200120 ;2.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127)
由于诉讼诈骗罪的独立犯罪化有其必要性与可行性,故本文的讨论不仅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也有着可能的或着眼于未来的现实意义。
一、诉讼诈骗的罪与非罪
诉讼诈骗的罪与非罪问题, 是诉讼诈骗罪的司法实践必然包含和首先要包含的内容。 诉讼诈骗的罪与非罪的讨论大致包括诉讼诈骗罪与相关诉讼现象的罪与非罪的区分和因诉讼诈骗自身情节而引起的罪与非罪的区分。
(一)诉讼诈骗罪与相关诉讼现象的区分
有人在讨论诉讼诈骗时指出, 应当将诉讼诈骗这种行为与“滥用诉权”以及诉讼中运用“诉讼技巧”的行为作出区分或辨别。 诉讼诈骗是以虚假事实为基础来谋取一种财产上的利益或其他利益,而“滥用诉权”则是基于真实的事实而过分行使了合法权利,即“滥用诉权”是在事实真实存在的前提下,当事人小题大做或者过于偏激而过分地行使了诉权。 “滥用诉权”的行为人没有主观恶意,没有虚构证据或恶意串通等,只是不合适地行使了诉权,从而给相对人带来不便和损失。 至于“诉讼技巧”,则可能是包括律师在内者为了获取对方当事人不愿提供的证据而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 同样不存在当事人的主观恶性或虚构证据等问题。 “滥用诉权”和“诉讼技巧”与以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甚至恶意串通来“欺骗”法院的诉讼诈骗有着本质的不同。[1]确实,“滥用诉权”和“诉讼技巧”与诉讼诈骗有着本质区别,且此本质区别意味着罪与非罪的区别。 但说“滥用诉权”没有主观恶意,则是不客观的,因为在“滥用诉权”这种诉讼现象中,当事人聘请通常是律师的代理人, 字斟句酌地填写诉状且一分不少地缴纳诉讼费用, 其煞有其事的做派足以引起法院以立案和安排开庭为体现的认真对待,则其随后撤诉又起诉,这不是在“欺骗”法院吗?其起诉又撤诉, 撤诉又起诉这不是有意让对方当事人去忍受一种“此起彼伏般”的心理煎熬,从而正常生活难得安宁吗? 于是,我们只能说“滥用诉权”还没有那种具有“刑罚可罚性”的主观恶意。
总之,“滥用诉权”和“诉讼技巧”与诉讼诈骗罪之间存在着罪与非罪的天壤之别。
(二)诉讼诈骗因情节轻重引起的罪与非罪的区分
有人指出,诉讼诈骗必须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从而制造彻头彻尾的骗局,才能构成犯罪,而如果只是在事实上略有出入,则不能认定为犯罪。[2]而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有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法院审理案件,或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恶劣手段阻止证人作伪证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等严重情节的情形。[3]尽管论者对诉讼诈骗罪的“情节严重”或许概括得有失全面,但情节轻重引起的诉讼诈骗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 当诉讼诈骗罪须以“情节严重”作为构罪要件,则意味着在诉讼诈骗罪的司法实践中, 情节轻重便构成了诉讼诈骗行为罪与非罪区分所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内容。 而按照刑法第13 条的“但书”规定,本来可以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可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从事物的逻辑上,任何本来可以构成犯罪的行为都存在着罪与非罪的区分, 即便像故意杀人罪这样的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如出于解除濒临死亡边缘的患者的极度病痛而实施“安乐死”的故意杀人行为,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规模大小的问题,而具体到违法行为,则都存在着情节轻重和社会危害性或法益侵害性大小的问题。 因此,诉讼诈骗行为也理当存在着罪与非罪的区分,即便这种违法行为侵害着复杂客体或具有双重的社会危害性或法益侵害的双重性, 而其罪与非罪的区分的根由即在轻重情节及其所说明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上。 至于一起诉讼诈骗案件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则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综合权衡,如诉讼诈骗所欲达到的目的本身的大小及其正当性或卑劣程度大小、诈骗手段本身的“技术含量”高低、诉讼诈骗给“对方当事人”①在诉讼诈骗罪中,本来意义上的对方当事人是不存在的,故采用引号形式予以特别强调或实际另有所指。所带来的“苦处”(包括财产损失)的大小、诉讼诈骗所引起的司法资源的耗费的大小、诉讼诈骗对司法公正形象的败坏程度等等。当然,诉讼诈骗罪的情节把握问题仍属司法者“自由裁量”范围的事项,故随着诉讼诈骗罪司法经验的不断积累,司法者对诉讼诈骗行为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的把握,也将越来越恰当和稳当。 至于有人指出, 对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的虚假诉讼行为,不做犯罪处理,而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如由人民法院通过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改变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 或将已执行的原被告人的财产执行回转, 并可依 《民事诉讼法》规定对行为人进行民事制裁。[4]显然,按照论者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把握,则诉讼诈骗罪便很难成立了。
二、诉讼诈骗罪的犯罪形态
(一)诉讼诈骗罪的共犯形态
诉讼诈骗罪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共犯形态问题。而本文要讨论的诉讼诈骗罪的共犯形态问题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诉讼诈骗罪作为共同犯罪本身的分类,二是诉讼诈骗罪的共犯角色。
就诉讼诈骗罪作为共同犯罪本身的分类问题而言,在任意的共犯与必要的共犯之间,诉讼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属于任意的共犯, 即其本为单人就可直接实行的犯罪。 而在属于任意的共犯的前提之下,诉讼诈骗罪的共同犯罪又完全可以因案而异地形成简单的诉讼诈骗共同犯罪, 即行为人同为实行犯的诉讼诈骗共同犯罪, 如夫妻俩共同直接实行诉讼诈骗行为,或形成复杂的诉讼诈骗共同犯罪,即行为人存在分工的诉讼诈骗共同犯罪, 或形成一般的诉讼诈骗共同犯罪, 即行为人之间不存在组织形式的诉讼诈骗共同犯罪,或形成特别的诉讼诈骗共同犯罪,即行为人之间存在一定组织形式的诉讼诈骗共同犯罪。
显然, 前述对诉讼诈骗罪作为共同犯罪本身的分类概括,已经牵扯到了诉讼诈骗的共犯角色问题。那么, 对诉讼诈骗共犯角色的讨论便是对诉讼诈骗罪作为共同犯罪本身的分类问题的继续。 就诉讼诈骗罪的共犯角色问题而言, 由于共同犯罪的行为分工包括实行行为、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5]故诉讼诈骗罪的共同犯罪中便相应地存在着诉讼诈骗罪的实行犯、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何谓诉讼诈骗罪的实行犯? 在刑法理论中,实行犯即正犯, 即以自己的身体动静直接实施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者②正犯有扩张的正犯概念和限制的正犯概念之分,限制的正犯概念对应着实行犯。。 那么,在我们看来,诉讼诈骗罪的实行犯, 即直接实施诉讼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者。 由于诉讼诈骗罪是复行为犯,故这里所说的诉讼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即开始启动虚假诉讼程序的行为,或干脆曰虚假立案行为。
何谓诉讼诈骗罪的组织犯? 在刑法理论中,这里的“组织”首先应作广义的把握,即包括狭义的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5]那么,诉讼诈骗罪的组织犯,便是实施诉讼诈骗的组织、领导、策划或指挥行为者。 或许有人会觉得对诉讼诈骗罪区分出组织犯属“小题大做”,但当诉讼诈骗罪是将法院作为蒙蔽对象,则其往往需要更高明的骗术,从而往往需要一番更加“周密”的部署,故将诉讼诈骗罪的共犯区分出组织犯也就“不足为奇”了。
何谓诉讼诈骗罪的教唆犯? 在刑法理论中,通俗地讲,教唆犯是指试图引起他人犯意者。 而正规一点讲, 故意唆使并引起他人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是教唆犯。[6]那么,在我们看来,诉讼诈骗罪的教唆犯, 即唆使并试图引起他人实施诉讼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行为者。 需要强调的是, 这里在“引起”前面加“试图”一词很有必要,因为教唆未遂也照样成立教唆犯。
何谓诉讼诈骗罪的帮助犯? 在刑法理论中,帮助行为是指故意提供信息、 工具或者排除障碍以协助他人故意实施犯罪的行为,[5]即帮助行为是使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更为容易的行为。[6]384那么,在我们看来,诉讼诈骗罪的帮助犯, 即使诉讼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更为容易”的行为者。 显然,这里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更为容易”的行为应在组织行为之外予以把握,如在实行犯与立案人员之间进行介绍或引见等,因为组织行为在广义上也可理解为使得诉讼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更加容易”的行为。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对共犯角色采用了以作用为主兼顾分工的分类标准并分类出主犯、 从犯和胁从犯, 故诉讼诈骗罪的共同犯罪中便相应地存在着诉讼诈骗罪的主犯、从犯和胁从犯。 若与共犯角色的分工标准的理论说辞相对应, 则诉讼诈骗罪的主犯便基本对应着诉讼诈骗罪的主要实行犯、 组织犯和教唆犯, 而诉讼诈骗罪的从犯则对应着诉讼诈骗罪的帮助犯包括“被胁迫帮助犯”和诉讼诈骗罪的次要实行犯①次要实行犯的“次要作用”是同时相对于帮助犯的“辅助作用”和主要实行犯的“主要作用”而言的,即对共同犯罪的形成与共同犯罪行为的实施、完成起次于“主要作用”的作用。。
对于诉讼诈骗罪的共犯形态问题, 我们还应在单位共同诉讼诈骗罪中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这里所说的单位共同诉讼诈骗罪包括单位主体与自然人主体共同实施的诉讼诈骗罪和单位主体与单位主体共同实施的诉讼诈骗罪。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单位共同诈骗罪, 将作用标准和地位标准紧密结合起来予以区分主犯、从犯乃至胁从犯,则是较为合理可行的, 即能够体现罪刑均衡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②在我们看来,罪刑均衡原则蕴含着刑罚个别化原则,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可以视为罪刑均衡原则的一种具体和担当。。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若单位主体在单位共同诉讼诈骗罪中已被确定为主犯且单位主体中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直接责任人员主体, 则直接责任人员主体内部还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主犯、 从犯乃至胁从犯,[7]且并不排除由于“旗鼓相当”而存在两个以上的(直接责任人员)主犯。
(二)诉讼诈骗罪的罪数形态
在刑法理论中, 罪数是指犯罪主体所犯之罪的数量, 而罪数问题的讨论就是要解决犯罪主体所犯是一罪还是数罪问题。 既然罪数形态问题直接事关准确定罪和适当量刑, 则诉讼诈骗罪的罪数形态问题便有予以讨论的必要, 因为此问题本来就是诉讼诈骗罪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实在问题。
实际上,诉讼诈骗罪的罪数形态问题,也就是在涉嫌诉讼诈骗罪的案件中, 行为人的行为如何论罪的问题。 首先,诉讼诈骗罪存在着连续犯的问题。 在刑法理论中, 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而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 并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 那么,诈骗罪的连续犯,是指基于诉讼诈骗的故意而连续实施数个诉讼诈骗行为, 并最终触犯诉讼诈骗罪的犯罪。 对于诉讼诈骗罪的连续犯,当然不存在以数个诉讼诈骗罪予以并罚的问题, 而只能论以诉讼诈骗罪一个罪名, 至于诉讼诈骗犯罪连续的数量可由司法者以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自由裁量。 自改革开放以后,借对方当事人的粗心大意或合同(法)知识欠缺而“发订合同之财”的现象,我们早有耳闻。 而在社会诚信普遍严重滑坡的当下,专营于打官司的“发诉讼之财”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 于是,诉讼诈骗罪的连续犯作为诉讼诈骗罪的一种罪数形态便完全有可能存在着。
再就是,诉讼诈骗罪存在着牵连犯问题。 在刑法理论中,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但最终只能“择重处罚”的犯罪。 那么,诉讼诈骗罪的牵连犯,是指以实施诉讼诈骗为目的, 而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但最终只能“择重处罚”的犯罪。 由于牵连犯存在着手段和目的的牵连犯、 原因和结果的牵连犯这两种类型, 故诉讼诈骗罪的牵连犯也便逻辑地存在着前述两种类型。 何谓诉讼诈骗罪的手段和目的的牵连犯? 如为了实施诉讼诈骗而先实施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其手段行为便触犯了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由于诉讼诈骗罪是重于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证件、 印章的犯罪,故理当最终按诉讼诈骗罪定罪处刑;又何谓诉讼诈骗罪的原因和结果的牵连犯? 如在实施诉讼诈骗犯罪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此过程的末尾(包括二审),行为人出于骗局被法官识破的担忧, 或骗局已经被法官识破而迫不得已对法官行贿, 则对法官行贿的行为可视为“结果行为”牵连触犯了行贿罪。 由于客体的复杂性或侵害的复合性而致诉讼诈骗罪在整体上重于行贿罪,故“择重处罚”便是按诉讼诈骗罪定罪处刑。 当然,如果前述诉讼诈骗罪的手段和目的的牵连犯与原因和结果的牵连犯发生了“交合”,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牵连犯形态,但照旧适用“择重处罚”原则。
围绕着诉讼诈骗有人指出, 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307条第1 款的规定,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3]23这里的“妨害作证罪”可以视为诉讼诈骗罪的手段牵连犯。 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哪一种形态的牵连犯,在诉讼诈骗罪的牵连犯的司法处置中, 没有被确定为个案最终罪名的罪名所对应的犯罪事实应作为最终罪名的酌定从重情节对待①实际上,在想象竞合犯、法规竞合犯和牵连犯的场合,应奉行"双重处罚"原则,即按"重罪名"定罪,而在量刑上将其他罪名所对应的犯罪事实作为酌定从重情节对待。,即按“双重处罚”原则予以处置,以体现罪刑均衡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 另有人指出,诉讼欺诈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行为,其目的可能是诋毁他人的名誉或法人的商誉, 不仅会破坏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 而且也会对法人的商誉或自然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同时触犯《刑法》第221 条或第246 条的规定,构成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或诽谤罪。[8]这里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或“诽谤罪”是诉讼诈骗犯罪的目的行为所直接对应的罪名,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之视为诉讼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也未尝不可。 对于诉讼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也理当按“双重原则”予以处置。
诉讼诈骗罪行为人的所作所为也可能引起数罪并罚。 如行为人不仅自己实施诉讼诈骗行为,还在他人的案件中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则对行为人应以诉讼诈骗罪和帮助毁灭、 伪造证据罪给予数罪并罚。 精于“诉讼发财”和“诉讼逞能”的心理使得前述例证所对应的犯罪情形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 至于有人指出,在诉讼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与主审法官进行通谋的情况在实践中也有发生。 对于这种情况,应当按照主犯的行为特征来定罪, 即如果诉讼欺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则应当对行为人按照诉讼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来处理; 而如果是法官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或者主次要作用无法区分,由于法官的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罪名,应当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从一重罪处罚” 。[9]其实,在论者所说的场合,对诉讼诈骗的行为人应以诉讼诈骗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从犯)予以数罪并罚, 方可在符合事件情理中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
(三)诉讼诈骗罪的阶段形态
诉讼诈骗罪是复行为犯, 其前行为即手段行为对应着间接故意, 而其后行为即目的行为则对应着直接故意。 既然是包含着直接故意的故意犯罪,则诉讼诈骗罪必然存在着阶段形态问题。 那么,诉讼诈骗罪的阶段形态问题是怎样的呢? 有人用 “恶意诉讼罪”来代替诉讼诈骗罪并提出“恶意诉讼罪”是典型的行为犯,行为人一旦实施了诉讼欺诈行为,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就成立本罪的既遂,而不要求出现行为人达到其非法目的或受害人遭到现实的损失等结果。[10]这一论断所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一旦……就……” 的句式使得诉讼诈骗罪几乎由行为犯变成举动犯②举动犯也称即时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完全符合犯罪构成,从而构成既遂的犯罪。。 但另一方面,由于“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判断,而在此非常模糊的判断中,诉讼诈骗罪的既遂也可能成立较晚或很晚, 故诉讼诈骗罪既遂的成立时点也是极难确定。 诉讼诈骗罪终究不同于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我们有必要将其认定为举动犯吗? “一旦实施”可以体现为提出伪造的证据并提供虚假的陈述,以下论断如出一辙,即诉讼欺诈罪属于行为犯,则犯罪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向法院提供虚假的陈述、 提出伪造的证据,或串通证人提出伪造的证据的行为,便构成诉讼欺诈罪的既遂, 而无须考虑其是否利用法院达到了其非法目的。 这是由行为犯是基于“行为无价值”的属性所决定的。[3]持前述看法的人为数并不少, 如行为人只要在诉讼中实施了向法院提供虚假的陈述、伪造的证据,或串通证人提出伪造的证据的行为,便构成诉讼欺诈犯罪的既遂,而这样才能对人民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从而减少行为人对另一个复杂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11]诉讼诈骗罪的既遂直接牵动着诉讼诈骗罪的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的成立空间,故论者的一个“只要……,就……”的句式乍一看便显得过于草率或武断了。 而几乎是将诉讼诈骗罪视为举动犯的主张,很有点让我们感到一种“局势紧张”甚而有些“咄咄逼人”。 于是,有点缓和的论断就是有人提出, 由于诉讼欺诈行为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审判机关的正常司法活动, 因而行为人经提起诉讼即已对司法活动造成破坏。 当事人毁灭、 伪造证据罪是行为犯,行为人一经提起诉讼,法院予以立案即属既遂,行为人最终获得胜诉裁判或者实际得到他人财产、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是认定行为人既遂、 未遂的标准, 可以将行为人最终获得胜诉裁判或者实际得到他人财产的结果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8]“立案即属既遂”仍让我们觉得有点“形势严峻”,于是又有点缓和的论断就是有人提出, 诉讼欺诈的着手须是提出虚假的证据并提起民事、行政诉讼或其他非诉程序,因为单纯的伪造虚假证据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诉讼欺诈行为,而只能是诉讼欺诈的预备行为;[8]39或有人提出,行为人必须毁灭、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并提起虚假诉讼,两者都具备才宜认定为着手。而如果单纯伪造证据、虚构事实而没有提起诉讼,更应当认定为预备行为;[11]32另有人提出, 行为人为达不法目的,所实施的虚构事实、作虚假陈述、伪造证据或指使、串通他人作伪证等行为,均为犯罪预备行为。 着手行为是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区分点,因而着手的认定关乎定罪与量刑。 具体到本罪中,即为行为人提供虚构事实、提供虚假证据并提起诉讼,缺乏提起诉讼这一要件, 前者充其量只能算是犯罪预备行为。[12]将“提起诉讼”作为诉讼诈骗罪的“着手”无疑把诉讼诈骗罪既遂的成立时点推后, 从而延展了诉讼诈骗罪既遂的成立空间, 同时也为诉讼诈骗罪的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延展了成立空间。 反映对诉讼诈骗罪的阶段形态有所延展的认识,还有人提出,具体到诉讼欺诈罪中, 其既遂即以法定的诉讼欺诈行为的完成,即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为标准。 如果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法院尚未做出错误的判决, 但情节也非常严重的,则属犯罪未遂。 如果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未达到情节严重的,不构成犯罪,更不是未遂;[12]另有人提出,只要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或是其他目的,并采取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并使得法院在行为人的误导下作出了错误的判决,即使判决最终未能执行,行为人也未能实现其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或者是其他的非法目的,也应当认定为本罪的既遂。 在法院未作出错误判决的情况下,其行为构成本罪的未遂。[9]34-35需要指出的是, 将情节是否严重作为诉讼诈骗罪既未遂的判别标准存在着一个刑法理论常识性的错误:犯罪既未遂的讨论是以犯罪的已然成立为前提条件的, 故论者等于是将犯罪成立的条件混同于犯罪既未遂的成立条件。
在讨论中, 关于诉讼诈骗罪阶段形态问题的认识不断向前迈进,并向客观合理的结论逐渐靠近,如有人提出, 行为人为实施诉讼诈骗而事先伪造印章以伪造或变造有关合同、协议等证据的,属于诉讼诈骗罪的预备; 通过出示虚假的证据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就是诉讼诈骗行为的着手;法院在受理诈骗人的虚假诉讼后,并没有陷入错误认识,或者虽已陷入错误认识但并未作出财产处分决定, 或者虽已作出财产处分决定但还未将受害人的财产转移给诈骗人或第三人所有的,属于诉讼诈骗未遂。[13]在我们看来,若要寻求对诉讼诈骗罪阶段形态问题的尽可能合理或最为合理的解答, 我们必须或最好要立足于两个因素:一是为罪犯架设一座被称为“黄金桥”的犯罪中止制度,一是诉讼诈骗罪本身的行为构造。 首先是犯罪中止制度。 通观以往关于诉讼诈骗罪的所有论述, 我们在诉讼诈骗罪的阶段形态问题上尚未看到有关犯罪中止的说法。 犯罪中止制度本是鼓励犯罪人停止犯罪的刑事奖励制度, 而在一种具体的犯罪中, 作为犯罪阶段形态一种的犯罪中止的成立空间将直接决定着其他犯罪阶段形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成立空间。 在刑法理论中,若以成立阶段为标准, 则犯罪中止可分为犯罪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 犯罪实行阶段的犯罪中止和犯罪实行后阶段的犯罪中止。 其中,所谓犯罪实行后阶段的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实行完毕之后,危害结果出现之前这一阶段的犯罪中止。 那么,当我们能够从犯罪预备到危害结果这条时间延长线上为犯罪中止安排出足够长的时段, 则或许将意味着犯罪着手和犯罪既遂的时点将尽可能地被延后,从而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将获得更多的成立机会, 而犯罪既遂的成立机会则相对减少。 这将使得刑法两种基本价值即对犯罪的惩罚正义和对犯罪的预防正义在一种兼顾或曰“双赢”之中得到实现。 那么,我们似乎应将对犯罪中止的前述认识落实在诉讼诈骗罪的犯罪中止问题上, 从而带动诉讼诈骗罪其他阶段形态包括犯罪预备、 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在成立空间上得到既能符合事件真相又能体现刑法价值的合理正当的拓展。
再就是诉讼诈骗罪本身的行为构造。 我们都已经或可以普遍接受诉讼诈骗罪是复行为犯, 且可最终在行为构造上将诉讼诈骗罪描述为 “复行为的目的犯”。 那么,正如有人指出,刑法中的复行为犯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 在一个独立的犯罪构成中包含了两个具有手段和目的关系的危害行为的一种犯罪形态。 复行为犯罪的客体均为复杂客体, 其着手应以“前一行为说”为宜,而其既遂则应当视行为犯或者结果犯而定。[14]行文至此,若将前述两个因素即犯罪中止制度和诉讼诈骗罪本身的行为构造结合起来,则我们似乎可以或应该对诉讼诈骗罪的阶段形态问题达成如下共识: 诉讼诈骗罪以开始提起诉讼为着手,则着手之前为诉讼诈骗罪的犯罪预备阶段,而着手之后则为诉讼诈骗罪的犯罪实行阶段; 诉讼诈骗罪以行为人不法目的(对应最终危害结果的出现)的达到为既遂,在实行完毕之前为犯罪实行阶段,而在实行完毕至最终危害结果(对应行为人的不法目的)出现之前则为诉讼诈骗罪的犯罪实行后阶段。 于是,在诉讼诈骗罪的犯罪预备阶段、 犯罪实行阶段和犯罪实行后阶段,都可成立诉讼诈骗罪的犯罪中止;在诉讼诈骗罪的犯罪预备阶段, 成立诉讼诈骗罪的预备犯;在诉讼诈骗罪的实行阶段和实行后阶段,成立诉讼诈骗罪的犯罪未遂即未遂犯; 而诉讼诈骗罪的既遂只能成立于诉讼诈骗行为的实行后阶段。 在前述共识之下,法院没有陷入被骗而未作出错误裁判,自然能够被接受为诉讼诈骗罪的犯罪未遂即未遂犯; 由于诉讼相对人或第三人的上诉或申诉而导致错误判决在最终危害结果出现之前或行为人的不法目的最终实现之前而被撤销, 也自然能够被接受为诉讼诈骗罪的犯罪未遂即未遂犯。 当然,如果诉讼诈骗已经导致诸如被害人的财产已经被实际执行,其后又因申诉成功而导致执行回转, 则丝毫不影响先前的诉讼诈骗犯罪已经成立犯罪既遂, 其道理正如抢劫罪,抢劫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而成立既遂,但被害人通过“事后自救”取回财物并不影响先前的抢劫行为已经成立犯罪既遂。
三、诉讼诈骗罪的加重犯
有人指出,根据司法实践,诉讼欺诈罪的情节加重犯应包括如下情形:(1)法院一审作出行为人胜诉的判决, 从而给诉讼相对人造成较大损失的;(2)法院二审作出行为人胜诉的裁判, 从而诉讼相对人的财产已被执行。[3]论者给我们道出了诉讼诈骗罪的加重犯问题。 但在我们看来,从刑法理论上,诉讼诈骗罪的加重犯应逻辑地包含着情节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 而无论是诉讼诈骗罪的情节加重犯,还是其结果加重犯, 都征表着诉讼诈骗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一种“加重”。 那么,对诉讼诈骗罪的加重犯的司法实践把握, 便直接关联着罪刑均衡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贯彻和落实,从而既关联着诉讼诈骗罪的惩罚正义, 也关联着诉讼诈骗罪的预防正义即功利正义。 如此看来,仅仅将诉讼诈骗罪的加重犯局限在情节加重犯便难免显得视野狭窄。 在我们看来,诉讼诈骗罪的情节加重犯基本上对应着诉讼诈骗罪的犯罪手段以及行为过程表现, 而其结果加重犯则基本上对应着诉讼诈骗罪的最终实际结果。 如果这样看问题,则诉讼诈骗行为给诉讼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与诉讼诈骗罪的结果加重犯相牵连,至于诉讼相对人的财产是否已被执行,显然不应是诉讼诈骗罪的加重犯问题, 而是其犯罪形态即既未遂问题。
当然,对诉讼诈骗罪的加重犯的司法实践把握,我们还应采取更加广阔的视野。 当行为人以严重违法的手段来实施诉讼诈骗罪, 如行为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行为人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来实施诉讼诈骗罪, 如行为人以发生性关系来获取虚假证据,凡此种种,我们应将其视为诉讼诈骗罪的情节加重犯; 当诉讼诈骗行为导致被害人巨大的财产损失, 甚或诉讼诈骗行为导致被害人不堪经济或精神重负而身患重病乃至自杀, 我们应将其视为诉讼诈骗罪的结果加重犯。 而当诉讼诈骗行为导致上诉和申诉即导致多轮诉讼, 则我们也应将其视为诉讼诈骗罪的结果加重犯, 因为诉讼诈骗行为所导致的多轮诉讼已经在导致诉讼相对人即被害人“马拉松式”的财产耗费和精神耗费的同时, 也导致了国家司法资源的“马拉松式耗费”,同时也会导致司法公正形象缺失的“雪上加霜”。 当然,诉讼诈骗罪的情节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可以在对诉讼诈骗罪作立法增设时就规定进去,也可在积累经验之后作出增补,或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规定。
[1] 介晓宇.诉讼诈骗的定性及其法律规制[D].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6.
[2] 董玉庭.论诉讼诈骗及其刑法评价[J].中国法学,2004,(2):140.
[3] 刘远,景年红.诉讼欺诈罪立法构想[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2):22.
[4] 欧柯邑.论虚假诉讼行为的刑法规制[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26.
[5] 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64.
[6]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79.
[7] 马荣春.刑法诸问题的新解说[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40-41.
[8] 曲艳红.论诉讼欺诈[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40-41.
[9] 陶文静.诉讼欺诈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33-34.
[10] 陈向阳.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定性[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9.
[11] 赵晶. 诉讼欺诈问题研究[D].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33.
[12] 朱红红.浅析诉讼欺诈[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5.
[13] 于改之,周玉华.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及相关问题探究[J].法商研究,2005,(4):87.
[14] 卢有学.复行为犯罪基本问题探讨[J].学术交流,2005,(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