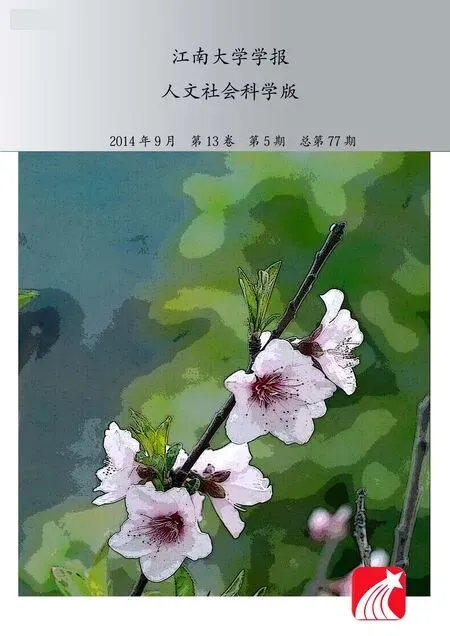翻译文学视野下的朱译莎剧研究
朱安博, 徐云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系, 北京 100070)
引 言
朱生豪(1912-1944),原名文森,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诗人。朱生豪从1935年至1944年,历时十年之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共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三十一部半。*到1944年去世前,朱生豪译出莎士比亚全部剧作37部中的喜剧13部、悲剧10部、传奇剧4部和历史剧4部及《亨利五世》(未译完),共31部半,遗憾的是,由于朱生豪英年早逝,历史剧中《理查三世》、《亨利五世》(部分)、《亨利六世》(上中下)、《亨利八世》6部未及翻译。他以生命译莎,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作为中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先行者和主要翻译者,朱生豪以特有的诗人气质和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成就了翻译莎剧的豪举,译作通俗易懂而文采四溢,以至成传世精品。目前关于朱生豪翻译研究的成果大都是集中在朱生豪的翻译思想概述、译作例句评析以及翻译的社会文化成因等方面。而从比较文学,特别是翻译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朱生豪比较鲜见。本文将朱译莎剧的翻译文学文本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来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在特定时代的关系,也给当代人一个重新认识翻译家朱生豪的过程。*本文部分内容详见笔者合著《朱生豪的文学翻译研究》,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一、 翻译研究中朱译莎剧的缺失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莎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展开了从语言学到文学、从殖民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等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显示出中国莎学研究的整体实力与水平。“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评论、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构成了评论、研究与演出的基础。……但是却鲜有人对他们的翻译经验,翻译研究中的各种批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显然,这与翻译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极不相称的”。[1]46中国的莎学研究者很多是依据译作来进行研究与评论的,因此,对于莎剧的译者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莎剧的主要译者朱生豪的研究来说,目前也只是有少数的文章,作者也往往只是根据一些例句来分析朱生豪翻译的优劣得失,或者简单笼统的翻译思想介绍,缺少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学理的探讨。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在研究我国传统译论和翻译家翻译思想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郭著章等编著的《翻译名家研究》集中研究了当代中国的翻译家。“书名中的‘翻译名家’者,乃在翻译业绩方面有特殊贡献的著名人物也,他们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林语堂、徐志摩、茅盾、梁实秋、钱歌川、张谷若、巴金、傅雷、萧乾、戈宝权、王佐良和许渊冲。……对每位名家发表的散见各处的翻译见解进行了发掘淘炼、爬罗剔抉乃至发幽显微的工作,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找出了其特点、渊源、发展和影响,指出其在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事业中的地位、作用或意义”。[2]3可遗憾的是,《翻译名家研究》中竟然使毕生译莎“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的朱生豪缺席。
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十大学说思想”(“文质说”,“信达雅说”,“信顺说”,“翻译创作论”,“翻译美学论”,“翻译艺术论”, “意境论”,“神似说”,“化境说”,“整体/全局论”)为中心命题,追溯其共同的历史渊源,继承、发扬、开拓传统译论思想;而朱生豪翻译莎剧提出的“神韵说”思想,却没有能够进入“十大学说思想”。
这些比较有影响的翻译史、翻译家研究,在面对朱生豪时候,竟然“不约而同”的集体失语,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与深思。从翻译研究角度来看,“多年来莎士比亚翻译研究并没有引起莎学界的足够重视,甚至也没有引起翻译界的重视,没有或很少有人进行全面总结研究,已经出版的莎学著作和莎士比亚辞典对这方面也少有述及。”[3]273虽然莎学研究成果是巨大的,但是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与莎学研究不相匹配,更是鲜有研究成果把朱译莎剧的翻译文学文本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来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
现代以来,尽管社会科技水平高度发展,时代特征也与莎士比亚时期有所不同,但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生死爱欲、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谐问题都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世界读书日(4月23日)正是莎士比亚的诞生日,彰显的不仅是阅读经典的意义,阅读莎士比亚的意义。经典作品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资源,阅读经典更是人类认知过去、期盼未来的必由之路。“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批评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梳理,或许我们会在现代意义上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3] 506优秀的译作能够而且应该与原作一样成为影响力巨大的经典作品。因此,阅读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研究朱译本的莎士比亚,不仅仅只是关注译文词语的翻译得失,目的是从文化、文学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艺术精髓,结合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特点进行阐释。
二、朱译莎剧的文化研究
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只注重翻译过程中的字词句转换等语言现象,并不关心它的文学和文化地位。在朱生豪等译者翻译的文字中找到一些批评的例子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真正从宏观上、从哲学、语言学、文化学、译介学的角度提出批评,指出整部莎剧或莎作全集翻译特点、风格则相对较难。……这种翻译批评虽然难以引起翻译者的注意,但是却应该引起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因为莎士比亚翻译批评研究为他们提供了分析材料,使比较文学研究者可以从译介学的角度研究不同莎作译本在创造性叛逆方面究竟走了多远?译者的翻译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翻译主张?他们的翻译异同在那里?对莎氏翻译家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思想的探讨基本上是空白。”[1]52因此,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朱生豪的文学翻译,不仅可以弥补只关注朱生豪在翻译中字词句的转换技巧等语言现象的不足,更能够从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层面多角度进行系统地研究朱生豪的翻译思想。
朱生豪译莎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白话散文体来翻译莎翁的诗体剧作,这也给后世研究者以诟病的理由。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其散文体莎剧翻译,要从当时朱生豪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看。朱生豪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他的诗词创作与他在译莎时采用的口语化的白话文散文体,对他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有很大关系。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素以准确、畅达、优美和传神而著称于世。例如《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ies!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 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 (Act Ⅱ, Scene ii)
朱译为: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4]314
这是哈姆莱特与两旧友对话的片断。这段台词文字庄重典雅,行文自然流畅,历来广为传颂,而朱生豪的译文也是高雅优美,脍炙人口。在翻译中,朱生豪秉承“志在神韵”的翻译原则,不拘泥于原文词义,而是根据语境作适当引申,译得灵活巧妙,更加贴切自如。如把apprehension译成“智慧”,beauty译成“精华”,paragon(原意是“完美无缺的人”)译成“灵长”等等。译文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充分发挥白话文的语言特色。充分展示了译者不拘泥辞典释义,能融汇句意化为妙文的高超译艺和诗人本色。译文虽然是白话文散文体形式,浅显通俗,但是在语言上,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朱生豪赶上汉语白话文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他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新文化运动又使他的白话文得到充分的发展。他写过诗,写过杂文,白话文的使用远远高出一般人。他翻译莎剧与其说选择了散文,不如说选择了极其口语化的白话文风格。这对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载体,是传统的典雅的文言文根本无法承载的。……要知道,能够熟练地富于创造性地驾驭口语,是运用语言的最高境界”。[5]24朱生豪的译文体现了文学语言的口语化,更有有现代口语的韵味。译文看不出刻意翻译的痕迹,仿佛是译者直抒胸臆,天然妙成,堪称名句佳译,神来之笔。
朱生豪译文的白话文风格有其诗学背景。在之江大学时期,他被誉为“之江诗人”,不仅写过大量的旧体诗词,也写过许多白话诗。朱生豪的时代,中国莎剧翻译还处于初始阶段,不仅译出的剧本数量很少,而且删改严重,大多还是以文言文形式翻译的故事梗概,莎剧的艺术价值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展现。因此,“朱生豪的莎剧翻译标志着我国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一度转向,即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零星翻译到系统翻译、从随意增删到忠实原文的转向”。[6]50在白话文由不成熟向成熟发展时期,在这种翻译诗学观背景下,朱生豪顺从了汉语白话的诗学规范,并以个人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对原作进行适度的改写,以求“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 朱生豪的译莎就是对这种文化语境的一种体现。在这种翻译诗学观背景下,朱生豪以体现原作的“神韵”为翻译原则,不在个别字句的得失上纠缠,而是着眼于剧情和阅读的需要。他用白话文来翻译莎剧,顺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潮流,不仅使莎剧更适合中国的舞台演出,也使得莎士比亚戏剧有了更广泛的读者。
“朱生豪的莎翁译作的一大特点和对国际莎学的贡献是他将莎士比亚式的英语翻译成现代的白话文,这在传播和接受意义上使得中国观众要比英语国家的观众更加容易理解。他的31部莎剧译作奠定了1978年在北京出版的《莎士比亚全剧》的基础,推动了莎学在中国的飞跃性发展”。[7]143朱生豪译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时期左翼戏剧家以戏曲作为文化载体,从而走向民众,以达到宣传革命的目的,朱生豪译莎的动力和爱国情怀不能说不受此影响。这一时期的戏剧翻译主要有作为文学作品阅读和作为舞台剧本上演两种目的,而作为文学阅读为目的的戏剧翻译反映了该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
一个翻译文本之所以在目的语系统中能够得以接受,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有着密切关系。翻译活动受到这一系统的意识形态及诗学上的准则制约和影响。朱生豪在莎剧翻译中不拘泥词句,而是以“神韵”翻译思想把莎士比亚戏剧文学的精髓通过精妙的语言和感悟,加以适当的改造以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心理。更重要的是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包含着爱国主义情怀,他以生命译莎,对人生意义价值有较为深入的理解。朱生豪以其特有的翻译诗学风格,以莎剧翻译为载体,是与莎士比亚穿越时空的灵魂相遇。
三、朱译莎剧的翻译文学研究
自从翻译文学概念提出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谢天振教授在国内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还提出了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转变。“我国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关注和重视,如果从梁启超、胡适算起,差不多正好是100年的历史。然而在这100年的时间里,前半个世纪,我们的学者大多只是注意到翻译文学的存在,认识到翻译文学的功用,却鲜有人从理论上、从学术层面上,对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文学类型的性质、归属等问题进行深人的研究。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翻译文学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8] 23
王向远教授的《翻译文学导论》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论述翻译文学的概念、特征、功用、方法等方面的理论专著,对于推动国内翻译文学研究的深人发展,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在讨论“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区别时,王向远教授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行为过程,也是一种中介或媒介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本体的概念;‘翻译文学’则是‘文学翻译’这一过程直接结果。”[9] 6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翻译这一过程的直接结果,那么所有已经翻译过的作品也就都“直接”成为了翻译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打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研究朱生豪的翻译文本来说,不仅只是从传统的字面翻译角度来探讨,还可以拓展研究领域与思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朱译莎剧,这无疑是开辟了朱生豪研究的新领域。
俗话说,文如其人,译如其文。之江大学的学习使朱生豪具备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古典诗词创作才能,这为他翻译莎剧奠定了基础。朱生豪在对原文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不完全受原文形式的束缚,而是对原文进行再创造、再加工,赋予了译文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息以及浓郁的中国古诗韵味,再现了原作的神韵。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中提到:“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10]263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时,始终努力坚持“保持原作之神韵”或“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的宗旨。比如在《无事生非》里面,有一段克劳狄奥到希罗墓前的挽歌:
歌
惟兰蕙之幽姿兮,
遽一朝而摧焚;
风云怫郁其变色兮,
月姊掩脸而似嗔:
语月姊兮毋嗔,
听长歌兮当哭,
绕墓门而逡巡兮,
岂百身之可赎!
风瑟瑟兮云漫漫,
纷助予之悲叹;
安得起重泉之白骨兮,
及长夜之未旦![11]531
读到此处,如果不说明这是一篇译文的话,谁又能看出这是翻译作品呢?若莎士比亚懂中文,也会为朱生豪的妙笔生花叫绝!“从翻译文学的角度来说,译作也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12]130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把译者当作“传声筒”或者是原作者的“影子”,而忽视了译者的再创造作用。上述译文,正是朱生豪凭借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莎剧的深层领悟,以互文性的创造手法,巧妙移植了屈原作品中“兰”和“蕙” 的意象,采用我国古代诗歌中的骚体来表现原文文体的优雅和感情的真挚,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和悲伤的心情,从形式到内容再现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神采和韵味。“文学翻译传递的是一个特殊对象──文学作品,是一部在异族环境中,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作品,这使得文学翻译这一跨越民族、跨越语言、跨越文化的传递变得相当复杂。因此,这是一种相当艰难的艺术再创造”。[13]132这种艺术再创造,朱生豪不仅只是凭借对莎剧原文较为透彻的理解以及灵活的翻译策略,更与他自身所具有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特别是他兼擅古典诗词与新诗的创作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种再创造,使译作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文学价值。
在中国,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莎剧译者各有特色,译者也总是在寻求最适合时代阅读的翻译文本。“文学作品在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为了能使译文的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同样的艺术感受,译者就不得不参照译语环境,找到能够调动译文读者产生审美阅读的语言手段。文学翻译不但使原作在另一种语言、文化和社会中得以新生,同时也在其中植入了新的表达方式、思想和视野”。[14]112就莎剧翻译而言,朱生豪翻译的散文体追求“神韵”,以其译笔流畅、通俗易懂为读者所称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梁实秋以“存真”为特征,译本为莎学研究者提供了参照,具有较高的可研究性;方平主译的《新莎士比亚全集》以全新的追求尝试以诗体译莎,体现了创新性特点。这些经典的译作以翻译文学的形式展现了中国莎剧研究的视角和翻译的价值。
四、从朱译莎剧的文学翻译转向翻译文学研究
在中国,特别是在当代,各种文学流派都把莎士比亚当作其理论的试金石,对莎剧的丰富解读使得莎学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展和延伸,所出现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浩如烟海。研究角度丰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充分显示了我国莎学学者思想的活跃和视野的开阔。无怪乎国际莎学界人士曾有“莎士比亚的春天今日是在中国”*1986年4月,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当时的国际莎士比亚学会主席菲利浦·布罗克班克在观看演出后慨然称赞:“莎士比亚的春天今日是在中国”。之赞。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莎学还未建立自己的体系,在‘以我为主’方面也做得不完善,还不能自然而自觉地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原则上来探究莎学”。[15]13王忠祥教授的“以我为主”就是要在莎学研究上不能仅仅为了研究而研究,要结合本土文化,真正做到“洋为中用”。无独有偶,吴笛教授也认为,为了从构成各民族文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提升外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学术地位,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应在原有基础上注重拓展和转向。为此,吴笛教授提出了“外国文学经典研究应从文学翻译研究转向翻译文学研究”等三个转向。这一转向,使“外国文学”不再是“外国的文学”,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将外国文学从文学翻译研究的词语对应中解救出来,关注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重点探究“外国的文学”怎样成为我国民族文学构成的重要部分以及对文化中国形象重塑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目的不是单纯地引进外国文化,而是服务于中国文化建设。[16]237
简单地说,吴笛教授的三个转向可以概括为:
①从文本本身研究转向文本生成与演变的研究,即审美转向认知。
②从文学翻译转向翻译文学研究。
③从外向型研究转向中外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研究。
这三点之间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第一个转向是研究的前提,即要认识到研究视角的转变,比如方平先生把莎士比亚的中译分为三个阶段:文言阶段、白话阶段和诗体阶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以研究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何会有不同的文本生成与演变;第二点是研究中心的转变,要重点关注翻译文学,要从翻译文学的性质以及归属等方面来论证与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第三个转向是目的,前两者的研究都是为了实现中外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重构。
朱生豪曾在书信中写道他翻译莎剧的动力:“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17]246这里撇开爱国主义角度不谈(已经有不少研究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朱生豪认为中文莎剧全集的翻译出版堪称“民族英雄”,其中的“民族性”主要是指莎剧译本有助于丰富民族文学与文化,是对本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贡献。劳伦斯·韦努蒂指出翻译有助于本土文学话语的建构,并参与了本土语言与文化的发展,翻译能够修订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群体的典律,而且可以促使另一文化群体创制译本并作出反应。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表述,为文化的抗争、革新及变动提供了各种可能性。[18]372另外,朱生豪的莎剧译本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表达出中文对于莎剧的独特解读方式,是民族精神在世界文学平台上发声的契机。由此可见,朱生豪这位之江大学(浙江大学前身)国文系出身的文学翻译家,其翻译的出发点始终是扎根于中国民族文学的繁荣。
因此,研究外国文学经典如莎剧等的译介与传播应该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相结合,树立我国莎剧等经典译介和研究的学术思想的民族立场。把对于莎剧翻译的研究仅仅只关注朱生豪等译者在翻译中的语言转换技巧扩大到翻译文学和文化的层面,因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结 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是翻译家,翻译文学构成了许多作家创作成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翻译文学和民族文学相互交织、互为影响,文学历史的发展已证实翻译文学直接参与了现代文学史的构建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在莎剧翻译中,朱生豪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语言演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翻译文学的角度来说,朱生豪的翻译成为他自己对莎剧的一种解读,他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他所展示的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翻译文学的真谛所在。把朱译莎剧的翻译文学文本纳入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来探讨翻译文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关注朱译莎剧在我国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李伟民. 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J]. 中国翻译, 2004,(5):46-53.
[2] 郭著章. 翻译名家研究.序言[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3] 李伟民. 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
[4] 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全集:第五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5] 苏福忠. 说说朱生豪的翻译[J]. 读书, 2004 ( 5):23-31.
[6] 邓笛. 从朱生豪到方平中国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二度转向[J]. 鲁迅研究月刊,2008 (9):46-51.
[7] 王心洁,王琼. 中国莎学译道之流变[J]. 学术研究, 2006(6 ):141-146.
[8] 谢天振. 关于翻译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J]. 中国比较文学, 2008 (1):22-30.
[9] 王向远. 翻译文学导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0] 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M]//吴洁敏,朱宏达.朱生豪传:附录二.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11] 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12] 谢天振.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3]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4] 曹顺庆. 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J]. 外国文学研究, 2011(6):111-117.
[15] 王忠祥.《外国文学研究》与莎士比亚情结[J].外国文学研究, 2004(5):5-15.
[16] 吴笛. 中国社会科学报[N].2011-11-12,第237期.
[17] 宋清如.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18] 劳伦斯·韦努蒂.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M]//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