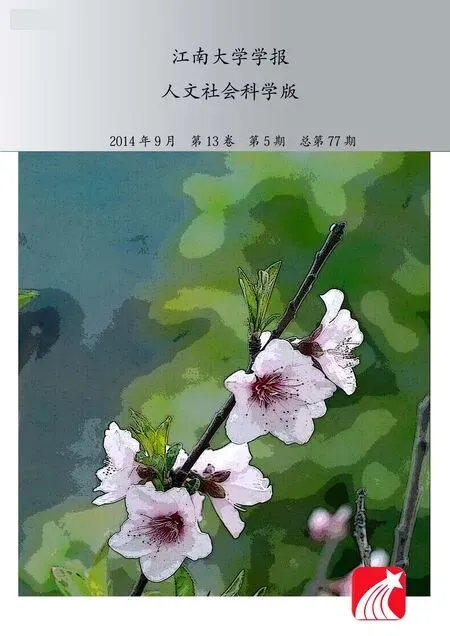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李志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自清赵翼《廿二史札记》谈到:“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1]始,研究唐代藩镇的论著,多侧重强调其损害中央集权之消极方面。安史乱之前,藩镇主要集中于边疆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出于平叛的需要,藩镇制度在内地迅速扩展。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林立的局面依然得以维持。此因藩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唐后期,藩镇对维护和保障漕运线路的作用显著,从而起到维护中央统治的作用。
关于唐后期的漕运,史念海先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认为,三门峡是历代关东西漕运的枢纽,是漕粮运输的必经之路。并详论了为解决关中粮食问题,秦汉隋唐历朝所实施的各种解决办法[2]35-47。潘鏞先生《中晚唐漕运史略》主要论述了唐人利用自然水道,在中晚唐时期实施漕运的情况,及其对唐王朝经济、政治的积极作用,并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漕运与唐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3]。吴立余先生《略论元和初期李巽的盐法漕运改革》认为,元和初李巽对当时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盐法漕运进行了改革,之后,提高了盐铁收入,扩大了漕运成果,不仅从经济上削弱了藩镇,而且支持和推动了宪宗朝的平叛事业,使中央强化了对东南财政权的控制[4]。关于唐后期漕运的论著还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论述。前贤关于中晚唐时期漕运的论著,加深了对唐后期政治经济联系的认识。本文试以唐后期藩镇与漕运的关系为着眼点,阐述在保障漕运方面,藩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起到了维护唐后期政治统治的作用。藩镇的存在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反映了安史乱后,唐廷对战后秩序重建所取得的成绩。
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地区藩镇林立,加之屯守重兵,难以稳定向中央贡献。随着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藩镇屯兵又较少,得以有余力向中央贡献。为了保证京畿物质需求,唐廷历来重视转漕东南粮物。关于漕运的特点,吴琦先生曾指出三点:第一,漕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路转运,而是特指朝廷的水上转运,即官家水道之运输;第二,漕运是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粮物征调,而非各地自下而上的粮物朝贡;第三,漕运是统一王朝的粮物运输,只有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方可确保这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常年物质运输,也只有中央政权才需要这种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5]。
本文认为,因唐后期藩镇林立的格局的形成,漕运经由地区,时有战乱或遭战火之威胁,漕运因此时断时续或转由他道,因而受到很大影响。为尽可能保证漕路畅通,势必需要沿途藩镇予以保障。在唐后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相关藩镇对漕运线路的保障基本得力,大大缓解了唐廷对于财货的需要,对维护唐后期的中央统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因大河南北陷入战火,洛阳丢失后,漕运路绝。王夫之《读通鉴论》记:“当其时,贼据幽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唯江淮”[6]。陈寅恪先生亦曾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7]。当时之人,亦有类似看法,如吕温《故太子少保韦府君神道碑》记:“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而食”[8]4745。
唐后期,唐廷依靠江淮财赋,故保护漕运线路至关重要。据此,杜希德先生将唐代几个重要区域,进行了分类:“这些关键区域的第一个当然是京师的关中道,那里的资源虽然减缩,但它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仍是至高无上的。第二个关键区是西北的边境区,它是掩护京师使之避免帝国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的盾牌。第三个是长江淮河流域,这一区域有迅速扩大的生产力、增长的人口和繁荣的商业,因此已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第四个是运河地带,它包括那些从南方运输税收所必经的几个镇”[9]。安史之乱的爆发,关中、大河南北等悉为战区,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此后中央赖以维持的经济基地,转由江淮等南方诸镇承担。因此保卫漕运来源和经由地带,是唐后期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之一。
将南方财赋迅速转运至抗敌前线,开辟一条新漕路势在必行。时“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10]2504。开辟一条从江淮经襄阳,最后到达关中的、完整的财赋运输线路,另外保证这条生命线的安全和畅通,都需要集结藩镇的力量方能解决,这是单个州郡力所难及的。因此为保证东南财赋的顺利运输,有必要在沿线地区设置藩镇,或藉助藩镇的力量予以保护。
安史乱后,漕运线路上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巨挑战。如所周知,自天宝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加之官府搜刮,小民难以生存,户口大量流散,导致租税日臻减少,地方官府更加紧搜刮,如此造成了恶性循环。伟大诗人杜甫所作《石壕吏》、柳宗元所作《捕蛇者说》,都反映了安史乱后地方官府搜刮之急迫,小民生存之艰难。安史之乱爆发后,大量难民又从中原逃往南方,其流离失所者多沦为盗贼,以劫掠为生。
如两浙地处两江一湖交汇之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参以官府横征暴敛,于地方治理上又难以触及,致“中原大乱,江淮多盗”[11]5164。至德年间“吴郡晋陵江东海陵诸界,已有草窃屯聚,居于洲岛,而新安郡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8]5121。宝应年间“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12]7105。唐后期长江沿线藩镇辖区内江贼活动猖獗[13]168,且祸害范围甚广。为此,江西、鄂岳、两浙、宣歙、淮南等南方诸镇,采取了相关措施,保护境内航运安全:“今若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择少健者为之主将。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拣择精锐,牢为舟棹,昼夜上下。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即由宣歙、浙西、江西、鄂岳、淮南等镇,联合打击江贼。当时国家依靠东南赋税,为维护财税地的治安和漕路安全关系重大:“今西北边,御未来之寇,备向化之戎,长倾东南物产,供百万口”。且打击江贼,可祛三害,收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乡闾获安,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贼,搜求财货,私茶尽黜,去三害也。收到三利:商旅通流,万货不乏,获一利也;乡闾安堵,狴犴空虚,获二利也;撷茶之饶,尽入公室,获三利也”。并且当时打击江贼有很多成功案例,证明其具有可行性。如江西观察使裴谊收降贼帅陈璠,“署以军中职名,委以江湖之任。自后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陈璠每出彭蠡湖口,领徒东下,商船百数,随璠行止”[13]168。
又自乾元元年起,两浙连续三年大饥,民众饿死无数。上元、宝应年间,江淮再次遭遇旱灾,继之以瘟疫。“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籍者,弥二千里,《春秋》已来不书”[11]4003。但官府并未因此放松对江淮的赋敛,“时天下饥谨,转钩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上元中)敕江淮堰壤商旅牵船过处,准斛斗纳钱,谓之棣程”[14]。迫于战争的需要,即使遇到大灾之年,唐廷对灾民的赋税依然难以减免。搜刮严急,自然会造成民乱。为此,保护漕运线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安史叛军攻陷洛阳后,立即与唐廷展开了对漕运线路控制权的争夺。叛军屡攻雎阳,企图切断漕运通道,进而占据江淮;又南攻襄城,企图阻扼汉水通道。这两条运道,都是当时唐王朝的生命线[15]。幸有睢阳张巡、许远和鲁炅等誓死抵御,使中原地区不至彻底沦陷。张巡死守睢阳,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面对外来冲击时,单个州郡的力量太弱,只有依赖藩镇,才可勉强与叛军作一较量。如此才能将南方诸镇物资,源源输入中央。当时江南财赋转运西北的路线,《通鉴》记“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然后由褒斜道“陆运至扶凤以助军”[12]7001。唐廷据此转运资粮,接济河西、陇右、朔方等镇军队,最终平定了叛军。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虽勉强弭平,但唐后期中央政府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并未因是衰减。大河南北诸镇,中央并未完全掌控,经由中原地区的漕运线路时有可虞。其关系唐廷死生存亡,中央势必要绝对掌控这条线路,为此拉开了诸镇护卫漕运的大幕。如大历十一年(776)李灵曜据汴宋叛,汴水受阻,忠武镇陈州刺史陈芃开通陈颖运道,利用古鸿沟旧渠,漕船由淮溯颖、蔡水而上,绕开了汴渠。建中时,成德、魏博、淄青、幽州四镇同叛,中央一面抽调禁军进讨,一面派精兵武装护航。不久,淮西李希烈屡欲切断运河与江汉通道,危急关头,江西节度使李皋转战数千里,保护饷道,“江汉依皋为固”[16]3580。元和中,淮西之役中,淄青李师道“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数余区”[16]5992。宪宗于宣武镇置淮颖水运使,将扬子院漕米自淮阴西入颖水,抵郾城,以馈诸军,“士饱而歌,马腾于槽”[17]。在粮响充足的情况下,最终平定淮西叛乱。
二、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我们知道,武宁镇徐泗二州为漕运要津,又毗邻河朔藩镇,成为护卫漕运的重要地带。广德二年(764),刘晏受命改革漕运,采用“分段交卸,依次进发”办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16]1365。就扬州漕船入汴而言,徐泗两州实当关键枢纽地位。建中时,田悦、李纳、梁崇义相继作乱,李、田扼守徐州涡口,致淮运断绝。梁崇义霸占襄邓二州后,江汉运路亦告受阻。两路漕运皆绝,关中处于恐慌状态。为此,江淮水路转运使杜佑曾建议别治运道,幸而淄青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朝,江淮运道复通,暂时缓和了中央的物资供应危机。
唐廷中央一直在努力确保徐泗二州的控制权。而武宁镇的存在,较好地弥补了汴宋、淮南间护卫漕运的空白。中原漕运的两个关键要地,分别是徐州以南的埇桥和汴州。在防遏河朔的同时,武宁镇起到了保护漕运的作用。建中二年(781),“李正已反,屯兵埇桥。江淮漕船积千余,不敢踰涡口。李泌建言:‘东南漕自淮达诸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口,请以建封帅徐’”[10]3441。东南漕运一度梗阻,及“李纳将李洧以徐州降”[16]183,汴水才得以重新打通。为缓解徐州地段的护漕压力,建中三年从李泌之请,德宗以徐州为中心,组建了武宁镇,命张建封为徐泗镇帅,以护卫漕运。有鉴于建中时漕运艰阻的现状,德宗还京后,为稳固江淮运道,派重兵守卫徐、汴州,确保淮上遭运。贞元四年(788),又派寿庐濠州都团练使张建封代替“年少不习兵事”的高明应镇徐州,扼制淄青,使运路畅通无阻:“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12]7509。贞元十六年,徐泗濠团练使张建封死,徐州兵变,劫建封子愔“令知军府事”,唐廷以淮南节度杜佑“兼徐泗濠节度使,使讨之。佑大具舟舰,遣牙将孟准为前锋;济淮而败,佑不敢进。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大败而还”。中央命淮南与武宁军作战的目的在于夺取埇桥,打通漕路。在淮南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除愔为徐州团练使[12]7586。但为保护泗水,中央采取了“复置泗濠二州观察使隶淮南”[16]1795的措施。可见,徐泗保护漕运地带,关系唐后期李唐国计,其不能不处心积虑加以控制。咸通三年(875),徐州兵变平定后,中央又废武宁军,“更于宿州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12]8096。其目的之一也在于肢解武宁军,削弱其实力,减少武宁残余叛军对漕路的威胁。
关于唐代江汉地区的漕运路线,王应麟《困学纪闻》记:“商州上津县,汉长利县。扶风郡,凤翔府。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德宗治上津道,置馆。洋川郡,洋州泝江汉而上,至洋川,陆运至扶风。汴水堙废,漕运自江汉抵梁洋”[18]。陕虢镇不仅沟通两京,又南邻汉、丹水,故其处于漕粮西入关中和梁洋二州的关键地带。陕虢镇的这种特殊地缘位置,对保护和协助漕运具有重要意义。隋唐时期漕粮西入关中,关键节点在陕虢。隋初,关东漕粮即在陕州小平津陆运,通过殽山道,运到陕州,再循河西运长安[19]。唐初东南漕粮,依然通过陕虢转漕。自唐后期始,主持漕运官员的一个重要职责,即为整顿陕虢水陆转运。此因陕州以南的殽山运道艰险无比,但又是关中沟通洛阳的必经之路;之外,陕州地处黄河中游,水流湍急,航运艰险,这更凸显了陕州的陆运地位[2]35-47。鉴于此,集中陕虢二州力量,于此置镇,负责调剂漕运,对维持唐后期政权而言关系重大。唐初,陕虢水陆运输整顿较好时,关东漕粮可大批调入,“唐都长安,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开元中,裴耀卿整顿陕虢漕运后,“凡三岁,漕七百万石”[16]1365,数目激增。
陕虢地势凶险,为便于将关东漕粮大批运抵关中。玄宗时,专置陕州水陆转运使[20]1898。安史乱后,为强化陕虢镇的转漕和护漕能力,保证漕粮西入关中数量的稳定,中央采取了两种措施:一,广德元年(763),皇甫温任陕州刺史时,“陕西观察使增领虢州”[16]1759。陕虢二州合并,结成藩镇。一方面增强了护卫关中的能力,另一方面集结当镇力量调剂、保护运输;二,安史乱后,陕州水陆运使似已重设。史籍中关于陕州运使乱后复置的情况,始见大历十四年(779)五月,《旧唐书·德宗纪上》记:“(本年,德宗)以江西观察使杜亚为陕州长史,充转运使”。因代宗广德二年(764),漕运即已由刘晏着手整顿,故陕州运使的复设、及陕州镇帅兼任运使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些[21]。陕州水陆运使设置后,期间因乘舆播迁,中原藩镇悉陷战火,漕粮由江汉转运梁洋,因此期间即使未废,实际上也未发挥作用。贞元十三年四月,于頔为陕虢观察使,重领水陆转运使[20]1898。其运使之名,之所以多以“陆”称,主要因为陕州黄河漕运地段比较凶险,很多时候要靠陆运,而非水运转输资粮。安史乱后,河淮遭叛乱冲击,汴渠航运陷入停滞,河运自然难以为继。
贞元元年(785),唐廷中央急于财货,德宗派李泌节制陕虢,“始凿山开车道至三门,以便饟漕。以劳,进检校礼部尚书。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累封邺县侯”[16]4631。李泌固为德宗亲信,但其得到德宗嘉赏,主要因为其节制陕虢时,主持转漕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输东渭桥太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16]1365。开成时,户部侍郎裴休主持陕虢漕事,“自江达渭,运米四十万石。居三岁,米至渭桥百二十万石”[16]1365。当关东形势险恶时,经由陕虢转漕意义更为重要。如《旧唐书·德宗纪》记,建中三年(782)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与朱滔等四盗胶固为逆”。因此两河地区悉陷战火,沿途漕运要路受到严重干扰,以致中断:“(李希烈)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12]7335。其后,汴河水路彻底中断。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取尉氏(汴州属县),围郑州。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12]7338。之所以开凿上津路,此因正常情况下,如汴宋道绝,漕路须转由江汉,经行陕虢西南,西入汉中。建中三年,李希烈平山南梁崇义后,虽从襄州撤离,但却屯兵邓州。邓州落入李希烈之手,使得中央不仅丧失了南阳盆地,且阻遏了重要的陆运通道——武关道。运路因是改道,即由襄阳溯汉水而上,取道上津。故建中四年(783)正月,德宗诏陕虢治上津山路,以打通运道[20]1249。开凿上津道的关键,在于陕虢镇的努力:“初,希烈自襄阳还,留姚詹戍邓州,贼又得汝,则武关梗绝。帝使陕虢观察使姚明敭治上津道,置馆通南方贡货”[16]6437。
当中原沦为战区时,南方漕运线路不得不转由江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为切断唐廷的漕运线路,史朝义分兵东出宋州,淮上战事紧张,江南运道受阻,于是江淮盐铁、租赋、粟帛,乃溯江而上,经由襄阳越汉水,抵达梁洋,陆运至长安。宝应元年(762),肃宗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兼鄂岳镇帅,以总东南贡赋,中央财政得以勉强维持。安史乱后,护卫江汉水运的任务依然艰巨。当中原漕路阻隔时,东南物资常经由江汉,运至汉中,接济关中。中原叛镇因是常着力攻击鄂岳,以求彻底切断江汉漕路,鄂岳镇不得不竭力抵御,《旧唐书·伊慎传》记:“建中末,车驾在梁、洋,盐铁使包佶以金币溯江将进献,次于蕲口。时贼已屠汴州,(李希烈)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黄梅,以绝江道”。在鄂岳将伊慎的阻击下,“贼军大乱,少诚脱身以免,江路遂通”。
其后,为阻断漕路,李希烈令部将坚守鄂岳镇安、随等州,以伺机威胁漕路,不时抄略。《旧唐书·伊慎传》记:第一次,建中时,伊慎兵围安州,“贼阻涢水,攻之不能下。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骑八千来援,慎分兵迎击,战于应山,擒戒虚,缚示城下,遂开门请罪”;第二次,李希烈遣将援隋州,伊慎“击之于厉乡,走康叔夜,斩首五千级。希烈死,李惠登为贼守隋州,慎飞书招谕,惠登遂以城降”。因常受北方藩镇袭扰,鄂岳等长江中游诸镇时有不宁,“今兵食所资在东南,但楚、越重山复江,自古中原扰则盗先起,宜时遣王以捍镇江淮”[16]5767。加之鄂岳地处长江中游,水网密布,江贼甚多:“鄂岳地囊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土多群盗,剽行舟,无老幼必尽杀乃已”[12]7873。为此,为保障漕运等交通线路畅通,鄂岳镇需时时防备、不时打击威胁漕路的盗贼。太和五年(831)八月,鄂岳镇帅崔郾“训卒治兵,作蒙冲追讨,岁中,悉诛之(贼盗)”[12]7873。
在保障漕运的初始阶段,东南藩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线路始发江淮,经由宣歙镇,其因此负有保护漕运职责。长庆二年(822)七月,江淮旱,漕河水浅,转运司钱帛委积不能漕,宣州将王国清怂恿士卒哄抢物资,激州兵谋乱。《旧唐书·窦易直传》记:“先事有告者,(宣歙观察使窦易直)乃收国清下狱。其党数千,大呼入狱中,篡取国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楼谓将吏曰:‘能诛为乱者,每获一人,赏十万’。众喜,倒戈击乱党,并擒之。国清等三百余人,皆斩之”。可见,除打击匪贼劫掠,当镇军将见财起心,也是防范的目标之一。
两浙是南方藩镇物资汇集地,又是漕路起点,保护漕运线路和物资安全责无旁贷。建中时,李希烈陷汴州,两浙节度使韩滉遣裨将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以劲卒万人进计,次睢阳,而贼已攻宁陵,栖耀等破走之,漕路无梗,完靖东南,滉功多”[16]4435。德宗播迁梁州后,令李晟、马燧、浑瑊等集兵收复长安,诸军“屯渭北,滉运米馈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贼不能剽”[16]4435。两浙及时、安全地将物资转漕长安,协助中央平叛,对延续唐廷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咸通五年(864),懿宗调兵镇压南蛮叛乱。湖南、桂管等诸镇是漕粮经由之地,其多次出动吏民协运:“西戎款附,北狄怀柔,独唯南蛮,奸宄不率。侵陷交趾,突犯郎宁。骚动黎元,疲力飞輓。如闻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凋伤转甚,宜有特恩。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与置本钱”[22]。漕粮经过当道时,一方面藩镇要集中人力协助转运;另一方面,自要派兵确保漕运线路和物资安全。因此,对诸镇的勋劳,中央赐钱饷馈,以示褒奖。
代宗时,李勉为江西观察使,署李芃为判官。《旧唐书·李芃传》记:“时宣、饶二州人方清、陈庄聚众据山洞,西绝江路,劫商旅以为乱。芃乃请于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谋。李勉然其计,以闻,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阳、饶州之至德置池州焉”。江西通过增置州郡的方式,增强当镇防御力量,保证了江路畅通。建中时,李希烈反。为保护江西和漕运,湖南观察使李皋调任江西节度使,多次与李希烈发生激战。为遏制李希烈占据江淮,切断漕运源头,江西镇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次,李皋与李希烈隔江而战,大败之。“会与贼夹江阵,皋勉慎立功,以所乘马及其铠赐之,使将先锋,斩贼数百级,乃免”;第二次,夺取李希烈蕲、黄二州。“皋声言西取蕲,引兵舰循崖溯江上。皋遣步士悉登舟,顺流下,攻蔡山,拔之。间一日,贼救至,遂大败,乃取蕲州,降其将李良,平黄州,兵益振”;第三次,驻防永安,打通江道。“天子狩奉天,盐铁使包佶为陈少游所窘,以运艚溯江,次蕲口,希烈使杜少诚将步骑三万将绝江道,皋遣伊慎兵七千御于永安,走之。以功进工部尚书。帝驻梁州,皋之贡助相望”。因打退李希烈的多次进攻,史称李皋“西道出九江,至大别,皆与贼接,皋转战数千里,饷路遂通,江汉倚皋为固”[16]3580。
史念海先生认为唐代漕运高潮为玄宗时,元和后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化,西入关中漕运量渐少[23]。如“(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16]1365,较之贞元时,年运江淮米最高七十万斛[24],数量仍有大幅下降。但对其原因,史先生并未指明。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指出:“唐中睿以后,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25]。玄宗时西北边兵甚多,自需漕运大量粮食入关。此后,随着吐蕃、回鹘的逐渐衰落,西北边患渐轻,屯兵不多,所需漕粮自然减少。建中时,出于平叛和收复关中的需要,大量漕米西入关中。宪宗平吴蜀河朔,只需将漕粮直输战场即可,无需入关。此后历朝,战乱虽多,但主战场不在关中,所需漕粮更无需西运关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唐后期政治和经济依赖中心的分离,使漕运成为中央政治统治的根本。漕运不仅维系关中政治集团的运转,而且是应对各种战事的物质后盾。宋人张方平《乐全集》称:“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26]。漕运对整个国家的稳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唐人吕温也说:“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而食”[8]4745。
三、结语
唐后期,中央“以江淮为国命”[8]3390,淮南、两浙、襄、邓、徐、蔡等“江淮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27]。其原因在于:“吴、越、闽、蜀之田,在古为瘠薄,在今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莫如吴、越、闽、蜀。其一亩所出,视它州辄数倍”[28]。加之江淮水网密布,便于运输,故“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29]。诸道通过漕运资粮西入关中,虽无兵兴之际运量那般大,却是源源不断的。唐末大乱,中央威权不行,中原藩镇多有首鼠两端者,但南方诸镇直至唐亡前,大都贡献不断。中原虽然纷扰,南方漕运通过江汉路线,并未完全受到阻隔。为此,对境内漕路等交通线的保护,也是经由诸镇职责所在。漕运关系国计,又因地方形势的混乱,对漕运线路构成了威胁,因而保卫漕运是诸镇的重要职责。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动乱后,唐王朝却依然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其中原因多样。相关诸镇对中央赖以生存的漕运线路保护的基本得力,应是其中原因之一。
[参 考 文 献]
[1] 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429-430.
[2] 史念海.三门峡与古代漕运[J].人文杂志,1960,(4):35-47.
[3] 潘鏞.中晚唐漕运史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1):16-22.
[4] 吴立余.略论元和初期李巽的盐法漕运改革[J].清华大学学报,1986,(2):87-97.
[5] 吴琦.“漕运”辨义[J].中国农史,1996,(4):65-66.
[6]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786.
[7]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204.
[8] 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9]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93.
[10] 王应麟.玉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1] 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3] 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248.
[15] 杨希义.略论唐代的漕运[J].中国史研究,1984,(2):53-66.
[16] 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74.
[18] 王应麟.困学纪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07.
[19]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71.
[20] 王溥.唐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1]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0:380-382.
[22]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10.
[23] 史念海.河山集[M].北京:三联书店,1963:208.
[24]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518.
[25]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4.
[26] 张方平.乐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25.
[27] 权载之.权载之文集[M]. 上海:上海书店,1989.
[28] 章汝愚.群书考索续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236.
[29]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9.
——从2018年高考全国卷Ⅰ第25题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