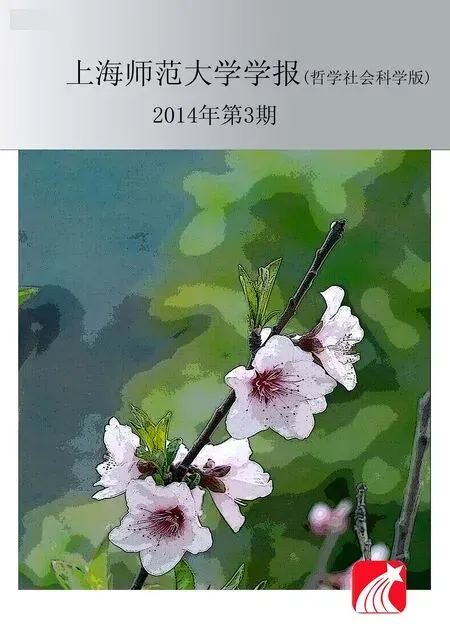六朝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探测
张剑光,邹国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编辑部,上海 200234)
城市是人口聚集密度较高的区域。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因而官员和军人众多,为官府劳作的各色服役人员也很多。城市生活的安逸使很多人居住到城市中,或是为了寻找个好职业和好生计,或是跟随家人到城市定居,或是到城市里追求奢侈生活。无论是都城还是州郡城、县城,都是人们追求舒适生活的好去处,因而六朝江南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
对城市人口有一个准确的估量,将十分有助于认识城市的发展水平,有益于对地区经济的研究。以往的研究一般注重整个地区的人口数量,而缺乏对城市人口的推测,因而要么对城市人口数量估计过高,拔高了对城市的认识,要么不太注意城市人口的数量,而将一郡或一县的人口当成郡城或县城的人口。那么,六朝江南地区的城市人口到底有多少?
本文所说的江南,指六朝扬州的东部地区,大致以丹阳、宣城、吴、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义兴、晋陵等郡为研究范围。
一、东吴城市人口数量的探测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江南地区动荡不定,居住在城市中的普通百姓数量减少,比如一些郡城中的人口数量最多只有万余人。孙坚季弟孙静之子孙瑜初领兵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瑜虚心绥抚,得其欢心。建安九年,领丹杨太守,为众所附,至万余人”。[1](卷51《吴书·孙瑜传》,P1206)这里的江西人,实指长江以北的人士。汉末,丹杨郡的人口有万余人,但这万余人恐怕不太会全部居住在郡城中,有些人可能居住在郡城周围的农村地区。
东吴建立,政局稳定后居住在城市的大族和普通百姓开始增多。比如江东土著大族和南来的北方大族,有不少人住进了城市。陆机《吴趋行》说:“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2](《晋诗》卷5,P664)吴郡在东吴前期曾作为都城,因而是人口较多的一个城市。根据陆机的说法,吴郡所属各城几乎都有大族生活,当然吴郡城里的人最多,除通常所说的顾、陆、朱、张四大姓外,还有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所谓的八族。这些大族在孙吴政权中担任高官,如顾雍、陆逊曾贵为丞相。除本地大族和百姓进入城市外,东吴初期十分注重人口的增加,想尽办法招徕。如孙策时,周瑜攻破皖城,把原属袁术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掠回江东。[1](卷46《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志》,P1108)这些百工、鼓吹,估计全部是为官方服务的,被安排在城内居住。因为吴郡当时为首都,这批人中的绝大部分应该是定居于吴郡城内。其次,战乱导致大量北方人口来到江南,不少中原士大夫生活习惯后也乐于在江南定居,孙吴政权中的大臣张昭等就是由北方带家族迁入吴地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定居于城内。当然,吴郡城内究竟有多少人口,今天恐怕很难准确推算,但一城有近10万人是可信的。
再如稍后东吴迁都建业,都城建业的人口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孙皓建衡二年(270),建业“大火烧万余家,死者七百人”。[1](卷48《吴书·孙皓传》,P1167)按一家5口人计,一场火灾建业城内受灾的人就达5万人左右。当然,这万余家肯定不是当时居民的全部,整个城区内的居民也肯定会有数个万家。
县城人口数量,东吴应和汉代相差不多,或者更少。汉制,万户以上设令,不满万户设长,大县设尉2人,小县设尉1人。西汉时丹徒县是东南地区的大县,户口应在万户以上。1980年在丹徒镇医院附近金家山西汉墓葬中出土一方“丹徒右尉”铜印,证明汉时丹徒县设置了左右两尉,属万户以上的大县。[3](P21)不过这里说的1万户并不全是在丹徒城内。东吴建立后,县仍分为大、小二等;江南大县较少,一般都是小县。大县有山阴、乌程及后来从小县升为大县的上虞、剡县等,而比如钱唐、海盐、富春、永兴、诸暨、余姚、太末、永宁、松阳等皆为小县。
孙权赤乌五年(242),有户52万3千,男女口240万。[4](卷14《地理志上》,P414)西晋灭东吴时,“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后宫五千余人”。[1](卷48《吴书·孙皓传》,P1177)根据平均计,每郡有户12163,口53488;每县有户1671,口7348。按这个数字推算,江南的县大多是不过万人的小县。至于居住在县城中的人口,按平均计算,估计不会超过2、3千人。当时每郡有县7个左右,就算郡城所在县人口最多,但一郡才5万多人口,郡城所在县也无非就是1、2万人。至于郡城内的人口,估计也就数千人至1万人左右。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州、郡、县户口一般就是城市的户口。[5](P42)笔者认为,当时的农业人口有不少确是居住在城市中或城市周围,但认为农业人口全部居住于城市可能性并不很大。如汉末贺齐守剡县长,县吏斯从为奸,贺齐斩之,斯从“族党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贺齐率吏民击破之。可知斯从一人在县城为吏,而全族千余人都住在农村。再如建安十六年(211),吴郡“余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贺齐出讨,“即复破稚”。[1](卷60《吴书·贺齐传》,P1379)这数千名的越贼,就是居住在余杭城外的农民。钱唐人全琮,“经过钱唐,修祭坟墓……请全邑人平生知旧、宗族六亲,施散惠与,千有余万,本土以为荣”。[1](卷60《吴书·全琮传》注引《江表志》,P1382)全琮人在外面为官,全族居住于农村。从这些史料来看,当时的一些官员以农村为根据地,政治上如遇颠簸或退职,就回到农村老家,城市并不是终身养老的地方,他们的家人大都是经营农业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将一县或一郡的户口都算作城市户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将户口数的一半算作城市户口,可能已是很高的估算了。
东吴时期,州、郡、县人口的数量很难有个明确的数字,人口数量时常发生变动。由于人口流动频繁,使江南部分郡、县的人口数量起伏较大。北方迁来的很多人会住进城市,比如会稽郡、吴郡是当时较为热门的城市,城市居民的数量上升较快。东汉末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6](卷76《循吏·任延传》,P2460~2461)东汉末年社会动乱,北方人避难来到南方,会稽地区是较为集中的。王朗任会稽太守时,为孙策攻逼,“虽流移穷困,朝不谋夕,而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著”。[1](卷613《魏书·王朗传》,P407)史书谈到许靖曾南依扬州刺史陈祎,后来祎死,“吴郡都尉许贡、会稽太守王朗素与靖有旧,故往保焉。靖收恤亲里,经纪振赡,出于仁厚”。[1](卷38《蜀书·许靖传》,P963)许靖在江南的活动路线是先到扬州,然后到达吴郡,再到达会稽,而且他是和整个家族的“亲里”们一起来到南方,人数不少。再如桓晔“到吴郡,扬州刺史刘繇振给谷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后东适会稽,住止山阴县故鲁相钟离意舍,太守王朗饷给粮食、布帛、牛羊,一无所留”。[6](卷37《桓荣传附桓晔传》注引《东观记》,P1260)由此可以看出,许多北方人都是将扬州、吴郡和会稽作为重要的避难地,往往是举族从扬州迁到吴郡和会稽。王朗、许贡、刘繇振等收容的北方亲旧,一般而言是跟随他们居住在城内,或者也有可能居住在城市的周围,一旦发生战争,可以马上撤进城内获得保护。就连一些县城中也来了不少北方人,如鲁肃带了族人300余人随周瑜来到江东,留家曲阿,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下子人气十足。大量北方人迁入,固然是使城市人口数量变动较大的缘故,而他们后来的迁出同样会使城市人口数量起伏不定。如北方迁到吴郡和会稽的人中,有一些后来返回北方,有的迁到了其他地方。如桓晔后来从会稽“浮海客交趾”,许靖也是“走交州以避其难,靖身坐岸边,先载附从,疏亲悉发,乃从后去”。因此,郡县人口的流动性极大,后代很难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数字,只能作大体的估算。
二、东晋南朝建康人口数量的探测
东晋南朝时期,关于城市人口数量的记载多了起来,为我们弄清江南人口的实际情况带来很多方便。作为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无疑是江南最大的城市。建康城内究竟有多少人口,一直是学术界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而且在具体表述上各不相同。
建康人口最直接的资料一般认为是《通鉴》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胡三省引《金陵记》中的一段话:“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余户,西至石头城,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岗,北国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其实稍早的《太平寰宇记》卷90《昇州》也引用了这段话,所以该书的确是记载了梁代都城中有28万余户。以这条资料为准,学术界推算出了建康城的口数。不少学者认为建康城的户口应该在140万左右。如罗宗真认为:“以建康为代表的商业城市的兴起,其周围有许多市场,贸易来往,舟船车辆云集,人口集中,最盛时达一百四十万左右。”①再如许辉等认为:“按一户5口计,梁时建康人口超过140万,不仅是南方最大城市,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确切人口数逾百万的大城市。”[7](P367)刘淑芬也持这种观点。[8](P135)同样以每户五口计,任重等认为建康的总人口为120万。[5](P42)更有学者认为总人口近200万。②
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唐代方德远《金陵记》记载的28万户的数字来自何处、有多少可信度,我们对这个数字多少是有点半信半疑的。比如,据《宋书·州郡志》记载的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各州郡户口数字,其时扬州10郡80县共有户143296,口1455685;南徐州17郡63县,共有户72472,口420640。这187万多人口分布的地区,实际已经超过了本文谈论的“江南”范围。建康所在的丹阳一郡8县,只有户41010,口237341。所以,如果单单以一个建康城计,户口是否真有28万余户,可能还需新材料的发现。其实,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种现象:建康城东晋初年只有4万户左右,而梁代急增至28万,短短200年左右的时间里增长了6倍。而同时期北方最大的都会城市洛阳的人口不过10万9千余户,尚不及建康的一半。[9](P167)从宋大明八年到梁太清三年(549),85年的时间人口这样突飞猛增,尽管存在一些其他的人口增加因素,但我们多少还是有点疑虑的,在推测建康户口时可能应有所保留,毕竟单凭《金陵记》一条资料来说明问题是不够的。
不过,六朝首都建康的确是江南第一大城市,城内户口众多,我们从以下资料中可以窥视一斑。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庚寅夜,涛水入石头。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江左虽有涛变,未有若斯之甚”。[10](卷33《五行志四》,P956)按这里的说法,单单贡使商旅的船只就有“万计”,虽不一定能够以实计算,但假如一船以8至10人计,江边的使者和商人就有近10万人。史书云,建康居民中,“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11](卷31《地理起下》,P887)商人数量众多应该是事实。
再如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时,渡江攻破建康,进围台城,前后相持130余天。台城被围之初,城内男女10余万人,甲士2万多人,米40万斛。至城破时,战死及饥饿疾疫而死者十之八九,“横尸满路,不可瘗埋”。[12](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条,P5008)台城只是梁朝的宫城部分,其中的人口是整个建康城的一小部分。对建康城来说,经过侯景之乱,“道路隔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那些“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金陵记》也说陈都建康时,“中外人物不迨宋、齐之半”。从这些话来推断,梁朝建康城内有数十万人不为过,退守台城的10万男女可能只是当时的士大夫和贵族,属于城市居民中的上层,一般的城市居民在侯景攻进建康时早就作鸟兽散,各自往他处逃难避祸了。
建康城内还有许多不计算在户籍中的人。如郭祖深向梁武帝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民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甚半。”[13](卷70《郭祖深传》,P1721~1722)关于梁朝寺庙,张承宗引沈曾植《南朝寺考序》引《释迦氏谱》说,梁朝有寺2846所,而建康都城地区有七百寺。[14](P99)郭祖深为了说明佛教对社会的危害,难免夸大,说户口的一半“不贯人籍”并不见得能据实统计,但他说的寺庙数量和“僧民十余万”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因此,今天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地推测出建康城的人口数量,但从泊在江中的商人10万、僧尼10万、台城有12万等数字来讨论,说六朝都城建康最高峰时人口有近百万,恐怕并不为过。
三、东晋南朝州郡城人口数量的探测
两晋时期,江南地区位于扬州管辖之内。不过扬州在都城建康附近,从其规模来看扬州的户口不是很多,城内主要是一批官方的行政人员。扬州辖丹阳、宣城、毗陵、吴郡、吴兴、会稽、东阳、新安、临海等郡。从西晋太康元年(280)的户口来看,各郡一般在数万户左右,如丹阳户51500、宣城户23500、毗陵户12000、吴郡户25000、吴兴户24000、会稽户30000、东阳户12000、新安户5000、临海户18000。除了丹阳和新安两郡较高或较低外,一般都是在30000~12000之间,20000多户的则占了多数。倘按每户5口计,每郡人口在10万左右。不过这个数字不是郡城内的口数,因为一般郡都有10县左右。扣除各县的平均数,郡城所在地的县就算户口最多,也不过只有数千户。因此,从两晋时各郡的户口数字推测,一般郡城内的户口估计也就万人左右,大的郡城估计不会超过2万。
东晋孝武帝时范宁疏云:“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4](卷75《范宁传》,P1986)因为其时郡县出现了滥置的现象,所以胡阿祥认为“按事实上五千户之郡、千户之县,在当时已属大郡大县”。[15]至南朝时,政区开始变得繁杂参差。《通鉴》卷一三五建元二年胡注曰:“有寄治者,有新置者,有但郡、僚郡、荒郡、左郡、无属县者,有或荒无民户者。郡县之建置虽多,而名存实亡。”侨州郡县大量出现,“上淆辰纪,下乱徽甸”,[10](卷82《周朗传》,P2098)一般都是“散居无实土,官长无廨舍,寄止民村”。[16](卷14《州郡志》,P256)其时江南地区在扬州和南徐州的行政辖区内,其中扬州辖区内江南有丹阳、会稽、吴郡、吴兴、宣城、东阳、临海、永嘉、新安9郡,南徐州辖区内江南有南东海、晋陵、义兴、南兰陵4郡。宋大明八年(464),上述各郡户数相差较大,其中满2万户的有丹阳(41010)、会稽(52228)、吴郡(50488)、吴兴(49609),超1万户的有宣城(10120)、东阳(16022)、新安(12058)、晋陵(15382)、义兴(13496),不满1万户的有临海(3961)、永嘉(6250)、南东海(5342)、南兰陵(1593)。与西晋太康年间相比较,户数一般都翻了一倍。因此从郡城的角度来说,户数估计也翻了一倍。不过江南各郡由于户数相差很大,必然会造成郡城内的居民数量也相差很大。如超过2万户的数郡,郡城内人口超过2、3万是有可能的;户数在1万户左右的郡,估计郡城内有万人左右的规模;至于不满万户的数郡,郡城内也就数千人而已。下面可以几个州郡为例来说明当时江南大城市中容纳的人口数量。
南徐州的州治在京口。汉末建安十四年(209),孙权自吴郡迁到丹徒,称该城为“京城”。建安十六年(211)迁都建业后,这里改为京口镇,“吴时或称京城,或称徐陵,或称丹徒,其实一也”。永嘉之乱后,北方人过江,“多侨居此处,吴、晋以后,皆为重镇”。晋咸和中,这里成为侨徐州的理所,后改为南徐州。[17](卷25《江南道一》,P589~590)原来的一个县城,至东晋南朝时,城市地位大大提高,变成了一个州城,成为建康以东的地区性政治中心。
京口的户口数从东晋开始剧增。郗鉴平定苏峻叛乱后,“遂城京口”,被封“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4](卷67《郗鉴传》,P1800)京口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起来。其时北方移民大量来到京口城,如祖逖率亲党数百家南渡后,居京口。[4](卷62《祖逖传》,P1694)徐邈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4](卷91《徐邈传》,P2356)官府曾在南徐州和南兖州两地侨民中召募兵士,称为北府兵,如祖籍徐州彭城、侨居京口的刘牢之后来成为北府兵大将。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刘裕在京口联合一批北府兵中下级军官如刘毅、何无忌、魏泳之、刘穆之、孟昶等人,及从者百余人,在京口起兵,说明京口驻扎着大量的军队。这批起兵的将领,大多是侨居京口的北方人,如刘裕家在丹徒县京口里。南朝时,南徐州成为北方南下移民的主要集中地。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来到丹徒,在《幸丹徒谒京陵诏》中称赞:“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衿带江山,表里华甸,经涂四达,利尽淮海,城邑高明,士风淳一,苞总形胜,实唯名都。”他又谈到“顷年岳牧迁回,军民徙散,廛里庐宇,不逮往日”,人口数量比东晋时有所下降,所以“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给以田宅,并蠲复”。[10](卷5《文帝纪》,P97)宋文帝下令迁百姓到京口落户,充实刘宋皇室的桑梓故里。这“数千家”的百姓,应该有2、3万人口的数量。萧子显说南徐州:“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16](卷14《州郡志》,P256)南徐州的人才多聚于京口,如檀道济、刘粹、孟怀玉、刘康祖、诸葛璩等都是北方人侨居于此。
罗宗真认为至刘宋时期,北方南迁人口达90万,“其中在江苏省最多,侨民约有二十六万,仅南徐州就有二十二万,占侨民总数的十分之九。而当时南徐州总人口才四十二万余,侨民就比本土旧民超出了二万多”。[18](P6)这一观点实际上见于谭其骧对当时移民的估计。谭其骧认为,永嘉乱后至刘宋初,南迁流民为90万人,占刘宋全境人口的1/6。其中江苏接纳移民最多达26万;而南徐州有侨口22万余,几乎占全省侨口的9/10,并且超过了当地人口,“所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则品质又最精”。③至于北方人有多少定居于京口城内,可以从宋大明八年的户口数中分析。南徐州42万人中,以郡为单位,晋陵和义兴的户口最多;丹徒县所在的南东海郡,共有口33658。南东海郡有6县,就算人口的一半归丹徒县,城内的居民数量恐怕也不到2万人。也就是说,当时大量的移民实际上并不全聚集于京口城内,而是定居于南徐州太湖西北部沿长江一线的广大区域。
不过,说京口城内只有2万不到的居民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城内有大量的军队,有州、郡、县三级官方行政人员,如东晋精锐的北府兵就驻扎于此。太元四年(379)二月,东晋曾派万余北府兵援救彭城,抵挡前秦的进攻。六月,谢玄与田洛帅北府兵5万败秦军于盱眙。太元八年(382)淝水之战,东晋用于淝水之战的军队共计8.5万人,其中有胡彬水军、谢琰“台兵”、桓伊西府兵,还有桓温部将檀玄所部,实际参战北府兵有5万左右。[19]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北府兵,兵力最盛时有士兵约5万多人。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北府兵在战争中有可能有其他军队的加盟,二是即使这支5万余人的部队平时驻扎在京口,也不见得都是住在城内。据此,可以认为,如果以这支部队的一半驻在城内、一半驻在城外估计,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京口城内的人数大概在4万到5万人左右。
会稽郡是扬州境内户数最多、口数第二的大郡,是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会稽郡治在山阴县,所以习惯上说的山阴县户口包括了郡城和山阴县的农村两个部分。关于会稽郡城的户口数,通过资料也可以作一些大致的了解。如史称:“海西公太和中,郗愔为会稽太守。六月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灭。”[4](卷27《五行志》,P806)会稽城遭受火灾,烧毁居民数千家,说明火势很猛,烧毁的民户数量很大,但同时也说明这数千家根本不是会稽城内居民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所以会稽城内的居民有1、2万户完全有可能。
东晋南朝时大量北人南迁,会稽郡由于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得到北方人的青睐,成了移民的重要居住地。西晋太康元年,会稽郡户30000,是除都城建康所在的丹阳郡以外的江南第二大郡。[4](卷15《地理志下》,P461)此后100多年间,会稽人口一直呈上升之势。到刘宋时,会稽郡户55228,超过丹阳郡。从会稽郡治所山阴县的户口中,也可以大致推测出郡城内的户口。元嘉十七年(440),山阴县“民户三万”,[10](卷81《顾恺之传》,P207)一县的户数已等于西晋整个会稽郡的户数。刘宋时会稽郡的平均每户口数为6.66,那么3万户就是199800口。假如人口的一半居住在郡城,估计会稽城内有居民10万人。再加上郡城内的官员、军队和流动人口,会稽城有10至11万人应该说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四、东晋南朝县城人口数量的探测
西晋建立后,曾规定“县千户以上,州、郡治五百户以上为令”,不满此数的为长。县有大小,大者满千户,小者不到千户。东晋孝武帝宁康年间,任余杭县令的范宁在陈述时政时曾指出:“今荒小郡县,皆宜并合,不满五千户,不得为郡,不满千户,不得为县。”[4](卷75《范宁传》,P1986)按照他的说法,当时满千户的县应该是大部分。
南朝宋大明八年,扬州和南徐州位于江南地区的各郡,平均统计,县均户数不满一千的只有临海(792)、南东海(890)、南兰陵(797)。后两郡因与当时的侨置有关,所以户数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真正县平均不到一千户的只有临海郡。江南各郡所属县的平均口数,丹阳为29680、会稽为34784、吴郡为35384、吴兴为31601、宣城为4797、东阳为11999、临海为4848、永嘉为7337、新安为7331、南东海为5609、晋陵为13357、义兴为17896、南兰陵为5321。考虑到郡城人数统计时是以总人口的一半来计算的,县城集聚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要低。假如我们以一县人口的四成作为县城人口数,那么江南大县县城中的口数,如吴郡各县平均为14153,会稽各县为13914,吴兴各县为12640;江南小县县城中的口数,如宣城各县平均为1919,临海各县平均为1939。由于一郡中各县的口数实际上不是一样的,所以一些大县的人口应该更多,如吴郡、会稽、吴兴等郡有的县城可能会达到2万人;一些小县县城中的人口数会更低,如宣城、临海有的县城可能连1500人也不到。同样是在江南,县城人口数量差别是很大的。
会稽郡余姚县,按郡平均数计,西晋太康年间有3000户,估计口约1.5万至2万之间;南朝刘宋大明年间,有口34784。不过,要判定余姚城内户数的实际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早在东晋咸康初,山遐做余姚县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4](卷43《山遐传》,P1230)山遐到任80天,查出私附1万余人,虞氏豪门竟占1/3。[20](P54)私附的情况,可能在农村地区比较厉害;城内也会有,但可能比较少。同时也可以知道,由于城市提供百姓就业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一般民众居住于农村,或依附于大族,聚居在城市的四周。《梁书》卷53《沈瑀传》谈到余姚虞氏大族千余家,“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这上百、数千大族,人数很多,估计不会少于1万,但这些人同样不是全部居住在县城内。虞氏家族“世贵盛,多开第宅”,在县北筑城而居,后代沿称“虞氏城”,遗址至今犹有残存。《嘉泰会稽志》卷3《余姚县》说:“沈瑀,字伯瑜,武康人,为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瑀以法绳之。又县南豪族子弟纵横,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小者补县佣,权右屏迹。”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县城里当差,可能居住于城南的郊区。对大族来说,居住在城市边,可以到城内当差出仕,经营商业也方便,战时可入城,平时过着依山傍水的生活。因此,可以认为在像余姚这种大族较多地居住在县城的周围,并且与县城内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居住在城内大体是有可能的。换句话说,南朝余姚城内的人口,大约在1.5万至2万之间。
不过,江南大多数县城中的人口达不到余姚的规模。如东晋时何琦为宣城泾县令,“及丁母忧……停柩在殡,为邻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计无从出,乃匍匐抚棺号哭。俄而风止火息,堂屋一间免烧”。[4](卷88《何琦传》,P2292)县城里人员稀少,县令即将被大火焚烧,也不见有人来扑救。县衙即使被烧,这里也说只是堂屋一间,所以整个县城给人十分冷落的感觉。再如新安郡建德县,“旧经载,晋太康户三百四十七,宋志户五百七十而不载”。[21](卷2《户口》,P4319)就按五百七十户计,平均按每户6人,也只3420人,更何况这3千余人不可能全部居住在县城中。倘按一半计,建德县城的人口仅1700人左右。再如清溪县,“旧经载,晋太康户六百二十六而不载”。[21](卷3《户口》,P4334)同样按一户6人计,清溪县(即始新县)仅有口3756;以一半居民在城内计,清溪县城的人口不到2千。
显然,六朝时期的江南各个县城,人口数量的差别很大,城内居民多的达到1、2万人,少的只有1、2千人。
五、六朝城市人口数量增加的原因
总的来说,从东吴至两晋南朝,江南各城市人口呈不断增加的态势。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功能的完善,城市中的人口不断增多。六朝江南既有人口近百万的都城建康,又有人口数万至10万左右的京口、会稽等州郡城。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恐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政府用行政手段将人口迁入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如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幸丹徒,谒金陵,大赦。三月乙丑,诏曰:“京口形胜,实为名郡。顷年岳牧迁回,军民徙散,廛里庐宇,不逮往日。皇基旧乡,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给以田宅,并蠲复。”[22](卷20《杂录·郡事》,P838)一道命令就将数千家老百姓迁到了京口城中。
2.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为老百姓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加速了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六朝江南城市商业活动越来越活跃,随着贩运商贸的发展,各个城市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江南许多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不再局限于本州郡或本县范围内简单的互通有无,而是在整个江南地区已初步形成市场销售网络。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服务业依托了城市发展而兴起,从传统的商业中分离出来。服务业是城市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一样,呈现出繁盛的景象,城市手工业种类众多,造船、纺织、铜器制造、制酒等各具特色。由于六朝中央政府在江南,因而城市手工业中官营的那部分所占份量较重。此外如外贸业、高利贷业、运输业等,对江南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城市的经济结构,推动城市经济产业的多样化、多层次,使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加强,为城市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3.北方人口大量迁入江南城市。从汉代开始,北方人迁入江南的渐渐增多。孙策占据扬州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1](卷13《华歆传》,P402)建安十四年(209),曹操“欲徙淮南民”至谯,消息传出,“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1](卷14《蒋济传》,P450)避乱到江东的人中大多是官僚或豪强地主,他们迁徙时往往携带大批部曲、奴婢和百姓随行。《三国志·吴书》及裴松之注中,北方人来到吴地并且有北方籍贯记载的有70人左右。西晋以后,江南地区曾有多次大规模接纳北方流民的高潮,“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4](卷65《王导传》,P1746)永嘉之乱后,北方流民相率过江,不少人在京口、晋陵境内定居。如东莞姑幕人徐澄,“率弟子及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4](卷91《儒林传》,P3356)此后如晋成帝时,苏峻、祖约之乱引起北人南侵,“民南渡江者转多,乃在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10](卷35《州郡志一》,P1034)东晋及南朝设侨州郡县管辖南来人口,其中以京口和晋陵最多,两地有侨置的郡16个、县60个。江南其他地区,如太湖周围的吴兴、吴以及浙东5郡,没有侨置,但也吸纳了大量的北方移民。这些北方移民,主要分布在会稽、吴兴和吴郡的余杭、钱唐、海盐、由拳等地。流寓会稽的北方士人,大多趁到会稽任官之机举家迁居。如以会稽太守身份到会稽的许归和庾琛,寓居于郡治所在地。东晋以后,大量的文化名流来到会稽,高僧名士云集。再如吴兴郡云集了许多江淮流人,如郭文在王导西园居住七年后,逃归临安,结庐于山中,临安令万宠迎至府中。东晋隆安年间(397—401),谢邈为吴兴太守,侄儿谢方明跟着来到吴兴,邈舅子长乐人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也俱往吴兴投邈。北方人大量来到南方,一部分分布在江南的农村地区,但也有很多居住在城市内,使得江南城市的人口激增。
4.城市中或者城市周围常出现聚族而居的现象,使得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增加。如宣城边洪,后来发狂,“绞杀两子,并杀妇,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创,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殡亡者”。[4](卷95《韩友传》,P2477)同族人家出了事情,族人会相互帮忙处理。南朝刘宋刘怀慎迁护军将军,“禄赐班于宗族,家无余财”,[10](卷45《刘怀慎传》,P1375)他为官时与同宗族关系密切。南齐崔慰祖,“家财千万,散与家族”,[16](卷52《崔慰祖传》,P901)整个家族和他可能一起居住在城市中或城市周围。城市和农村关系紧密,不少人就将从城市中得到的经济收益转移到农村,要么分给同宗,要么购买土地。魏晋前期, 一般人常常聚族居住在城市的周围,所以城内和城外的人关系紧密,宗族中的杰出人物随时会到城内任职,退职就回到农村。东晋王敦叛乱,王含、沈充等攻逼京城,虞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4](卷76《虞潭传》,P2013)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到城市居住还是回到农村。聚族而居的习惯,使一部分人一段时间进入城市,一段时间又回到农村,城市和农村之间人口的流动变得十分普遍。
当然,六朝江南城市人口不是直线增加,由于受到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也常会发生一些户口减少的状况。如孙恩起义结束后,“三吴大饥,户口减半,会稽减什三、四,临海、永嘉殆尽,富室皆衣罗纨,怀金玉,闭门相守饿死”。[12](卷112晋安帝元兴元年四月条,P3542)不过,由于恢复发展较快,总体上城市户口恢复较快,呈总量越来越多的趋势。
注释:
①罗宗真:《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考古、历史研究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另第27页也称:“那时140万的京师人口,每月至少需粮42万斤。”
②蔡震:《南京市发现建康城壕,千古“台城”之谜渐渐揭开》(《扬子晚报》2007年11月5日)认为:“历载建康城鼎盛时期有28万户、近200万人口,街市热闹繁华,整个城市规整而实用。”200万的推测不知何据。
③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原载《燕京学报》1934年第15期,又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220页。
[1]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 严其林.镇江史要[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4]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任重,等.魏晋南北朝城市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许辉,等.六朝经济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8] 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9] 简修炜,等.六朝史稿[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0]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3]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4] 张承宗,等.六朝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5] 胡阿祥.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3).
[16]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 罗宗真.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考古、历史研究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9] 杨德炳.关于北府兵的兵数与兵将来源[J].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983,(5).
[20] 乐承耀.宁波古代史纲[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5.
[21] 刘文富.淳熙严州图经[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
[22]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