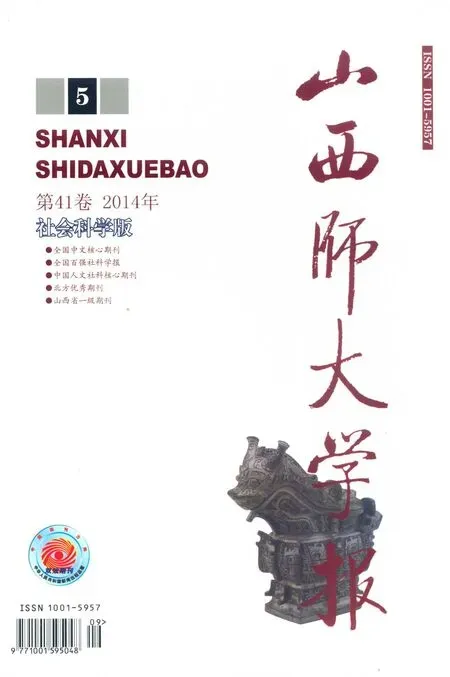《诗经》中的“中+名词”结构
赵国栋
《诗经》一书中,“中+名词”结构因为与现代汉语语序之间的差异,成为众多语法学者关注的对象。关于这一现象,历来各家看法不一,最早也是最常见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倒文协韵现象,是为了押韵的整齐。其次有认为这是古汉语固有的语序,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邢公畹先生。他谈到“有人认为‘倒植’是一种未尽涤除的草昧未开之世的句法(《章氏丛书》:《检论五·订文篇》所附之《正名杂义》),这种说法是对的,只是限于知识,说得很含混罢了”。另外,还有方有国先生在其有关“所”字结构的论文中,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再次,就是目前最新的一种看法,是徐刚先生在其《论〈诗经〉的“中+名词”结构》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这一结构表示的是“与边缘相对的中间部分”,“中”表示“中间的”、“中部的”、“中心的”,与“名词+中”结构是迥然不同的。从以上几种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其争议的关键有两点:其一、上古汉语中,“中+名词”是否为一种正常的语序;其二、其结构义是否与现代汉语中的“名词+中”结构一致。有关语序问题,事实正像邢先生所讲,“限于知识”,我们很难确定。语序的正常与否,同样存在其可能性。对此,我们作出如下假设:
第一种,我们同意邢先生的观点,认为它是古汉语固有的语序。联系其它现象来观察,古汉语无论在语序还是词序上都存在着不稳定性,同时这种不稳定中又蕴含着一定的惯性,亦即人们在长期的使用中所形成的倾向。当这种倾向、趋势进一步发展,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到最后便作为一种规律确定下来。当然,某一种形式能够占据趋势的主流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确定下来,也必然受到其它相关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能凭空出现。拿“中国”来讲,可能“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对于国都或封国内部进行指称时所用到的词,但它同时也因为与国都相联系而在人们头脑中留下了地位相对重要的印象。后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国之间交流的频繁,人们对于外界认识进一步扩大,他们逐渐对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并且,由于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在生产以及文明上的先进性,在自然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从而也就在各国之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优越地位,于是人们就逐渐给这片为四面边国环绕的土地以一个专名,即“中国”,以与四方荒蛮之地相区别。但它原来的意义在它成为专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也是存在的,不可能立即消亡,只是随着中部与四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上差距的逐步加大,才使“中国”作为专名的优势彻底压倒本义,从而固定下来。于是本义也要求有一个新的词来表示,“国中”就应运而生了。
徐刚先生说:“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所用到的‘中+名词’结构绝大多数是能够用‘名词+中’解释通的,而只有极个别成为专名的,如‘中国’在特定语境中不能够随便加以替换。”这就说明,当时两种结构的结构义已经开始分化,像“中国”这样有特定意义的词的独立转变分化,带动了整个“中+名词”结构系统的变化,“名词+中”格式取代“中+名词”结构,而“中+名词”则只褪变为少数专有名词的格式,或者凝固为一个词,或者只作为文人拟古的一种形式,而从其表示本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格式逐渐消亡了。这便是词汇学中的类推作用,一个词的构成模式发生变化,其影响可以波及到整个同类型的词汇系统,促使整个词汇系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便推动了新的词汇模式的产生和旧的词汇模式的消亡。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渐变而非突变的过程,在整个词汇系统中有的词转变早,有的词转变晚,这便产生了一个相当长的新旧共存时期,所以在意义上不能机械地硬把它们区分开来。
古代汉语中与“中+名词”结构相类似的语序最显著的是“大名冠小名”现象。这种现象,在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和王引之《经义述闻》中都有提及,实际上也就是《荀子·正名篇》中所提到的“共名”加“别名”,这与现代汉语的语序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从现汉的角度来看,同样也可以用“倒置”来指称这种语法现象。但是,“大名冠小名”在上古汉语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在文献典籍中一般可用之于国名、地名、城名、庙号、人名、植物名、动物名等等。从它历时的发展来看,罗绮《〈诗经〉中的“木”字和“琼”字》认为:“时间越早,它使用的范围越广泛。夏代以前几乎是大名冠小名一统天下的时期,……商周两代这一语序又经历过一段和小名冠大名并存、竞争的阶段……大概在秦汉时期小名冠大名语序取得了绝对优势,已经成为主导的甚至唯一的语序,而原来的大名冠小名语序则有三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趋于消亡,另一种是反映古代文化的历史名词保留下来,还有一种是由专指变为泛指,……”另外,从横向角度来看,邢公畹先生《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中就“大名冠小名”现象,也大量列举了台语中的这种用例。而“中+名词”结构虽然与“大名冠小名”并不属于同一语义类型,但从他们的发展历程来看是极为相似的,并且“中+名词”结构似乎可以与台语对限制关系造成的复词的语序相对应比较,在这一类型的复词中也找到了渊源关系。但是,这仅仅是猜测,因为它只是限制关系的一个极小的组成部分,还不能代表全部,毕竟我们还没有发现其它偏正关系的复合词在上古汉语中使用了这样的语序。不管怎么说,这种相似性为“中+名词”提供了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是修辞上的需要。《诗经》中大量存在节与节之间排比复沓的例子,以形成诗歌所特有的回环往复的节奏和气势。从大量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替换部分是动词的除外,绝大多数被替换部分都是前半部分相同而后半部分换一个字或词,如:
一、1)唯叶萋萋。2)唯叶莫莫。二、1)陟彼高冈,我马玄黄。2)陟彼崔嵬,我马虺頹。三、1)遵彼汝坟,伐其条枚。2)遵彼汝坟,伐其条肄。四、1)未见君子,忧心忡忡。2)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五、1)绿兮衣兮,绿衣黄里。2)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六、1)凯风自南,吹彼棘心。2)凯风自南,吹彼棘薪。七、1)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2)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八、1)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公所茇。2)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公所憩。3)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九、1)羔羊之皮,素丝五紽。2)羔羊之革,素丝五緎。3)羔羊之缝,素丝五总。
这样的形式俯拾皆是。“汉语从单音节词为主向双音节词发展的过程中,汉字就以语素的身份出现在词中。作为独立使用的汉字逐渐失去了独立记录词的资格,渐渐担负起构造双音词的作用。与此同时,汉字独立记录语素义的作用仍然存在,因此当汉语韵律对音节有需要时,语素次序的对调和交换使用成为常有的事。”当然,尽管它们在排列顺序上体现出极强的规律性,但毕竟与我们所讨论的“中+名词”情况有别,即它们基本上使用的是正常的语序,而“中+名词”则呈现出我们今天所困惑的顺序。但在诗歌语言这种特定的环境中,似乎很有可能“中+名词”受到其它语序的影响而发生不合于常的变异,这也是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起作用的结果。而对于那些并不处于此种重复结构中的“中+名词”结构,它们的出现大概也可以解释为连类而及。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并且是在诗歌这种语言具有很大灵活性、随意性的语境中,要像在其它同时代的典籍中寻找佐证,往往是不合适的,它们在体裁上缺乏可比性。
另外,我们认为,徐文的论述中存在着以下几点不当之处:
一、《诗经》中存在大量的“中+名词”结构,如果都按照徐文的观点来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很少有句子用到“名词+中”结构,那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地方用到“在……之内”的意义,这在习惯上是讲不通的。“在……之内”这个惯常的、高度抽象的、使用广泛的意义不用,反而大量使用表示某一具体方位的意义,这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讲通,就《诗经》这种体裁而言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诗歌是一种艺术作品,并不要求表义上的高度精确化。
二、作者所提出的指与“边缘相对的中间部分”的意义,不具备解释的普遍性。如:第一,中唐有甓,邛有旨鹝。《陈风·防有鹊巢》。“唐”古为“庭涂”也,为庭中路,“甓”为砖。既然处所是路,那么路中必为砖所在之地,为什么又会特意来强调是路中间呢?这显然有悖常理。第二,中田有庐,疆场有瓜。《小雅·信南山》“疆,界也。场,畔也。”那么,相对于田界来讲,到底应该被看作是“田里”,还是应该看作“田的中间”,就很清楚了。更何况,关于“庐”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庐,寄也。”(《公刘传》)《说文》:“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此即在田曰庐之谓也。关于“庐”的位置,各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在公田中,有认为是“田畔为之,以避雨与暑。”第二种认为“廬”即“盧”字,亦即壶盧。之前郭沫若就曾以“南山有臺,北山有莱”为例,认为:“既与莱对文,而其余数章又都是桑、杨、杞、李等植物名汇,则臺断非亭台楼阁之台。故古时注家即破台为苔,训为莎草,这便与苔为类了。和这同,与瓜为对文,而可剥可菹(摘来做鹹菜)的廬,也必然是假借字。我看这一定是蘆字的假借,《说文》云‘芦,芦菔也’,便是如今的萝菔。中田者田中,‘中田有庐’亦犹‘中谷有蓷’,就是说田当中有萝菔。”由此可见,理解为“田里”比“田中间”更为合适。第三,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小雅·正月》。陈奂疏:薪蒸不能为大木……笺:林中大木之处而维有薪蒸尔。不难理解,树木所长之处为林中,而不必为树林中部,更不必为树林深处。
三、徐刚先生认为“‘中+名词’的这一意义汉代可能已经开始消失了,因此毛传径直以‘谷中’、‘林中’解释‘中谷’、‘中林’这一类结构。汉代人用‘中庭’这个词时,已经开始等于‘庭中’了……可证汉人已不用‘中庭’的上述意义了,这一语法范畴已经消失。”我们则认为恰恰相反,因为无论从汉人对先秦其它古籍的训释,还是从汉代本身的典籍来看,“中+名词”的这种意义反而是日益固定下来了。一部分是从先秦继承下来的那部分已经固定了的词,如“中庭”、“中道”等,一部分是汉代人自己在“中间部分”这一意义基础上所新造的词。当然也还存在着一部分是拟古所作,与“名词+中”结构的意义相同,就像作者所举到的《哀时命》一例。总之,从汉代以后,“中+名词”结构与“名词+中”结构的意义明显分道扬镳,而并不是如作者所说“把‘中庭’当作‘庭中’这一意义来用却一直延续到很晚的时候”,“是在语言结构变化之后的一种‘重新分析’。”但是,我们知道,汉语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复杂走向简单,没有道理本来有“名词+中”结构表示“在……之内”的意思,再增添一个“中+名词”结构来表示同一语义。这两种结构在后代部分并存并表示同意语义,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文人拟古。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排除“在……正中间”的语义存在于“中+名词”结构中。因为“在……中间”与“在……之内”的意义本身就有关联,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引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名词”所代表的结构义也是由前者引申出来的,因为这关系到古代汉语的语序问题,与词本身的意义发展是有区别的。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前一义项很可能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或者是一种特殊用法,因为它在使用的广泛性上是相对有限的,不像后者那样普遍。
徐文所讲的意思可能是“中+名词”结构在开始与“在……之间”所共有的意思,后来为了区分,增强表达的严密性,才从原来的结构中分化出另外一类“名词+中”结构。后代文中许多都属于刻意模仿,因为从汉代郑玄解经的情况看,大概从汉代起就已经不存在“中+名词”结构来表达“在……之内”的意思了,仅仅是为了拟古,文人学者才采用这样的格式,并且与它分化以后的意思混合在一起,因而使人产生错误的联想和假设。
不管哪一种结构出现在前,或者说开始时哪一种语序为常例,哪一种为变例,这是我们现在很难考订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结构当时所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都表示“在……之间”、“在……之内”。
总之,“中+名词”结构在《诗经》中所表达的意义与“名词+中”是一致的。这种结构形式的存在,或者是古代语序的一种残留,而这种语序,很可能是古汉语本身固有的语序。照邢公畹先生的分析,很可能源自于“汉语和台语在原始汉台语中的血缘关系。”或者是由于修辞上的需要,修辞的作用再加上语词的类推,形成了“中+名词”结构。
[1]邢公畹.《诗经》“中”字倒置问题[A].语言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方有国.上古汉语“所”字结构与所字结构再研究[A].上古汉语语法研究[C].四川:巴蜀书社,2002.
[3]徐刚.论《诗经》的“中 +名词”结构[J].语文研究,2004,(1).
[4]罗琦.《诗经》中的“木”字和“琼”字[J].贵州文史丛刊,2003,(2).
[5]邢公畹.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A].语言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