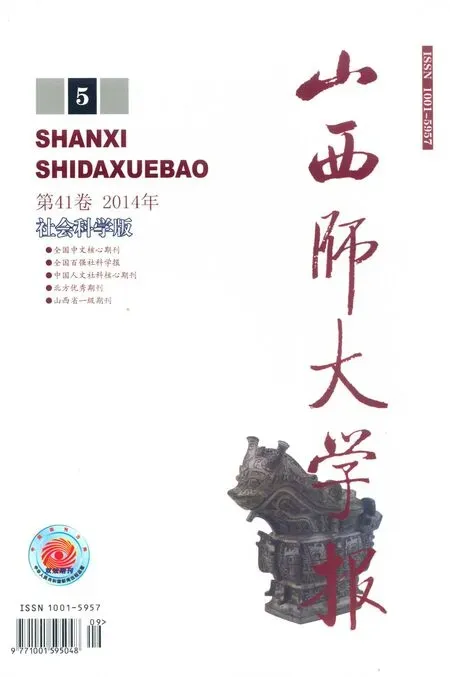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何以可能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合法性解读
陈永盛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875)
在理性的统治下,康德通过批判建构纯粹理性的体系,向形而上学许诺一条科学的可靠道路。一方面,纯粹理性在思辨运用中发动“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革命”使其如愿成功。另一方面,这种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纯粹理性能力自身的批判却恰恰与理性的本质特性相背反,即超越一切可能经验的界限追问绝对的无条件者。因此,康德“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1]BXXX,22。康德认为,这属于纯粹理性实践运用的考察,这种考察“不是看作例如仅仅要用来弥补思辨理性之批判体系的漏洞的插叙(因为这个体系在自己的意图中是完备的),也不是像在一栋仓促建造的房子那里常会做的那样,在后面还安上支柱和扶垛,而是看作使体系的关联变得明显可见的真实环节,为的是使那些在彼处只能悬拟地设想的概念,现在可以在其实在的体现中被看出来”[2]7。可见,在康德那里,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是纯粹理性体系的重要一环,其目的在于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但这种与思辨理性同属纯粹理性的实践理性,其实践的运用何以可能?康德认为只有澄清这个问题,才能确保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具有合法性,否则其仍属理性的僭妄,深陷形而上学无休止的争吵中。
一、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
在传统形而上学中,理性不断地陷入困境,沉溺于不知疲倦的来回摸索,然而,却未能发现一条科学的可靠道路,以致或走向独断论的放纵,或沉溺于怀疑论的绝望。在康德看来,人类理性陷入这种困境并非它自身之过,而是因为人们不加批判就盲目地使用理性。因此,必须对理性进行重新认识,并且把它当作进行哲学思考的首要任务。
“理性”,在康德看来,是全部高级的认识能力,其出自先天原则的认识能力则称为纯粹理性。就其对我们根据先天原则进行判断的能力而言,只要与对象发生关系,就拥有自己的领地。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指出,我们先天地立法的全部认识能力只有两个领地,即自然概念的领地和自由概念的领地。据此,康德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3]KU8因此,纯粹理性根据先天原则来运用以及借这种运用所达到的范围就分为纯粹理性的理论运用(思辨运用)和实践运用,对应的是理论理性(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
理论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的思辨运用,通过自然概念来立法,关心的是单纯认识能力的对象,即存在的一切。其主旨在于考察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追问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对此,康德认为,理论理性的关键在于必须对纯粹理性能力自身进行批判,即对它的可能性和界限进行规定。这种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是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同时,由于理论理性所涉及的对象是自然,与那些能够被提供给知性的对象的知识打交道,所以它“必须从直观、因而从感性开始,但从那里首先进展到(这直观的诸对象的)概念,并只有在预先准备了这两者之后才以诸原理结束”。[2]122
实践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通过自由概念来立法,关心的是意志的规定根据,只针对应当存在的一切。其主旨在于考察我应当做什么,如何达到符合一切道德法则的世界,即道德的世界。对此,康德认为,因为纯粹理性自身就足以对意志进行规定,并且意志自由,因而纯粹理性是无条件地实践的,所以在实践运用中不需要对纯粹理性自身进行任何批判,它只需阐明有纯粹实践理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同时,与理论理性不同的是,由于实践理性涉及的是意志,只在与这个意志及其原因性的关系中考虑理性,只与使诸对象实现出来的能力打交道,因而其无须指出任何直观的客体,所以与理论理性相反,它经原理开始进到概念,再从概念出发进达感觉。康德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运用将纯粹理性进行的二分是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的表达,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并直接影响了后世哲人。
但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两者对立。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同属纯粹理性,是纯粹理性不同兴趣的不同运用,“它的思辨运用的兴趣在于认识客体,直到那些最高的先天原则,而实践运用的兴趣则在于就最后的完整的目的而言规定意志”[2]164。同时,“实践理性并不要求我们反对理论理性已经确立的和能确立的一切东西”[4]308,它们都彰显纯粹理性的特质,即为有条件者寻求无条件者。可见,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结合是先天地建立在纯粹理性本身之上的,是必然的。然而,康德认为这种结合只构成拥有理性的一般条件,或只能证实一般理性运用的可能性,而不构成理性兴趣的任何部分。因为只有理性的扩展,而不仅仅是与自身相一致,才被算做理性的兴趣。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两者结合为一种知识时,何种兴趣将是至上的兴趣,“因为如果两者只是相互并列(并立),前者就会独自紧紧地封锁住它的边界,而不从后者中接受任何东西到自己的领域中来,后者却仍然会把自己的边界扩展到一切之上,并且在自己需要的要求下就会力图把前者一起包括到自己的边界之内来”[2]167。也就是说,如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不存在谁领有优先的关系,纯粹理性就会在不同兴趣的不同运用中产生冲突,不能形成理性的合法扩展。
“优先权”(优先性),在康德看来,指的是在两个或多个由理性结合起来的事物之间,其中之一是与所有其他事物相结合的最初规定根据。“在狭义的实践意义上,这意味着其中之一的兴趣在其他事物的兴趣都服从于它(这种兴趣决不能置于其他兴趣之后)的场合下具有优先权。”[2]164康德首先否认理论理性具有优先权,因为他认为理论理性的兴趣是有条件的,一切超出经验范围的运用都是僭妄,并且一切兴趣最后都是实践的,唯有在实践的运用中才是完整的。由此,康德认为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为一种知识时,后者具有优先地位。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实践理性的优先性主要表现为:理论理性在先验运用中引领我们在经验领域中对对象进行逐一考察,但这并不能使理性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理性由其本性驱使自己超出经验领域,试图借助终极理念冲破一切知识的极限。这些终极理念就是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但这三个理念对于知识来说是根本不必要的,它们只会造成二律背反和先验幻相。康德认为,如果这些思辨的终极理念在当下仍然被理性迫切地追求——这是理性的本质特性所在——那么它们就必须只涉及到实践,因为这三个命题的深远意图在于“如果意志自由,如果有上帝和来世,那么应该做什么”。[1]A800=B828,609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实践理性的优先性主要体现在至善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上。康德把至善看作纯粹意志的全部对象的总体,它是德性与幸福的先天综合,是在实践理性的辩论中作为纯粹理性为有条件者寻求无条件者而被提出来的。但并非是一个悬拟的概念,因为康德认为至善在现世中的实现是一个可以通过道德律来规定的意志的必然客体,即至善在现世中可以通过意志与道德律的完全适合而成为可能。因为意志与道德律的完全适合是神圣的,是任何有限存在者都不能做到的,它必须要在永恒中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同时,这种完全适合也必然只能是出于不偏不倚的理性,康德认为这个不偏不倚的理性就是上帝。因此,不朽和上帝就是在道德上被规定了的意志运用于先天地被给予它的那个客体(至善)之上的条件,并且它们的可能性由于自由是现实的而得到了证明。也就是说,由于上帝和不朽与自由相联结,而自由的实在性是通过道德律而被证实了的,所以它们同它一起并通过它而得到了持存和客观实在性。由此,至善作为纯粹理性的终极目的成为可能,因而实践理性也就具有优先性,是纯粹理性的最初规定根据。
二、纯粹理性在实践运用中具有扩展权
实践理性作为纯粹理性的最初根据,领有优先地位,表明纯粹理性批判只是纯粹理性体系的预科,其最终都指向实践。由此,康德把纯粹理性的运用引向实践领域。
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由于只关心意志的规定根据,只在与这个意志及其原因性的关系中考虑理性,因此,康德认为如若纯粹理性能够对意志在其原因性方面做出规定,那么纯粹理性的知识就会扩展到感官世界的边界之外,从而表明纯粹理性在实践运用中进行一种在思辨运用中它自身不可能的扩展权。
在感官世界中,纯粹理性对存在者进行原因性规定的是自然规律,是从有条件者到条件的无穷回溯。但意志完全独立于现象的自然规律,独立于因果性法则,独立于相继法则,即意志自由,所以自然界中作为各种事件的任何规定根据的因果性法则都不能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在康德看来,“唯有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才是一个意志的充分的规定根据”[2]36。他认为,这种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的规定根据就是实践法则,是形式的普遍立法的原则,其对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因而是超越于感官世界的一切条件之上的原因性法则。康德把关于这个基本法则的意识称为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并且认为由于它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而被给予,所以纯粹理性借此宣布自己是原始立法的。这样,在道德原则上,通过纯粹理性自己的原始立法,表明意志自律,即意志的德性的唯一原则通过准则的单纯普遍立法形式来规定任意与纯粹理性自己立法的实践法则一致,从而实现纯粹理性对意志在其原因性方面进行规定。因此,纯粹理性在实践运用中具有扩展权。
但是,康德指出,在哲学史上由于存在否认存在先天判断的客观必然性有对对象下判断的能力的传统观念,因此实践理性中作为内蕴于纯粹理性的各种权利内的扩展权就被彻底否认了。他认为这种否认主要反映在休谟的哲学中,他说:“对于大卫·休谟,人们可以说他真正开始了对纯粹理性各种权利的一切反驳。”[2]67康德认为,休谟的反驳只是在原因概念中假定一个单纯主观的必然性含义,即用习惯来取代必然性的一切客观含义,以便否定理性的一切有关上帝、自由和不朽的判断。也就是否认原因概念具有客观必然性,用主观必然性的习惯来说明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都有一个原因这件事是必然的,从而否认纯粹理性的一切权利。这样,在休谟那里,一切奠基于客观必然性的原因概念之上的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就把经验主义当作它们的各种推理原则的唯一来源,从而设定理性不能对原因概念作超出一切经验之上的运用。因为在他的推论中,因果关系、同一关系和时空关系都不是由观念所决定,但从经验得来的仅是存在物接近和接续存在,而不是存在物必然这样存在,接近和接续并不足以断言任何两个对象是因和果。休谟意识到了这点,他说:“一个对象可以和另一对象接近、并且是先在的,而仍不被认为是另一个对象的原因。”[5]93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休谟发现对象间总是“恒常结合”,并且相似的例证屡见不鲜。由此,他认为人们会从这种反复出现的“恒常结合”中形成一种“习惯性期待”,他说:“人心借习惯性的转移,会在此一物象出现后,相信有另一物象。”[6]83因此,休谟断言,原因概念不存在客观必然性,其必然的联系乃是我们在经验中形成的主观必然性的习惯。因而他把涉及事物实存的一切知识都局限在经验主义中。对此,康德指出:“休谟的原理中的经验主义也就以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甚至是在数学上的、因而是在理性的一切科学的理论运用上(因为这种运用不是属于哲学就是属于数学)的怀疑论。”[2]70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使人类理性无可挽回地陷入到如同一切知识那样所遭受到的毁灭中。
因此,为了拯救人类理性,捍卫纯粹理性的权利,康德认为必须揭示休谟的推论是谬误推理,重新审视因果性范畴。在康德看来,当休谟把经验对象当成自在之物时——他确实也是这样做——以习惯代替因果性范畴的客观必然性,这无疑是对的。因为在自在之物中根本看不出设定了某物A,不同于A的某物B也一定会被必然设定,所以他否认在自在之物中存在先天的知识,尽管他也否认因果性范畴有一个经验性的起源。但在康德看来,经验对象作为现象绝对不是自在之物本身,并且现象自身在经验中就是以某种方式必然结合着的。他认为这不仅可以按照其在经验对象方面的客观实在性来加以证明,而且可以把它作为先天概念演绎出来。因为“我们在先验逻辑中已看到:尽管我们永远不能直接超越所给予我们的概念的内容,我们毕竟可以完全先天地——但却与一个第三者即可能的经验相关,因而毕竟是先天地——认识那个与其他事物相连结的法则”[1]A766=B794,587。例如,虽然离开经验不能先天地确定蜡块融化是太阳晒,也不能先天地从太阳晒就推出结果蜡块融化,但毕竟能先天地从蜡块融化中断定有某种东西先行了(如太阳晒),融化是按照某种固定的规律而跟随其后的。因此,因果性范畴在经验对象领域内可以依据没有经验来源的纯粹知性加以阐明,取消它的经验主义来源,从而彻底铲除经验主义造成的怀疑论。
“但是,这个因果性范畴(并且一切其他范畴也是一样,因为没有它们就没有任何关于实存着的东西的知识能够实现出来)在那些并非可能经验对象之物、而是超越于可能经验的边界之外的物上面的应用,情况又是如何呢?”[2]72从康德的推论可以看出,由于纯粹理性不仅在理论运用中与对象发生关系,而且也在实践运用中与意志发生关系,并且最终都是为了实践。同时,纯粹理性通过不同于自然规律的实践法则对意志在其原因性上进行规定,使其客观实在性在先天的道德律中被给予。因此,从意志自由与其原因性的规定中就能推出在意志概念中包含一个自由的原因概念,由于这都是出于实践的意图,“于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者的概念就是一个 causa noumenon(本体因)的概念”[2]74。这样,原因的概念变为本体因的概念应用于超验存在的事物之上也就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康德强调,由于这种应用没有任何直观支持,所以其在理论运用中虽然是一个可能的、可思维的概念,却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像休谟一样,剥夺其使用的权利。因为在此过程中并不要求其做出理论上的认识,只是仅仅把原因性概念与意志自由结合起来,因而是在道德律上、在实践的关系上来使用。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变为本体因的原因性概念通过自身与自由意志结合,表明其具有实践运用上的实在性。康德认为,这从此也就给一切其他范畴提供出也是客观的、只不过是单纯实践应用上的实在性,但永远只是就这些范畴与纯粹意志的规定根据(与道德律)处于必然的结合之中而言。可见,纯粹理性通过对意志在其原因性方面进行规定,使其获得实在性,从而表明其在实践运用中具有扩展权,把纯粹理性的知识扩展到感官世界的边界之外。但康德强调,这种扩展对于纯粹理性的理论知识(思辨知识),即凭借纯粹理性对对象的本性加以洞见而形成的知识,却没有丝毫影响。因为此时纯粹理性只与意志相关,因而只与实践相关,所以并不要求对这些超感官东西形成任何有关其本质认识的理论知识。
三、思辨的知识在实践理性进行权利扩展时保存自身
不可否认,实践理性具有扩展权必然会产生一个批判之谜,即:“为什么我们能够否认在思辨中诸范畴的超感官运用有客观的实在性,却又承认它们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方面有这种实在性。”[2]4对此,康德强调纯粹理性在实践意图中的扩展只与实践相关,不要求形成理论知识。那么如何能够设想纯粹理性在实践意图中的扩展却不与此同时扩展其思辨的知识?
在先验要素论中,康德就理性本身进行了批判考察,确定它具有哪些先天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规定用这些要素能建造科学形而上学这座大厦的高度和强度。然而,康德发现,“虽然我们在思想中有一座本应是高耸入云的高塔,材料的储备却只够一栋住房”[1]A707=B735,549。对此,康德认为必须要按照材料的适用程度对大厦做出估计,也就是在先验方法论中对构成纯粹理性完备系统的诸形式条件进行规定,通过“纯粹理性的训练”限制并最终清除经常要从某些规则中偏离开来的倾向;同时通过“纯粹理性的法规”把心中的理念还原给理性的实践运用,进而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出发,勾画未来科学形而上学的总体构成。就此而言,《纯粹理性批判》不过是消极的。但正如康德所言,不能因为警察的职责在于阻止暴力行为发生就说警察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仔细考察不难发现,限制理性扩展的批判事实上具有积极的用途,因为“它同时借此排除了那限制甚至威胁要完全取消理性实践运用的障碍物”[1]BXXV,19,也就是排除思辨理性冒险用超出界限的原理试图把感性界限扩展到无所不包从而完全排斥掉实践运用的僭妄,最终限制自身运用,进而给实践运用腾出位置。
康德认为,在这种积极的用途中,尽管理性的一切思辨知识都严格限制在经验的对象上,因为一切理论知识如果没有与知性概念相应的直观就不可能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自在之物,否则“就会推导出荒谬的命题:没有某种显现着的东西却有现象”[1]BXXVI~BXXVII,20。同时,他指出自在之物与现象又是必须要区别开的,否则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二律背反中。因为现象只遵循自然法则,受客观必然性制约;而自在之物并不服从自然法则,它自身是自由的。现在,由于自由不能作为现象在感官世界中的效果来认识,因为没有任何直观能加之于其上,但毕竟可以思维自由,否则自在之物也将不得不由自然法则规定。并且道德以意志自由为前提,自由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所以在道德上,只要可以思维自由,不一定要认识它,就可能使道德保存自己的位置,而不与自然相矛盾。尽管如此,在康德看来,这种保留自由的积极用途也只不过是为了确保纯粹理性自身批判的合法进行。
可见,对纯粹理性自身的批判,使其思辨的运用尽管需要承认存在与自然不相矛盾的自由领域,但却要求严格地限制在自身领域内保存自身。康德认为,这是思辨知识的主动不扩展。但纯粹理性在实践运用中具有扩展权,把纯粹理性的知识扩展到感官世界的边界之外,这是事实。因此这种扩展是否会形成思辨知识,即思辨的知识是否会在实践理性行使扩展权时被动扩展,这仍需澄清。
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行使自身的扩展权,把纯粹理性的知识扩展到感官世界的边界之外,这必然要通过意志之客体被先天地给予出来才能得到体现。康德认为,这个意志客体就是至善,它是独立于一切理论的原理,并通过道德律而被表象为实践上的必要,因为它是道德律规定意志的必然客体。但至善成为可能又必然要预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三个理念。在此,意志自由通过道德律而被证明是客观实在的;同时,尽管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不是道德律的条件,但却是意志客体(至善)的条件,因而出于实践上绝对必要的至善客体的可能性和在实践的关系上与意志自由相联结,通过意志自由获得持存及客观实在性。所以纯粹理性的这种扩展只是在实践运用上扩展,对思辨知识没有丝毫影响。
除此之外,康德还认为,“思辨理性的上述三种理念本身还不是什么知识”[2]184,因为它们只是出于至善客体的可能性而被预设,在任何经验中都不可能被给予出来。我们不能对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按照它们自在本身所是而有所认识,自由也仅仅只是受道德律规定的意志的属性,而不能作为现象在感官世界中的效果得到认识。同时,即使它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本性而得到规定(人的本性总是试图追问对象是什么,因而总是试图通过对其加以规定来达到认识),那也不能形成纯粹理性理念的思辨知识,因为作出这种规定的无非就是知性和意志,确切地说无非是在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中出于至善之需并严格遵循道德律而被考察的知性和意志,因而是完全先天地借助于道德律、并且也只在与道德律的关系中就其所要求的客体而言通过知性与意志对它们进行规定。因此,它们根本不可能在这方面形成任何思辨知识,而只是仅仅局限在实践的意图中。可见,在实践理性进行权利扩展时,思辨的知识也没有因而被扩展,而是仍保存自身。
综上,康德通过实践理性的优先权和扩展权,证实了思辨知识在实践理性进行权利扩展时保存自身,从而确保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成为可能并具合法性,因而也第一次把纯粹理性的不同运用引入不同领域。但却也从此在它们之间固定下了一道不可估量的鸿沟,而这只能在《判断力批判》中得到解决。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美)刘易斯·贝克.《实践理性批判》通释[M].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