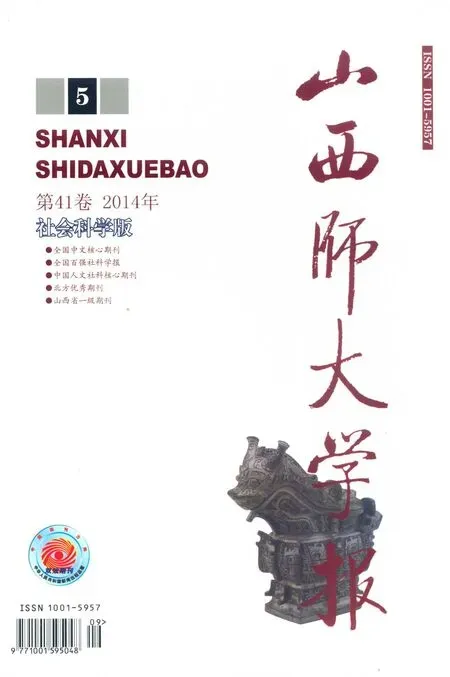科学哲学化或哲学科学化:消解生态危机的哲学进路
张星萍,孙道进
(西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人类利用科学这把“利刃”对自然及人类自身进行着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改造,这种对自然的合理性的破坏造成了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自然科学的“双刃剑”效应已经在国内外学术界达成普遍共识,正是基于这点,科技哲学找到了它作为一门学科而成立的“充足理由律”和逻辑支点。
一、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科学的反动
20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人类与自然环境冲突的加剧——森林面积锐减、土地盐碱化加速、淡水资源匮乏、全球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空洞等成为时代的表征,生态问题成为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海德格尔笔下“诗意的栖居”。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基于人对人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猛烈抨击中应运而生,它是以自然的系统性和自组织性为本体论依据,主张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倡导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伦理观对人的“顾恋”[1]。
1.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科学的形象——在以人类主观意志的主导下破坏有机的自然,加剧了人类的生存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阿尔贝特·史怀泽在《敬畏生命》一书中,把“自然—人—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认为科学知识割裂或肢解了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并非呈线性的正向增长关系,这不过说明了人类的“幼稚”从“天真”走向“深刻”的事实。科学从零星的、松散的知识结构逐渐演变成一种权力的象征,影响甚至支配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人自身之间的关系,具体表现在:(1)人与自然之间紧张的关系:在科学理性的作用下,世界只有自然的人化而不再有人的自然化;人类以自然的主宰者出场而不再是自然的伙伴,自然从孕育万物的大地之母沦为屈从于人类权威的奴仆。(2)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潜在战争的破坏性因科学的进步而大得惊人;战争被视为“净化政治空气的雷雨”;在谋杀机器的意志面前,文化不得不羞愧地低下它那高贵的头颅。(3)人从自我肯定蜕变为自我否定:人自身在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的科学载体上逐渐客体化,“我们大家几乎都受到太规则化、太死板、太紧张的劳动的折磨……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丧失个性而沦为机械的危险”。[2]35科学知识的单极作用内在地预设了人之为人的单向度性以及对自身本质规定性的丧失。
由于非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自在的荒野自然而不见人的自然,只看到原生态的自然而不见历史的自然,因此,在自然保护的方法论问题上,他们同样就自然而论自然,忽视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忽视了对人自身的改变和对“否定社会”的再否定[3]55。客观自然(自然界)与主观自然(人类社会)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改造自然必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则意味着改造自然。例如,在对待自然科学的问题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只看到自然科学的生态破坏,而不见隐藏在科学背后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的破坏。诚然,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机械性为科学对自然的破坏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只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科学对自然的现实性破坏本质上是由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恶化、环境危机归咎于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机械性,这种做法本身也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因为“人—自然”与“人—社会”的关系也是有机统一的,环境伦理学只看到科学——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看不到操纵科学的幕后黑手——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它又是单边主义的伦理学。
2.科学发展的动力在于向自然的“偶然性”挑战,而科学发展的使命则在于认清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对科学的质疑固然存在其理论缺陷,但却引发对科学“伟人形象”的冷思考。科学及其思维方式所面临的挑战,相对于科学作为自然界的某个局部的“必然性”而言不过是“偶然性”,是自然的偶然性(实质是一定时期人类尚未认识到的自然的必然性)在挑战科学的必然性。与其说这种挑战是对科学的破坏,还不如说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动力。在《自然界的辩证法: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一章中,恩格斯对此予以了辩证地解读:科学本身之所以为科学,换句话说,科学本身之所以具有同一性,是因为科学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本身就包含着非科学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是科学发展的源泉,是科学范畴的差异。也就是说,科学是对必然性的描述,是必然性的代名词,而科学的动力则在于偶然性,科学的使命就是要认清这些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如果仅仅因为自然界某个偶然性的出现而不假思索地全盘否定科学的必然性,势必导致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问题上的形而上学。
“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毁灭自己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另外的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4]23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其自身也在不断地实现自我否定并以更新的形态出现,正如法国物理学家昂利·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一书中所说:“拉瓦锡原理或质量守恒原理被物质的电子论推翻了,科学迎来了‘原理的普遍毁灭’,迎来了普遍的‘怀疑时期’。”于是科学也在遭遇偶然的“反例”和悖论危机时不断地自我完善。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以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机械性而否定其本身的科学性,并非如彭加勒那样“批判实证科学的合理性,批判认识客体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连糊涂虫或半马赫主义者的莱伊也不如。我们所要阐发的主旨也不是要彻底消解机械论范式,而是在肯定机械论范式作为自然科学的基本条件的同时,强调它与辩证思维方式或有机论范式的相互耦合。因为从哲学层面看,纯粹的机械论范式不仅决定了科学真理的相对性,而且决定了在这种机械论科学反作用下的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机械唯物主义)。如果仅以机械论范式的局限性为由而彻底否定自然科学,就必然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功利的手段或经验的线性累加。这正如马赫主义因“现代物理学的危机”而对唯物主义的修正,如此因噎废食之举只能使哲学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沼。
二、“红”与“绿”的结合:“环境友好型社会”建构的最终选择
在西方生态哲学中,“红”与“绿”作为生态政治运动的两大阵营,是“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简称。我们在此仅就其对“科学是否负载价值”的不同回答而言,“红”意味着将伦理责任赋予科学似乎显得“过于苛刻”和“不近人情”,主张科学的客观立场;“绿”则将环境问题纳入自然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主张科学负载生态价值。回到我们最初的论题:如何化解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呢?如何辩证地看待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向度耦合呢?
(一)科学的背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生态矛盾”
在对生态问题的溯源上,不少人往往将目光聚焦于科学本身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科学如何转换为生产力,或科学的主体性之合理纬度。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大机器生产方式为主,而与之相伴的环境问题实则是“对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所致。当资本家只关心利润,消费者只在乎产品的使用价值时,森林是否被毁、海洋是否被污染、动物是否被猎杀又与之有何关系呢?如此便形成了工业时代的独特景象:滚滚黑烟从高耸的烟囱向洁净的天空源源不断地排放,各种化学物质混杂的工业废水进入清澈的溪流,城市垃圾的乱置和过度耕伐造成土壤污染……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个别的资本家所能够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出来的或交换了的商品的用途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在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4]307当时的西方社会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家为了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显然只注意到眼前最近的、最直接的后果,离开了土地的工人为了生存也只是充当了大机器生产的“零部件”。资本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借助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革新,而以认识世界为旨趣的科学和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技术却从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立场出发走向了“唯利是图”的人类社会的自我异化,这些行为在生态方面的影响也不外如是——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便是最好的例证,以利润为轴心的生产只能使整个社会在形而上学的思维主导下自我迷失。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
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直接的结果,然后人们却感到惊讶:为达到上述结果而从事的行为的比较远的后果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大多数情形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协调转变成它们的两极对立,如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循环的过程所展示了的那样:建立在本人劳动基础之上的私有制,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财产的丧失,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多地集中到不劳动的人的手中。[4]307—308可见,恩格斯并不反对自然科学的价值负载,但自然科学的价值转向必须附加一个时空限度——在时间上,我们只能以我们可观察、可感知、可预料的阶段性影响为根据;在空间上必须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前提。同时,恩格斯反对“敬畏生命”的生态中心主义,反对生物平等主义的实践方法论,肯定了人对自然改造的必要性。
(二)“红”与“绿”结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之为人,不能离开历史境遇来孤立看待其存在;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离开了人的社会也只能是浮夸的谎言;人类实践推动着社会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又赋予了人类新的内涵。工业社会的思维逻辑是机械论范式,是科学理性之光普照、宗教信仰无处遁形之时代,因此割裂了社会的自然与人的自然之联系。当人类以“奇技淫巧”之心对自然进行大肆地“巧取豪夺”,当科学本着“求真”、“祛魅”的初衷而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当社会以粗放的方式换取经济的不断攀升直至巅峰时,必然会走向相反的方向。科学对科学的否定、人对人自身的否定、社会对社会的否定,由此而形成自身的不断完善并以新的形态在历史中出场。
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在工业文明之后亦即“后工业时代”,在人们对科学异化的反思与解构中生态文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指出对科学的控制实质上是对人永无止境欲望的把握。“红”与“绿”的结合意味着以改良社会的方式改善环境,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即以一种环境哲学的视野看待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建构,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当代科学危机启示现代人将科学的价值导向、伦理学转向、人文精神均纳入其考量范围,从另一个侧面揭示科学与人文相耦合之必要性与合理性,科学哲学存在之合法性。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之立身处地的场所都没有了,何谈社会发展问题?这也就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第一步应该始于对环境的建设——还自然以“碧海蓝天”、“青山常在”,赋人文环境以质朴纯真、宽容和谐,这意味着对以人为载体和要素的社会进行环境伦理学的重构,对人类的思想观念与生产实践方式进行“绿色”变革。从学理上分析,不论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相对主义方法论,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主义的“敬畏生命”方法论,都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与实践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就是从实践论出发,实现辩证法的自觉复归以保证科学与哲学之间必要的张力:科学的哲学审视与人文关怀是消解科学副作用的充分条件,实现“红”与“绿”有机结合是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已成为社会风尚的新指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彰显公平正义的伦理精神。
三、实现科学的哲学转向:回归自然辩证法
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哲学呈现出逐渐分离的发展趋势,离开哲学的科学在自然观领域坚持唯物主义但在此之外却陷入了唯心主义的“黑洞”。科学的负面效应使“科学万能论”宣告破产,科学在反思之后发现其“跛脚前行”之根源在于缺乏哲学的价值导向。
(一)科学哲学化的必要性:只有辩证法思维才能破解科学发展的负面效应
恩格斯说:“要处理的事情决不是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去那些在错误的、然而对它的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里面获得的成果。而这件事是何等地困难这一点,许许多多的那些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信奉正教的基督教徒。”[4]32这里,恩格斯不仅说明了哲学的使命——批判——的艰难性,也说明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家们的唯心主义性质——尽管他们的本体论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环境伦理学家与其说他们是哲学家,不如说他们是生态学家;他们之所以在除了自然观以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上陷入唯心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脱离了哲学,“生态学就是伦理学”的谬论原因就在于此。
科学自近代以来便不再是宗教的“婢女”,开始了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独立“探险”,科学体系愈是完善则愈是要经历谬误的考验。然而,对于一切都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必然性上面的确信,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个特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自然界各种对象的混杂的集合,即使是来自永恒的、一切原初决定的,却仍旧像过去一样——是偶然的”[4]94。恩格斯通过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描述,既是对矛盾同一性包含差异性的补充证明,也说明了科学的同一性是包含差异的同一性,必然性是包含偶然性的必然性,还说明了科学本身的非科学性,以及科学的相对性与条件性。科学是有界的,仅在其领域内是真的,否则“科学非科学”,科学在其固有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上才能实现所谓的“绝对真理”。这样,科学的作用也就不是万能的了。“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起来,就等于把人类任意作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一般地宣布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4]95。当科学信仰被打破而导致科学大厦的坍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危机时,需要哲学来做补充,科学思维一刻也离不开哲学的理论思维,“波粒二象性”的发现即是最好的例证。
自然科学哲学化的现实必要性源于自然界联系的客观性和辩证法的“联系”的总特征。由于自然哲学的认识论基础是机械论范式——把高级的还原为低级的、把复杂的分解为简单的、把整体的肢解为部分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但其认识的客体——自然界本身的一个客观事实是普遍联系的、有机的、系统的整体性存在。因此,自然科学要实现主客观的统一,把握整个世界而非局部的、狭隘的、为人而在的世界,就必须实现机械论范式与有机论范式的耦合——自然科学的哲学化转向。因哲学作为对自然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统摄着各门科学的具体性。就此而言,哲学是一般的科学,科学是具体的哲学,因此,哲学为科学提供这样一个准则——有机论范式指导具体科学,正如纳什所言:“当科学因陷入细节的海洋而丧失宏观角度时,哲学就重新调整科学的观察‘焦距’。”[5]82
(二)生态副作用消解的两条道路:一是改变社会,二是实现自然科学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
改变社会即是对人的改造,对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改造,是对负载价值的自然科学本身的变革。因为科学副作用毕竟不能简单地将错误归结为科学或某个科学家,科学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具体地、历史地发展着的,而社会的变革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就后者而言,首先,自然科学与辩证法的结合实际上意味着在科学与价值之间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寻求二者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仅仅依靠发展科学来消解其自身的副作用是远远不够的。[6]170正如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一文的导言中所说的,自然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知道”永远只是有局限的“知道”。因此,科学的副作用并不像“2×2=4”那样一目了然,可能在很多年以后才会显现(即滞后性)。所有的科学理性都只是有条件的相对真理,这决定了科学(精神)与哲学(精神)相整合与融通的必要性。科学与辩证法的结合具体体现为各学科发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综合化与整体化趋势:其一,边缘(或交叉)学科兴起。新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是由两三门传统学科的分支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如由物理、化学、生物学结合而形成的分子生物学,由经济学发展出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其二,“纬线学科”迅速发展。纬线学科是从一个角度在某个领域内综合各门学科的学科,如能源学、旅游学、管理科学等,其特点是应用性强;其三,总体化综合性学科的发展。这类学科是由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形成,如青年学、老年学等。新兴学科打破了学科间的隔离封闭状态,通过专业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以实现科学与哲学的相互融通与对话,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能够尽可能避免视域盲区以减少科学副作用的影响,但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科学不负载价值本身就是价值,即没有“善”的单向度之“真”就是最大的“善”,至于权衡利弊则是处于科学与价值中间的类主体——实践。
自然科学与辩证法的结合意味着通过发展科学的办法来消解科学副作用。恩格斯以热情的语言讴歌了19世纪中叶物理学(迈尔、焦耳、格罗夫等人关于热与机械力的转化)、化学(道尔顿以后关于无机物与有机物都遵循化学定律的证明)和生物学(沃尔弗、奥肯、拉马克、贝尔等的种源说)发现对确立“新的自然观”的巨大作用。他把这一时期的科学发现比喻为古希腊神话中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复杂问题的“阿莉阿德尼线”。恩格斯不仅赞美自然科学相对于古代人的直觉而言所具有的“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而且为自然科学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的确,这种循环在经验上的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比起已经确立了的东西来是无足轻重的,并且一年一年地弥补起来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自然科学短暂的发展历程,那么,“这种证明在细节上又怎么能够是没有缺陷的呢?”[4]15据此,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科学远比因科学的时代局限性而取消科学来得更为合理,“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其本身则更应该当心。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日臻完善的过程,科学是历史的科学,过度的享受、片面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确实令人触目惊心。但这并非科学的错,亦不是发展的错,恰恰是没有发展科学的错。例如,绿色科学就是对传统科学的否定,通过环保技术的发展来保护环境是不同于浪漫环境主义者“回归原始森林,摆脱科学统治”的不切实际。事实上,辩证地看待科学发展比纯粹发展科学本身更为重要!
[1] 孙道进.“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悖论[J].天府新论,2004,(5).
[2] (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美)纳什.大自然的权利[M].杨通进译.山东:青岛出版社,1999.
[6] 肖显静.环境·科学——非自然、反自然与回归自然[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