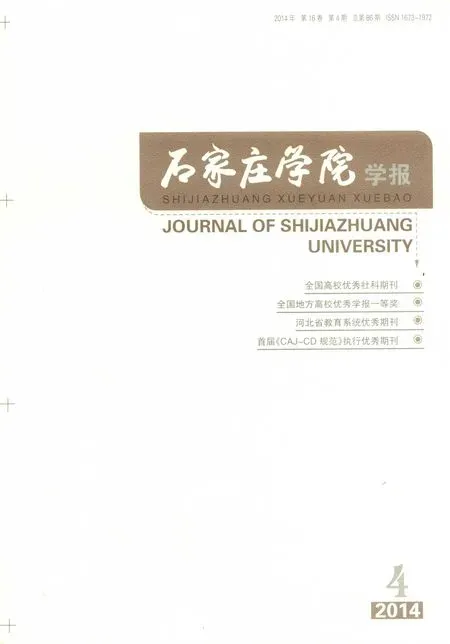论元人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刘倢彤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51)
论元人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刘倢彤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中国古代文人崇尚山水之风由来已久,于元代尤为炽烈,并集中表现在描写山水景致的散曲作品和大量山水画作中。由于元代文人生活极为苦闷,对现实充满了无奈与恐惧,使得他们把目光和感情转移到大自然之中,寄情山水,挥毫泼墨。共同的社会感受使个体情感具有了趋同性。相同的时代精神,趋同一致的文人心态,加之“诗画一体”——文学艺术本身的共通性,造就了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元代;文人;山水散曲;山水画
描写山水林泉等自然景物是古代诗词中常见的内容之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曾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也。”[1]3写景之作总是或明或暗地反映着作者的感情心态、审美情趣乃至整个社会的时代风貌。元代散曲中描写山水景物的作品同样如此。这些作品与诗词一样,反映了元代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元代文人的思想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时代风貌。
无独有偶,元代另一代表性艺术门类——山水画通过对山水景物或精细、或写意的描摹,同样展现出鲜明的“文人化”特征,反映出独具特色的时代精神,从而达到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
元散曲与元代山水画同为元代的代表性文学艺术门类,又大都出自文人笔下,二者所蕴含的元代文人特有的情感心态、审美意趣以及元代的社会风貌定有不少相似之处。本文通过对两种艺术门类的代表性作品的分析与比较,试图找出二者的相似之处,一探元人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的异曲同工之妙。
一、创作主题的相似之处
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虽然都是描绘景物的艺术作品,但透过对山水林泉等自然景物的描摹,作者的创作主题也依稀可见。
(一)江南景致的集中展现
众所周知,元曲作家主要分为北方与南方两大作家群,二者的创作主题与创作风格有明显区别。综观元代大量创作山水散曲的文人作者,大部分都属南方作家群,如张可久、乔吉、徐再思等人都来自江浙一带。这些南方曲作家基本都以自己家乡的景物作为描写对象,通过对青山绿水的诗化描摹,抒写胸中情志。即便是马致远、张养浩、卢挚等擅于创作山水散曲的北方作家,笔下之景也以江南风物为多。如:
鸣榔罢,闪暮光,绿杨啼数声渔唱,挂柴门几家闲晒网,都撮在捕鱼图上。(马致远《双调·寿阳曲·渔村夕照》)[2]102
碧波中范蠡乘舟,醉酒簪花,乐以忘忧。荡荡悠悠,点秋江白鹭沙鸥。急棹不过黄芦岸白蘋渡口,且湾在绿杨堤红蓼滩头。醉时方休,醒时扶头。傲煞人间,伯子公候。(卢挚《双调·蟾宫曲》)[2]235
以上描写山水的散曲作品虽然都出自北方曲作家之手,但通过“渔唱”“长江”“山水相连”“白鹭沙鸥”“绿杨堤”“黄芦岸”等充满江南气息的字眼,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曲子所描写的均是诗情画意的江南景致。
与元人山水散曲类似,元代山水画所展现的景物也不例外。代表了元代山水画最高成就的 “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都为江浙文人,他们的生花妙笔所描画的山水景物也大都是江浙一带的青山秀水、江渚渔泊。如黄公望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所画内容就是浙江桐庐境内的富春江及两岸的山川美景,是元人山水画作的典范。其他画作如《天池石壁图》《丹崖玉树图》等,也都描绘了江南的层峦叠翠、高松小舍。又如另一著名山水画家倪瓒,他晚年隐居太湖,寄情山水,行踪飘泊不定,足迹遍及江阴、宜兴、常州、吴江、湖州、嘉兴、松江一带。他对太湖清幽秀丽的山光水色细心观察,领会其特点,并加以集中、提炼、概括,创造出新的构图形式和新的笔墨技法,逐步形成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这一阶段,倪瓒创作了《松林亭子图》《渔庄秋霁图》《怪石丛篁图》《汀树遥岑图》《江上秋色图》《虞山林壑图》等许多力作,给后来的明清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3]136
集中展现江南的山水景物,可以说是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一个表层的相似之处,但其中却也有深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江南景物自身所具有的易入诗画作品的特点。江南一带多水,山奇貌而秀丽,花草树木丛生。奇山秀水相互映衬,层次分明,极富色彩感,令人赏心悦目,易引发文人的创作意趣。另外,元代长江以北地区长年战火频繁,加之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得许多文人无立锥之地。相比之下,温润的江南水乡繁华富庶、风景如画,成为众多文人雅士的“避难所”与精神上的一片净土。关汉卿就在曲中描写杭州是 “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4]28。面对美景如斯,关汉卿也情不自禁地“一陀儿一句诗题,行一步扇面屏帏”,“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4]28。总之,江南山水如画卷,如锦绣,如仙境,令元代文人流连忘返,使他们得以暂时忘却一切俗世烦恼,在一片烟雨氤氲中寻找欢乐,萌生诗情画意,任山水景物与闲情逸致在笔下肆意流淌,从而才有了这许多传世的山水散曲名篇与山水画佳作。
(二)隐逸主题的突出体现
隐逸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它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更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恒久的主题。到了元代,这类作品更是大量出现,形成了我国文化史上一个隐逸文化发展的高峰。我们在山水散曲与山水画中都可找到大量这个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或直接描绘悠游于山水间的隐逸生活,或通过对山水景物的诗意描摹,间接流露出企羡隐逸的心态。
元代文人由于对仕途的失望和对社会的无奈,所以不少人选择了隐居或入道。有些文人即使身在官场,但由于所承受的沉重的压迫与歧视,内心也向往着隐居之乐。因此,歌咏隐逸生活成为元代散曲的主潮之一,特别是描写山水景物的散曲。元代创作山水散曲的文人们很少像诗词中那样借山水抒发壮怀豪情,而是希望避开喧嚣,在纯净的山水间中寻找尘世遗落的美,在清幽的意境中寻求心灵的安宁和精神的慰藉。如以下作品:
花村外,草店西,晚霞明雨收天霁。四围山一竿残照里,锦屏山又添铺翠。(马致远《双调·寿阳曲·山市晴岚》)[2]127
自隐居,谢尘俗,云共烟,也欢虞。万山青绕一茆庐,恰便似画图中间里。著老夫对着无限景,怎下的又做官去。(张养浩《双调·胡十八》)[2]309
掩柴门笑傲烟霞,隐隐林峦,小小山家。楼外白云,窗前翠竹,井底朱砂。五亩宅无人种瓜,一村庵有客分茶。春色无多,开到蔷薇,落尽梨花。(张可久《双调·折桂令·村庵即事》)[2]251
元人描写隐逸生活,追求大自然的清幽宁静,并不同于传统文人那种高雅与超脱,也不像苦心孤诣修行的僧道那般心如枯木,而是追求脱离官场生活的闲逸和精神的自由。散曲作家笔下的山水之景,常常带有灵虚、缥缈的感觉,似乎存在于现实之中,又浑然独立于现实之外,蕴含着着清幽、寂寥、宁静的独特气韵。在山水之境中,他们“醉月悠悠,漱石休休,水可融情,花可融愁”[2]273,“看春花又看秋花,不管颠风狂雨。尽人间白浪滔滔,我自醉歌眠去”[2]290,使激荡的心情平复下来,静心体悟自然与人生的和谐之趣,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境界,得到精神上的补偿与满足。
由于隐逸在元代已成为一种文人群体性的行为,元代的山水画家也普遍对隐逸情有独钟,“隐逸”自然也成为了元代山水画的一个显著的主题思想。纵观元代山水画,表现遁隐山林、泛舟江湖主题的画作不胜枚举,如赵孟頫的《幼舆丘壑图》、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幽居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倪瓒的《水竹居图》《渔庄秋霁图》、吴镇的《溪山高隐图》《渔父图》《洞庭渔隐图》、王蒙的《青卞隐居图》《夏日山居图》、朱德润的《秀野轩图》、盛懋《秋林高士图》《秋林渔隐图》等。元四家中吴镇更是偏好“渔隐”主题,通过大量描绘这一主题将元人的隐逸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隐逸主题无论在山水散曲还是在山水画作品中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元代文人士大夫身份地位的变化。尽管蒙元统治者意识到汉文化的优越性,也采取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来吸引汉族士人参与朝政,但依然改变不了民族歧视政策的客观存在。虽然随着蒙元统治的稳固,民族敌对情绪逐渐淡化,但在汉族士人心理上造成的阴影却是整体而持久的,汉族文人士大夫骨子里的民族意识是不可能完全得以消除的。这就给元代文学艺术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从而使山林之趣、自然之神通过山水散曲与山水画的“隐逸”主题在这一阶段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而士人的林泉高致亦得以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艺术技法与风格意境的相互借鉴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史上,对诗与画的关系曾有“诗画同一”的言论。唐代著名诗人、画家王维云之“画乃无声之箴颂”[5]53,,即是说画为无声之诗。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6]244元代的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杨维桢说:“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形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7]105上述言论都道出了诗与画的相通之处。所谓诗画同体,就是诗与画的互相渗透与融合,用北宋张舜民的话说,就是“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6]280;用苏轼的话说就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6]116。 所谓“诗中有画”,指诗歌中有鲜明的形象,或山川或泉石,或人物或村落,组合成一幅画景,让读者反复玩味,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所谓“画中有诗”,指画面上直观可视的景物中,熔铸着画家的感情,营造出一种意境,让读者领悟到象外之象、象外之意。
与诗相比,元曲不单注重抒情,还特别注重构境,善于将各个分散的景物形象组合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画面,而且画面本身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如马致远那首著名的《天净沙·秋思》,那淡烟暮霭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以及夕阳映照下的古道行人、西风瘦马,本身就很协调地组成了一幅淡远凄清的水墨山水画。所以,虽然诗与曲在表现山水题材时都属于 “造境”,但是山水诗为诗人所造之境,而山水散曲则为画家所造之境。诗人之境,尤重情深意挚;而画家之境,除重诗情,尤重画意。“赏诗人之境,得情而可忘景;赏画家之景,得情而更可转而赏景。”[8]467从此种意义上讲,“诗画同一”论对元代的山水散曲与山水画同样适用。
(一)散点结合,层次分明的艺术构图
从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说,元散曲写景之作直露显豁,少用比兴,将山水景物直接铺陈甚至堆砌在眼前,以简单直白的描写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山水画。
作为元代新体诗歌的散曲,体现了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趋势,它广泛借鉴山水画的技法来描写景物,注重场景的色彩和构图效果,所表现的意境、意象与山水画如出一辙。如白朴的《越调·天净沙·秋》:“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4]54作者将看似随意实际极为着意的景物铺陈罗列,采用元代山水画散点结合的方式,构成秋天的画面,呈现出静谧、淳淡、幽静的旨意。尤其是轻烟遮罩下,景物变得朦胧模糊、流溢飘动、难以把握,整个场景寂静得近乎无声,然后在几乎幽绝的凝静中用“飞鸿”影子的掠过,给画面增添一点动感。而孤寂中有一个生命的迹象,正符合元代文人画“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3]26的特点。又如贯云石 《正宫·小梁州·秋》中:“芙蓉映水菊花黄,枯荷叶底鹭鸶藏。金风荡,飘动桂枝香。雷锋塔畔登高望,见钱塘一派长江。湖水清,江潮漾。天边斜月,新雁两三行”[2]110,“晚云收,夕阳挂。一川枫叶,两岸芦花。鸥鹭栖,牛羊下。万顷波光天图画,水晶宫冷浸红霞”[2]172,“长天落霞,方池睡鸭,老树昏鸦。几句杜陵诗,一幅王维画”[2]277,“长江万里白如练,淮山数点青如淀”[2]315等。这类句子俯拾皆是,色调浓淡有致,色彩对比浓烈,层次皴染分明,气韵处理到位,较好地表现了闲逸的心理状态。
元散曲善于利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来表现山水之景,元代山水画同样借鉴了此种艺术手法。元代山水画是中国画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元初山水画 “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代表了山水画的最高成就,他们主张诗画合一,将古朴、淡远的艺术理想寄情于山水之间,善于对山水景致作诗化的描摹。画作落笔纯净利落,构图简洁,充满寂寥、淡然的情致,洋溢着一种苍茫萧疏、淡远空灵之意。
元代山水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散点结合、层次分明。以黄公望著名的《富春山居图》为例,此画堪称画家呕心沥血之作,代表了画家一生的艺术追求和水平。他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江水浩渺的富春江及其两岸山峦起伏、苍茫萧散的初秋景色。
虽然此画在一场大火中有所损坏,但依然不影响它的艺术性。画面山峦参差,由近及远,近处是突起的高峰,远处则是起伏不大的山丘,连绵不断,富有层次;平缓的山丘汀岸,杂树萧疏,江水茫茫,水天一色,水面朦胧,迷离恍惚,分不清是白云还是雾气;山间的沙汀上点缀以丛林、村舍、茅亭,水中点缀以渔舟。全图展现了江南秀丽的山水,气势宏大,步步可观,变幻无穷。布局上,山水相间,疏密有致,层次分明,且山与水富于变化,大片的空白突出了江南水面的浩大。画面只用水墨渲染,完全靠墨色的浓淡和空白展现山水的空间感和层次感,给人以真实感、亲切感。用笔上以披麻皴表现江南土质的平缓、山丘的圆润松秀,山石的勾、皴,自然随意,简约洒脱。整幅画极富灵气和神韵,颇有些元山水散曲自然率真、酣畅淋漓的意味。
(二)简淡闲远与空旷孤寂的审美意境
在元代,对简淡闲远之意境美的追求成为元代文人最普遍的审美风尚。这不仅从山水散曲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在元人的山水画中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在元代文人中,普遍崇尚的是那种取景简单平凡,用干墨枯笔而信手挥洒出来的简淡闲远、枯瘦寂寥的画面。他们似乎并不太重视选景、构思、调色、用笔。“元四家”中的王蒙就曾说过:“画家以冲淡胜者为至,若瘦硬严谨,则又涉作者气,知音世人所不贵也。”[3]83倪瓒也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3]26自来诗画相通,所以,这些“以冲淡胜者为至”“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画论,实际上反映了元代文人普遍的艺术情趣和审美理想,这与散曲作家们在山水散曲作品中大量地描写“简淡闲放”之境是息息相通的。
除去简淡闲远这一普遍的审美意境之外,元代不少山水散曲还具有空旷孤寂的突出特点。如果说前一类作品重在对景物的描摹,那么这一类作品则重在抒发胸中之情。出现在作品中的景物往往是夕阳、远山、流水、飞云、落花、残鸿,大多为晚春衰残之景,深秋萧条之物,景物本身不仅萧瑟,还带有几分孤寂与悲凉;所描绘的画面意境往往空旷辽阔,仿佛横无际涯,从而更加衬托出作者内心的孤独。
以下散曲作品,便突出反映了元人这两种审美意境。
滕斌《中吕·普天乐》:“晚天凉,熏风细。浮云暗淡,远水茫微。江水清,遥山碧。喜驾孤舟潇湘内,伴纶杆箬笠蓑衣。垂杨树底,芦花影里。归去来兮!”[2]336
姚燧《中吕·满庭芳》:“我到此显登眺,日远天高。山接水茫茫渺渺,水连天隐隐迢迢。”[2]309
唐毅夫 《双调·殿前欢·大都西山》:“冷云间,夕阳楼外数峰闲。等闲不许俗人看。雨髻烟鬟,依西十二栏。休长叹,不多时暮霭风吹散。西山看我,我看西山。 ”[2]415
与散曲创作相似的是,元代山水画所表现的多为枯木寒林、远山野水,很少画人物,且大多不设色。近景常是一带土丘,旁边三五株树木,一二座茅屋草亭,中间上方以空白展示湖波粼粼、渺远的天空,远景多为几抹淡淡的山脉,画面静谧恬淡,意境旷远。布景萧疏,笔墨简净淡雅,意境清旷空幽,似出尘超俗,不食人间烟火,流露出画家淡然、孤寂的心境。此种风格在倪瓒的画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倪瓒作品个性鲜明,笔墨奇峭简拔,多描绘江南烟雨迷茫的湖光山色,爱取平远之景,常常不着人物,用笔柔润简淡,意境萧散空蒙,创折带皴,自成一家,人称“疏体”。所谓“平远”,即自近山而望远山,近于平视,画中景物一般是近大远小,近高远低,似在地面上平着一层层铺开,直达天际,显得茫茫浩远。如《六君子图》所描绘的江南秋色,近景是松、柏、樟、楠、槐、榆六棵姿态挺拔的树木,疏密掩映,简洁疏放;中景是宽广无垠的湖面,水天相接;远景是起伏的岗峦。全图布局疏朗,笔墨简净,气象萧索,营造出一种荒凉空寂的意境。画家托物寄情,以树象征孤高正直、特立独行的君子人格。倪瓒逸笔草草,笔简形具,在苍茫空灵之中突显出一种孤傲清高、洁身自好的人格理想,以及高处不胜寒的思想境界,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的鲜明个性,意蕴丰富,令人玩味不尽。
元代山水散曲与山水画的“逸笔”及简淡闲远、空旷孤寂的风格意境,成为元代文人高雅人格的表征,受到后代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的仰慕和推崇。元代文人以独特的艺术创造精神,将鲜明的主观性情融入艺术作品中,以抒写自己强烈的个性和胸中的逸气,从而推动了元代文学艺术的整体发展。
三、文人心态与时代精神的突出体现
从对元代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作品相似之处的对比与分析中,不但可以看到元代文人忘情人世的淡泊胸怀,还可以看到他们以淡泊心胸去欣赏自然之美的闲情逸趣。虽然这当中也有前人“悠然见南山”[7]22之恬淡与“相看两不厌”[7]64之亲切的影响,但卓然而成为一时代之风尚的却只有元代。元代山水散曲与元代山水画作为元代的主流文学艺术,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多种相似之处,与时代环境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文人心态——社会压迫下的愤激不平之情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汉代,自隋唐以来,历代知识分子大都以科举入仕。但元代的科举录取名额少,汉族文人录取后任命官职时还要比蒙古人再下一等。这种不平等的歧视政策使得元代文人失去了人生的追求目标,整日闲来无事。
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元散曲作家较之前代文人更接近社会底层,对社会、人生有着郁积的情绪和不断涌动的愤激之情,而这种感情便时常借助山水之景流露出来。他们的山水之作不仅仅局限于遣兴抒怀,而是明显带有一种历经沧桑和劫后余生的苍凉情绪。如卢挚《沉醉东风·秋景》:“挂绝壁松枯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四围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2]267大写意的暮秋景色,枯松倒挂,云帆月影,纯净、凄迷的气氛中隐隐透出作者心头的一丝凉意。从这一点说,元散曲之景是“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情溢于海”[9]185理论的最好阐释。
另外,“渔父”形象在山水散曲中的大量出现,也突出反映了元代文人的这种心态。“渔父”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形象,其思想意蕴相当复杂,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赋予其新的涵义。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庄子·渔父》,二是《楚辞·渔父》,三是《吕氏春秋》中写到的姜太公。自此之后,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渔父”可谓层出不穷,在元散曲创作中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不过,在前人的文学作品中,渔父的人生哲学一般被解读为避世、出世,元人则在此基础上又赋予了其一种新的内涵——玩世、混世。
如乔吉的《中吕·满庭芳·渔父词》:
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疼,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4]45
这首曲中的“卧御榻”和“坐羊皮”句引用严子陵的故事,一反一正,说明在皇帝身边令人浑身不自在,归隐江湖反能卸去精神上的沉重负担,正因如此,严子陵的隐居生活道路才令后世文人心向往之。又如白贲的《正宫·鹦鹉曲》:
侬家鹦鹉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浪花中一叶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觉来满眼青山,抖擞绿蓑归去。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4]68这首曲将一个玩世不恭的渔父形象描写得活灵活现。此曲一出,影响极大,不仅伶人广泛传唱,更引得后辈的词曲家纷纷续作。由此可见,在元代文人心中,这种渔父情结的广泛存在。元代文人将历代文学作品中渔父的人生哲学解读为玩世、混世,也是一种愤激之情的自然流露。
“渔父”形象在元代的山水画作中同样出现得非常频繁,不少画家将“渔隐”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在“元四家”中,吴镇最擅创作此类作品,《渔父图》是他经常表现的题材。以吴镇为子敬戏作的《渔父图》为例,此图取景于秀美的江南水乡一带,笔法圆润,意境幽深。两棵高树耸立湖畔,湖沿蒲草萋萋,随风摇拂,对江平沙曲岸,远岫遥岑,更远处隐隐现一山峦,山色入湖,水波涟漪之中,一叶渔舟飘荡其间,给人以安闲惬意之感。画中题道:“西风潇潇下木叶,江上青山愁万叠。长年悠优乐竿线,蓑笠几番风雨歇。渔童鼓棹忘西东,放歌荡漾芦花风。玉壶深长曲未终,举头明月磨青铜。夜深船尾鱼泼刺,云散天空烟水阔。”[10]157这正是他远避俗世、寄兴山水、浪迹江湖的生活写照。
(二)时代精神——道家思想影响下的自然本真之志
除了社会现实政治对文人的排挤,全真教在元代的盛行,也是崇尚山水成为元代文学艺术之一代风尚的重要原因。元代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需要借助信仰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化解心头的郁结。方值道教大盛,而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与世无争的精神追求,正好能够化解他们的心结,令他们暂时逃避现实的痛苦;道家精神崇尚的逍遥、自由之旨,极大地刺激了文人的浪漫情感;道教的云游、打坐、降心、炼性、离凡世等宗教修炼,帮助元代文人涤尽尘世俗念,获得了精神解脱,对他们的思想产生极大影响。
从官场失意到入教,正是元代许多文人的思想从入世到隐世的转折点。如果说黑暗的社会政治只是将他们抛弃,迫使他们远离现实而醉心于林泉,那么以道家思想为基础的全真教义则使他们在离开之后能够逐渐平息心中的愤懑之气,让他们得以在山水间安静下来。前者使其“来之”,后者使其“安之”。最初可能还有被迫的情绪,在道家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开始心安理得地在“竹篱茅舍”中“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4]42,悠然纵情于青山绿水之间了。这时,他们对于自然山水,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欣赏,而是很自然地将它们当做了知己挚友,他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热爱,当然比那些所谓的庙堂文人和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的假隐士们更为自然,更为亲切,更为真挚,更为深沉。所以,他们在散曲中所表现出的林泉高致、山水神韵无疑体现出了在道家思想深刻影响下的自然与本真。
道家思想不仅对元代山水散曲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山水画的创作也不例外。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达到最高境界的艺术,所包含的内涵和精神与道家的顺应自然、修心养身有着完全相通的理念。元代特殊的社会现实为这两种精神和艺术的结合,创造了有利的契机。元代不少山水画家都与全真教有不解之缘,“元四家”更是皆为全真教徒。从黄公望的浑厚圆融到倪瓒的萧疏空灵,从吴镇的逍遥渔隐到王蒙的隐居山庄,无一不贯穿着道教的精神。元代山水画所表现出的大自然的开阔和广袤、深邃和神秘、不可违抗的力量和精神,正是道教思想的外化体现。
四、结语
元曲山水之作与元代山水画都有着古朴而苍茫的景象,有着恬淡寂寥的情调,有着失意放歌的士人感情,是极为复杂而矛盾的思想的混合体,表现了元代文人特有的精神和艺术追求,体现着他们寄情山水的观念在特定时代的新变化。
通过元散曲与画作中对山水之景的描绘可以窥见,元代文人的心灵在压抑下孤独地徘徊,感情在山水之间流动,思想在寂寥无奈中迷茫,而二者的共通之处正折射出元代别具一格的时代精神与一代文人之审美意趣。
[1]王国维.人间词话[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2]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王伯敏.山水画纵横谈[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
[4]赵义山.元曲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王维.为画人谢赐表[M]//吴彤.自然与文化——中国的诗,画与炼丹.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6]曹慕樊,徐永年.东坡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7]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陈平原.词曲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9]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中国传世名画[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周亚红)
Comments on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Prose of Natural Scenery and Painting of Landscape in Yuan Dynasty
LIU Jie-tong
(School of Arts,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51,China)
The ancient Chinese men of letters had long advocated landscape,and this vogue became tremendous in the Yuan Dynasty,focusing on the prose of natural scenery and the painting of landscape. Because the Yuan literati felt much depressed,helpless and horrified,they had to shift their vision and emotion to natural scenery,and gave themselves to it.Common social feelings had the individual emotion move towards convergence.The same spirit of the times,the same mental state of the scholars,an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rt made the prose of natural scenery and painting of landscape in the Yuan Dynasty equally good in thought and art.
the Yuan Dynasty;man of letters;prose of natural scenery;landscape painting
I207.24;J212
A
:1673-1972(2014)04-0070-06
2014-05-15
刘倢彤(1989-),女,河北衡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