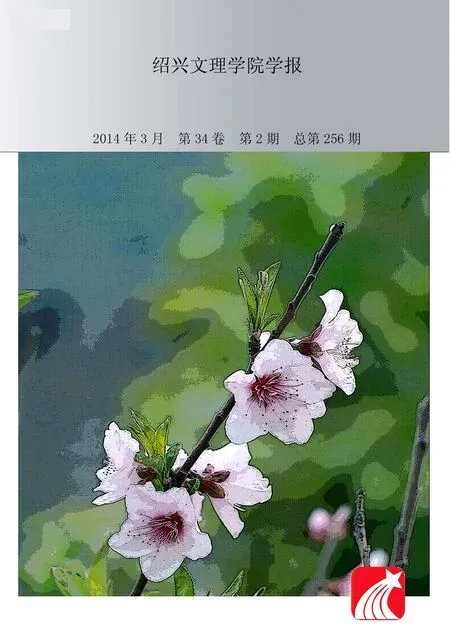论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法国形象
徐雨桐 王 芳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夏洛蒂·勃朗特一生从未去过法国,但她的四部小说—— 《教师》《简·爱》《谢利》《维莱特》中不乏关于法国的描写,这些和法国相关的描写,构成了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法国形象。有“维多利亚雄鹰”美誉的夏洛蒂·勃朗特的法国形象塑造,既是维多利亚盛期英国社会对法国的集体想象物,也是其个性的忠实反映,研究她小说中的法国形象,对于我们了解维多利亚盛期的英国文化,深化夏洛蒂·勃朗特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至今为止,学界对此罕有涉及。笔者不揣鄙陋,试勉力为之,做这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
一、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法国形象
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是指“出自一个民族 (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有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1]和一般的文学形象研究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为重心不同,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指涉的范围较为广泛,它既指涉文本中的异国人形象,又可包括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实物、异国地理环境、异国观念、异国言词等构成的形象;既可指涉文本形象,又可与文本以外的社会文化形象相联系,它重视形象制作主体对他者的创造式的阅读和接受。根据形象学的这种特征,本文所分析的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法国形象,不仅包括其小说中的法国人,还包括法国语言文化、来自法国的装饰、法国用品、法式妆扮等其它和法国相关的东西,它们共同构成了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法国形象。
(一)法国人物形象
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法国人并不多,但他们对小说的思想主题的表达却是必不可少的。大致说来,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法国人从表面看总是具有吸引力的,作者并不吝啬对他们外貌的赞扬,但对他们的道德习性却十分反感,尤其是当这些法国人与小说的英国主人公发生了利益冲突时,人物的道德水平更是直线下降,而作者对法国人道德的指控,对于女性更为严厉。
1.法国女人
对于和主人公只是泛泛之交,而无利益冲突的法国女人,夏洛蒂虽然强调她们卖弄风情、态度轻浮,但一般并不对其道德水平做出盖棺定论式的评价。《维莱特》中的女杂务工萝芯妮·玛脱,人物出场便伴随着“一阵轻浮的最高音部的笑声”,她给露西的直接印象是:“生得漂亮却不讲节操的法国小女工,生性轻浮,反复无常,好打扮,爱虚荣,贪小利”。从外貌上说,“她长得俊俏,年纪轻,穿一套做工精湛的衣服”。从作风上看,约翰医生被她羞辱,而她却用“尖锐刺耳的清脆的嗓子”唱起了“轻松的法国歌曲”;她给人开门的时候“从小房间里箭一般地窜出来,奔过去打开大门”,“蹦蹦跳跳”的;“她的法国拖鞋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冒冒失失,高声喧哗”总是有失稳重。起初她和约翰医生之间有着让人迷惑的暧昧,她对他说话时“撒娇地笑着喊”,“一点都不难为情”,还会“撅起嘴巴”撒娇。别人在场她并不回避,“不害怕”“不害臊”地“瞟着约翰医生”,露西还目睹了萝芯妮毫无顾忌地拿了约翰医生给她的一块金币。但总的来说,“她并不是那种坏人,也没有一种概念认为捞取自己能够捞到的东西会有什么难为情,或者像一只喜鹊那样喋喋不休地对基督教徒之中最好的绅士说话会有什么厚颜无耻之处。”
《简·爱》中瓦朗的女儿阿黛勒,表现出了巴黎式的对物质、妆扮的热忱。面对索要礼物的阿黛勒,罗切斯特先生用讽刺的态度说:“是的,你的‘boite’终于到了……你这位地道的巴黎女儿”,他猜测“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件粉红色丝绸小上衣,打开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喜悦,媚俗之气流动在她的血液里,融化在她的脑髓里,沉淀在她的骨髓里”。这天生对妆扮的执着使她“看上去多么矫揉造作”。简也认为“在这位巴黎小女子天生对服饰的热烈追求中,既有几分可笑,又有几分可悲”。而在一群成年女性之间,简注意到阿黛勒尽力地惹人关注,她“心满意足地受着大伙的宠爱”。但是简对阿黛勒仍是喜欢的。
而对于与小说主人公直接或间接发生了冲突的法国女人,夏洛蒂·勃朗特的描写就严厉得多,语气之间充满了嘲讽和鄙夷。《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巴黎情妇塞莉纳·瓦朗,被描写成一个水性杨花、放荡贪婪的女人,她用色迷住了罗切斯特,得到他大量的物质供养,却在罗切斯特的眼皮底下将一个法国恶少带回家中,最后将自己的私生子扔给罗切斯特,跟一个音乐家私奔了,她“把英国钱从我的英国裤袋里骗走了,可是却把那朵法国小花留在我手里”。罗切斯特的叙述中充满了对她的厌恶,即使在热恋时他也“从来不认为她身上有什么神圣的德性”,“对于一个演歌剧的inamorata(情妇),这个词正合适”。
《维莱特》中巴黎女教师圣比埃尔小姐尽力讨好保罗先生,是主人公露西的最有威胁的情敌。夏洛蒂第一次介绍她时就直接指出她“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却道德败坏——没有虔诚,没有原则,没有爱心”,并且“对于礼物具有异常的热情”,为了满足对衣服、化妆品、糖果点心的欲望预支薪水。她具有“优美的风度”,“斯文得体的举止”能给别人好印象。但在露西眼里,她“冰冷冷的眼神,闪着既渴求什么又忘恩负义的光”。作者通过两次圣名瞻礼日集中表现了人物性格:第一次,她秘密送贝克夫人昂贵的礼物,在保罗先生面前阿谀奉承,但对工作却“恨得要命”。先生的圣名瞻礼日时,她穿上被认为是“危险的豪华和奢侈的”绸袍子,请理发师做头发,用新出的香水。当她发现露西并没有带来鲜花的时候,她“笑逐颜开”,极尽所能地当众讽刺露西。在人物谈话中,圣比埃尔小姐总是被作为反例:贝克夫人谈到她语气中带着“不屑、冷漠和反感”;评论她的节日妆扮时说:“她的样子像一个卖弄风情的老妇人装成一个单纯的少女”;保罗先生说:“我看到了她的积怨,她的虚荣,她的轻浮”。
2.法国男人
夏洛蒂笔下的法国男人也可以分成一般和特殊两类。对于那些泛泛涉及的法国男人,作者往往很平淡地一笔带过,不急于做道德判断。《维莱特》中,在克莱西公馆的聚会时出席的几个法国学者,一个“彬彬有礼”,是一位“饱学之士,但是相当优雅殷勤”,另一些法国人“富有思考力”,波琳娜的文雅和智力“很配他们民族的口胃”,他们谈论的问题也懂得顾及波琳娜而避开科学,而谈“文学、艺术和生活上的许多问题”,多么绅士的形象。另外一位人物——希拉斯神父,是“一位好心的神父”,具有“一种充满柔情的法国人的善心”。他会讲很多浪漫色彩的故事,多用法语、“卢梭式感伤情调”,是个容易动情的人。法国人似乎还有优雅、温柔的特点,《教师》中在形容人物擦鼻子时,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词:“法国式的优雅风度”,而那位“鲁特夫人可没那么易动感情,因为她是佛兰芒人,而不是法国人”。
与法国女人一样,夏洛蒂笔下的法国男人也有讨人喜欢的外表,衣着装饰儒雅;但是如果深入交往,就会发现他们的虚伪残暴。 《教师》中的佩利特先生是这类人物的典型。起初他的外貌蒙骗了“我”,他“五官端正、十分好看,一副法国人的模样;虽然脸上仍带着高卢人固有的严厉,但其程度已被他那双温和的蓝眼睛以及他那忧郁的、几乎是痛苦的面部表情大大软化了。他的相貌‘漂亮又精神’……他眉宇间所流露出的那种智慧。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有趣而富于魅力的人”。作者用了这么多褒义的句子来赞扬这个法国男校长表达“我”——克利姆斯沃思对他的敬仰。但是在交往中“我”也发现他对于比利时助教“严峻、冷淡”并且带着嘲弄和轻蔑,如果他们犯了一点小错误他定会严酷惩罚。在“我”发现了他和佐蕾德之间的关系后,更加认清了佩利特先生的背信弃义,也明白了他的温和有礼只是虚伪的表演。而对于“我”冷淡的态度,他却更加殷勤,“礼貌到低三下四的程度”,最后终于“撕破所有热情友好的伪装”:一次喝醉,他对“我”的“仇视和妒忌的情绪”爆发出来,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法国人”性格中的“残暴的佛兰西民族特点”,暴露了他的“凶恶个性”。但是不久后,由于鲁特小姐的平复,他又对“我”“心平气和、彬彬有礼”了,还有一些“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夏洛蒂·勃朗特用这些细节,写足了人物的虚伪善妒。
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个别法国人物时,还时常会借机对法国整体道德水平进行评价,如《教师》中“我”认为“佩利特的单身生活是以地地道道的法国方式度过的,从来无视道德的约束。我认为,他的婚姻生活必然也会是法国式的”,“我”对于他“残暴的佛兰西民族特点”,“十足的法国式的、得意而嘲弄的笑声”都充满了鄙视,这些评价代表着作者对法国道德水平的看法。
(二)其他法国相关事物
除了法国人,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中还有许多和法国相关的事物,法语、法国书籍、法国时装等。和对法国人道德水平的不屑不同,这些和法国相关的事物,似乎意味着优雅、高贵、精致。
在描述一些精致的、高贵的装饰、布置或食物时,夏洛蒂·勃朗特总会加入一些“法国式”的物件,“法国的小马车”“法国的床”“法国式的时钟和一盏灯”都是她小说中最常见的物品,《简·爱》中那些来桑菲尔德参加舞会的女人“裹着一条装饰着貂皮的贵重丝绒披巾,额前披着法国式的假卷发”;《维莱特》中外出郊游时穿的较好的衣服是“干净的崭新的印花连衣裙和轻便草帽就像唯有法国的女工能够缝制和装饰的”;贝克夫人“黑色的绸连衣裙很合身,那好像是只有法国女裁缝才能够缝制的合身衣服”;《教师》中“两小碟鲜美可口的肉,制作精良,摆放考究;外加一盘色拉和一盘法国奶酪”。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人物计划或真正外出旅游时总免不了去往法国,罗切斯特在向简示爱时说:“我将带我的宝贝去阳光明媚的地方,到法国的葡萄园和意大利的平原去……你得到我在法国南部拥有的一个地方,地中海沿岸一座墙壁雪白的别墅。在那里有人守护着你,你准会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维莱特》中暑假的时候姞妮芙拉去“作穿越法国南部的旅游去了”,而波琳娜·玛丽和巴桑皮尔先生外出旅行又是“把几个星期分别用在法国各省和首都”;《教师》中佩利特夫妇新婚蜜月去的也是巴黎。不管成行与否,这些被提及的各式各样的“法国之旅”都引导着读者想象法国的闲适,显然,在夏洛蒂·勃朗特眼里,法国是一个适合资产阶级享乐的乐土。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中主人公对学习法语、法国文学、哲学书籍总有一种热情。《简·爱》中,简对新学校有“能翻译的法文书”、被答应“让我学法文”感到非常高兴。她也以此为修养、优雅的象征:“她们掌握的知识真丰富!随后她们似乎对法国人名和法国作者了如指掌。”贝茜在简离开学校即将去桑菲尔德做家庭教师之前,来看望简,开头便问:“你学法语了吗?”并据此判断简是个“大家闺秀”。《教师》中“我”听到两位绅士用法语交谈,那法语“对我来说简直就像音乐一样动听”。《谢利》中:“在她的功课中,她已经念了许多高乃依和拉辛的诗,念得十分认真严肃,这正是叫我满意的地方。”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中还常常出现一些用法语写的信件、法国俚语等,这些使用法语的时刻往往不够严肃,《维莱特》中露西就坦言,讲“特别没有心肝的乖张的话的时候,常常求助于法语”。又如,作者时常用这样的表述:“如法国人所说,失常了”,“不洼湿客”“落石莫得”先生,原文用法语,指的是“干木头”和“死石块”,用以调侃。可见,在作者看来,法语在表达时更活泼、更自由。
不管是法式用品、妆扮的精美,还是法国之旅的享受,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里都只是一笔带过,从来没有成为主人公追求的目标,甚至还隐约指向一种道德水平值得质疑的享乐主义。这些物品的出现,只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物质风尚,对法语的钦羡,对法国文学作品等的偶尔涉猎与评价表面看来是对这种倾向的颠覆,但考虑到法语一直是上层阶级使用的语言,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对法语的使用又多数是不大庄重、严肃的场合,因此,这些和法国相关的事物,同样表现了作者对法国形象的贬低。
二、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法国形象的成因及意义
一个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塑造,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认为“形象是描述,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的在场成分的描述”。[2]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法国形象,与其说是她对法国的认知,还不如是她在英国维多利亚文化背景下关于法国的想象;与其是在言说法国,不如是在言说作家本人和她所代表的某种文化心理。
先说说作家本人的经历、个性对这种法国形象形成的影响。夏洛蒂对法国道德形象的贬低和她的家庭背景有明显的关系。夏洛蒂的父亲是一个严峻的清教徒,她的思维未能打破郊区牧师女儿的局限,认为“俗世和肉欲,对她来说都同样是魔鬼。她蔑视世俗的飞黄腾达,世俗的功名利禄。她对声色之娱也不抱有更多的同情”。[3]315拮据的、清苦的家庭境况,使她养成了艰苦、勤俭、顽强的习惯。为了补贴家用,夏洛蒂做过教师,还一再想开办寄宿学校,这种穷困和她爱尔兰血统中凯尔特族的高傲、羞涩和隐忍,使她“蔑视普通的利益,普通的享受”[3]225-226,以严格的清教徒道德约束自己,维持自己强烈的自尊。这各种经历必然导致她对法国式奢靡淫逸生活状态、法国女人放荡轻浮的态度的反感。
不过,所谓的法国式奢靡淫逸生活状态、法国女人放荡轻浮这种印象,并不是夏洛蒂·勃朗特亲身体验,夏洛蒂·勃朗特一生从未到过法国,她对法国的印象主要来自当时社会媒体所制造出来的法国,是在各种形式的布道、各类报刊杂志中体现出来的英国社会集体想象物。不过,她的学习经历使她对英国集体想象物的法国的接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并且因其欲望的投射而变得细腻、丰富,富于强烈的情感。
为了谋生,夏洛蒂一直想和妹妹们办一所学校,而要办学,必须教授法语。这种动机让她努力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化,在学习过程中,她的智慧让她感受到了法国文学、哲学的精妙,并产生了对法国文化的某种尊重。她在书信中写道:“我记得,我小时候……阅读一本有关某个法国贵族的传记的时候,我常常有这种感觉。这个法国贵族达到的神圣境界,比从最早的殉道者那个时代以来人们所知道的更为纯洁,更为崇高。”“最好的一点是,这些书使读者对法国和巴黎有了一个彻底的了解”[4]。夏洛蒂还受法国浪漫主义书籍影响,她细腻、凝练的写实手法与自己的想象力相结合,还在其创作中使用了法国文学中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的手法,《简·爱》就创作于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尽管“她认为法国书籍是‘聪明的,邪恶的,老于世故的,不道德的’,可是她还是要读法国文学”。[3]225-226夏洛蒂不吝啬对法国哲学、文艺的成就表示欣赏,“艺术的行家——思想细致、眼光锐利、感觉敏锐的法国人,懂得他所分析的作品的构成成分的真正性质——他懂得事物的真正性质,他还给与他们恰当的名称。”[3]72
在布鲁塞尔学法语的期间,夏洛蒂接触到了一些法国人及大量的法国用品,并爱上了自己的老师埃热先生。在布鲁塞尔,法国的异国形象是繁荣、自由、富有激情的,身处这样的语境中,夏洛蒂也免不了受到影响。这使得夏洛蒂对法国男人的儒雅不乏好感。《夏洛蒂的秘密日记》中一段夏洛蒂的真实经历:夏洛蒂在从谢菲尔德到利兹的火车车厢碰到一位法国绅士,“那位绅士一定是法国人,我是那么肯定,一阵激动的感觉涌上我的脊骨。”[5]她同这位法国绅士交谈,感到很愉快。
学习法语、阅读法语文献、与法国人接触,都让夏洛蒂产生了进一步了解法国的渴望,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法国之旅”正是她这种欲望的投射,自由的进行一次法国之旅的描述,是对其压抑个人情绪自由的补偿。她通过这种方式不自觉地表述了自己隐秘的渴望,排解了其矛盾、焦虑的情绪。
那么,为什么夏洛蒂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强调不愿去法国,强硬的摆出要与法国撇清关系的姿态呢?除了她的清教徒道德情感,还和她的民族主义情感有相当大的关系。英法两国自百年战争始,已经积累了数百年的宿怨,到了夏洛蒂身处的19世纪,两国通过殖民地争夺而争夺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更是愈演愈烈。在这场霸权的争夺战中,各种媒介都被用作凝聚民族的手段:“文化民族主义对内力图通过宣传、教育来建构一种同质性的民族文化以唤起本民族成员对这种共同民族文化的集体认同,对外则强调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区别,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6]而事实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也非常强盛,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称霸全球,这给英国国民一种毫不掩饰的优越感。
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说中酣畅淋漓地表现了英国对法国的民族优越感。《简·爱》中罗切斯特收养阿黛勒是为了“把这个可怜虫带出了巴黎的泥坑,转移到这里,让她在英国乡间花园健康的土壤中,干干净净地成长”。简则明显地表现出对“情妇式”法国妇女和淫靡的法国生活的轻蔑,她觉得在“健康的英国中部一个山风吹拂的角落”比“在南方的气候中一觉醒来,置身于享乐别墅的奢华之中,原来已住在法国,做了罗切斯特先生的情妇”高尚得多。另外,她还认为阿黛勒“长大以后,健全的英国教育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她的法国式缺陷”,表达了作者对英国教育的充分认可和信心。在《维莱特》中,当保罗先生在圣名瞻礼日痛骂英国女人时,露西大喊:“英国、历史和英雄们万岁!打倒法国、捏造和欺骗!”在《谢利》中,穆尔口中“这个罗地的征服者怎么居然纡尊降贵地当了皇帝……我鄙视法国!”
当然,夏洛蒂·勃朗特在将法国贬为放荡、淫乱之所在,把英国视为健康、正直、活力的代表时虽然有意识地使用了对比等叙述策略,但她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放纵也并非毫无察觉。她在《维莱特》中称伦敦是奢华淫靡的“巴比伦”;《简·爱》中罗切斯特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放荡公子,到处找情妇过着纵欲的生活;而《教师》中直接道出英国国内因为习惯于“对于外界舆论的顾忌,对保持体面外表的渴望”而大肆挥霍,正是在这样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简·爱式的清教徒道德才突显出无穷的魅力,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强烈意志才得以扩张到一个更大的空间。
巴柔曾精辟地指出,“所有对自身身份依据进行思考的文学,甚至通过虚构作品来思考的文学,都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他者的形象,以便进行自我结构和自我言说:对他者的思辨就变成了自我思辨。”[7]总的来说,夏洛蒂扩大其对法国形象的贬低,隐藏其欲望补偿,是为了迎合本人或所处群体的文化语境需要,表现出一种“当英国文化自我认同、自我扩张时,法国形象往往就表现为其否定面;英国文化自我批判、自我改造时,法国形象就可能展示为肯定面”[8]的言语策略。
[1]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M]//孟华,译.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5.
[2][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M]//孟华,译.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6.
[3]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315.
[4][英]盖斯凯尔夫人.夏洛蒂·勃朗特传[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美]塞尔丽·詹姆斯.夏洛蒂·勃朗特的秘密日记[M].陈俊群,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77.
[6]杨丽.《简·爱》中的法国形象及民族主义话语[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7][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88.
[8]杨丽.作为文化想象的法国——解读《简·爱》与《还乡》中的法国形象[D].武汉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