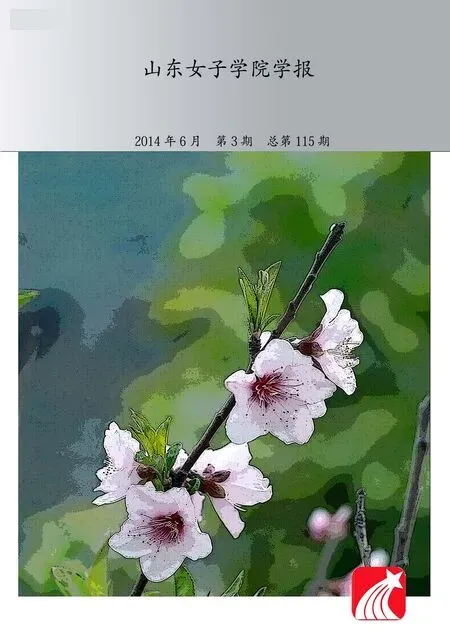从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的人物情感谈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
刘维春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 福州 350025)
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社会主体地位一直以来既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母题,也是女性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制度和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法规政策,女性的独立和自由状况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匮乏局面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巨大改观,陈旧男权文化仍然是女性主体意识建构中的痼疾,女性主体意识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构建。
一、传统婚恋观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影响
人的主体意识是主体的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人的主体意识具有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特征[1],是人们追求解放的一种内在要求。女性主体意识是激发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精神及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内在动机,由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和成就意识等组成。与主体性意识的发展进程相比,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则显得迟缓得多。虽然,女性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但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其主体意识仍处于未成熟阶段。历史地看,影响女性主体意识构建的因素很多,但具有根深蒂固影响的当属于传统的婚恋观。笔者试从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的人物情感来分析婚恋观对女性主体意识构建的影响。根据都梁同名小说改编,由腾文骥执导的电视剧《血色浪漫》讲述了“文革”时期北京大院里一群热血青年上山下乡、从军、创业的情感和成长历程。故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从1968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既记录了从打架斗殴中的“血色”到陕北信天游的“浪漫”,也清晰反映了在当时的国家制度和生活状态下不同性格和不同人生选择的差异性。1968年还在读书的北京青年钟跃民和好友袁军、郑桐整日在大街上游荡。他们为了给单调的生活寻找刺激经常制造恶作剧。也正是在一场恶作剧中,周晓白第一个闯进了钟跃民的情感生活。当周晓白日益沉浸在爱情的快乐中时,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因父亲政治问题不能参军的钟跃民被迫到陕北插队,意想不到的是在贫瘠的陕北他碰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秦岭。对苦难的本能逃避使钟跃民走上了参军之路,而这一选择又注定了他和秦岭的分离。改革开放后,复原转业玩世不恭的钟跃民在军人安置办碰到了同样转业的高玥。共同的对生活的茫然和对自由的渴望又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出于文章主题的需要,我们不对钟跃民这个人物做过多评价,而是把重点放在同他发生情感关系的三个女性身上。
在传统的爱情文化里,服从和柔顺被认为是女人的一个首要标准。男权两性文化要求,女人要一直信奉感情和家庭的观念。女性既是家务的承担者,又是照顾家人的无私奉献者。正是在这样一种诠释下,女性常常把自己连同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创造能力一起奉献给了爱和家庭。应该说,在《血色浪漫》故事发展的脉络中,受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比较深的是周晓白。她出身于高干家庭,父亲是军区副司令,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尽管优越的家境背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使她养成了高高在上的小姐脾气,甚至在爱情上也喜欢主导别人,但是她最终却没能挣脱男权文化的束缚而活出有个性的自我。正统文化的长期熏陶一方面让她乐于接受父母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安排,另一方面也让她承袭了提干走仕途、相夫教子,把命运拴在丈夫身上的传统观念。她喜欢稳定的生活,并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在周晓白看来,在得不到真爱的情况下,婚姻就是每个女性在一定年龄阶段必修的课程,而不管这课程她喜不喜欢。当然,周晓白对爱情的忠诚和执着,我们应该加以肯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份忠诚背后,她对男权文化的秉承。在提倡恋爱婚姻自由的新时期,她竟能为自己无爱的婚姻埋单,并逐渐适应这种徒有虚名的家庭生活。
同周晓白相比,高玥的出身显得有些草根。她从小与哥哥一起生活,因此传统的“稳定”观念对她来说没多少。在生活上,她能在大街上卖煎饼,也能在公司里做白领,还能和钟跃民一起开饭店。尽管高玥身上有着“非传统”的因素,甚至也能打破生活的常规,但是在情感问题上,她却被正统观念所缠绕。一方面,高玥几乎是按照钟跃民的喜好来重塑自己。当他需要她的时候她就会温情出现,而当他不需要她的时候她又能够及时退出。另一方面,高玥从内心深处渴望一份稳固长久、可以终身依靠的伴侣。为此她还就怎么能拴住钟跃民的心去求助于周晓白。尽管她在工作上没有周晓白那样“传统”,但是在感情问题上她却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最终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当然,同周晓白相比,高玥有冲破正统的努力,也有试图打破传统的勇气,这是我们必须要肯定的。
上述女性人物在情感中的表现说明,传统的婚恋观不仅束缚着女性的情感意识,使女性处于被动地位,而且还直接阻碍了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进程。这种陈旧的传统婚恋模式对女性的直接影响就是使其屈求于男性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失落。她们在以男性标尺戒律自己的同时,其精神也渐渐萎顿,双眼也失去了灵性的光辉。对爱情的屈从和对家庭的迁就使女性在背离自己心灵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
二、对男权文化的质疑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正如人类前进的速度不可能整齐划一一样,传统男权观念对女性的影响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也呈多样化态势:既有固执坚守传统观念的正统分子,也有质疑、打破男权文化传统的新形象。以《血色浪漫》为例,如果说周晓白是把自己安置在男权观念的格子中,选择走亿万人都走的常规道路的话,那么钟跃民遇到的第二位女性——秦岭则是试图超越男权文化的典型代表。
同周晓白在婚恋方面喜欢稳定的家庭生活,并把命运系在另一人身上相比,秦岭则更多展示了主宰命运的一面。她的超常冷静和理性以及对自由追求的不羁性格,使她活得从容、淡定而又不失个性。她把人生比作游戏,而游戏的乐趣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当钟跃民向她坦承自己之前有过一个女朋友时,秦岭立刻打断了他的话:“不要提以前的事了,我没有兴趣,因为这不关我的事”。而当钟跃民问她关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生活中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她看似对命运、爱情和前途都漠不关心,但实际上她时刻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从不失去自我。她会因为寂寞而接受钟跃民的爱情,也会因为生活的变化做出新的选择。在钟跃民的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后,她没有答应给他回信,而是毅然放弃了这份感情。在遇到新加坡富商叶楚良之后,她没有因为别人的眼光和看法而逃避和他交往,而是做了他的情人。在这里,抛开她做这种选择的无奈和其中的道德问题,单就她敢于挑战传统,敢从自己的灵魂出发做自己想做的事本身而言是值得肯定的。秦岭似乎并不看重婚姻和家庭,她一直追求的是生活的精彩性,而不是婚姻的趋同性。当然,完整地看,秦岭并非是一个完整的形象,至少她在生活上依靠叶楚良这一事实就是其女性主体意识的很大欠缺。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
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则是实现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应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不仅对女性地位和女性价值进行了肯定,而且还对女性作为主体的权利意识、独立个体的存在意识、对自身未来强烈追求的发展意识以及性意识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应该说,从追求“人的平等”到追求“人的独立、自由”,从权利的剥夺到政治经济的平等无不彰显了两性文化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在“人的解放”主流话语的召唤下及普泛意义上“人”的命名和社会解放价值载体的定位下,女性的解放在人类史上做了一次大跨步。客观地说,这次大跨步不仅实现了女性在政治和经济上与男性的平等,而且也催生了像秦岭这样的女性在情感观念上的觉醒。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的政治的解放不能代替宗教的解放一样,政治的解放也不能代替个人灵魂的拯救。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和政治的独立是精神独立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能直接导致精神和主体意识的形成。西蒙·波伏娃曾经说过,“女性的真义就在于她是一个活的存在,生理上的差别和心理上的什么情结都无法规定她们生命的轨迹,她们是靠自己的价值选择来开拓自己的解放之路的。”[2]女性在被“人”的概念命名的同时还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女人的天性具有双重性,因为她们既是总体社会的一部分,同时还拥有自己的独特性,而女人的独特性只有女人自己才能体会和感悟”[3]。
长期以来,男权社会文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以及社会无形的规训和女性意识中仍旧存在的深层男权文化的疾痼,使女性难以实现其主体建构的艰难蜕变。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不仅使女性的生命主体遭到了时代主流话语的诱惑与背叛,使妇女解放只停留在形式层面,而且也使女性丧失了独立思考、独立行为、独立追求的能力,从而使女性意识彻底迷失在男权预设的文化中。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既是女性发展,改变社会性别中男主女从思想,从根本上取得男女实际平等的关键,也是构建具有平权意识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是个复杂的工程,一方面需要对女性外部的生存环境进行质疑、批判和解构,对千年来由男性话语建构的男权文化进行颠覆和重新界定,对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制度加以驳击;另一方面,在自我意识方面,也需要女性对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行深刻的思考,对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把握,主宰好自己的命运。
首先,对女性外部生存环境的质疑、批判和解构。长期男权文化的统治和压抑,不仅使女性的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甚至连女性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活力也受到窒息。作为父权制体系的从属和附庸,女性不仅被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权观念也将女性“合法”地禁锢于家庭内室之中,剥夺了女性的社会主体性。正如美国学者詹尼特·A·克莱尼所说,“在传统上,结婚是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之间一种终身的伴侣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男女双方的个人资源、爱好乃至身份实现了完全的结合,不论单方在外工作的家庭,或双方都在外工作的家庭,婚姻都是一种经济合作关系。在这种家庭里,女方会优先做家务,照料孩子,而男方则会优先发展他的事业。根据传统的思想观念,一个女性一旦做了母亲,她就不再拥有属于她自己的身份和爱好了。从此以后,她只是满足她孩子需要的工具而已。”[4]女性要获得自我意识,找到自己的身份,首先必须对男权文化进行批判和解构,摆脱父权制的控制。这既包括女性对男权文化所规定的“妻”的内涵做重新的界定,在自身之中和自身之外感知并消除男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好恶倾向和审美标准,不再将恐惧和软弱投射给男人充当其替罪羊,也包括对存在于女性日常生活背后任何残存诗意的剔除和对女性身体的他者化以及女性话语权丧失的批判。女性只有摆脱日常生活的琐屑和繁杂背后的对抗性,彻底铲除虚无与孤独的生存体验,才能通过自我审视来艰难蜕变,实现女性主体的自我认同,确立女性主体生存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正如电视剧中的秦岭,她既不接受凡事都重结果的传统论调,也不喜欢按部就班地安排自己的人生;她不但敢于挑战和打破传统束缚,更敢于实际地超越传统。
女性的外部生存环境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大家庭的逐渐消失,核心家庭结构的形成以及家庭保障功能的减弱,使广大女性面临着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国家政策的保护引导不到位,使女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的共享方面严重欠缺。社会成员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不但影响了男女平等、共同发展和共同受益的原则,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拉大了男女两性的差距。为此,广大女性在破除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健全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质疑。
其次,女性要从心灵深处出发对自身存在的本质和价值进行深刻的思考,对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把握。现代产业的发展的确对男女平等进程的推进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女性要想找到自己理想的位置,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找到自己应有的生存价值,除了要审视和质疑外部生存环境之外,还必须积极探索内在的自我能力和生命价值。今天,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同时也把女性推向了一个知识化的社会。知识既是女性武装自己的武器,也是女性胜任工作和自我发展之必需。如果说以往的妇女解放取决于社会革命和国家法律、制度的保障,那么今天的女性解放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既包括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包括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朱清.《金色笔记》女性视角下的女性主体意识[J].外语研究,2009,(3).
[2] 牧原.给女人讨个说法[M].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247.
[3] 周艳丽.延安文学中女性意识的遮蔽[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4] [美]詹尼特·A·克莱尼.女权主义哲学——问题、理论和应用[M].李燕,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