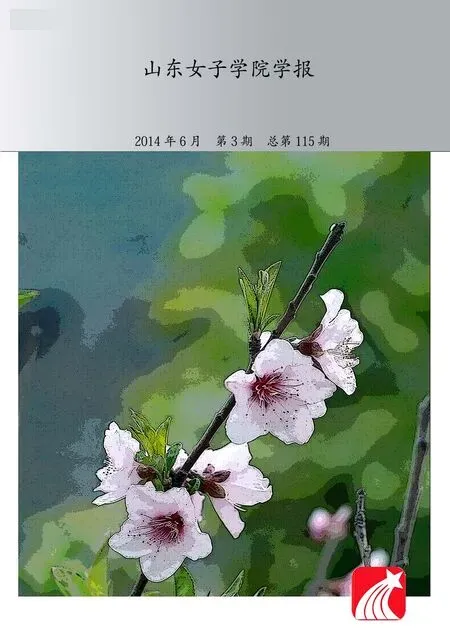论清代女词人熊琏的薄命词
杜 霖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江苏 宿迁 223800)
在中国文化中,“薄命”一词常是人们对悲惨命运探求无果后所表现出的一种宿命论,由此衍生的“红颜薄命”之叹更是史不绝书。明清时代,随着女性文学的繁荣,基于女性生活的悲惨境遇仍未有任何改观,“红颜薄命”成为许多女性作家表现的常见主题。对这一现象,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红颜薄命之说如果洗刷去才子佳人式的陈词滥调的尘埃,那么这四字原本是向封建制度及其统治下的社会的抗诉之辞。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命题,它浓缩进的是无数血泪和鹃魂。”[1](P548)而把这种抗诉引向集中和深化的作家当属活跃于乾隆、嘉庆年间的江苏如皋女词人熊琏。
熊琏字商珍,号澹仙,又号茹雪山人。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尚健在,卒年无考。熊琏“幼颖慧,好读书,喜为诗赋,间出奇句。惊其长老,长益耽之,古文制义俱娴。”[2]作品有《澹仙诗钞》四卷、《词钞》四卷、《赋钞》一卷、《文钞》一卷,以及被当代学者[3]誉为女性诗话发轫之作的《澹仙诗话》行世。清末的词评家况周颐在《玉栖述雅》中对熊琏的词尤其欣赏:“清疏之笔,雅正之音,自是专家格调。视小慧为词者,何止上下楼之别。”[4]刘启瑞则言:“……词则格律高而韵调严,亟得大家之旨;小令则继响南唐;慢声则希声两宋,而于辛稼轩尤为近似……”并誉其为“闺秀中之杰才也”[2]。
然而,和封建时代的许多才女一样,熊琏没有能够逃脱“才女命薄”的魔咒。澹仙自幼即许配同邑陈遵,后陈遵得疾,废,陈家允悔婚,而琏本人则坚持不可,在封建礼教的“烛照”下,熊琏抱着殉道的热情,把教养里的辞藻当成了生活的真理,卒归陈家。熊琏的从一而终之举被时人赞为“大节凛然,尤足昭垂千古也”[5]。然而,熊琏为这些虚誉在现实生活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澹仙在婆家时克尽妇道,30多岁时,婆母死,受到“杂沓群嚣”的欺凌、连“故庐”亦无权拥有的熊琏只得离开“不解事”的丈夫,回到母家①。她后半生依母弟居,以私塾自养。终其一生,熊琏都遭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基于异常悲惨的自我遭遇,“薄命”, 首先就成为了词人对自身命运痛彻的理性思考与抒写。在此基点上,词人又以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浓郁的生命意识,去观照他人的生命存在,在“薄命”主题的逐层突破与推进中完成了词人思想上的“三级跳”。其词作在更逼近人的真实存在的理性思考中显示出沉郁、激愤、峭拔的刚性抒情色彩。
一、自信生来命薄②——对自我不幸的泣血诉说
“诗的活动起点,始终是一种生命体验。”[6]熊琏的薄命体验首先来自于封建社会女性精神的主要支撑点——婚姻。正是不幸的婚姻将她置于四顾茫然的孤独境地。她总是在寂寥愁苦的状态中咀嚼着不幸的婚姻带来的种种不可承受之悲。在她的许多咏怀词中,有很多抒情性强烈的字眼,如 “愁”“恨”“怨”“凄婉”“泪珠”“哭杀”等,所写的景物也是最能触动人的悲凉、孤独体验的“凄风”“苦雨”“雁鸣”“清漏”“冷月”“残灯”……这些抒情布景织就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不幸”罗网:有“深恩未卜,何时能返乌哺”(《百字令·书感》)的人生憾恨;有“天高有梦难寻觅,瑶琴一曲无人识”(《忆秦娥·闲情》)的孤独;有“最堪怜电光石火,年华转瞬”(《金缕曲·感怀》)的惆怅;有“断炊时节春衣典”(《满江红·春怀》)的困窘;有“身后不知谁吊我”(《浪淘沙·寒食感怀》)的绝望……在不幸罗网的裹挟中,词人生发出了对自身命运的无可奈何的哀叹——“不是才人多磨折,自信生来命薄”(《贺新凉·感怀》)。这种饱含悲情的认知使得词人常有被“薄命”感吞噬的痛苦。在《蝶恋花·写怀》一词中,熊琏就细致生动地抒发了逼仄的命运引发的精神风暴:
湖海作风天作雪。浩浩茫茫,何处逃磨劫?薄幸一生真百折,无家燕子秋风叶。 稽首遥空先悲咽,欲诉嫦娥,花外云遮月。偏是深情无可说,冤魂都迸啼鹃血。
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悲剧命运,其心灵必定会发出沉痛至极的悲呼,在一组以“秋”为题的词中,她就将自己对于世间生活的否定与倦怠,凝聚成了寒意逼人的萧条意象:“古冢磷飘,荒阶雨打,六朝败柳西风挂”(《踏莎行·秋魂》);“远魂疑断,蕉雨惊回夜正长”(《鹧鸪天·秋梦》);“荒砌风凄虫语碎,海棠红惨蝶魂消”(《浣溪沙·秋况》);“无雨无风都惨切,况是飕飕”(《浪淘沙·秋感》)。在这种生意寥落、生命悲凉的生存体验中,词人时常产生一种自我毁弃的决绝心理:“把卷无心读。已拼着、烧琴煮鹤,除松砍菊” (《百字令·有感》);“弱息茕茕曾未死,生受消魂光景”(《金缕曲·感怀》)……
同顾贞立、吴藻、秋瑾等人的“天壤王郎”之叹相比,如果说这几位女诗人发出的“薄命”之叹,还只是精神上的痛苦的话,那么,熊琏抒写的薄命之叹,则显现了封建时代一个女性在遭遇婚姻大不幸后空前的生的艰难和心的绝望。她对自我不幸的抒写辐射了古往今来众多被损害和侮辱的妇女的生命状态,其作品更具有“诗史”的性质——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看到了那些曾经矗立在中国古老乡村、街市中的“贞节牌坊”上的斑斑血泪——那些在人们面前总是显得贞方、贤淑、持重的烈妇们,该忍受着怎样的身心煎熬。
二、薄命千般苦——为同类者挥毫吐气
把熊琏从自我不幸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一种力量,乃是她在不幸婚姻的废墟上重新建起的新的人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转折与确立在她的一首词作中有鲜明的传达:
灯昏斗帐,叶想空阶,虚壁风来枕底。正痛苦无端,凄然欲涕。种种旧恨新愁,都并在、五更钟里。怎禁它,梦又难成,起还未起。 如此。铄骨销魂,问弱息何堪,浮生有几? 想落落乾坤,茫茫青史。多少锦绣心传,幸千古、才人不死。且强自,拥被清吟、放怀高寄。(《凤凰台上忆吹箫·病中不寐》)
在这首词中,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词人对不幸命运的痛楚体验,但在“问弱息何堪,浮生有几”的生命价值的探寻与思考中,词人最终发出了不甘沉沦的生命呼喊:“多少锦绣心传,幸千古、才人不死。且强自,拥被清吟、放怀高寄。”这种要用文才来实现生命救赎的价值观的确立,使得词人能够放眼身外,发现与自己具有相同命运的女性实在数不胜数。她们所遭遇的苦难激起了词人强烈的义愤和使命感。试看其《金缕曲》:
薄命千般苦!极堪哀、生生死死,情痴何补?多少幽贞人未识,兰消蕙息荒圃。埋不了、茫茫黄土。花落鹃啼凄欲绝,剪轻绡、那是招魂处?静里把,芳名数。 同声一哭三生误。恁无端、聪明磨折,无分今古。玉貌清才凭吊里,望断天风海雾。未全入、江郎《恨赋》。我为红颜聊吐气,拂醉毫、几按凄凉谱。闺怨切,共谁诉?
可见,对同类女性命运的发现与思考,使她的心灵脱离了对于自我不幸境遇的沉沦,词情显得慷慨奋起:“我为红颜聊吐气,拂醉毫、几按凄凉谱。”这可以说是词人向世界发布的人生宣言。在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支配下,词人曾为过往女性中的薄命者作有“感悼词”数十首,集名曰《长恨编》。可惜这些词作未存,但在词钞中仍有为数较多的反映女性薄命的词篇。这些女性有历史上的红颜薄命者,如王昭君、西施等,也有生活在澹仙身边的不幸者。对于女性薄命的遭遇,许多男性文人也曾表示过同情,但男性文人的写作大多数缺少强烈的自我生命感受。相比起来,熊琏的抒写,则是以“仆本恨人”同人式的贴己体验来检阅这些女性的生命存在。邻女归宁母家,离别前伤心悲啼,澹仙“闻之恻然”;富家女远嫁他乡,归宁叙海上风景之苦,澹仙亦为之唏嘘不已;而里女陈氏夭折,更让澹仙为之伤心痛哭:
佳人沦落,讶诗书未习、天然绝俗。生小蓬门知礼数,邻里争传贤淑。不厌荆钗,能甘菽水,想见如冰玉。含凄敛怨、双眉那肯轻蹙。 可怜一载姻缘,百端磨折,转眼天年促。断送青春愁病死,说甚洞房花烛。薄命如斯,幽闺谁念,我为伤心哭。霜摧雨打,芳兰竟萎空谷。(《百字令·陈氏女》)
词中所写陈氏女在《澹仙诗话》中亦有记:“里女陈氏,生长寒微,素行贤淑。夫家贫,不能娶。百计借贷始克成礼。于归后,女脱簪珥以偿。未几,夫翁以他事致讼,累女焦思成疾。不一载,卒。”[7]从中可见,陈氏女是那个时代被闺范驯服的“典范”,她在沉沉的暗夜中,循着礼法的轨道,始终以牺牲奉献的人生姿态对待自己的丈夫及其家人。然而,就是这样典型的妇道仪范,美好的生命之花还没有开放就遭遇“霜催雨打”,“断送青春愁病死”。是怎样的“霜”与“雨”使“芳兰竟萎空谷”?这里既有所指,又无坐实,词人词情激烈,着力点就在于控诉那不可知的杀手——“命运”。
经受过深重的磨难,也就更能体会那些无法言说的女性生存的痛苦。在令广大女性窒息的封建秩序中,熊琏自觉地扮演着广大妇女代言人的角色。在表现女性不幸命运时,她常把自身生存体验中获得的薄命感推而广之为对整个女性命运的解读和思考——“须知道、无多绝代,同兹命薄”(《满江红·明妃词》)。这是有意识地把女性群体置于整个历史环境中的一种思考,意味着熊琏把女性的苦难有意识地提升为一种历史经验贯穿诗史,这种具有鲜明女性生存悲剧意识的抒写因此也就获得了一种哲学高度。从其旗帜鲜明的创作态度、立场以及词作量来看,熊琏可谓是近古女性文学史上具有女性主义写作特征的先行者。
三、自古才人都冷落——超越性别的慷慨悲歌
“古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有感》),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不仅造成了女性的悲剧,同样也造成了众多的“士不遇”。白居易在悼念李白时说:“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白居易《李白墓》)古往今来,像李白这样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的薄命诗人实在是数不胜数。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史有很大部分就是诗人的“不遇史”。处于南北文化交流中心的如皋,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明亡后,如皋诗人冒襄以家中的水绘园为中心,延揽天下奇杰,一时聚集了众多才士。冒襄与当时的歌女董小宛的浪漫故事给如皋这块土地注入了民主与个性解放的活跃因子,并形成了对女性才学欣赏与重视的文化风气。到熊琏生活的乾嘉时代,这种风气仍然盛行。熊琏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很幸运地得到过许多才士的帮助和提携,其中许多是身处下层的“不遇”者。在与这些文人切磋和交往的过程中,熊琏进一步认识到“才人薄命”的法则同样也通行于男性世界。她把这种认识有意识地贯穿于词作中,常使其作充溢着一种按捺不住的愤懑与不平之气。
试看其《沁园春·题片石夫子独立图》:
有句惊人,无钱使鬼,与水同清。望长空万里,萧萧暮景;荒原一带,浩浩秋声。胸里奇书,意中往哲,此外何妨影伴形。余何有?有奚囊锦灿,彩笔花生。 词流从古飘零。唯挥洒千言抒不平。叹青云梦冷,才人薄命;红尘福浊,竖子成名。门掩疏灯,村丛黄竹,风冷霜高鹤自鸣。谁堪拟?似苍松独秀,皓月孤明。
本词开篇即着力突出才士的出众才华和高洁品质:“胸里奇书,意中往哲”“有奚囊锦灿,彩笔花生”“似苍松、皓月”。然而,这样的才士却穷愁潦倒、四处飘零,“长空万里,萧萧暮景,荒原一带,浩浩秋声”,这荒原式的冷落景象正是“词流”们一生冷落的写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竖子成名”的腐败现象。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倒错与无序的有力控诉,凸显了澹仙对社会的批判能力。
在《百字令·题江西吴退菴先生诗草》中,诗人更是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处在所谓的乾嘉盛世的下层文人那郁愤与冷落交织的不幸命运:
愁中展卷,讶伤心,字字穷途滋味。时俗争高薪米价,纸上珠玑不贵。孤棹空江,荒山斜日,木叶纷纷坠。艰辛客况、白头未了尘累。 说甚吊古评今,吟风啸月,都是才人泪。恸哭文章才绝世,清澈一泓秋水。笑口难开,赏音有几?只合沉沉醉。苍茫独咏,瑶笙原吹鹤背。
此词充分展现了才士的“薄命”内涵:世俗之人追逐的是“利禄”之实惠——“高薪米价“,而才士们费尽心血的“纸上珠玑”卑贱得难以维持生计。在封建社会,真正的才士们把对理想的追求变成了一场争取生存的斗争,他们不得不奔走于冷漠的人间,在“空江”“荒山”“斜日”之间消耗着生命,饱尝人世的辛酸和命运的逼仄。但熬至白头,仍然“未了尘累”。贫穷、衰老、压抑、孤独、不遇就是他们体验到的种种人生况味。“说甚吊古评今,吟风啸月,都是才人泪”,词人愤慨之语脱口而出,道出了今古文章乃是才人们的“字字穷途滋味”。在这声声愤慨里我们似乎听到古往诗人们的浩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赠别崔纯亮》);“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弃野藤中”(徐渭《题墨葡萄图》)……
熊琏在闺中叹息自我不幸命运时,常是黯然神伤甚至因成为命运的弃儿而产生自卑感、绝望感,词中充满了对人世的厌倦。然而,纵观熊琏为他人呼号的词篇,则议论纵横,境界开阔,笔力矫健,抒情恣放而快意,其中激荡着慷慨、激愤与不平之气。和抒写女性群体的薄命词篇一样,词人为男性才人呼吁的词作同样有意识地把男性个体的不幸置于广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思考——“花月凄凉,文章歌哭,今古无分别。英雄眼冷、等闲白了华发”(《百字令·有感》)。在词人反复的咏叹中,“才人命薄”成为熊琏对社会历史规律的一个毋庸置疑的论断。严迪昌先生在评论熊琏此类词作时曾说:“文人怀才不遇之悲愤,曾经有多少文字写它、表现它,熊琏以女性手笔竟能为之大挥清泪,这才真正印合着青衫红妆、千古同悲之说了。”[1](P550)这种要为不幸者呐喊的创作态度同样表现在熊琏《澹仙诗话》的写作中,以致于许多落魄诗人发出了“须眉气藉蛾眉吐”③的感慨,把她视为精神上互通的“知音”。
从自我薄命感的抒写到女性群体的薄命思考,以致最终超越性别,将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自古才人都冷落” 的社会悲剧尽纳眼底,这种逐层的突破和推进完成了词人思想上的“三级跳”,从中也显示了“女性词的自励与成长”[8]。不仅如此,熊琏还为后世女作家树立了一个理想的“双性同体”的书写模式。“女性最终解放自己,必须从单纯的性别意识中挣脱出来,把视界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树立人类整体意识。”[9]“一个具有广角视界的作家,必定是个心胸博大的人。一个心胸博大的人,就不会仅仅关注自我的小天地,一味咀嚼个人的小悲欢。放眼世界,面向整个人类,题材会更多、更广、更丰富;文学也会更真实,更客观,更具崇高美。”[9]这些在现代社会中才提出的对于女性写作的期待,在一百多年前的熊琏的创作中已经表现得近乎完美。
注释:
① 熊琏在《先姑忌日追恸二首》诗中有云:“茕茕子媳弱难支,杂沓群嚣占一枝。罗纲自离缘避恶,螟蛉虽续等无儿”,这些词句对其离开婆家时的原因有所交代。
② 本篇凡引熊琏词皆出自熊琏著《澹仙诗钞词钞赋钞》,见南山居藏本,道光乙巳年重刊,金陵杜新孚刻。
③ 此为安徽诗人吴苏桥在澹仙五十岁生日时赠诗中所云。《澹仙诗话》卷三有记。
参考文献:
[1] 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2]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C].济南:齐鲁书社,1996(29).33.
[3] 张宏生.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831.
[4] 况周颐.玉栖述雅[A].唐圭璋.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1(5).4616.
[5] 雷缙.闺秀诗话[C].扫叶山房版本,1925(8).8.
[6] [德]狄尔泰.《体验与诗》[A].诗探索[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49.
[7] [清]熊琏.澹仙诗话(卷一)[M].南山居藏本,道光已巳年重刊,金陵杜新孚刻.
[8] 邓红梅.女性词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313.
[9] 王春荣.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