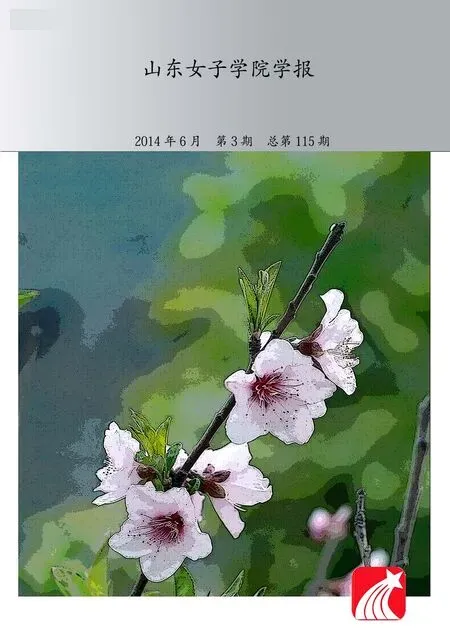芳流剑阁光被利州
——广元“女儿节”女性主体性价值研究
崔显艳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内江 641000)
四川广元皇泽寺的中心大殿为则天殿,殿门上高悬温庭宽手书匾额“则天殿”,两侧是郭沫若亲笔题书楹联:“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上联凸显武周政治方面的突出作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下联强调的是武则天对家乡四川与广元的巨大影响。剑阁古籍中代指蜀地,利州是今日之广元即武则天出生地,女皇是蜀地的骄傲,给利州带来了无限荣光。不仅如此,武则天也是广元“女儿节”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女性主体性价值属性的象征。
一、与传统“女儿节”相比较,从形成背景看广元“女儿节”的女性主体性价值
在旧时汉族的岁时节日里,称为“女儿节”的最突出的至少有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七月初七的七夕节、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关于“女儿节”,元代《析津志》载:“宫廷宰辅之士庶之家成做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邀女流做巧节会,称曰女孩儿节。”[1]明代《宛署杂记》记载:“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2]。《帝京景物略》记载:“九月九日面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日花糕,糕肆标彩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来食花糕,或不得迎,母则诟,女则怨诧,小妹则泣,望其姊姨,亦曰女儿节”[3]。上巳节在今天成为“女儿节”主要受到日本三月三日女儿节的影响,而日本的节日形成与中国古代节日关系极为密切,因此,三月初三也有“女儿节”的别称。
(一)中国传统“女儿节”象征着中国传统女性的客体性特征
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的日子演变成“女儿节”具有漫长历史过程。首先,恶日阶段。因这些日子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曾给人们带来不祥而被视为恶日,除恶是节日中应有的内容,像沐浴习俗的意图就是要以此方式除掉人们身上的污秽、疾病、晦气、不祥之气。如《韩诗》载:“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也。”汉代的阴阳学解释恶日之由,认为这些日子两个奇数重叠,两“阳”相重阳气过旺导致阴阳失调,阴阳失调便会带来灾祸。一旦岁时的演化本身被认为是阴阳的演化,那么作为标志这一演化特殊节点的“节”,与阴阳的变化自然存在对应关系,从此阴阳观念作为一条隐而不显的复线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体系的背后[4]。其次,纪念性与娱乐性凸显阶段。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渐渐将传说与节日联系起来以表达愿望。传说成为节日的灵魂并消解了节日产生之真正缘由,丰富了节日内涵,方便记忆与传播,因此被人们广泛接受。比如真武出生于三月三,屈原死于五月五,牛郎织女相会于七月七,贾佩兰从宫廷中带出九月九日佩茱萸的传说。与纪念性相关的节俗活动的展开大大提高了节日的娱乐性。如踏百草、祭祀真武、吃粽子、龙舟竞赛、祭祖、登高等。再次,元明清之际“女儿节”真正确立阶段。传统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女儿节”的出现与女性社会地位、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息息相关。隋唐以前的女性可以拥有生产资料,士族大家庭的唐朝女性也可以游走于父家与夫家生活,女性身份认同具有两个家族之间的选择性。但宋代以后,女性身份认同只能从夫,与娘家的联系更多局限于精神情感层面,女性的身体被包裹,其双足逐渐被变形缩小,活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明清之前贞洁是社会的一种崇高道德,但明清以后则是妇女的生活准则。男女区分严格,家所辐射的领域成为女性活动的规定边界。元明时代“女儿节”说法的诞生就属情理之中。4个节日在其形成与发展中是全民参与的活动,是男女共同休息、娱乐与交流的盛会,是人们约定俗成从繁重的劳动工作中解放出来追求精神放松并与自然亲近的方式。而“女儿节”的出现则成为女性地位急剧下降、女性主体性特征丧失客体性特征形成的标志。女性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严重缺乏,绝大多数女性的自我意识难以形成,独立人格无以构建,女性成为无知的象征、家的符号、男性的附属,是一种客体性存在。只有在节日期间,社会才会给予女性在相对封闭的场合(家与家之间)游走(归宁)、休息、出现的机会,搭建展现她们才能的平台(乞巧),并给予她们表达其在男权文化下的愿望的机会。
(二)广元“女儿节”的形成彰显出女性的主体性价值
“正月二十三妇女游河湾”,历代传袭至今,已成习俗。正月二十三是广元城乡妇女的特别节日[5],唐末已有。明、清、民国初期,在各种节日活动中,妇女一般不抛头露面,唯独这一天皇泽寺百戏俱陈,摊贩云集,为妇女服务。妇女还划彩绘“龙舟”游河湾,社会、家庭皆予以支持。因正月二十三日是女皇武则天生日[6]。1998年广元建市后,将九月一日至五日定为“女儿节”。这样的妇女活动之所以定于广元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出生于广元,其核心习俗是妇女正月二十三游河湾,尤为引人思考的是明清两朝妇女抛头露面,社会和家庭会予以支持。广元女性活动的形成背景是在广元出现了与最杰出的男性一样优秀的女性,它是女性社会价值或主体性价值的真正体现,并且这一价值是唐以来人们的共识。这一天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在公共场合参与活动,人们以武则天在广元生活过而自豪。广元“女儿节”是在当代中国政府打响文化牌的前提下明确规定并真正定型的女性节日。
广元“女儿节”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空间铺展上都具有浓厚的女性元素,女皇文化成为广元文化的鲜明特色。广元有凤凰楼、则天坝、皇泽寺,有传说(江潭感孕)、有故事(望云铺)、有诗作(以李商隐的为代表)、有碑文(皇泽寺广政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广元“女儿节”参与主体主要都是妇女,她们借此表现女性欢乐,表达女性愿望,展现女性才能,体现女性主体性价值。古代活动有妇女集会游河湾、逛庙会、祭祀女皇等。现代广元“女儿节”活动有凤舟比赛、水上凤舟展示、大型女子综艺晚会、武则天故里形象大使选拔活动、招商引资投资说明会暨项目集中签约仪式、饮料行业饮品展销、对外宣传等。现代广元“女儿节”不仅是女性狂欢的日子,而且充分体现出女性在体育、文艺、经济领域的重要价值。在广元“女儿节”中,女性不是客体,而是主体,由女性主导、女性参与,展示女性风采,表达女性愿望,充分体现出女性的主体性特征。
传统“女儿节”的形成过程是女性从公共空间退回以夫姓为主、父性为辅的家的空间的演变过程,广元“女儿节”恰恰是女性从家走向社会的反向活动。传统“女儿节”虽有祈求心灵手巧的技术性愿望,但仍然囿于传统女性“三从四德”的妇女规范之中,广元“女儿节”摆脱传统女性规范,主动参与公共活动,享受社会服务,展现自身风采,表达个体愿望,并在非主流意识的佛教文化中寻求精神皈依。传统“女儿节”有女性崇拜对象,但广元“女儿节”的崇拜对象主要是来自于真实生活的女性武则天。总之,传统“女儿节”是女性客体性价值的表现形式,广元“女儿节”体现的则是女性的主体性价值。
二、广元“女儿节”核心人物武则天的身世之谜、多样称谓与其丰功伟绩之间的张力是夫权制度下的女性主体性价值的最佳诠释,并映射出父权社会两性之间非单一对立关系的真实存在方式
(一)武则天的身世之谜、多样称谓是父权制度下女性附属地位的象征
武则天的名字、名号多样。“武则天”是后人将她的“姓”和“谥号”组合成的一个特殊称谓。称“则天”是因其在洛阳的则天门上宣布改唐为周,“则天”又典出《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到唐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在编撰《则天实录》一书时特用“则天”二字。但直到近代的所有史书仍将其称为太后或天后,随着近代对她评价的升高,“则天”的称谓才流行。《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明确记载:“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讳珝,并州文水人也。”后人根据女皇在生时某些时代特征及文献中避讳的现象推测其真实名字为华姑、华娘、武约、武华、明空等。武媚娘是唐太宗给她的赐号,武曌是女皇登基称帝时自己的取名。总之,武则天的名字大概为:原名为“武珝”,太宗赐名“武媚娘”,正式名字后世定为“武曌” ,武则天则是近代人们对女皇的称谓。女皇生前名号甚多:有才人、昭仪、皇后、天后、皇太后表示身份的称呼;还有成为女皇后自封富于神秘色彩的吉祥尊号:圣母神皇、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等,退位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 天宝八载被加谥“则天顺圣皇后”(正式的谥号)。
女皇的出生地和出生时间仍然是个谜。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有几种代表性说法。一是并州文水说,理由是武则天曾自称并州人。二是利州(今四川广元)说,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其根据是晚唐诗人李义山《利州江潭作》一诗。1954年修筑宝成铁路时,在皇泽寺出土了《广政碑》,碑正面刻有“利州都督府广元皇泽寺唐武则天皇后武氏新庙记”。三是扬州(今江苏扬州)说,代表人物是吴晗,证据取材于《册府元龟》,武则天出生于武德九年(626年),时武士彟任扬州都督府长史。四是长安(今陕西西安)说,代表人物是陈振、罗元贞(罗元贞驳郭沫若“武则天出生在广元的根据”)。理由是长安元年(701年)武则天于文水为其父立的《攀龙台碑》记载了武士彟的一生经历,是考证武则天出生地最可靠的材料。李商隐的诗作及注带有个人色彩,且是女皇死后150年的事,皇泽寺碑是女皇死后200余年的事,可靠性欠佳。《攀龙台碑》说武德七年武则天出生,而武士彟任在长安为工部尚书,武德八年武士彟任在扬州长史,武德九年任利州都督。还有出生洛阳说[6]等。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没有获得学界的公认,随之其出生时间也难以确定。
女皇名字、出生地、出生时间的含混性立体地标示出当时女性的附属性地位。一个像女皇一样对中国影响巨大的男性皇帝,这一切都应该不太成问题。对于广元女性在正月二十三的活动宋元明清的记载还不如乞巧节详细,以至于成为民间隐约习俗,这一切都与产生这一节日的核心人物的女性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男性经过漫长的斗争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通过文化系统将女性变成一种附属物,剥夺其主体性特征,努力将女性意识束缚于男权文化思想的框架内。牝鸡无晨、主中馈,“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是男性对女性的社会分工;贱内、内人、中馈、拙荆是男性对女性的身份定位;女子无名、女子非子是对女性人格权利的否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是对女性精神与行为限制的道德规范。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武则天的出生时间、地点、名字只不过是极为平常的事情,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与重视,没有成为女皇的武则天婴幼儿时期的状况就是千千万万古代妇女的一个缩影,至于袁天罡预言、乌龙感应都是后人的附会。作为成人后成为女皇的武则天的出生地及出生时间成为文化史上之谜就是理所当然之事,这恰好充分证明了中国文明社会女性客体性的鲜明特征[7]。
(二)武则天的丰功伟绩是夫权制度下女性主体性价值的最佳诠释
文明社会可以用一套文字体系记载历史,但也可以用非物质非文字的方式承载人类痕迹。文明社会可以用一套肯定性价值塑造历史甚至改变历史事实,但肯定性价值中同样透现出非肯定价值的事实。广元“女儿节”就是记载女性主体性价值的民间形式。无论文明社会中主流意识如何排挤女性主体性,但庞大的妇女群体还会在历史舞台上用实际行动证明这一性别所具有的巨大能动性。杨联陞在《中国历史上的女主》中指出,虽然众所周知,传统社会是一个男权和父系社会,但妇女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力,历代女主便是不能忽视的力量[8]。武则天就是女性争取并实现女性主体性价值的最集中、最鲜明、最突出的典型。
武则天是一个诗人、作家、编辑、书法家,写过《女诫》,撰有《臣轨》《百僚新诫》《垂拱集》等著作,亲自撰文并书写的《升仙太子庙碑》堪称传世精品。组织编辑了大量的典籍,如《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列女传》《保傅乳母传》等。武则天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她掌权50多年,开疆扩土,国富民强。女皇还是一个为提高女性地位做出了实际贡献的人。第一,重视女性的劳动。整个唐代皇后只行过8次先蚕礼(重视妇女劳动),武则天登位后仅5个月就亲祭先蚕,身为皇后28年间,亲蚕4次。第二,重视女性的参政能力。在高宗龙朔二年二月更改嫔妃的名衔,将夫人改为赞德,九嫔改为宣仪,婕妤改为承闺,美人改为承旨,才人改为卫仙,宝林改为供奉,御女改为侍栉,采女改为侍巾,皇帝的妻妾变为内廷的官僚,宫中女性有权参与公共事务,重视展示女性在政治或实务上的功能。第三,重视女性在社会中享受与男性平等的受尊重权。武则天屡次接见妇女、把父在为母服延为三年,尊崇老子的母亲,编写妇女书籍,让妇女参与禅让等。武则天给世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称帝。她突破了三从四德,突破了牝鸡无晨、主中馈,突破了男外女内原则,抛弃了传统规范所认同并规范的女人作为妻子、母亲的“从”的身份,使其拥有了和男性一样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一切职能,其行为直接影响到韦后、太平公主等人,使她们敢于挑战男权文化[9]。
夫权制度下的女皇武则天现象展现出女性与男性错综复杂而非简单对立的多元事实而非一元理论的关系,证明了女性在文明社会中的附属定位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当设计的静态制度与妇女多元动态的生活经验相遇时礼法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崩解。母系氏族的余痕、母权的存在、唐代女性的显赫地位、秦淮八艳、清代大量的女诗人群体、三姑六婆的女性职业、观音菩萨的女性造型、大量女性参与种类繁多的生产劳动等等就是生动的证明。女皇武则天的存在鲜活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妇女主体性价值实现的可能。正如费里克斯·格林所说的:初唐参政女性推动的妇女政策无法茁壮发展,不令人惊奇,但女性意识会存在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也不应令人惊奇[10]。现代社会的广元“女儿节”背后潜藏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参考文献:
[1]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20.
[2] 沈榜.宛署杂记[M].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91.
[3]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东城内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4.
[4] 刘晓峰.东亚的时间——岁时文化的比较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2007. 37.
[5] 广元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元县志·社会风土卷·习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821-822.
[6] 王恺.洛阳:武则天的出生地[J].寻根,2011,(5).
[7] 陈振.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和出身[N].光明日报,1961-05-24.
[8] 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女主·中国妇女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
[9] 陈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中国妇女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8.
[10] [英]费里克斯·格林.觉醒了的中国——美国人不了解的国家[M].五岳,初扬,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