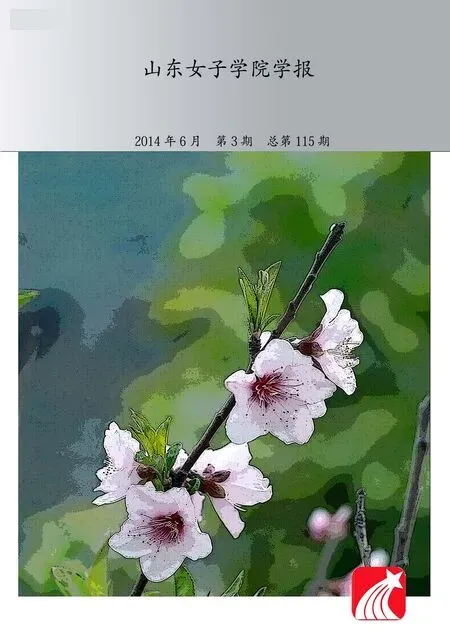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回顾和展望
杜美玲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女性政治参与是指女性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即女性公民通过一些合法的途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以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它包括“女公务员的非职业行为政治参与”和“普通女性公民的政治参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走出国门的便捷、全球互联网及自媒体出现带来的眼界的开阔,公民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越来越多,政治参与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但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并不能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热情。女性作为占中国人口一半的群体,在政治参与中不仅面临着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参与问题,并且还面临着一些带有女性特征的参与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前后相因,绵延不绝,研究中国社会,不从历史观点着手,很难窥探全豹。”[1]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我们首先应考察它的历史源流,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关的特征,为未来的发展做一展望。
一、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三个历史阶段
(一)20世纪初以“女子参政权”为导向的自发式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妇女解放的是维新派,但是他们主张的妇女解放是与“去缠足”“强国保种”等交织在一起的,培养相夫教子的妇女,并未涉及女性应享有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即使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有关于妇女参政的理想,在当时也是“秘不告人”的。当时少数资产阶级妇女在西方进步思潮的影响下萌发了参政意识,在《女学报》上发表《男女平等说》等文章,要求有权“联名上书,直陈所见”,荐拔女性“受职理事”等[2]。不过这时的诉求还只是停留在让少数贵妇参与政事。
正式提出“女子参与政治”的是金天翮,她在《女界钟》中专门用一节讨论了女子参政的问题。当时妇女参政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同男子一起投身革命,推翻清政府。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自由思想高涨,各地的中国女性要求参政权的运动也进入第一个高潮期。但是,随着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1913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被勒令解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也从此消退。
五四时期,西方女权主义被大量介绍进来,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影响中国的妇女运动,并再次掀起了高潮。这时的中国女性认识到妇女参政运动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与社会政治斗争相结合,因此,她们把争取妇女的平等参政权的运动与当时的省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结合起来。湖南、广东、四川、浙江、江西等省的妇女通过积极投入地方的政治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省的新宪法都先后承认了妇女的参政权。但是,随着省自治运动的消失,那些由各地妇女辛苦争取来的,规定着妇女的平等参政权的法律条文也失去了效力[3]。
综上可看出,这时期妇女的政治参与目标明确——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和西学东渐的思潮中,争取“女子参政权”。主体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为主,是在西方先进思想的鼓舞和中国思想先进的男性的支持下自发形成的。但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不具备发展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社会条件,妇女解放需要唤起整个妇女界的觉醒。资产阶级领导的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只靠少数上层知识妇女上书请愿,没有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尤其是广大劳动妇女,以致最后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也说明“在当时”企图通过独立的“女权运动”实现妇女解放道路是走不通的[4]。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劳动妇女逐渐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角,妇女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联结在一起,中国妇女运动的性质也由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女权运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
(二)1949年后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动员式政治参与
动员式政治参与是指民众受到号召、暗示或动员而被动地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实践过程[5]。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主动式的政治参与其实出现过一个短暂的春天。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人数急剧上升,在很多过去没有女性身影的领域都出现了女性。但是由于这时期关于政治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制度更多地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原则规定和宣言上,并没有具体的执行政策和操作程序,缺乏制度化的基础和发展空间,从而使得政治参与很快被动员式的群众运动所替代。
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得一些民主党派的女性受到打击和排挤,中国的政治发展开始偏离正常的轨道,大搞群众运动。1958 年,人民公社运动兴起。自“人民公社化”运动完成以后,在整齐划一的所有制情况下,人们失去了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而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主的利益诉求就被突显出来[6]。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这时期女性的政治参与也主要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导向。
1964年毛泽东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出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句话不仅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之一,也成为推动中国男女平等的动力之一[7]。但是“文革”十年,女性参政是以牺牲女性特质,完全男性化的扭曲发展为代价的。而且群众运动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万能手段,似乎做什么都要搞群众运动,年年、月月、日日都应该搞群众运动,结果使中国社会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之中[6]。致使全国人大的工作从1964年到1975年出现了10年的空白。全国政协及民主党派机关、各地的妇联等组织也被迫停止工作,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完全中断,女性主要以动员式的群众运动方式参与政治生活。
采用动员的方式很容易声势浩大,且因力量集中,也很容易实现预期的影响力。但是这种被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对情绪和非理性的利用,不可能长久保持。因为虽然大家明白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中包含着个人利益,但从个人的角度看这些利益离自己太遥远,难以激发起大众持续的政治参与动机[6]。另外,动员式政治参与是一种没有反馈的系统和环境之间单向的运作模式,不利于政治系统的逐步完善。动员式政治系统并不一定给参与的大众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往往是一次政治运动结束后,参与的渠道也就消失了。因此,这种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靠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的“不断革命”式的非制度化的途径来进行的政治参与,是不现实也是不可持续的[8]。而且事事都要进行动员,都要进行群众运动,已严重干扰和打断了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进程,影响到了大众的基本生活,使得大众对这种动员式的政治参与极度厌恶,广大女性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也大大降低,产生了政治冷漠和政治疏离感。
(三)改革开放后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主动式政治参与
主动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参与行为”[9]。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不再把政治参与视为一种义务,而是把它当做维护和表达自身利益的一种权利,政治参与由一种义务观转为权利观。女性的政治参与也由完全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动员式的义务性参与变为注重“个人利益”的主动式的权利性参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拨乱反正,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广大妇女的社会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政治权利。
1.女党员在党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增加,发展女党员工作得到了增强。1995年全国有女党员891.6万名,占党员总数的15.6%,2000年达到1119.9万名,占17. 4%,增加了228.3万名,提高了1.8个百分点[10]。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女党员中有53.5%是在近10年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女党员2026.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3.8%[11]。
2.女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总体稳中有升,改革开放以来都保持在20%以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女性比例在1970年代后期急剧上升,但是从1983 年初开始受到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影响,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女常委人数比例由21%降到9%。不过,随着人员比例快速下跌问题的日益被重视,从1988年开始女性比例就一直在稳步上升。在2013年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代表总人数维持2987人不变的情况下,女代表由2012年的637人上升至699人,占总人数的23.4%,比十一届全国人大时期提高了2.07%,也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设立以来的占比例最高的一届[12]。另外,女企业家中担任过各级人大代表的有29.9%,高于只有26.1%的男企业家人数[3]。
3.女性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比例基本呈稳定增长的趋势,女性政协委员的比例稍高于政协常委。不过有意思的是,如前所述,女性人大常委在1983年的比例跌到了9%,而政协常委的女性比例在1983年忽然从1978年的7.6%增加到11%,比后来的1988年和1993年的9.7%都高。2013年,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237人,妇女委员399名,妇女委员人选占17.8%,高于十一届一次会议时的比例①。另外,女企业家担任过政协委员的有19.8%,高于只有11.2%的男企业家人数[13]。
4.女性参与农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和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比例在增加。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83.6%的农村女性近5年来参与了村委会换届选举[13]。另据有的学者的调查显示,农村女性在参与选举中,一般会把“能够带领全村致富”“能够为百姓说话”等有利自身利益的人选为村委会主任[14]。城市社区治理有女性化的倾向,城市社区女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比农村女性强,参与的技巧和能力也更成熟化、个性化、自主化[15]。
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利益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同质化、均益化的倾向,这使得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的利益诉求也趋同,没有差异,即在宣传导向上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为重。改革开放后的女性政治参与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分化的利益诉求,再加上女性公民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法制意识的提高,使得女性主体开始由过去的动员式参与者变成为力求实现自身合法利益诉求的主动式参与者。女性的参与积极性在提高,也更敢于以一种主动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来表达个人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比如女企业家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明显提高。这或许是因为女企业家认识到,企业的发展与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因此她们有足够的动力去积极进行主动式的政治参与。另外,许多农村女性也很坦然地承认在参加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出于比较现实的个人利益考虑,她们更乐意选那些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候选人。
二、中国女性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以个人利益为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参与缺乏
这里所指的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参与,与改革开放前的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政治参与是不同的,前者是女性公民“主动”进行的政治参与,而后者很大程度上是被动进行的政治参与。
相较于改革开放前女性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的压抑,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能主动发出自身独特的和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现阶段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仍然还是以个别特殊人物参与为主,涉及的往往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无法反映女性群体的普遍利益需求和政治意愿,其产生的社会回应力也小,对总体政治过程的影响非常有限。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公民接触地方领导人,77.37%的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②。也即现在的女性政治参与偏向于个人的短期利益,缺乏公共精神,较少关注整体或长远的利益,公益性政治参与偏少。
(二)政治参与程度低:比例少、边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出现了主动式政治参与,并且比例在逐渐提高,但总的来说,女性的政治参与程度仍比较低,女性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并未得到充分表达。《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的数据表明,女性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均低于男性公民[16]。《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的调查分析显示,女性被试者的‘实际政策参与’,也即政治参与的“行为”方面,得分(0.27分)低于男性被试者(0.36分)”[17]。
女性主义政治学用“数量性的代表”(Numerical Representation)和“实质性的代表”(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来描述女性的政治参与力度。女性主义政治学对代表的划分旨在强调,女性政治参与不仅要有一定数量的妇女进入政治组织,这些妇女还应具备相当的影响力,特别是应代表妇女利益,积极倡导将性别平等纳入法律和政策[18]。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程度低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从女性在政治组织中的比例,也即“数量性的代表”角度看,女性的政治参与比例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限。
(1)女性参与政党的成员数量明显偏少。从女性政治参与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看到,在中共党员中,女党员人数占党员总人数的23.8%,男女比例处于非常不平衡的状态。
(2)当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女性比例增长缓慢。“议会女议员的比例”是联合国用于衡量各国性别平等情况的主要工具,也是“性别不平等指数”的核心指标之一。到2012年,全世界女议员比例达30%以上的有33个国家,全球国会中女性议员比例比上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 ,达到20.3%。此外,还有15个国家的女议员比例在25%~29.9%[19]。与世界女议员比例不断提高的趋势不同,中国女性人大代表的比例却在近30多年来一直呈现徘徊不前的局面,并且女议员比例的国际排名也从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12年的第64位。2013年的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数量已经高于上一届,但妇女委员人选仍只占17.8%。
(3)女性在农村基层组织中的职位少。许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女党员数量少,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女党员,这影响了妇女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中的职位的比例。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表明,在全国1178个村委会样本中,尚有24.1%的村委会干部中没有女委员,党支部中没有女委员的高达57.6%。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与当前农村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所做的贡献极不成比例。
2.从进入政治组织的女性对决策的影响力,也即“实质性的代表”角度看,女性政治参与者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限。这具体可以从进入政治组织的女性人大代表的影响力看出。
(1)女代表群体往往集“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于一身,被人们嘲讽为“无知少女”。女性中国共产党党员比例只有23.8%,但在其他7个民主党派中,女党员的比例都在30%以上,有的党派如农工党,女党员比例达到了44.1%[20]。另外,据有的学者的相关调查显示,女代表中少数民族占19.3%,而男代表中少数民族占6.1%。
(2)女代表在所属单位多处于较低职位,且多分管非重要领域工作。从女代表所在单位的职位看,她们往往是基层管理者或普通员工,而男代表多担任负责人和中层管理者;从女代表所在单位的类型和所分管的工作看,一般多集中于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且多分管“科教文卫”这些领域,而男性多集中于经济金融等重要领域。
(3)女代表的性别意识不强。从前文可知,女代表比例一直在20%左右徘徊,而这其中有超过60%的女代表在最近一次的人代会上没有提出或附议涉及性别平等或妇女权益内容的提案和建议,有11.9%的女代表对落实促进女性政治参与的政策缺乏动力。这说明女性人大代表将性别平等纳入法律和政策的性别意识不敏感[21]。
(4)女代表从女性视角提出的一些议案受重视程度不高。比如反家暴的提案。2008年起,全国妇联已连续4年向全国人大建言,制定一部国家社会领域的综合性反家暴法。2011年,全国妇联和中国法学会相继向立法机关递交了各自的《〈反家庭暴力法〉专家建议稿》。2013年两会,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晓驷委员提交的提案中,再度呼吁尽快为反家暴立法,但至今仍未有结果。
三、对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展望
(一)中国女性政治参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1.女性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主动式政治参与将继续增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也是一种文化。它注重的是效率,少投入多产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虽然是有限理性的,但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关注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利益自觉性、自主性的增长成为一般趋势,个性的张扬也是社会思想层面的集中诉求。因此,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后女性的个人利益诉求必然会越来越多,女性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主动式政治参与愿望也会越来越强烈。
良好的社会制度应该兼顾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以制度建设减缓二者的天然张力,凸显二者的同一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整体的发展会更好地保护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不会宣扬以无条件地牺牲个人权利、利益为代价追求整体利益,反之亦然。
女性曾经经历了没有政治话语权,及后来的“男女都一样”——女性需求完全被遮盖,女性男性化的历史。现如今的女性能主动表达自身“不同”的利益诉求,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男性不能比拟的。
2.女性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主动式政治参与也将增多。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催促公民社会的生长。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位公民利益的实现都要依赖其他公民利益的实现,因此,对于任何公民个体利益的侵害也会被自然地视作对社会整体的侵害……今天是张三受侵害,如果大家不做点什么,那么明天自己可能遭受同样的侵害”[16]。因此,女性以后不但要继续进行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主动式政治参与,同时,也要为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主动式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逐步树立广泛的公共精神。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一些妇女权利倡导者通过微博、微信互动进行主动式的政治参与,组织了一系列以“公益”为目的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如“美丽的女权徒步”就是为了“防治校园性侵害”,当徒步行走到第46天时,终于获得有关部门积极的回复:“邢台市教育局正在制定相关的防治校园性侵机制和防止二次伤害的意见,并会及时面向社会公开”。这些现象的出现可以视为公民社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女性公民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主动式政治参与增进“公益”的成熟表现之一③。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条文。要求加快实施政社分开,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22]。女性非政府组织应抓住这个机会,争取能以NGO的形式更好地表达女性整体的公共利益诉求以影响政府决策。
(二)中国女性政治参与可能的实现途径
现在女性可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的制度化参与途径很少,而且利用程度也不高;另外,相较男性,女性可利用的政治社会资本较少,政治参与效能感较低。而政治参与效能感低容易导致公民对政治权力系统产生不信任、不支持和不服从,甚至会采取非制度化参与途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进而导致政治体系的失序和混乱[23]。因此,以后应增加女性的“制度化参与途径”及其利用程度,挖掘网络参与的“制度性空间”,使得女性可以继续以主动式的政治参与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或争取公共利益。
1.提高人大、政协等制度性间接参与途径的利用程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在表达、整合民意,并将民意上升为国家意志,及监督公共权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只有高度重视这一特有价值,才能挖掘出人大的“制度空间”[24],从而为女性提供足够顺畅的“表达”个人利益诉求或政治意愿的制度化途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暨立法机关,是“我们这个共和国中最高层次上的、最具代表性的民选机构”[25]。多年来,中国女性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1%左右,2013年才历史性地突破到23.4%。“根据联合国的有关研究,任何一个群体的代表在决策层达到 30%以上,才可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实际影响力……从而保证女性的声音也能在决策层得以表达。”[26]以后应找出女性达到30%比例的困难所在及克服方法,争取早日使女性的声音能在决策层也得以表达。并进一步提高女性代表政治参与的专业能力,多提一些有代表性的、有质量的议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协提案是政协委员向人民政协组织,并通过政协组织向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政府就有关国家或地方大政方针、社会生活等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形式……提案办理有专门机构负责,要求件件有着落,案案有答复。”[27]在有关“女性政治参与”的调查中一些女性不积极进行政治参与的原因之一是“觉得参与了也没用”。因此以后可利用政协提案要求的“件件有着落,案案有答复”的特点,提高女性政治参与的效能感,从而激发女性政治参与的主动性。
有的人仍认为 “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但最近几年我们明显可看到人大、政协的作用在提升,代表们提出的议案也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受到关注。“两会机制”已经成为中国健全制度化参政途径的重要增长点。作为政治生活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女性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到“两会”中,在“两会”机制日益完善的过程中,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实质性地影响政府的立法和决策。
2.提高听证、政策公示参与、政务信息网参与等制度性直接参与途径的利用程度[28]。通过听证制度、政策公示、政务信息网直接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是政治民主发展的特征之一。现阶段中国在立法听证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关方面的制度仍然随意性过强,缺乏规范性;政府期望通过政策公示、政务信息网让大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有的政府部门网站还设立了留言板、领导人信箱、电子信箱等征询民意的联系方式,可是现有条件下政府对大众的诉求和政治意愿做出“回应”的能力仍有欠缺……如果不解决这些制度性直接参与途径存在的问题,女性公民的参与效果不容乐观。
3.挖掘网络参与的“制度性空间”,促使网络参与成为女性进行政治参与的一个新制度化途径。女性群体,尤其是有“家庭和工作”双重压力的女性,以前很难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但随着具有强烈的自媒体属性的微博、微信等的出现,女性也能更容易更自由地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自媒体的平等开放性打破了过去只有特定阶层的群体才能影响政府决策的状况,给普通女性也提供了一个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平台。
如今微博、微信已经成为公民传递信息、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在通过类似微博、微信这样的网络形式进行政治参与,仍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且因其表达平台门槛较低、自由度较高、信息发布便捷,使得大众表达和参与更为直接和情绪化,这其中可能带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再加上相关部门对网络用户并不存在回应的压力,用户的政治参与效能感比较低,参与热情随着微博热、微信热下降也将逐渐降低。因此,应挖掘类似微博、微信这样的自媒体网络参与方式的“制度性空间”,充分利用网络发起话题讨论,与网民互动,以收集不同意见,让其成为女性进行政治参与的一个稳定、持久的制度化途径。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产生何种效果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与政治制度的承载能力;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不及公民参与意愿扩大的速度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29]。因此,女性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的增多和使用程度的深入,不但有利于女性以更主动的方式表达“个人利益”或争取“公共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两性平等政治参与,促进社会稳定。
注释: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共2237人,2013年2月1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② 有的学者把中国公民的这种参与归为对“低级政治”感兴趣。把政治分为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笔者不够苟同,所以没有借用。参见王丽萍、方然的《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具体见微博“美丽的女权徒步”。
参考文献:
[1] 杜正胜.中国式家庭与社会[M].合肥:黄山书社,2012.封面.
[2] 黄锦君.古今女性发展纵横谈[M].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02.
[3] 师凤莲.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研究综述[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80-82.
[4] 李静之.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48-150
[5]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里·沃玛克.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46.
[6] 梁丽萍,邱尚琪.建国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 2004,(5).
[7] [日]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M].姚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序论.
[8] 王婧旖.从动员式政治参与到主动式政治参与的嬗变[D].杭州:浙江大学,2013.
[9] 陶东明,陈明明.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28.
[10] 王立.对我国女性政治参与发展的历史考察[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4).
[11] 全国女党员已超2000万名[N].中国妇女报,2013-07-01.
[12] 2013年“两会”女代表比例首超22% ,超八成大学毕业 [EB/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3-03/07/content_28165697.htm,2013-07-07.
[13] 超八成农村女性近年参与了村委会选举[N].人民政协报,2011-10-24.
[14] 郭夏娟.两性政治参与的异与同——从女性角度看浙江农村的村民自治[J].开放时代,2003,(4).
[15] 孙璐.城市社区治理的女性化[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16] 房宁.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55.
[17] 史为民,郭巍青,等.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
[18] 王金玲.中国妇女发展报告——妇女与农村基层治理[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19] 全球议会女性比例中国排名64[N].成都晚报,2013-03-09.
[20] 何锡蓉.提高女党员比例 促进性别平等——学习党章的一点体会[EB/OL]. http://dangj.sass.org.cn/show.asp id=932.
[21] 张永英.妇女在人大中的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A].谭琳,姜秀花.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历史、现实、挑战[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39-149.
[22] 三中全会《决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1001-23559218.html,2013-11-15.
[23] 王明生,杨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清华大学学报,2011,(6).
[24] 浦兴祖.用足人大制度的“制度优势”[N].北京日报,2009-02-24.
[25] 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8-32.
[26] 钟丽娟.人大代表女性占比多少为宜[N].学习时报,2013-03-18.
[27] 人大议案与政协提案有何区别?[EB/OL].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74015.htm.
[28] 孙永怡.试析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途径[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6,(3).
[29]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