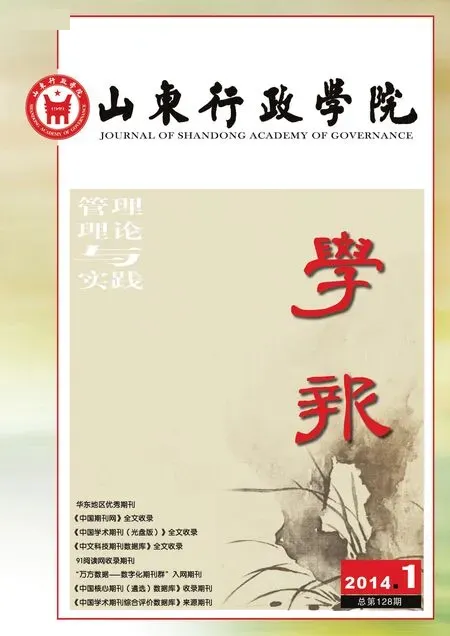组织决策模式研究:基于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程 宇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公共管理系,广东珠海519000)
不管是在公共组织,还是在私人组织中,决策都是最复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决策贯穿于组织的整个活动中,可以把决策理解为组织决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可行方案中,选择其中一个方案。因此,当观察一个组织的运作,尤其是观察政府这种科层制组织的运作过程时,决策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通过组织决策的过程,不仅能关注到不同的组织结构是如何互动的,而且还能关注到组织如何分配注意力,获取并加工信息,如何改变或重新定义规则来影响组织决策过程,最后实现组织目标。组织决策是如何产生的?影响组织决策的机制有哪些?本文旨在对此做有益探讨。
一、理性决策模式——充分信息下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
在对组织决策过程的最早研究中,主流研究范式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采用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这一研究思路认为,人们的决策行为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思考,并由此选择自己的行为,实现个人的目标。这一决策模式通常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或假设:1.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2.人们知道面对的选择;3.人们知道这些选择的后果;4.人们知道并遵守(最大化)决策的规则以进行选择。[1]也就是说,基于这种“最大化”原则的理性决策模式,要求人们同时考虑所面临的所有选择,按照“最大化”的决策规则从中选出最佳方案。根据这一决策模式的四个假设,马奇和西蒙对其基本步骤进行了详细介绍,他们将理性决策的过程分成4个步骤:1.对于组织决策而言,组织目标或政策目标通常被认为是给定的,也就是说它是由外部政策制定者所设定。同样,它假定所有完成目标的替代方案或手段也是给定的;2.所有的替代方案或程序需要接受彻底的分析和检验,以识别他们各种可能的后果,这些后果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3.需要按照价值偏好对这些决策方案的可能后果进行排序;4.最能够实现决策者偏好和价值最大化的决策方案被选择。[2]
总的来看,理性决策模式有两个核心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决策者占有“充分信息”,即人们知道面临的各种选择和这些选择的后果;第二个假设是决策者有“充分理性”,即人们不仅有能力来收集、加工这些信息,而且有能力做出理性的决断。[3]但人们渐渐发现,理性决策模式的“充分理性”和“充分信息”的假设,与现实中的很多情况并不相符。因此,在后续研究中,这一决策模式遭到很多批评。例如,西蒙在观察组织决策的实际过程时发现,人们的决策行为常常与完全理性的决策模式相悖,他认为理性决策模式的前提假设并不符合实践中的决策过程。现实中人类行为至少在3方面偏离客观理性:(1)理性要求对每一种选择的可能后果拥有完全知识和想象力,很明显,关于后果的知识总是破碎的;(2)由于后果发生在未来,在使用价值标准对这些后果进行评价时,必须使用想象力弥补经验不足;(3)理性需要在所有可能方案中进行选择,但在实际决策过程中,通常只拥有有限几个方案供选择。[4]
二、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满意原则”的决策过程
基于充分信息的理性决策模式遭到了批评。之后的研究开始尝试放宽理性决策中的充分信息假设,认为在实践中,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才是常态。由此,大多数研究开始用这两个假设来分析决策行为。在此基础上,马奇和西蒙等人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模式。西蒙等人认为:第一,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决策过程并非是在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从所有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而只是基于有限的信息考虑其中的部分选择。第二,人们在对不同备选方案进行选择比较时,并不是同时对所有的方案进行比较,而是采取循序成对比较的方式,两两比较选择其一。第三,基于实践中的信息并非充分信息,人们也并非完全理性,因此,人们在对备选方案进行选择时,所依照的是“满意”原则,而非“最大化”原则,即一旦在循序成对比较中找到“满意”的目标,搜寻过程即告结束。[3]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以此来解释实际运行中的组织决策。在“有限理性”的假设之下,人们所获取的信息是有限的,并且其加工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们没有能力、也无法在获取充分信息的同时考虑各种选择方案,无法总是在决策中实现效率最大化。[4]无论是作为决策者的个人,还是从事集体决策的组织,都是采取“满意”决策,即从所有可能选择的方案中追求“满意”,而不是追求“最优”。
按照“有限理性”的逻辑,组织的决策是在信息不确定和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的。例如,放松“充分信息”的假设,提出“不确定条件下的最大化”决策模式,其实也就是在概率基础上做出的决策,人们据以决策的信息从“确定性”的知识转变为“概率性”的知识。在这一理论模式下,充分理性这一假设并没有实质的变化。[3]除了认为信息是不完备或不确定的以外,还从博弈论中引入“信息不对称”的假设来分析组织的决策过程。在过去的决策理论中,认为信息是中立的,多多益善。而在博弈论中,多人之间的博弈意味着信息是策略性的,是可以为多方所使用的,而不是中立的。因此,获取更多的信息量并不意味着信息质量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决策参与过程中各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人们可以通过策略地使用信息来达到私有利益。不对称信息的引进是理性决策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以前的理论模式把决策环境看作是被动不变的,不会因为人们的行为而做出反应。但是,在博弈论的框架中,一个人决策必须考虑另外一方的利益、信息和反应。这一理论思路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决策选择可能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的选择;而且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结果。[3]
在“有限理性”的理念之下,马奇对组织决策研究的思想进行了回顾,主要思想包括:注意力分配与组织决策;利益冲突与组织决策;适应型规则与组织决策;模糊性与组织决策。[5]而其中最基础的就是组织中时间与注意力的分配。马奇等认为,在组织决策中,时间和注意力如同信息一样是稀缺资源,组织对某件事情分配不同的时间,投入不同的注意力,其实这本就是一个组织的决策过程。
另外,林德布鲁姆在批评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式时,首次提出了渐进决策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种模式看作是“有限理性”决策模式的延续。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由于时间、信息和成本的限制,决策者无法对所有政策选项及其后果进行充分的评估;由于政治的限制,往往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目标和进行精确的成本-收益计算。决策者一般都认同既有项目的合理性,同时同意延续原来的政策。因此,渐进决策模式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加保守的决策过程。[6]
可以看出,在上述理性模式的演变过程中,有关“充分信息”的假设被大大放松了,但“充分理性”的假设维持不变。尽管经济学家们现在常常使用“有限理性”这个概念来讨论决策行为,但他们所谓的“有限理性”大多是指人们在不充分信息、非对称信息情况下无法达到“最优”选择的状况。在这些信息条件下,人们的行为仍然被假定是遵守理性选择逻辑的。[3]因此,用西蒙和马奇的话来讲,有限理性决策与理性决策的最大不同在于,“理性决策在大杆草棚中寻找最锋利的针,而有限理性决策则试图在大杆草棚中寻找能够用于缝纫的针”。[2]127
为更好地理解在“有限理性”的逻辑下,组织决策的影响机制,学者们在讨论中引进新的变量:组织的规章制度、利益、时间动态、注意力分配、组织学习、组织结构与地位(身份)以及组织内部的动态过程等。
周雪光认为,组织决策常常为稳定的规章制度所制约。[3]大多数组织决策都是规章制度下的循规行为。组织规章制度可理解为作为集体理性、作为背景理性的制度,以此来分析组织决策过程与组织规章制度制定过程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些规章制度决定谁可以参加决策过程,在什么阶段参加决策过程,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进入决策过程,以及决策过程的注意力分配和进程。[3]组织规章制度除了正式制度外,还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和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马奇提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逻辑”的决策模式。其中心思想是:在很多情形下人们的决策过程是受“合乎情理的逻辑”所支配的,这里说的“合乎情理的逻辑”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的制约。[7]马奇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决策过程中面对三个问题:1.这是什么样的情形?2.我在扮演什么角色?3.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的角色应该如何行为?在这个模式中,人们的行为不是像理性模式规定的那样追求最大化目标,而是受到“合乎情理的逻辑”的制约。[8]也就是说,“行动常常更多地建立在规范上合乎情理的认同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计算不同选择的预期收益上”。[9]22
组织内部还存在着不同利益和不同偏好的多样性,这是在理性决策模式所忽略掉的变量。在1962年,马奇就将商业组织看作是一个政治联合体,并认为在这样一个政治联合体中,组织决策会受到各种利益和偏好的影响。马奇这样的描述为我们理解组织决策的过程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对组织决策不仅仅要从组织学的视角进行理解,实践中的组织决策还是一个政治过程,是由组织中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讨价还价、相互妥协和谈判的过程。在这样一种对商业组织的重新定义中,信息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为各利益主体方策略性地使用;组织决策是否能达到理性的目标,不得而知,要受到不同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的影响;各种利益集团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阶段参与组织决策。正如阿利森所言,组织决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组织决策的政治过程应该包括:谁参与了决策制定;什么决定了参与者关于某个问题的立场;什么决定了每个参与者的相对权力;决策过程是如何达到决策结果的,也即各种不同偏好是如何转化为决策的。[10]在组织决策的政治过程中,所强调的是组织并没有预先的目标,一切组织决策过程都是组织中政治权力讨价还价的过程,即便有组织决策的目标,组织的决策过程也不会按照最大化目标进行决策。[11]
在理性决策模式中,研究者的前提假设是信息是明确无误的,并且还是中立客观的。因此,只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就有助于提高组织决策的质量。但是,在有限理性的模式里,信息并非如此。它不仅仅是策略性的,受政治利益的支配,而且在决策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常常是不一致的,其意义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需要加以解释,而且常常被重新定义。[12]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解释活动呢?周雪光提出了三种影响决策的机制:1.人们根据自己过去的经历、经验来解释信息,不同经历可能导致不同的解释。2.人们根据自己的角色、身份来解释信息,不同角色对同一信息可能有着不同的解释。3.不同利益也会导致对同一信息的不同决策。这为我们从微观机制理解组织决策提供了新视角。[3]
以上强调的是理性决策模式的有限性,都是从影响组织决策机制的变量上来分析。那么,组织决策过程是如何启动的呢?周雪光提出了两种启动决策过程的机制:问题导向的决策过程和答案导向的组织决策。[3]在前面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中提到,组织决策追求的是“满意原则”,而不是“最优决策”。组织只有在经历到或觉察到“不满意”的状态时才会启动组织决策过程去解决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许多组织决策是由“问题”诱发的,类似于“救火”式决策过程。[13]那么,组织是从哪里寻找的答案呢?1.可能通过解释历史来寻找答案;2.可能从其它组织的行为中寻找答案,制度学派提出的模仿机制、合法机制可以提供分析的角度。[14]组织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搜寻新的答案呢?只有当它不满意它现在的行为的时候才可能去做这样的寻求。那么,组织如何确定“满意度”呢?组织对“成功”与“失败”这两种状态是如何区分的呢?因为,当组织对“失败”进行定义时,就会诱致组织的注意力转向“问题”领域,启动组织决策过程去解决问题。另外,时间压力这一因素也会影响到组织的决策方向和质量。另外一种决策的启动机制:答案导向的组织决策,是指组织得到一种新的手段、技术或认识角度后便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寻找问题、解决问题。它们为已有答案所驱动。答案导向过程的机制有诸多渊源:1.与制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模仿机制”;2.高层领导的过去经验;3.组织内部的注意力分配和多余资源的配置。[3]
三、垃圾箱决策模式——基于时机的决策过程
虽然组织决策过程会受到组织的规章制度、利益、时间动态、注意力分配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组织决策过程的影响也可能是同时的、平行的,但如果只是分别考虑这些因素,势必会有简化复杂的组织决策过程之嫌,与现实世界相去甚远。因此,需要综合地考虑这些多重的影响因素和过程。“垃圾箱决策模式”正是对这一复杂的组织决策过程的分析模式。
科恩、马奇和奥尔森在1972年提出了“垃圾箱决策模式”。[15]他们认为,组织决策过程表现为“组织化的无序”,这种状态下,组织决策有3个特征:偏好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明确性;参与的流动性。可以说,他们“只是在逐渐放宽理性决策模式过于严格的假设而已”。[16]该决策模式假设,在组织化的无序状态下,需要特别考虑以下四个因素:1.问题流程:不同的问题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逗留、消失的流动过程;2.答案过程: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逗留、消失的流动过程;3.参与过程:不同的人员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和阶段;4.决策机会:各种决策机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分布状况。[15]
这一模式还特别强调,在决策过程中这四个因素是多重、互相独立的。因此,从“垃圾箱决策模式”角度来看,要解释一个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必须从动态过程中认识这些不同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下几个因素尤为重要:1.各种过程相互作用的时间性;2.决策的负荷,注意力的竞争性;3.决策的结构。参与结构是指人们参与决策的规章制度。决策结构决定了决策参与者与决策机会的关系。不同的参与结构和决策结构会对“垃圾箱过程”的互动和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垃圾箱决策模式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特别强调决策过程中一系列通常不为人注意的因素和机制。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重独立的过程同时运行,使得决策的动态难以把握。而且,还在决策中引入了“模糊性”的概念,包括经验模糊、权力和成功模糊、自身利益界定的模糊、最后期限的模糊、智识和意义的模糊等。[17]
但是,这一决策模式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如本多、莫和肖特指责该模式偏离了有限理性的前提框架。[18]他们认为,垃圾箱决策模式与经验现象不符,在经验现象中,问题流程、答案流程、参与流程这三个过程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这一决策模式的结果是对决策过程漫无边际的自由讨论。[15]184另外,如果这些过程之间是相互作用的,那么,这些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呢?这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四、结语
不论是理性决策模式、有限理性决策模式,还是垃圾箱决策模式,都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给我们呈现了一幅组织决策过程的动态画面。如果我们要理解组织实际运作的过程,那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影响组织决策的更深层次机制是什么?如:一个组织是怎样分配注意力的?人们是如何解释历史、解释过去经验的?在复杂的组织中,多重的决策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决策的微观过程,也是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Jeffrey, Pfeffer. Power in organizations[M]. Marshfield, Mass, Pitman Publishing, 1981.
[2]马奇,西蒙.组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西蒙.管理行为(第2版)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5]March, James G. Decisions and Organizations[M]. Oxford, Bail Blackwell Ltd,1988.
[6]Lindblom, Charles E.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2nd edition)[M]. Prentice-Hall, 1980.
[7]March, James. GA primer on decision making: how decisions happen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8]周雪光.组织规章制度与组织决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7).
[9]阿利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 March, J.G.,& Olsen, J.P.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11]李文钊.公共组织决策理论:起源、模型与发展趋势[J].管理世界,2006(12).
[12]李路路,宋臻.“有限理性”视角下的组织决策:基于一个援助扶贫项目的个案研究[J] .社会,2007(6).
[13]Radner, Roy& Michael Rothschild. On the allocation of effort[J]. Journal of Econominc Theory,1975(10).
[14]DiMaggion, Paul& Walter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2).
[15]Michael D.Cohen, James G. March & Johan P.Olson.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2, 17(1).
[16]James G. March & Johan P. Olson. garbage can model of decision making in organization[A]. In James March and Roger Weissinger-Baylom Eds. ambiguity and command. Marshfield, MA: pitman,1986.
[17]March,James & Johan Olsen.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organizations[M]. Bergen Norway:Universeitetsforiaget,1976.
[18]Bendor,Moe,Shott. recycling the garbage can: an assessment of the research program[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 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