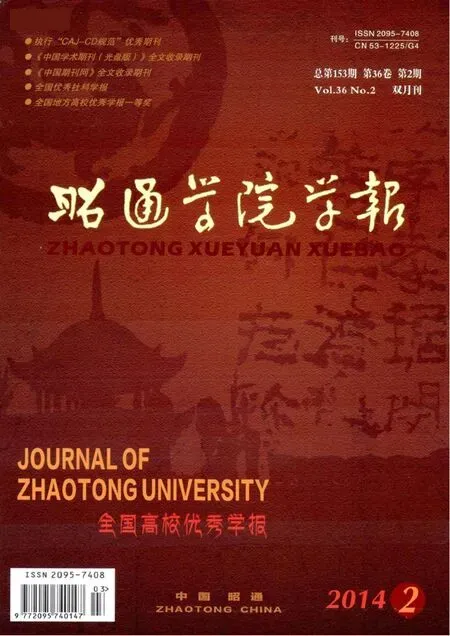基督教与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现代化成因分析
罗 锋
(昭通学院 管理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乌蒙山区是指以乌蒙山脉为核心的自然和行政区的总称①,它是川滇黔三省的结合部。20世纪初,居住在这里的民族有汉族、彝族、苗族、回族、布依族等民族。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在乌蒙山区建立了流官制度,地主经济也逐步确立。但在乌蒙山区的核心地带滇东北、黔西北地区边远民族乡村,彝族土目还大量存在,他们把持了乡土权力。[1](P.6)长期 以 来,乌 蒙 山 区 经 济 落 后、社 会 封闭,各族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但就是在这片封闭、落后的地方,1904年至1949年,基督教循道公会②以柏格理(Rev.Samuel Pollard)为代表的传教士带领苗族群众,在滇东北、黔西北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苗族社会中,通过创办学校、设立医院、创建苗文、设推广部、建立孤儿院、麻风病院、引进西式体育、进行社会改良等一系列措施,发起了一场苗族社会的现代化运动。到1950年,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的“西南教区”建立16个联区,116个堂区(教堂),发展教徒二万余人,并先后开办了13所初级小学、15所完全小学、3所初级中学、4所完全中学、1所护士学校、1所神学校、2所医院、4个联区诊所和两个幼儿园。[2]“西南教区”被西方称为“海外天国”,苗族一跃从落后民族变成“引领”民族,“海外天国”的传奇以及与之相随的苗族社会现代化运动,在中国基督教历史和全球化与现代化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苗族中的“大花苗”作为一个群体几乎全民信教,可以说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在西南边疆历经无数挫折之后取得的重要突破,乌蒙山区以苗族石门坎为中心的“西南教区”成为中国基督教教区的典范;二是在传教士的带领下,在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方,在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少数民族中,建起了一个梦幻般的基督教“海外天国”,而且,这个“海外天国”已经具有西方文明和现代化的一些要素,有了“西化”的一些现象,成为“基督教式全球化”的部分。乌蒙山区的苗族社会开始为西方世界所关注,不自觉地融入了全球化发展进程;三是这场现代化运动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里苗族的命运,促进了苗族社会的改良与进步,而且,苗族也从一个文化落后民族变成中国西南地区的“引领”民族,对乌蒙山区的其他民族也产生重大影响。
在乌蒙山区苗族社会中发生的这场具有宗教意义的现代化运动,看似突兀,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基督教在世界落后国家、地区和民族中广泛传播所形成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也有乌蒙山区苗族希望摆脱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在需要。
一、民族地区“宗教式”全球化、现代化理论分析
关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外著述甚多,观点不尽一致。一般来说,全球化是指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致使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联系日趋紧密,逐渐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和现状。现代化则是指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全球化与现代化关系密切,两者有同源性、同步性、交叉性,全球化包含了现代化内容,现代化则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3]
全球化与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转变过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纵向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横向看,经历了从点到面的扩展,从内容上看有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两种类型,从动因看有内源型与外源型的区别。全球化让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冲破空间限制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现代化则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全球化起源于资本时代,形成于资本主义时期。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P.426)“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 了 一 种 世 界 的 文 学。”[4](P.426)资 本 主 义 在 全世界的扩张产生了全球化,推动了现代化,所以全球化与现代化一开始便主要是“资本主义”化,以致西方有意或无意地把全球化与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和“西化”。近代中国的全球化与现代化也是拜西方列强所赐,经历了抵触、反抗、和被迫接受这样一个过程,中国既不自愿,也不自觉地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
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全球化冲击中,基督教的传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在中国政权中心和沿海地区的全球化所涉及的领域是全方位的,那么,在内地落后民族地区则是一种基督教式全球化。其主要表现:一是宗教的先导性,民族地区的全球化首先接受的是基督教全球化,首先开始的是教育、卫生和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其次才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二是传播的两面性,传教士集基督教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使者为一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在推动全球化;三是领域的局限性,基督教式全球化是服务于宗教传播的,其全球化与现代化活动也就主要局限在与宗教传播有关的西方教育、卫生、社会思想、社会改良等文化领域,基本没有涉及全球化比较重要的西方政治、经济、生产技术等主要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基督教式全球化”,很好地实现了与中国内地民族落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无缝对接,它可以跨越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另辟奇径,直接进入精神与文化层面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先是宗教信仰的“西化”——皈依基督教,再不自觉地进入教育、卫生、社会改良和“人”的现代化与全球化。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19世纪末,当基督教差会的传教士进入乌蒙山区传教时,全球化的触角便延伸到了乌蒙山区。传教士的政治特权,为苗族“打抱不平”的形象以及对苗族的宗教关爱和热情相待,感动了苗族,吸引了苗族,为当时深受民族压迫的苗族提供了一个“学道图变”历史契机,苗族在选择基督教的同时,也就被传教士带进了全球化与现代化。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基督教与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现代化分析
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现代化运动的产生离不开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正是全球化把现代化带进了乌蒙山区,带进了苗族社会中。没有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便不会有苗族近现代基督教式现代化运动的产生。
从新航路开辟、新大陆发现,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疯狂的政治、经济扩张,他们抢占殖民地,建立起世界市场,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地区卷入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和世界市场中,导致世界各国和各个民族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呈现显著的全球化趋势和现象。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自我发展的历史被打断,民族、国家和地区边界被打开,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全球化特征。基督教传教士带来的宗教和文化全球化,使得全球化的意义更加全面和广泛,联系也更为紧密。而且,宗教以及随之而来文化渗透性和影响力带来的全球化远比火炮的冲击效果更隐蔽、更持久,也更容易被接受。
基督教传教士带着神圣使命,一手拿着“圣经”布道、一手带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利器走进了乌蒙山区。早在明末清初时,天主教就进到乌蒙山区的盐津、大关等地,盐津一度是云南教区的所在地。[1](P.159)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北京条约》,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开始进入乌蒙山区的核心地区昭通传教。光绪初年法国天主教进入昭通传教,天主教在昭通的汉族、彝族、苗族中发展一些信徒。19世纪70年代,基督教内地会经四川进入贵阳、安顺,并逐步进入乌蒙山区的黔西、织金、纳雍、毕节传教。受内地会影响,循道公会也在1883年派万斯通(T.G.Vasnstone)和索恩(Samuel T.Thome)抵达昭通,设立传教点开始传教。1888年,柏格理与邰慕廉(Frank J.Dymond)到达昭通。循道公会最初的传教群体目标指向汉族,但却收效甚微,教会甚至一度想放弃在昭通的传教,只因柏格理的执着才得以坚持下来。为了扩大社会影响,柏格理开始利用办医院、建学校、搞慈善、进行科普宣传等方式吸引人们信教。这些做法虽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对于传教而言却帮助不大。但柏格理已经把西方现代化器物(望远镜、幻灯机等)、医疗技术、社会公益思想等“西化”的东西带到了昭通,将资本主义现代化种子播种到了乌蒙山区。循道公会在传教中,重视利用办学校、建医院、搞慈善来促进传教,这就客观上把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也传播进入了乌蒙山区。因此,到19世纪末,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已经开始冲击封闭落后的乌蒙山区。乌蒙山区的各民族,包括社会最底层的苗族,已经不可能再像“世外桃源”那样自我封闭、自我进化了。1904年,当安顺内地会传教士党居仁(J.R.Adam)把在昭通传教的柏格理介绍给威宁求道苗族时,不经意间成就了柏格理与乌蒙山区苗族相结合而产生的奇迹。1904年7月,大量威宁苗族前往昭通柏格理的传教所学道,“有些天他们以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一伙来到!又有几天是六十多个或七十多个!随之来了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四百人!最后,说也凑巧,在一天之中竟有一千名山里的苗族汉子到来!他们来时正值白雪覆地,而必须穿行的山中冷得出奇。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群体!……有一次经我们清点,当晚同我一家一起过夜的就有六百个人。”[5]苗族皈依基督教已经势不可挡,他们就像一叶扁舟般被传教士领进了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主动寻找“救星”,选择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也不自觉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
三、乌蒙山区苗族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希望“学道图变”内源性动力分析
乌蒙山区的苗族是在元、明和清初逐渐迁入的。云南《马关县志》(卷二)所云:“苗族本三苗后裔,其先自湘窜黔,由黔入滇,其来久矣!”苗族分为“花苗”、“白苗”、“青苗”、“黑苗”、“红苗”五大支系,乌蒙山区的苗族主要属于“花苗”支系,也有部分白苗。花苗语系为川滇黔方言,核心区的滇东北、黔西北地区的苗族则为川滇黔方言滇东北次方言。近代乌蒙山区苗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苗族是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他们依附于当地的汉族地主和彝族土目,成为他们的农奴,受到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社会地位低下,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生活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是当地最底层的民族。这时,苗族社会内部还保留着大量的氏族公社残余制度,内部社会管理实行寨老制(寨老制、理老制、六色六巴制、满初、满自与母克制),宗教信仰盛行崇拜天地鬼神和祖先的原始宗教。这种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原始宗教难以解决苗族面临的生存困境,激发苗族的民族精神,慰藉民族受伤的心灵。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起义(1855—1872年)失败后,苗族社会更是遭到沉重的打击。贵州苗族地区,田园荒芜,庐舍为墟,人口大量逃亡,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据记载,起义被镇压后,贵州“上下游废田不下数百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降苗所存户口,较前不过十之三”。[6]苗族悲惨的遭遇,无助的原始宗教,看不见希望的世境,为基督教传入苗族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苗族凭借自身的反抗精神,通过武装起义不能解苗族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水火,依靠传统政治力量官府和彝族土目既无无现实性,更无可能性。谁来拯救陷入灾难深渊的苗族呢?正当苗族在黑暗中寻找救星的过程中,一股新的势力——西方基督教教会出现在乌蒙山区。教会和传教士凭借手中特权成为乌蒙山区的强势力量,连官府都要“礼让三分”,而传教士却热情对待苗族,说苗语、穿苗服,为苗族“打抱不平”,保护苗族,于是安顺苗族便到处宣传,安顺出了个“苗王”(党居仁),上帝派他来拯救苗族。可见,在基督教与苗族的结合中,苗族并非简单出于信仰空白而被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而是有其内源性动力去主动皈依基督教,以利用外国教会势力来“拯救”陷入灾难深渊中的民族,以争取苗族最基本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并进而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发展。
1.苗族在选择信仰基督教时就有比较明显的“借洋自强”目的。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国家在中国获得大量的侵略特权,教会势力在西南地区不断增强,影响日渐扩大。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不仅获得内地传教权,而且还通过“宽容条款”争得了更大的特权,即不管是外国传教士、还是中国信徒都不能因为信仰的原故,受到骚扰和迫害。美国教会传教史专家拉脱勒特指出,“1858年和1860年的条约使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地位起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并且使教会的大发展成为可能。”[7](P.-)清政府这时也再三下渝各地官员,要“厚待传教士”,“务须示以体面”。凡遇民教争执,官府也是一味袒护教会。从此,教会势力大大发展。”[8](P.528)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王朝完全投靠西方列强,教会在乌蒙山区的影响更加扩大。滇东北、黔西北各地军政绅商各界、彝、苗土目皆邀请昭通、安顺的传教士到各地开堂讲道,教会势力一时大兴。[8](P.531)
对教会在乌蒙山区势力坐大,“官怕洋人”这种政治局面,苗族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和亲身感受的。《苗族百年实录》有这样一段描述:“1904年,安顺知府翟鸿锡和咸宁州官邓循卿受上司指令,召集当地豪富绅士共同商议建堂一事,党居仁为在威宁建堂,来回有武装护卫,当时闻者无不奔走相告,有的称‘洋官过路’。从此威宁苗族亲串亲,威连戚,便跟着信仰基督教。”[9](P.77)
2.苗族信仰基督教后,获得了一定政治地位,经济权利受到保护,更加坚定了苗族皈依基督教的信心和决心。党居仁和柏格理在传教中,为了争取苗族信徒和保护信教苗族的权利,都或多或少地利用了传教士手中的特权来维护苗族的利益。党居仁曾经为了追回苗族猎人张雅各被汉族恶霸抢去的猎物,向官府施压,帮其讨回了猎物。安顺苗族第一个入教的杨庆安在教会的培养和帮助下,担任了安顺附廓保董,让苗族为之鼓舞。白马洞的苗族信徒李约翰被安土司毒打致伤后,党居仁要求安顺地方官派人处理,迫使安土司认罪。柏格理在昭通也多次向官府和彝族土司、土目交涉保护苗族信徒,使其免遭迫害。柏格理还在官府对土目任意加租加押不问不管的情况下,亲自出面与威宁各地土目进行交涉,迫使土目收回成命,使得苗族群众免遭土目的横征暴敛。在苗族遭受沉重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情况下,传教士的帮助,使苗族群众看到了希望,他们把信仰基督教看成是能帮助他们跳出民族压迫苦海的唯一途径,把柏格理、党居仁看成是“苗族救星”,于是入教苗民日益增多。
四、传教士在基督教与乌蒙山区苗族现代化运动成因中的个人作用分析
近代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现代化运动,是因苗族皈依基督教卷入传教士带来的宗教式全球化的结果,苗族并不是先知先觉地选择现代化道路,而是因信仰基督教“被”传教士现代化的。“苗族是经由信教才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9](P.79-80)基于这一认识 可以让 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到其现代化的局限性。因此,在基督教与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现代化成因中,苗族信仰基督教就成为其能否走进现代化的关键点。基督教式的全球化背景、苗族的内源性要求都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决定这场现代化运动一定会发生,或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和水平,产生这么巨大影响。传教士在这一结合过程中的个人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基督教在苗族社会中的传教也并不都像柏格里、党居仁这样高歌猛进、成效显著、一帆风顺的,也有一些地方的传教因传教士自身的问题而遭遇挫败。
在争取苗族皈依基督教的传教中,以柏格理、党居仁为代表的传教士身上所具有的宗教献身精神、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格力量是成功吸引苗族信教的关键。柏格理、党居仁都十分同情苗族群众,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为苗族“打抱不平”,在传教和生活中,与苗族同吃、同穿、同住,学苗言、用苗语,对苗族平等相待,尊重苗族,关心苗族,进而感动了苗族,获得了认同。柏格理在第一次到威宁苗族中传教时,“每到一地对苗族都很仁爱。为受害的苗族打抱不平,过去害怕洋人的苗族见到柏格理和蔼的态度,不嫌苗族污垢肮脏和衣服褴褛。因此,苗族村连村、户连户相继到昭通求道读书。”[10]柏格理在石门坎兴办学校、开设药房、医院、建立麻风病院、开展社会改良等现代化运动,一方面是为了传教工作服务,另一方面也是真心实意为苗族信徒做实事,促进苗族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柏格理在进行西方现代化改良、带进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还注重本土化文化建设。他把拉丁文字母与苗族服饰图案结合起来,帮助苗族创制了苗文,实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挖掘和发展了苗族本土文化,大大促进了苗族文化教育的进步。柏格理对苗族的友善关爱以及利用教会特权保护苗族利益的政治倾向,让乌蒙山区长期受到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苗族群众第一次感受到了关爱与温暖、光明与希望,苗族群众把柏格理称之为“苗族救星”,党居仁称为“苗王”,他们争先恐后地投入了“救星”的怀抱。
近代,在基督教全球化历史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教士,有的传教士怀揣着虔诚的宗教使命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把全球化和现代化带到传教之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有的传教士却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文化侵略,为西方殖民势力服务,充当了侵华势力的工具。柏格理显然是前者,他在石门坎带领苗族创建了苗文,建立了苗族第一所学校,首开双语教学,为苗族培养了第一个博士,建立了苗族第一医院等等,全面促进了苗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柏格里等传教士以对宗教的虔诚、对苗族的关爱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把世境不同的基督教与苗族群众在乌蒙山区结合起来,在落后的苗族社会中发起了一场追求进步的基督教式全球化与现代化运动,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双重使命。
1904年至1949年发生在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的这场现代化运动是世界历史朝着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传教士来到乌蒙山区不仅带来了基督教,还带来了全球化与现代化,改变了乌蒙山区各民族自我封闭发展的状况。由于乌蒙山区,特别是滇东北、黔西北地区的苗族受到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最为深重,生活极其艰苦,苗族主动选择了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基督教为拯救自己的依靠力量。同时,由于基督教在汉族、彝族中的传教进展缓慢,传教士也正准备把传教目标选择为“上帝心中的花朵”——苗族。相向而行的苗族与传教士终于在乌蒙山区会聚在一起。因此,基督教与苗族的结合不是简单的单向选择,而是主动的双向选择。这样来理解基督教与乌蒙山区苗族社会现代化成因,就可以找到其深刻的全球化背景、现代化运动与苗族“学道图变”内源性动力之间的必然逻辑联系。
注:①百度百科:乌蒙山区的行政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毗邻地区的38个县(市、区),其中四川省13个县、贵州省10个县(市、区)、云南15个县(市、区,),国土总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2010年末,苗族人口逾100万之多。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于一体。
②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是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宗教会在中国的“差会”,最初称为“优美会”、“圣道公会”,1931年后改为“循道公会”。
[1]东人达.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杨学政,韩军学,李荣昆.云南境内的世界三大宗教——地域宗教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71—172.
[3]王文凯.全球化视阈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柏格理.苗族纪实[J].东人达,译.贵州文史丛刊,1999,(3):86.
[6]罗文彬,王秉恩.平黔纪略(卷十九)[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7]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之三)——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EB/OL].人民网,(2000-12-29).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929/255570.html
[8]武新福.龙伯亚苗族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9]苏文清.威宁苗族百年实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10]沈红.结构域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