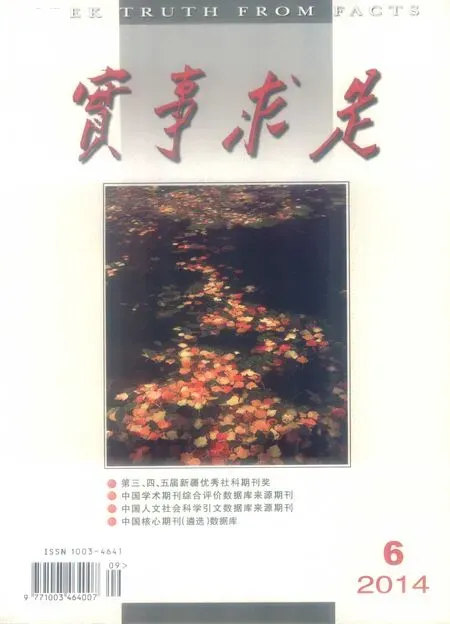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刘嘉尧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0)
经济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刘嘉尧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认为,我们既要从人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又要从自然的需要出发,强调要坚持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先在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特殊性和脆弱性。西部地区构建生态文明,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理论导向,以西部地区生态和社会构成的现实情况为基本依据,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西部地区面积为660余万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约占14.9%,草场面积约占48.1%,耕地保有面积占6.8%,湿地面积占2.8%,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1]近些年来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却总跳不出“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现实情况。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中关于人化自然观的理念,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奠定了基础。要改善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发展模式,必须立足西部地区的实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价值导向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中关于人化自然观的理念,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奠定了基础。面对当前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我们首先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认知。在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过于强调以人自身为中心的理念,认为人类利益是一切问题的中心,如果自然存在物对人类失去了价值,那么对人来说它就没有意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强调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应该尊重自然,与自然为伴,主张消除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主张抽象的“万物平等”。
新中国建国初期,尤其是“大跃进”前后我们的生态意识是“向自然开战”。这种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实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态问题。实践证明,这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死胡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生态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找到了快速发展的契机和平台。但是有些地区简单地把“开发”理解成“开挖”,把发展理解成为简单的生产总值数字的增长。这些行为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退化及环境污染的加剧。针对这种情况,很多学者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把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扭转成“非人类中心主义”,提倡自然与人是完全平等的,其理论基础是超功利主义的自然观。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西部民族地区有着较好的传统文化基础。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且呈现聚居状态,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原始崇拜等宗教文化中非常强调万物平等、保护自然等思想内容。但我们也该理性地看到,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将人和自然的关系孤立起来,忽略了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非人类中心主义”看似解决了人和自然最根本的矛盾,但实际上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并不适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语境,是一种消极的处理模式。西部地区的生态坏境如果只靠单纯的维持和保护,靠自然本身的恢复能力来达到原先的水平,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另外,西部地区生态资源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资源支撑,不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是不现实的。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利用资源的同时,一方面保持生态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又可以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这需要我们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可以找到相应的价值指导。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认为,我们既要从人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又要从自然的需要出发,强调要坚持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先在性相统一。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观”的理论,详细阐述了人与自然间的辩证关系,它所贯穿的不是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也不是今天狭隘的自然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人本主义意义上的生态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要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以单纯的人道主义或单纯的自然主义作为理论基础,都是难以胜任的。我们要将人道主义充分发展以至包含了自然主义的全部合理思想,上升为一种自然人道主义;使自然主义充分发展以至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全部合理思想,上升为一种人道自然主义。[2]只有如此,才能为建立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以及可能给自然带来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同进化与和谐发展。在实践中,人类需要做到超脱自身需要的狭隘束缚,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出发,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自然万物共存共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树立了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是处于自然生态系统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为了人类的永续存在和健康发展,人类既要关注和追求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要尊重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还要在发展生产、提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更加合理、科学地对待自然,保护环境,从而更好地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地球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扬弃的过程,指导我们建立新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指导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西部地区生态问题解决的社会化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P519)可见,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解决生态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实现形式,在这里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前提。人们总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结合方式与自然界打交道,“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4](P344)正是通过社会关系的整合,人们才克服了单个自然人所固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实践活动的存在基础,并规定着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的方式、性质与前景。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关系矛盾的解决,有赖于对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矛盾解决和生态民主缺失的完善。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角度,还是当今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都要求我们将处理好社会关系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前提,重视环境正义和社会公平建设。社会制度构建与社会公平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解决生态问题的一个基本视阈。结合马克思的观点与西部地区生态实践的经验,以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应的完善。
首先,要完善西部地区生态民主,尤其是基层生态民主。美国生态政治学家丹尼尔·科尔曼在其著作《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中讲到:“我们之所以强调基层民主,因为我把基层民主视为生态社会的根本特征和转变活动得以取得成功的中心环节。我也十分强调由社群为本的经济推衍而来的合作和社群概念。在此意义上的社群将成为社会责任、可持续性、权力放下、尊重多样性和生态智慧的组成要素。”[5](P9)
在一个真正的生态社会,我们强调的是生态权益清晰,决定生态未来分权化的民主环境,让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构制度将权力留在行之有效的、离个人家园最近的基层。在西部地区生活的民众,最了解他们的环境现状与发展趋势,有关的决策权和监护权应当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基层生态民主的完善可以更好地降低民族地区因生态问题而产生的不必要的群体性事件,当民意达成一致的时候,生态“暴力”事件就会泯灭在萌芽阶段。
其次,关于国家权力和西部地区生态社会的良性互动方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应当秉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允许公民社会在这个领域中决定自己的生态社会发展。这个公民社会的组成是多元的,它既包括本地的少数民族群众,也包括非政府组织成员,既可是关注生态环境的学者,也包括环境公益企业。西部地区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把握方向,一方面需要不同的声音,这是我们当今提倡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实现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国家权力和公民社会的不断磨合与谅解。但我们要认识到,建立一个长久的、稳定的生态文明制度,需要这种生态政治层面的调试。只有当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真正实现了良性互动,才能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西部地区生态产业的发展
不可否认,近十年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所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速度是惊人的,但在财政数字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却看到那日益枯萎的草原和伤痕累累的山脊。如何从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转变为绿色生态产业模式,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关于“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念,为我们确立正确的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无法循环和持续会同时危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一旦这种“物质变换的过程”超出了自然的实际承载能力,必然会影响自然的正常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从而引发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6]这便是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本质原因。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如何有效地平衡“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进行了详细地阐述,他强调,要“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7](P117)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谈到的这些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正是一种“再利用”或“再循环”的过程。它依据一种“资源——生产——再生资源”的新陈代谢模式来实现物质的不断循环,减少人类社会线形物质代谢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8]当今,我们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从其实现基础上来看就是通过改变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消费模式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恢复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物质循环,消除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裂缝,使人及其社会的发展始终保持在自然所能承载的范围之内,并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可持续的平衡。
在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蓝图中,无论是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思想、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思想,还是生态问题解决的社会制度变革思想等,都是当代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源泉。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确立西部地区生态建设正确的价值导向,通过完善生态民主和制度建设等社会化路径来解决相应的生态问题,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改造,重构西部地区生态产业体系,形成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模式。
[1]清华大学生态环境保护研究中心.西部生态现状与因应策略[EB/OL].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0-12-02/114521571368.shtml.
[2]黄斌.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当代价值[J].理论探索,2010(0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丹尼尔·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赵成.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02).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严文波.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现实意义[J].鄱阳湖学刊,2012(06).
责任编辑:哈丽云
A81
A
10.3969/j.issn.1003-4641.2014.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