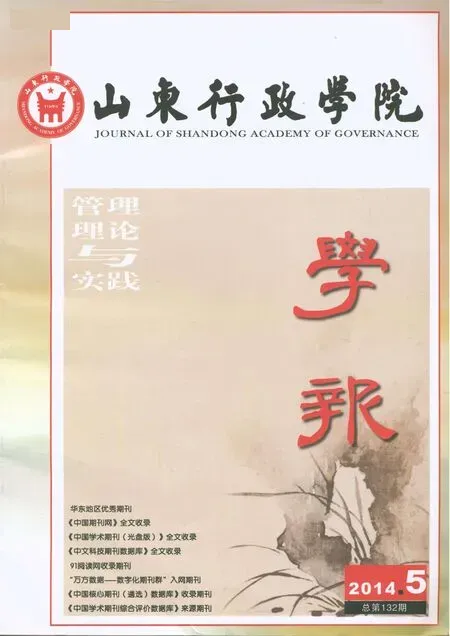论明末士人的休闲意识
——以袁宏道的适意人生观为例
吕红梅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北京100191)
对于明朝末年的士风,大部分学者都认同“浮躁”“狂悖”的说法。此时,肩负着社会诸多责任的士人从专制束缚中摆脱了出来,表现出了特立独行的特征。如将原来炙手可热的仕途视为草芥,追求个人生活的快意,埋头学问,不理世事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作士人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而士人对个体兴趣爱好的追求和肆意发展则可以与我们现代研究的“休闲哲学”相联系。从“休闲”的角度来看明末士人的举动,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成素梅先生在《休闲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当下意义》一文中认为,“休闲”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概念,具有从占有、雇佣、约束中解脱出来的含义,也隐含有“教养”的意思。士人阶层是专制社会中的知识阶层,教养与他们当然是分不开的。士人本来是以入仕、治理天下为己任,在专制时代的入仕,其实就相当于人生自由被统治集团占有了,处世原则由统治集团制定,士人是统治集团的雇佣者。如果不脱离政治,那么就不能说有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明末士人的“休闲”举动不是整个阶层的动向,只为少数士人所享用,在此选取袁宏道为例,探究明末士人休闲意识出现的原因、表现及存在的问题等。
一、政治黑暗,经济发展:士人休闲生活的前提条件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认为,社会哲学产生于社会有病的时候,政治哲学产生于政治有病的时候。那么,明末士人之所以萌发“休闲”意识,也是因为此时的很多人无法正确地对待休闲,无法将自己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求得个性的自由和发展。
士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自愿将自己束缚在政治的包裹里面,终生为君主、朝廷的命运奔波劳累。随着秦汉以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于皇帝一人的效忠逐渐成为了士人们毕生的约束,研究者多以“忠君观念”一词概括。忠君观念贯穿了整个的封建社会,是士人从政或在野都无法摆脱的一个理念。在皇权的束缚下,士人们要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就必须仰仗皇帝的赏识。统治者也注意对忠臣大肆宣扬。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士人就成了政治的附属品,成了君主的思想机器,因此,士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占主流的,“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广泛实行,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不被提倡的,甚至要受到极端的排斥或压抑,思想往往被压抑在狭窄的维度空间而得不到伸展,并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1]而在明末,事情出现了转机。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士人摆脱束缚、追求个性提供了条件。
自明朝中叶以来,政治就开始日趋腐败,万历皇帝长期怠政,宦官专权,官员们拉帮结派,内讧不已,“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正直的官员动辄丢官丢命,朝廷的官位填充没有正常的秩序。“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用”。阁臣们“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2]。这就是袁宏道为代表的士人们所处的大背景。
袁宏道出身于湖北公安的名门望族,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其后在苏州吴县当县令。吴县非常富庶,而在此做县令的袁宏道也治理有方,在任仅仅两年就“一县大治”,此时的袁宏道可谓仕途一片光明。然而,也就是两年之后,袁宏道就以病为借口辞去了官职,开始了四处游玩、寄情声色的生活。从袁宏道任职期间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到,县令一职对他的束缚让他苦不堪言:“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3]繁杂的政务、官场的迎来送往、繁文缛节让他厌倦了政治。而辞官后的袁宏道就可以充分享受个人的喜好了。万历年间,虽然政治日趋黑暗,经济的发展却非常迅速。万历《重修昆山县志·疆域·风俗》中说:“邸第从御之美,服饰珍馐之盛,古或无之。甚至储隶卖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长,往往有僭礼踰分焉。”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旅游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士人的休闲生活成为可能。
二、休闲旅游兴起,在自然中寻找适意
古代专制社会为了防止官员利用地缘关系贪赃枉法,往往会将官员派往本藉之外的地方任职,而官员到了外地正好可以借为官之际将此处的名胜古迹游赏一番。因此“宦游四方”的说法历来有之。到了晚明,随着整个社会旅游风气的盛行,“宦游”逐渐增加了休闲的意味。
袁宏道讲究的是“适意”,即追求自己认为的舒适和快乐。他说世间有四种人:玩世、出世、谐世、适世,而“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是天下最不要紧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离开官场的袁宏道描述自己“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他将官场视作一张“网”,被网在其中如何能快活?辞官后的袁宏道对自然山水的酷爱甚至超越了生命。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过了一年多的快意生活之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了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在京为官期间,袁宏道也在政务之余充分享受兴趣爱好给他带来的快乐。他认为,只要是心境平和,哪里都可以作为隐居之地。他描述自己在京城的生活是“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袁宏道游历了北京的很多名胜古迹,如满井、高粱桥、盘山等,并写下了著名的《满井游记》。袁宏道留下的诗作中极力赞叹游山玩水之乐趣。袁宏道游山玩水的经历即可视作他休闲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游玩使他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解脱了出来,直面了人性,极大地满足了精神需求。现代研究者认为,休闲是人类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才开始关注的问题,袁宏道将妻子儿女安置好没有后顾之忧才开始纵情游乐,不正是与休闲的必要条件合在一起了吗?
袁宏道的旅游生活除了在辞官期间刻意经营之外,还有在为官期间就近游玩名胜古迹。如在陕西任乡试主考官时,他就游历了嵩山和华山。像袁宏道在为官之余或者专门辞官游山玩水之士人绝不在少数。这正是说明了晚明士人休闲意识的觉醒,也是其表现之一。
三、以文载思:士人休闲的文化内涵
休闲又含有“教养”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休闲生活并不是单纯的娱乐生活,它还应该有更深的文化内涵,这也是明末士人的休闲生活不同于大众阶层的主要原因。士人们的休闲生活对大众娱乐具有榜样的力量,而正是因为士人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不会盲从和习惯于大众,而成为他们的引领者。即使是游玩,也会留下优美的文字,为后世追溯美景留下线索。例如,袁宏道并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他还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这些优美的写景文字至今文采充溢,让人神往。
除了休闲旅游,袁宏道还喜酒、茶、花等,《觞政》即是袁宏道品酒、评酒的作品。他还精通茶道,有些结论对于后世爱茶人也颇有影响。袁宏道还专门写了介绍插花艺术的《瓶史》。近代“休闲文学”的倡导者林语堂先生为之感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得从来乱狂呼。”
求禅问道也是袁宏道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从禅中寻求精神深处的闲适。他崇拜“时代狂人”李贽,并与他商讨禅学,深得李贽的赞赏。在京做官期间,他经常与哥哥袁宗道以及一些朋友一起谈论禅道。袁宏道的佛学著作有《宗镜摄录》、《西方合论》、《坛经删》等。在京为官期间,他还作《广庄》七篇,对《庄子》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后世评价颇高。
适意是袁宏道的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在他登第后的十九年中,曾经三次为官,时间持续八年,而剩下的十一年的时间他都是弃官赋闲。可见袁宏道不单受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且由于他是心学的信奉者之一,为了研究心学接受了佛、道思想,进而引发了很大的兴致,心学的入世观和佛道的出世思想在他的身上都有体现,“这造成了他入世不深,出世不力,非儒非隐,非僧非道,造成了他在艰难时世中适意与避世的心态”[4]。
四、纵情声色:休闲生活中的负面信息
美国著名的休闲学家凯普兰认为,任何一种活动都有可能成为休闲的基础;把社会角色所承担的责任最小化;具有自由的心理感觉等都是休闲的前提。在休闲过程中,人们感觉悠闲自得、顾虑最小、最放松。但人又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如果过分强调不合理或者无意义的休闲活动,那就会给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进步带来负面的影响。在明末,士人休闲活动的开展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多消极因素。袁宏道总结对于人生的看法,即有“五快活”之说,这被很多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那个时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书。袁宏道的快活之道就包含了明末士人的狎妓、纵情声色、不考虑结局只注重享受的过度休闲。
晚明士人的休闲意识开始觉醒,袁宏道就是很好的个案。同时,这个时期的士人对于休闲的理解又存在一些问题,如内容过于消极、对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等,都有待于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寻求解决的途径。
[1]向燕南.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J].史学月刊,2005(4).
[2]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袁宏道.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