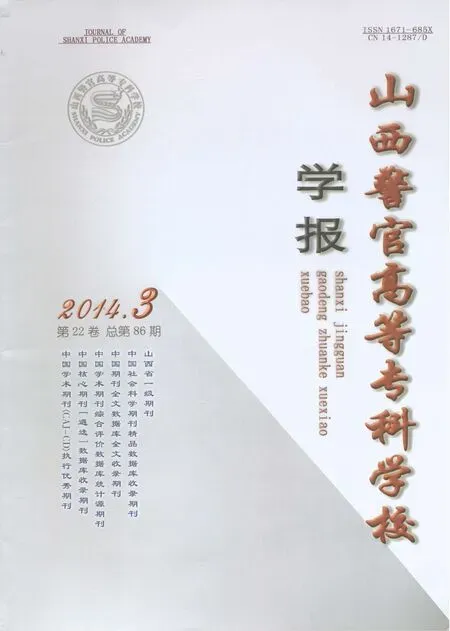试论许诺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
□张冬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刑事侦查与技术】
试论许诺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
□张冬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方法是否具有适法性在学界一直具有争议,近年来关于应对“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策略方法具有一定容许度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许诺的实质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利益诱导,其与引诱的区别何在,在我国侦查讯问中能否适用及如何使用值得探讨。
许诺;侦查讯问;适用
我国刑诉法自1979年开始便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6年第一次修正后的刑诉法延续了这一规定,而第二次修正刑诉法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的草案中删去了“威胁”、“引诱”和“欺骗”字样,基于立法者、专家学者及实务部门的再三权衡,在二审提交的草案中又将其恢复,但是在非法证据排除时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与之前已经生效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关规定保持一致。类似地,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80条规定,“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四)被告人的供述有无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讯问中“严禁威胁、引诱、欺骗”,但对带有“威胁、引诱、欺骗”性的讯问策略方法特别是后两种情况还是有一定容许度的。许诺是指侦查人员承诺犯罪嫌疑人一定利益,以换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侦查讯问中的引诱是指侦查人员给犯罪嫌疑人许诺某种利益,使其供述的行为;也包括采用诱导式发问。从本质上讲,许诺与利益式的引诱都是以一定利益换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其区别在于利益的适法性,因此,许诺可以认为是带有诱导性质的讯问策略方法。
一、许诺的含义
许诺在汉语词典中是指“应允,允诺;同意”,也指“所应允的话”。从字面理解,许诺就是行为人答应、承诺对方所提出的条件、要求或者行为人承诺对方做出某种行为来换取对方做出一定行为;也可以指行为人向对方所承诺的内容。在本文中的许诺主要指许诺的行为。在侦查讯问中许诺的主体是侦查人员,许诺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通过许诺犯罪嫌疑人一定利益来换取其对自己或者共同犯罪组织中其他成员罪行的供述。有学者认为“引诱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利益作为诱饵,即对被讯问人许以某些好处,从而促使其陈述;……二是采用诱导式发问,即在提出的问题中已经包含了答案,通过这种方式提问,旨在要求或暗示被讯问人按预设的答案作出回答”。[1]许诺与引诱的第一种情况具有相似之处,都是以一定利益来换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但是作为非法讯问方法的引诱向犯罪嫌疑人许以的利益法律是不允许的,或是不可能实现的,带有欺骗的性质;而作为诱导性讯问策略方法的许诺是以法律规定之利益为基础的。许诺的方式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主动提出条件,侦查人员根据政策法律规定作出许诺,称之为被动型许诺;其二是侦查人员根据政策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感化,许诺其一定利益,称之为主动型许诺。所许诺之利益为法律所允许之利益,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之利益,如“坦白从宽”、“立功从轻、减轻处罚”等;二是政策规定之利益,如“宽严相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三是人道主义之利益,如对身体虚弱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改善伙食等。不论是主动型还是被动型许诺,其本质都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利益交换,若能对许诺控制到位,无疑是对侦讯双方都有利的讯问方式。
二、许诺在讯问中适用的价值分析
在法定证据时期,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随着诉讼文明的进步,保障人权观念的发展,人们逐渐转变“口供中心主义”的观念,但不能否认时至今日口供在中国哪怕是在全世界都还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犯罪侦查中,甚至在最有效的侦查中,完全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其他可能了解案情的人”。[2]侦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一场较量、博弈,在侦查讯问这场博弈当中,“侦查人员要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口供,而讯问的另一方,即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在讯问中少供或不供”。[3]基于侦查讯问这种利益的冲突性,犯罪嫌疑人会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在讯问中采用各种反讯问伎俩对抗讯问。在缺乏甚至没有实物证据的案件中,侦查工作的开展主要依赖讯问工作的进程,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侦查人员需要采用讯问策略方法,传统上侦查人员多采用压制性的讯问策略方法,甚至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手段,造成对人权和司法正义的践踏,玷污公安机关甚至是整个政府的形象。在当今新形势下,这些“硬”审讯方法已经被时代所摒弃,“软”审讯逐步被实务部门所认可。侦查讯问双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许诺的本质正是为双方提供一个利益交换的平台,许诺的本质就是侦讯双方的一种利益交易,通过交换来满足双方各自的需求。
在讯问中侦查人员的目的是获得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口供,犯罪嫌疑人虽然希望拒绝供述而逃避刑事处罚,但也深知自己所犯罪行迟早会被查清,自己现在供述的态度将会影响到未来所受处罚,因此他们处于拒供与供述的矛盾心理状态。在犯罪嫌疑人这种矛盾心理下,他们也希望通过从侦查人员那里获得一些利益而交代自己的罪行,而侦查人员同样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快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加快破案进度,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侦查人员更希望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达成一种“交易”,获得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节省办案时间,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及时受到法律的惩处。
三、侦查讯问中许诺的适法性
在侦查讯问许诺犯罪嫌疑人一定利益诱导其供述自己罪行是侦查实务中普遍存在的,不仅在我国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只要许诺的利益是法律所允许的,则通过许诺得到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就是正当的,合法有效的。
美国刑事司法专家阿瑟·S·奥布里等著《刑事审讯》一书中包含有 “强烈诱惑法”、“提供帮助法”、“减轻处罚法”等与许诺相关的讯问方法。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禁止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可以看出,德国刑诉法是从确保被控诉人意志自由的角度禁止对其许诺非法利益,但是可以通过许诺被控诉人法律规定的利益来获取其供述。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制度其实质也是控方许诺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罚来换取其对罪行的供述。辩诉交易源于美国,美国司法实践中以辩诉交易结案的占到90%,这种特殊的“许诺”极大地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我国法律和政策中也不乏与“许诺”有关的规定,这些规定为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开展“许诺”的讯问策略方法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如前文所述,许诺之利益为法律所允许之利益,笔者且从许诺利益角度简单阐述一下我国法律与政策中关于“许诺”的规定。
首先,法律规定之利益。即我国法律规定中允许侦查人员在讯问时许给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它包括:(1)坦白从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自刑法修正案八及新的刑诉法将“坦白从宽”纳入法律规定之后,解决了公安机关承诺的坦白从宽处罚在法院以没有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的尴尬局面。我国现行刑法第67条第3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相应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也对坦白从宽的告知作出了规定,第118条第2款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理的法律规定。”当然,刑诉法此处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不单指坦白,还包括自首的情形。(2)自首、立功而从轻、减轻、免除处罚。对有自首、立功情节的犯罪嫌疑人给予从轻或者减免处罚是各国的通行做法,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中也会经常用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罚之利益来诱导、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罪行以及检举揭发同案犯或者其他犯罪,也是在讯问有组织共同犯罪时运用分化瓦解策略的重要基础。(3)不起诉。虽然不起诉决定由检察机关作出,但公安机关在起诉意见书里可以向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建议,因此,对于罪行轻微的犯罪嫌疑人,不起诉的建议也可以作为许诺之利益在讯问中诱导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罪行。(4)快速办案,减少讼累。刑事案件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的讼累也是不可忽视的,为了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讼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先后出台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和《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等多个文件,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简易审来审理案件。人民检察院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前提都是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实施了犯罪为必要条件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会给予一定从宽处理,同时简化办案程序也会极大地减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友的讼累,因此,主动认罪,快速办案,减少讼累,减轻处罚,也可称为侦查人员在讯问中许诺的重要利益。
其次,政策规定之利益。与侦查讯问相关的刑事政策包括两个,其一是“宽严相济”,其二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许诺相关的主要是“宽”,所谓“宽”是指对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未成年人、老年人或在校生犯罪较轻以及存在法定从宽情节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这是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许诺的政策基础,当然,仅仅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许诺缺乏可行性,往往要配合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来换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虽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坚持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其在讯问中适用的效果并不理想,[4]在监所内一度盛行“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种不良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侦查机关在讯问中许诺的从宽处罚在法院往往以没有法律依据而不予支持,极大地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司法公信力。
此外,基于人道主义的许诺以及轻微的不足以影响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的许诺都应该是被允许的。比如,侦查人员对于身体有所不适的犯罪嫌疑人提出“我承认我的罪行可不可以给我改善一下伙食”予以答应;再如,“克莱德,你如实承认这件事,这对你是有好处的”;“克莱德,现在你对此事放一些,这将有助于你在审讯期间获得保释”。[5]由于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的选择,在侦查讯问中想让他们自愿如实供述是较为困难的,讯问策略方法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有限度地允许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中运用许诺的讯问策略方法是成功获得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重要条件。需要说明的是侦查人员许诺时应当明确自己的身份,对从宽处罚、自首、立功等只有建议的权利而非决定之权力。
四、许诺在侦查讯问中的适用
(一)确立司法诚信原则和供述自愿性规则
1.司法诚信原则
在刑事法中,司法诚信原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司法人员代表国家实施的司法行为若不讲诚信,则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势必荡然无存。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运用许诺的讯问策略方法首先必须遵守司法诚信原则,侦查人员不守信的行为虽然是短暂的,但是其这种代表国家而实施的不守信行为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它的示范效应会对以后司法行为的开展带来重大困难。我国司法实践中“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不良风气的形成与侦查人员承诺未能兑现不无关系。侦查人员在讯问中进行许诺,遵守司法诚信原则必须做到:其一,许诺的利益必须是法律所允许的,非法利益不可能实现,本身就是欺骗,并且会严重损害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其二,对犯罪嫌疑人许诺的利益必须兑现,否则,应当排除犯罪嫌疑人因许诺而供述的证据效力。
2.供述自愿性规则
供述自愿性也称自白任意性,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理智清醒和意志自由的前提下自主作出承认其犯罪事实的陈述。西方许多国家都确立了自白任意性规则,自白应当出于犯罪嫌疑人自愿才具有可采性已成为法治成熟国家的共识,我国在确保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特别是在新刑诉法中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不可否认,我国尚未确立供述自愿性规则。确保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是尊重其人格尊严的内在要求,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要求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确保获得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的必然要求。“‘引诱’、‘欺骗’需要作为非法取证方法予以规制,这是因为不适当的引诱、欺骗将损害证据的真实性、取证的正当性,乃至其他合法利益(如司法诚信原则)”,[6]为了防止侦查人员在讯问中偏离许诺的合法轨道,应当确立供述自愿性规则对侦查人员行为作出限制。作为供述自愿性规则的保障性制度,沉默权制度和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也应当逐步确立。
(二)建立许诺规则,规范许诺行为
通过建立许诺程序,规范侦查人员的许诺行为,一方面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另一方面也能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合法、有效。
1.许诺利益及责任的告知
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告知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同案犯罪行及揭发检举他人犯罪、提供犯罪线索得以侦破其他案件会受到从宽处理的情况,并告知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等与许诺相关的法律利益。告知犯罪嫌疑人许诺之利益是侦查人员在讯问中运用许诺的讯问策略方法的基础,犯罪嫌疑人明确自己所处的状态及供述自己或者揭发他人罪行所带来的利益是侦讯双方这种特殊“交易”成功的必要前提。另外,侦查人员还要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许诺的情况下自己供述非真实的法律责任以及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而侦查人员未兑现之责任,以激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
2.许诺结果的确认
当侦查人员的许诺发挥效果,双方达成“交易”时,需要对许诺结果进行固定。许诺结果的固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内容包括侦查人员许诺的法律利益以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内容。固定许诺结果的法律文件应当交犯罪嫌疑人过目,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读给他听,犯罪嫌疑人没有异议的应当签字,侦查人员也要签字,犯罪嫌疑人可以要求驻所检察人员作为证明人签字。
3.许诺后果的责任
许诺后果的责任是指,侦讯双方达成许诺这种“交易”后,一方未履约(虚假供述、承诺未履行)或者毁约(翻供)所带来的法律后果。首先,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如果其供述被证实为虚假供述,或者在以后的诉讼程序中出现翻供行为的,则其应当承担无法得到相应许诺利益的并可能作为其认罪态度不好依据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对于侦查人员来说,若其未按照履行其许诺之利益,则犯罪嫌疑人因其许诺而发生之行为将不具有证据效力。
[1]刘梅湘.刑诉法第43条之反思[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3):89-94.
[2][美]弗雷德·英博.审讯与供述[M].何家弘,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2.
[3]毕惜茜.论侦讯双方的人际交往关系对侦查讯问的影响[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3):70.
[4]何泉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问卷调查与分析[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9(5):7-12,43.
[5][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M].何家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272..
[6]龙宗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的“痛苦规则”及相关问题[J].政法论坛,2013(5):20.
(责任编辑:黄美珍)
ApplicationofCommitmentinInterrogation
ZHANG Dong-ran
(ChinesePeople’sPublicSecurityUniversity,Beijing100038,China)
There have always been disputes on whether tactical interrogation method such as threat,attraction and cheat are legal.The idea that tolerates the tactical interrogation method such as threat,attraction and cheat is approved by more and more scholars.Commitment is essentially an attraction.It is worth discussing that what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them,whether it is workable in Chinese interrogation and how to operate.
commitment;interrogation;application
2014-05-14
张冬然(1987-),男,河南安阳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侦查学。
D918
A
1671-685X(2014)03-0080-04
——以被告人翻供为主要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