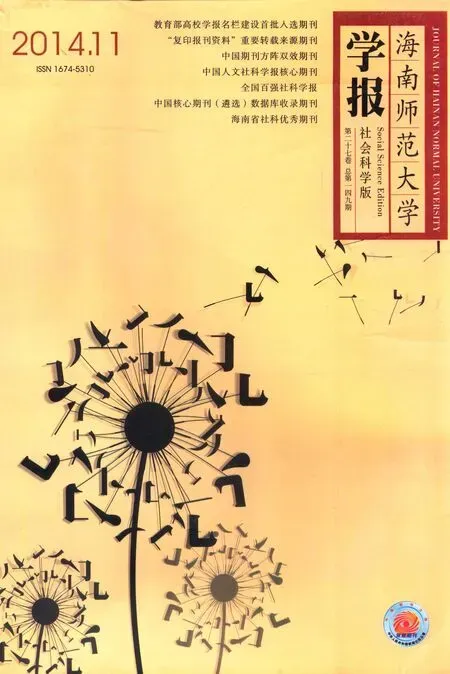文学信仰与批评家的宿命
——雷达文学批评思想论纲
宋俊宏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文学信仰与批评家的宿命
——雷达文学批评思想论纲
宋俊宏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雷达先生以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批评理论探讨铸造着自己的文学批评世界,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理论谱系、批评话语和美学原则,坚守着文学批评的尊严和独立价值,自觉地充当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导航者”和“守夜人”。在当今人情批评、圈子批评、酷评、媚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日嚣尘上,学院式批评走火入魔且大行其道的批评风气下,探讨和研究雷达文学批评思想对进一步认识雷达的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和建设中国化当代文学批评理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雷达;文学批评思想;文学信仰
杨光祖在《雷达论》中说:“雷达怎么30多年来能够一直保持鲜活的阅读冲动,和批评感觉?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天赋好,有超人的直觉。”[1]应该说,杨光祖对雷达先生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但我认为,雷达先生如果仅仅凭借其过人的文学天赋和敏锐的艺术直觉是不能成就其目前在评坛上“这一个”的地位和成就的,更不可能使其三十多年来一直处于中国文学的现场,发出自己独到而且富于穿透力的批评声音的。就像别林斯基说的那样,“敏锐的诗意感觉,对美文学印象的强大的感受力”只是一个人“从事批评的首要条件”。[2]所以在我看来,雷达先生之所以在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关注、思考和批评中国文学,不仅仅在于他有着敏锐的文学感知力和超人的艺术直觉力,更在于他对文学和文学批评在“为时代立像,为民族铸魂”[3]上所具有的其他艺术无法替代的价值的那份执着信仰。
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雷达先生以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批评理论探讨铸造着自己的文学批评世界,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理论谱系、批评话语和美学原则,坚守着文学批评的尊严和独立价值,自觉地充当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导航者”和“守夜人”。在当今人情批评、圈子批评、酷评、媚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日嚣尘上,学院式批评走火入魔且大行其道的批评风气下,探讨和研究雷达文学批评思想对进一步认识雷达的文学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和建设中国化当代文学批评理论都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一
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是雷达文学批评思想的灵魂。1986年9月,雷达先生在持续了将近8年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基础上,在《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一文中首次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文学思想,“什么是艺术作品价值更替和魅力浮沉的秘密?什么是通向获得强固艺术生命和不竭艺术魅力的道路?我们说,这‘秘密’和‘道路’只能是,看一部作品在多大幅度和多深程度上体现出变动着的民族精神和魂魄;愈是能够在纵的历史精神连结和横的世界文化参照下挖掘、重铸民族灵魂的作品,其价值就愈高,超越时空的魅力就愈久。”[4]400这就是说,在雷达先生看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悠久的艺术魅力,首先看其在多大幅度和多深程度上挖掘和重铸了民族灵魂。在这一具有高瞻远瞩的文学思想的指领下,雷达先生在搜索、扫描和评析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时就显得很大气,游刃有余。这在他评论张炜的《古船》、路遥的《平凡世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如1987年4月,在《论〈古船〉》一文中,他认为张炜的《古船》就是一部踏上“对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的“悲壮之途”的“长篇巨制”,称其为我们“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并断定,“即使作为个体的《古船》本身因多种原因湮没了的话(这要看时间老人的脾气如何了),它所奋力开辟的审美途径,在中国、在中国关于农村的长篇创作上,将不可能身后寂寞。”[4]137事实证明,先生的这一论断是精准而有先见之明的。
雷达先生始终坚持文学在“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上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其实是他在坚持一份文学理想——杰出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具备思想性和精神性。因为在他看来,思想和精神是文学之钙,是决定文学品味和前途的最根本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学若普遍缺钙的话,就失去了理想的光亮和审美的热力,这个民族的文学乃至这个民族将是没有任何希望和前途可言的。2005年4月,在《新世纪文学初论》一文中,针对上个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中思想缺席的写作倾向时,他就明确指出:“文学不承担直接表述思想的任务,思想在文学中也并非重要的东西,但没有深刻思想底蕴作支撑,断然不能成就杰出作品。”并引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有关文学与思想关系的论说来强调思想性对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思想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5]133
可是,在当下这个娱乐至死的欲望化消费时代,我们的文学早已放逐了文学的思想性和精神性,开始去政治化,躲避崇高,逃避自由,否弃社会问题,甚至亵渎诸如爱、尊严、信仰、公平、正义、道德和理想等人类的普世价值。即便表现所谓“人性”,也已下降为人的生物属性。只讲本能,不讲精神;只讲下半身,不讲灵魂;只讲快感,不讲耻感。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雷达先生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学的思想性和精神性——“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的批评思想就显得尤其弥足珍贵。他身上那种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魅力也就显得格外迷人,难怪他长期以来一直会赢得无论是同行还是作家与读者的热爱和敬重!
近年来,基于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全面观察和深入研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当今文学,虽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不缺少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但大都“缺少信仰的力量,净化的力量”[6]297,“缺乏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和希望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因此他又提出文学要有“正面的精神价值”的思想。因为他深信,“正面的精神价值”才是文学真正的魂魄。“一个民族的文学倘若没有自己正面的精神价值作为基础,作为理想,作为照彻寒夜的火光,它的作品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它的思想艺术的境界,就要大打折扣。”[5]28他的这一思想道出了有关文学正能量的问题,在当下中国文学严重缺钙而导致的萎缩化状态下,这一思想的提出显得分外沉重,透亮。
二
强化和张扬主体意识是雷达先生在文学评论实践和文学批评理论的探究和建设中始终强调和坚持的原则。上世纪80年代,在《主体意识的强化》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作家的主体意识才是作品价值的立法者,作家的主体意识的深浅强弱广狭决定着作品价值的大小。”[4]43~46但同时,他在《强化了主体之后……》一文中又强调,主体意识不是作家单方面的孤立的绝对的活动,不是作家“自我”凭空的发挥和张扬,而是作家主体在尊重客体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进入客体、把握客体后的“主客体交相感应的浑一境界”。否则,我们就会在“迷信主观可以绝对和无限”的情况下,“弄出些非驴非马,非僧非俗的悖离美的起码规律的玩艺儿。”为此他批评莫言的《红蝗》《欢乐》等作品既得益于他“天马行空”的主体想象能力,但又有着“超出陌生化的极限的明显失控状态”。[7]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雷达先生有感于创作中复制化、拼贴化、制作化现象的日趋严重,进一步提出了灵魂写作、生命写作的观念。他说:“生命写作是个很高的标准,多数情况下,它与作家的亲身经历和血肉体验相联系,常以自述形式出现。将生命外化,用以写外部世界的当然也不少,如文王演周易,孙子修兵法,司马迁著史记,曹雪芹叙金陵十二钗者即是,但作者显然把生命投注进描写的对象中了。总之,以生命写作者,是跳进艺术的火海,让自己的生命与描写的对象一起燃烧殆尽者。”[8]26如果我们以他的这一文学主张为参照,考量当下中国作家的创作的话,我们就会痛苦地发现,当下很多中国作家最缺失的就是灵魂写作和生命写作了。因为当下大多数作家是不甘寂寞的。没有成名的,为了让人们知道他,想尽一切办法要出名;有了名气的,为了让人们不遗忘他,想尽一切办法要保住名气。于是,再也没有作家会静下心来去读书,去体验生活,去几年甚至十几年如一日地精心营构、创作自己的作品了。
在文学批评理论的探究和建设上,雷达先生也一贯强调批评家要强化和高扬自我主体意识,不要成为作家的奴仆,完全看作家的脸色行事。1985年7月2日,他给《文学自由谈》编辑滕云的一封信——《铸造自己的评论世界》中就明确主张:“评论家是人而非镜子,他自有其主体心理结构、气质性格、审美个性的特殊点,他自有其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美学观的侧重点,他完全有权利对他人的作品作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和参悟。与作家的自我解释不同又有什么关系?不同是正常的,处处贴然无间的相同一致,反倒是值得骇怪的现象。”[6]457在三十余年的文学批评生涯中,他始终在坚持这一信念。正是有这一信念垫底,在批评对象时,他总是底气十足,理直气壮,很少受到各种与批评对象本身无关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有优点谈优点,有问题说问题,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自由评说的批评姿态,从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形成了他独具个人魅力的文学评论风格。譬如他对莫言的《檀香刑》的评价。他认为,“《檀香刑》,作为演示刽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但是作为人的文学,不能不说寒气逼人。我总感到,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某种薄弱面。”但同时,他又肯定了《檀香刑》在本土化、民族化创作风格上的独特贡献。
在张扬和坚持批评家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过程中,雷达先生还不遗余力地批评那种失去自我、没有自我的评论者,认为他们仅是“机械地复述作品的机器,是反映现代规范和教条的镜子”[6]459。 特别是近年来,面对人情批评、圈子批评、媚评、酷评、空头批评、好话主义的泛滥,学院式批评的资料化、概念化、复制化的严重倾向,他向整个批评界发出了一声沉重而令人警醒并深思的天问——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9]在他看来,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批评主体的疲软乃至消失。
三
雷达先生在《文学的青春·前记》里曾这样谈及自己在文学批评上的追求,“我追求赤诚和热情,追求犀利和明快,追求‘修辞立其诚’,尽量贴近读者的心灵,热衷于立足‘个别’,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美学评价,来捕捉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在这里,前几个“追求”表明的是他的批评风格,后一个“追求”表明的则是他批评的目的。也就是说,他在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总是企图通过独具个人色彩的批评风格来努力“捕捉”批评对象所蕴涵的“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事实上,我们阅读他的任何一个批评文本都会发现,对作品的当代性和时代精神的挖掘和阐释成了他文学批评思想的一大显著特色。
1984年11月,在《论小说家的转折》一文中,他在分析和批评一些热衷于描写“角落”、热衷于赏玩过时的风俗人情、完全沉醉在古朴美中而时代感非常淡薄的作品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史证明,只有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灵魂’的作品,才有永久价值。”并进一步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生在现世却要‘做’给将来人的作品,不过是心造的幻影。因为,失去了现在,也不会有将来。为现代人,才可能会为将来人接受。”[10]44这就是说,在他看来,作家在创作时不能让自己悬空起来,而要立足于当下,要表现现实生活,要反映时代的灵魂和时代的精神,要尊重现代的读者,要有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的信念,不然,作家及其作品也必然不会赢得读者的关注和尊重,最终走向沉寂、枯萎、湮灭。的确,正如雷达先生在不少文章中引用过的普列汉诺夫的话:“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
在雷达先生看来,文学作品的当代性,“不仅在于它的题材的当代性,而且在于它所具有的时代精神,它对生活所作的富有当代性的艺术阐释。”[10]150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当代性决定于作家主体意识的当代性。如果作家的思想是陈旧的,即使他书写的是当代生活,那他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思想精神也依然是陈旧的,没有活力的;相反,如果作家的思想是当代的,即使他书写的是历史题材,那他的作品显示出来的思想精神也仍然是当代的,新鲜的。在《转型中的文学》一文中,他对作品的当代性和时代精神又作了更全面的概括和阐释,“我不主张用‘回到文学本身’的提法。如果硬要给文学找个‘家’,那就是寻找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连结,借用周介人同志的话,文学的生命‘就在于对当代生活强有力的吐纳,对民族的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强有力的关注。’”“我们强调寻求文学与时代精神连结;当然绝非停留在题材现时性的浅表层面,满足短视目标,而是追求创作精神的当代性,那就是立足于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对民族精神历程的反思和当代性揭示;及于此,无论什么题材都能实现与时代的精神连结。”[8]54
他对文学作品当代性的追求所带来的另一批评特色就是他对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的追求。关于文学作品与时代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雷达在1982年4月的《答问》中就有着充分而精辟的表达:“真正能够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与人民血肉相连,喊出人民的心声、理想、情绪的文学,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镜子’,‘时代的灵魂’。”[11]时隔30年后,他在《地气·人气·正气》一文中又重申这一观点:“人民对忘记他们,脱离他们的作品,从来是不感兴趣的,只有通过作家这个个体的心灵,写出人民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传达出人民心声的作品,才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作家如若冷淡了人民,远离人民,过度自恋,只迷信内宇宙,他的创作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丢掉了人民,也就丧失了人气之源,其作品至多是昙花一现。”正是因为他对人民性的这一独到识见,在他三十多年的评论生涯中,他始终密切关注并热情地评论着那些表现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疾苦和生存、发现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作品及其作家。
四
本土性或者说民族化是雷达先生文学批评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是国内文坛狂热追逐西方现代思潮的时候,也是国内文坛不断“蜕变”并产生“新潮”的时候,就像黄子平曾形象而生动地概括的那样,“新观念像条狗,撵得人连撒尿的工夫都没有。”雷达先生虽成名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我们在雷达先生这时期的评论文章中却几乎看不到他对某些西方现代理论的直接引用乃至生搬硬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就没有受到各种“新潮”的影响,就像他在《蜕变与新潮·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倘若在今天有谁封闭而满足,那真是要把灵魂押给恶魔靡菲斯特做俘虏。”“我所抱的似乎仍然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更注重表现时代运转,生活流动,贯彻着现实主义精神,散溢着人民意识的作品的文学观念。”[10]436而是说他在接受并吸收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同时,总是不忘自己评论的是中国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中国社会出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总是能够做到在接受并消化的同时,结合本民族的文学的实际情状将其创化为有益于发展和繁荣本民族文学的思想。
纵观雷达先生三十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本土化、民族化是其一直倡扬和坚守的文学理念。1986年1月,在《在蜕变中奋进》一文中,面对1985年中篇小说创作中呈现出的“探索、尝试和更新、蜕变”的可喜势头,他在欣喜的同时又冷静地指出:“当前小说形式的创新是生活和文学发展的必然现象,但要保持这种新形式的生命活力,唯有不断输入当代精神的血脉。在形式的横向移植和纵向继承上,首先要问,是否找到了民族魂、中国气,这样不论你是魔幻手法,还是笔记小说,都会令人赏心悦目。”[10]147进入新的世纪,在全球化语境咄咄逼人的情势下,他又在不少文章中反复强调文学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的风格和精神。譬如他在《小说进入21世纪》中说:“在新的世纪,全球化的倾向肯定要比本土化的倾向更为强大,势不可挡,但本土文化仍然是基础,异质文化只能在被筛选,被改写的情况下融入。所以,我们的小说要在不断吸纳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紧密连接本土现实生活的血脉和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刺激的情势下,强化自身的活力。”[8]153在《读〈带灯〉的一些感想》一文中,他就赞许贾平凹长期以来在民族化、本土化和中国经验表达方式上的努力。“我认为,贾平凹从早期的青春写作,到二月杏,到黑氏,到天狗,再到浮躁,到废都,到病相报告,到高老庄直至带灯,他一直在求索着世界背景下的民族化书写,或世界语境下的中国化,本土化写作,求索着中国经验的表达方式。”认为《带灯》就有“汉魏风骨的表述,有的行文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面简劲的,明快的,言简意赅的短句子”。
在文学批评理论上,三十多年来,雷达先生也一直努力构建本土化、民族化的文学批评理论。上世纪90年代,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文艺思潮,国内批评界大多数人对之趋之若鹜,纷纷拿起这些尚未来得及消化吸收的“新潮”武器来批评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各种文学现象。对此现象,1995年他著文批评道:“‘新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现代批评等等,名目繁多,晃人眼目,全都进来了,十分热闹,总体上活跃批评,是大好事,但循名而责实,有的只是引进了一堆术语,消化谈不上,结合我们的国情和文情加以改铸就更谈不上。说句笑话,有些引进不过是换了个说法,如‘一堆胡萝卜’,改称‘胡萝卜系列’就是了。”[6]470因此,他非常看重和欣赏那些结合了中国本土创作经验,把西方各种文论完全中国化的批评文章,如他对何向阳的《复制时代的艺术和观念》一书的赞许,“《复制时代的艺术和观念》中的‘复制’或‘复制时代’的概念无疑是从现代西方文化论著中借来的,但文章所举事象,展开的分析和归纳,却是从当代中国的人文语境出发的,而且充分中国化了。”[8]530但这不意味着他就拒斥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而是以宽阔的胸襟和高远的眼界吸纳西方各种健康的有益于创建本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文艺批评理论资源,就像他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晋舒瑜的访问时说的那样,“我不否认马列文论对我的影响很深,同时,19世纪的别、车、杜以及后来的泰纳对我影响也很大。新时期以来我还是注意吸收国外社科的思想成果的,我既喜欢读斯宾诺莎、叔本华、尼采、萨特、加缪,也喜欢读本雅明、巴赫金、福柯、伊格尔顿、杰姆逊,但都不系统,随兴之所至。”[12]
在中国文学逐渐汇入世界文学潮流的进程中,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批评家们对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学思潮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学习和借鉴是必要的,他们热切渴望世界认可甚至青睐中国文学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若是丢弃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文学之根,丧失了创建本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自信心,以西方社会的认可为惟一追求,完全运用西方的文艺思潮来演绎和诠释中国本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则是可悲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若丧失了本民族的精神和魂魄是悲哀的,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自然也不会最终获得世界的认可和赞许,或者可能会得到世界的认可,但绝对不会赢得世界的赞许和尊重的,这是整个世界文学史早已证明了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毕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这种意义上,雷达先生坚守并致力于创建本土化、民族化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自信力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五
作家李国文在评价雷达先生时说:“他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评论家。”因为他发现,“雷达不择言,好反弹,小不忍,情绪化的气质,更接近于诗人。”可以说,李国文对雷达先生的观察和评价是极为准确的。作为先生的学生,我对他的“小不忍,情绪化的”诗人气质是深有感触的,记得有一次他来兰州大学参加一个师兄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学院安排他住在一个没电梯而且周围正在施工的招待所的六楼房间,当我和师兄接他到招待所的时候,他一看这情形,就显出了不悦的神色,马上给学院领导打电话,要求更换住所,在学院尚未解决的时候,他又打电话自己联系住所,当一切安排妥当后,他随即就又恢复了谈笑风生的神情,反过来安慰我和师兄,一再解释这和我们没关系,努力打消我俩的不安和忧虑。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他耍大牌,其实这恰恰反映出正是他的“小不忍,情绪化的”诗人气质,是他诗人的天真和真诚所在。因为他不会像某些人表现的那样,心里不痛快,可嘴里不说出来。这就是“诗人”雷达。
作为富有诗人气质的雷达,在写评论的时候,总是能够做到把生命的激情和深刻的理性合二为一,进而将其熔铸成一篇篇充满诗意的风格独具的精彩华章,以至像贾平凹、杨光祖等作家和评论家将其评论文章当散文来欣赏。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他评论《远村》的文章《〈远村〉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中的一段话来感知和印证他评论文章的诗意所在。“《远村》在表面静寂中内蕴着强劲的动势。这是因为万牛经常沉溺于往事和梦幻的回顾决定的,也是用‘拉边套’这一现象作为历史运动的风俗‘化石’的性质决定的。黑虎则以犷悍的野性打破了这种静寂。所以,它既有月光下的爱情,也有荒山中的搏击。对于自由的文学来说,‘远村’和闹市,牧歌和喧嚣,都有各自的地位和价值。”[10]193正是这种诗人的气质,决定了他在评论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时候,就特别看重那些富有诗性的作品,从而对文学作品诗性的把捉和评析就成了他文学批评思想的又一明显特征。
在《诗性:没有结果的问询》一文中,他不仅明确提出诗性是小说创作的最终目的,而且还毫不隐晦地表明了自己心目中的诗性标准。“我认为,小说创作的最终鹄的应是诗性,惟有通向了诗性,一个作者才算是完成了他对生活的审美判断。揭露尖锐的矛盾,提出重大问题,直面丑恶的灵魂,状绘惊人的情节,都很好,但它们不应是艺术创作的最终目的,倘满足于此,那等于旅行只走了一半,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对于诗性,或者直白点说,叫诗意,人们曾是有误解的,认为甜蜜的梦想,空洞的豪放,软绵绵的咏叹,就叫诗意。其实大谬不然,诗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我看来,富于诗性的小说,总是那种既让我们看清了脚下的泥泞,又领我们张望闪烁不定的星斗,且能唤起无尽的遐想和追问者。”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和《药》等作品虽然表现出的是惨痛和闷暗,但其内质却是富于诗意的。[8]395~398
雷达先生之所以在小说评论中始终坚守和倡扬作品的诗性品质,在我看来,这不仅在于他的诗人气质和诗人的天性,而且还在于他对当代中国小说普遍缺失诗意的一种焦虑和忧思,期望通过自己对诗性的坚守和倡扬来拯救中国小说的诗意,乃至期望以此来唤醒人们心中早已沉睡的那份诗意。
六
在雷达先生的文学批评思想体系中,不断发现并推荐新人新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雷达先生总是以敏锐的感知力发现新人新作,并不遗余力地将其推介到读者和评论家面前。如果我们了解他的批评的话,就会发现,当下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大多数中青年作家,在他们起步阶段,大都得到过雷达先生的关注和批评,而且大多数是雷达先生第一个站出来作出批评的。了解雷达先生批评风格的人都知道,他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既不是无原则的“捧”,也不是毫无道理的“棒”,而总是站在发展和繁荣中国文学乃是世界文学的高度,把批评对象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从而对其作出客观、公正而又不无中肯的评价。因此,他的批评不是一味地提出问题,指出不足,而是努力挖掘作品蕴涵的新意和创新之处,指出其创作上的独特性和对作者自身的创作和整个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启示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达先生的批评其实就是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发现和推荐。
甘肃作家雪漠的《大漠祭》出版之初,虽然上海的一些批评家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虽然《大漠祭》在读者的选择下也连续加印几次,但雪漠及其《大漠祭》真正得到整个文坛的认可和赏识还要归因于雷达先生的评价和推荐。2001年8月6日,雷达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读〈大漠祭〉》一文,称《大漠祭》“是一部出类拔萃的表现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是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写作”,“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2004年6月18日,他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雪漠小说的意义》一文,对雪漠及其《大漠祭》进行绍介和推荐。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种场合推荐和介绍雪漠及其《大漠祭》,以至《大漠祭》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此外他对山西作家陈亚珍的推荐和提携也让陈亚珍一直感铭于心。
雷达先生这种极力发现和热情推介新人新作的精神不由让人想起鲁迅当年对萧红、萧军等人的大力推荐和提携。鲁迅先生曾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花,还得浇灌佳花,——佳花的苗。”[13]在“剪除恶花”方面,也许雷达先生表现得不是那么积极那么充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一贯坚持“批评要着眼于发展”的批评观的缘故吧,但这不等于他对一些“恶花”就没有他的臧否。正如他说的那样,“批评作家要慎重,尤其是青年作家。我在这个位置上,稍有不慎,就可能断送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打击他们创作的积极性。我不表态,就是一种态度,一种评价。”*转引自李清霞《政治话语与美学话语的整合平衡》,《文艺争鸣》2012年第7期。因此,他几乎把全部的心智和激情都投注在浇灌“佳花——佳花的苗”上。当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为了使中国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领地,所以他才不会像某些批评家那样全盘否定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试想,当我们全盘否定了整个当代文学成就的时候,我们在文学上还有什么?
[1] 杨光祖.雷达论[J].南方文坛,2012(5).
[2]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24.
[3] 雷达.地气·人气·正气[N].解放日报,2011-02-28.
[4] 雷达.民族灵魂的重铸[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5] 雷达.当前文学症候分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6] 雷达.雷达自选集:文论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7] 雷达.强化了主体之后[J].小说评论,1988(4).
[8] 雷达.思潮与文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9] 雷达.真正透彻的批评为何总难出现[N].文汇报,2011-02-28.
[10] 雷达.新潮与蜕变[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11] 雷达.文学的青春[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317.
[12] 晋舒瑜.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N].中华读书报, 2010-09-22(07).
[13] 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二)[M]//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21.
(责任编辑:毕光明)
AnOutlineofLeiDa’sViewonLiteraryCriticism
SONG Jun-hong
(SchoolofLiteratureandCommunication,HubeiMinzuUniversity,Enshi445000,China)
For 30-odd years since the new era, Mr. Lei Da has explored and developed his own domain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rough his unique literary criticism practice and theories, thus having set up his own theory system, criticism discourse and aesthetic principles. Moreover, by adhering to the dignity and independent value of literary criticism, he has consciously acted as the “navigator” and night watcher”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various criticism marked by excessive compliment, emptiness, personal remarks, academicism, etc., a probe into and study of Lei Da’s idea in his literary critic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his literary criticism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o reconstructing the spiritual image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o developing the contemporary China-style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Lei Da; ideas of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belief
2014-09-23
宋俊宏(1977-),男,甘肃宕昌人,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I206.09
A
1674-5310(2014)-11-0045-07